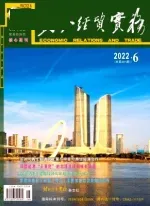我國企業對非投資法律問題研究
張迪 王利彬
摘要:對在非投資的中國投資者來說,本土化理念的貫徹對投資法律風險的防范至關重要。通過對典型案件的分析,總結得出了中國對非投資面臨的主要風險,包括法律規范保障不足、司法預警機制不完善、環保法律責任、習慣法律風險和政治法律風險等。對此,本土化理念的貫徹是企業切實可行的措施,不僅有助于其他風險防范策略的高效運行,還能夠從更根本的意義上降低風險發生的幾率,從而切實為企業投資風險“減負”。
關鍵詞:本土化理念;文化差異;法律風險;風險預警
隨著“一帶一路”的建設,中國對非投資的熱情也隨之上漲,當然,相關的法律風險問題也一并顯現,引起了廣泛重視。考慮到國際市場風險、政治風險、國家間雙邊投資立法等風險因素非企業自身所能決定,所以從企業的眼光看待對非投資過程中所遭遇的風險,并站在企業的角度,在企業通過自身努力能夠切實看到成效的方面,提出對策和建議至關重要,其中,本土化經營理念是當今企業應重視的問題。
一、中企對非投資法律環境狀況堪憂
(一)非洲國家國內立法繁冗且與國際協定缺乏協調
非洲各國國內立法體系雜駁。第一,部門法中,非洲勞工法律比較健全,但帶有濃厚的習慣法色彩;環境保護法律不斷完善,但也存在朝令夕改現象;第二,法律淵源上,由于歷史原因,非洲法律兼具大陸法系和普通法系的特征,習慣法、宗教法、大陸法系、普通法系以及混合法系并存,法律淵源紛繁復雜,法律規定零碎繁瑣、難以預測。第三,非洲各國為了解決上述問題,已經進行了一系列的法律一體化,但進程緩慢,且協調后形成的公約或文件認可度不高,或因規定空泛等問題,沒有真正落實到各國的法律實踐中。
中國政府未雨綢繆,在中國企業對非投資穩步增長的同時,與非洲國家簽訂了34份雙邊投資協定(BIT),其中已經正式生效的有20份。但雙邊投資協定的簽訂步伐跟不上中企對外投資的進度。截至目前,我國企業投資已經遍布52個非洲國家的多個項目,其中,規模較大的投資集中在埃塞俄比亞、剛果(金)、南非、莫桑比克、安哥拉、贊比亞、肯尼亞等國家。從中非投資協定的實施效果看,主要存在以下問題:第一,中非投資協定覆蓋面有待擴張;第二,既存的雙邊投資協定條款相對陳舊,存在法律保障制度不完善的問題,不適用當代投資需要;第三,雙邊投資保護協定與東道國國內法存在兼容問題。
(二)非洲國家執法與司法程序有待完善
非洲大多數國家的執法與司法體制雖已初具框架,但仍然存在許多阻礙在非中企正常經營的不良司法因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司法權政治化。即司法權的行使經常受到政治意志的干擾,偏離司法正義。如,司法機關常常成為政府實施國有化、進行征收的工具,對中國投資企業刻意巨額罰款或賠償,這本質上是披著司法的外衣進行一種不規范的間接征收。其二,忽視程序正義。執法司法的程序規范過于粗泛,對司法執法人員缺乏相應的約束與監督,導致司法執法過程不嚴謹、不規范、不公正。其三,司法腐敗現象嚴重。司法執法人員職業素養不高,同時缺乏相應的監督和打擊,導致出現東道國官員對中國投資者進行敲詐勒索的現象。其四,司法歧視。東道國司法偏向于保護本國現有利益,而加重中國投資者法律責任,或惡意延長糾紛解決時間,增加在非中國企業的損失。
(三)在非中企需要熟悉和了解東道國的法律法規
在非中企對東道國法律仍然缺乏足夠的熟悉和了解。近年來,因“不知法”而犯法的現象大量存在,如許多學者研究得出,勞動法律風險突出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國企業不熟悉、不遵守當地勞動法規定。因此,身為在非投資的企業,必須首先對東道國的法律法規有充分的了解與認識,才能較好地遵守法律,進而為投資活動的順利開展營造良好的法律環境;否則,很容易觸犯禁止性規定,招致法律責任。
二、我國企業對非投資遇到的法律問題
面對非洲相對嚴峻的自然環境、復雜多變的人文環境,在非投資企業在獲取收益的同時也承擔著形式多樣、變幻莫測的法律風險。下面將從企業的角度,具體分析我國企業對非投資過程中所遭遇的風險。
(一)法律規范風險
一般說來,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兩國間雙邊投資法律規范彈性越大,存在的解釋空間就越大,中國投資者對法律規范風險防范的難度就越大,投資風險也隨之升高。在中非雙多邊投資協定中,存在著大量過于抽象模糊的條文規范,還有許多保護性規范的空白地帶。這些不明確的“一般性”規定給了部分有心人惡意解釋法律的空間;加上缺乏相應的投資保護性解釋規范,使得雙邊投資法律很容易成為惡意東道主斷章取義的對象,進而損害在非中企的合法權益。
塞內加爾水電工程建設案是法律規范被惡意利用的典型案例。本案中,為了應對財政困難的新政府向一般性條款逃逸,利用“依照國內法定程序”“公共利益”等缺乏明確界定的條款對在非企業實施直接或間接的征收。此外,中國與南非的BIT中也存在許多模糊字眼。飽受爭議的——在征收條款中,何為“為了公共目的”?在賠償責任中,如何“充分補償”?諸如此類都沒有明確解釋,往往造成雙方法律關系待定以及爭議的久拖不決。
(二)司法預警風險
司法預警機制漏洞與風險現實化機率升高密切相關,還會增加危機的解決難度。首先,司法預警機制的不完備,通常導致企業對危機喪失高度警覺性,不利于企業防患未然;其次,司法預警機制的不周全,很容易出現意料之外的惡意訴訟事件,導致企業對危機措手不及;最后,即使企業能夠安全渡過司法危機,但是危機的解決也給企業帶來了不必要的損失,降低收益率。而如果企業能夠健全司法預警機制,則可以防微杜漸,避免風險現實化帶來的損害。
在中華建筑工程公司應對惡意訴訟案中,進一步完善和加強司法預警機制的重要性得到體現。2017年4月3日,埃塞阿爾法州法院開庭審理埃塞當地公司KasechHiluf控告中華建筑公司的案件。訴訟中,法庭不采納中華建筑公司的意見,拒絕中華建筑的證人到庭,即判決其敗訴,并計劃在判決書下達后立即將凍結的資金劃轉給控方。可以說,這是控方利用法院地惡劣的司法環境、鉆取司法預警機制的漏洞,而進行的一場惡意訴訟。
(三)環境法律風險
隨著非洲環境立法加快,在非中企的環境法律風險也隨之升高。第一,非洲各國環保力度正在加強,企業如果沒能準確跟蹤環保政策要求并隨之做出相應的升級調整,很容易觸發環境法律風險;第二,如果不熟悉當地惡劣的自然地理環境,很可能出現環保安全方面的意外事故;第三,當地不穩定的環境保護立法也增加了企業守法難度,直接或間接引發環境法律風險,使企業付出十分沉重的代價。
以下兩個案例的對比突出了環境保護方面的重要性。第一個是中石油乍得叫停事件。2013年8月13日,乍得政府發現,中石油在開采過程中原油溢漏且不清理,給當地環境造成污染,對中石油開出了“無限期暫停”的開采禁令。這不僅阻礙了中石油在當地的生產作業,也使其他中國企業在當地的聲譽下滑。
而中蘇喀土穆煉油廠則形成鮮明對比。在環境保護方面,喀土穆煉油廠嚴格執行環保標準,投入大量資金建成花園式煉油廠;自投產來,煉油廠從未出現污染事故。因此,企業獲得當地政府和相關國際機構的大力支持,也得以在當地順利擴展生產規模,提高收益率。
因此,做好環保工作不僅可以抵御環境法律風險,也利于為企業樹立良好的環保形象,獲得當地政府的支持,加快在非中企的發展。
(四)習慣法律風險
不成文的習慣往往也是招致法律責任的一大因素。在非中企常常忽視不成文的習慣法的重要性,因而在面對此類法律風險時,顯得格格不入、無從下手。而如果企業能夠全面掌握當地不成文的習慣法傳統,也許能夠應時順勢,避免風險爆發,或者緩解危機的突發性,防止措手不及。
這一點在以下兩個案件中表現明顯。在中鋼BEE法案股權修改案中,正是企業不了解的“提高黑人權力”運動,使得中鋼集團面臨是否股改的實質威脅,最終中鋼轉入虧損狀態;在贊比亞謙比希銅礦應對勞資關系風險案件中,正是由于對“每年都要求漲工資”的勞工法律傳統不熟悉,企業才輕易發布抵抗聲明,激化了勞工情緒,直接導致罷工潮爆發。
(五)政治法律風險
政治不穩定是影響投資項目運行的又一大干擾因素。非洲許多國家政治環境較為惡劣,武裝沖突不斷,地區局勢緊張。如贊比亞謙比希銅礦應對勞資關系風險案件中,因贊比亞大選而惡化的“漲工資”情緒,間接引發了大規模罷工潮;塞內加爾大型水電建設項目受政權變更風險影響而損失上百億資金;還有剛果時有發生的武裝沖突、騷亂,2012年的“3·23運動”等,這些局勢變化都會對在非投資項目有著或多或少的阻礙。
三、應對我國企業對非投資法律問題的措施
(一)立足雙邊協定,企業治理本土化
立足雙邊協定,著眼企業自身。在非中企應立足于兩國間投資的雙邊協定,從自身出發,原因如下:第一,兩國雙邊協定是中國對非投資的前提和基礎,任何投資都必然在這一框架下進行;第二,雖然中非雙多邊投資規范彈性過大,但涉及公法領域的立法政策事項,企業自身無法或難以改變;第三,考慮到最惠國待遇等國際交往習慣,設立彈性的投資協定具有必要性和存在合理性。因此,基于國際交往的“公平互利”原則,不要對單方面保護中國投資者或偏益于中國投資方的法律抱有幻想或希望。鑒于此,企業最好的抓手是著眼于自身。
從自身出發,貫徹治理本土化理念。第一,經營理念本土化。企業可以吸收當地人才加入企業發展上的經營策劃,建構起全方位、多層次的本土化經營框架,使企業更接地氣、發展更順暢。第二,管理理念本土化。面對歷史悠久、復雜繁碎的宗教法、習慣法傳統,企業僅依靠自身學習或培養中國的“復合型人才”難以做到真正的“感同身受”。但是,通過本地人經營管理,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企業“親民”“親文化”和“入鄉隨俗”,最大程度減少因文化差異而導致的管理關系摩擦。
(二)掌握法律法規,預警機制本土化
掌握法律法規,了解司法程序。預警機制的完善離不開對東道國實體法和程序法方面的掌握。在實體法方面,企業不僅應該注重雙邊投資規范的規定、企業自身與東道國的投資合同約定,還要看到東道國國內法規范的約束;不僅要注重成文法規定,還要了解不成文的法律傳統;不僅要注重當前的法律規定,還要能夠預測立法變化趨勢;不僅要注重行業經營規范,還要注意企業管理方面的勞工法律規范。總之,在實體法上,企業要對相關法律法規做好全方位、多層次、動態化的掌握,建立起一個適用于企業自身的東道國法律信息庫。在程序法方面,對東道國司法執法傳統的了解也很重要。所謂“司法是法律的真正表達”,司法正義關乎實體正義。因此,企業不僅要掌握當地程序法成文規定與解釋,更要了解當地不成文的司法執法傳統與習慣;不僅要熟悉司法執法程序,還要了解司法執法機構的設置與特點,對司法執法環境有一個全面清晰的把握。
引進本地法律人才,健全司法預警機制。本地法律人才對完善司法預警機制至關重要。首先,在實體法方面,本地司法人才兼顧本土文化背景優勢,能夠彌補企業在不成文法律傳統方面的不足;其次,在程序法方面,面對非洲司法執法不嚴、缺乏相應成文法規制度的情況,企業對此往往感到難以捉摸,而本地法律人才恰恰在這方面發揮著難以替代的優勢,本地法律人才通常以其多年從業經驗,對本地司法執法傳統擁有較高的熟悉程度和運用能力,幫助在非中企打通東道國司法執法的“任督二脈”。最后,本地人才正是憑借其對當地實體法和程序法方面的把握,加入到企業預警機制的完善過程中來,彌補風險預警機制漏洞,全面準確地預測司法執法風險,將風險預警機制做密做全。
(三)生態保護先行,環保工作本土化
生態保護先行,遵守環保法規。做好投資過程中的環境保護工作,不僅可以減少環境法律風險,還利于在非中企贏得當地政府支持進而擴大投資規模。因此,在非中企要堅持生態保護先行的原則,完善環保方案,健全污染防治體系,遵守東道國環保法律規定,保護當地自然生態環境。
吸收當地環保人才,環保工作本土化。在很多情況下,并非企業刻意違反法律法規,而是當地惡劣的自然環境和多變的法律政策使得守法這個目標變得“高不可攀”。此時,當地環保工作人才的加入是關鍵。第一,本地人員更了解當地的自然地理環境,對易引發環境風險的惡劣自然地理環境具有更高的熟悉程度和預測能力;第二,法律政策的變化并非毫無規律可循,當地工作人員對不穩定的環保規范的修改趨勢通常具有較高的嗅覺和靈敏度,可以幫助企業預測環保法規的變化規律,進而提高企業對環境法律風險的預測和防范能力;第三,吸收當地環保方面的法律人才進駐企業,利于企業了解當地環保司法情況和執法程序,進而在風險萌芽時,能夠及時有效地將其化解。
(四)尊重人文習俗,溝通協商本土化
尊重人文習俗,融入企業文化。由于民族文化差異的存在,在非中企常常面臨著難以預料的風俗習慣,像贊比亞每年的“漲工資”風潮。一方面,面對此類帶有牢固風俗傳統的要求,企業不應貿然試圖改變或完全抵制,或采取偏激措施激化矛盾,防止造成難以控制的局面、擴大損失范圍。另一方面,在投資經營過程中,企業還可以積極了解工會的勞動文化和理念,尊重民眾的態度,和當地勞動人民建立友好合作關系,甚至可以將當地優秀的文化作為企業文化加以推廣宣傳。
吸收本地公關人才,溝通協商本土化。熟悉當地人文習俗、法律規范的本土人才在處理與東道國勞工、社區居民和政府的關系,優勢顯著。首先,由于東道國悠久的習慣法、宗教法傳統具有不成文、主觀性強以及復雜晦澀的特點,其內國性特征明顯,外來人員很難掌握。其次,將本國相關人才培養成兼備東道國文化的復合型人才雖然有一定可行性,但培養時間長、經濟成本高,且在遇到微小卻重要的細節時,外來人員往往難以全面關注。
(五)規避政治風險,投資理念本土化
提前評估,合理規避。面對力量強勢、企業難以決定的政局變動風險,如下兩種思路可以參考。第一,企業在投資前就要對風險進行全面考察評估,預測投資的收益率,進而決定是否投資以及投資后如何防范風險;第二,面對收益率高、但政治風險也很高的情況,可以采取本土化投資的策略進行合理規避。
本土化投資理念的貫徹可以分為以下兩種:一,完全本土化。企業可以通過當地人代為持股的隱名投資方式,避免與東道國政治力量發生正面沖突,從而減輕政治利益變動對企業發展的影響;二,部分本土化。企業可以通過吸引當地資本加入,使其擁有部分股權;以及采取其他方式與東道國利益建立緊密聯系。這樣做既可以增加企業親和力,幫助企業進一步實現本土化,又可以以此為持,盡可能避免企業遭受歧視性、排擠性對待,最大程度避免投資利益遭受政治利益博弈的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