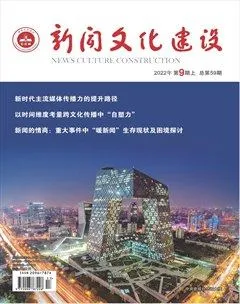老年題材紀錄片的形象探究與主題分析
馬書雅

摘要:老齡社會的加速到來,與老年人相關的議題進入大眾視野,紀錄片作為信息傳播的重要載體,應肩負起引導受眾聚焦老年問題的責任,推動國家對老年群體的關注與建設。本文以多部老年題材紀錄片為例,進行了老年題材紀錄片的形象探究與主題分析。
關鍵詞:老年題材紀錄片;紀錄片創作;老年傳播
自2000年邁入老齡化社會后,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持續增加。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多部紀錄片為研究對象,探究紀錄片中老年群體的形象呈現及未來如何積極引導大眾對于老年問題的關注。
一、研究背景
隨著老齡社會的加速到來,由此引發的老年問題關系著諸多社會議題,如社會保障、勞動就業、醫療、心理健康等,在老年傳播領域也存在諸多如“代際鴻溝”“數字難民”“后喻文化”“文化反哺”“老年群體數字化生存”等議題。紀錄片是對現實的創造性處理,它所營造的現實被觀眾接觸、感知進而被等同于現實世界本身。[1]其最重要的作用是記錄社會現狀、發展轉向及未來走勢,紀錄片通過攝影機展現了社會的不同“切面”,不同的“切面”中映射著不同的社會群體和社會現狀。是具有強大社會價值的藝術作品,帶有濃厚的人文主義色彩。
二、紀錄片中老年群體的形象展現
回顧自1990年《老年婚姻咨詢所見所聞》至2020年《大國養老》《人生第一次》以來老年題材領域紀錄片的發展,影片中呈現的內容大致可分為五類:一是受到廣泛關注的老年人身體健康問題;二是如何度過、在哪里度過老年的問題;三是老年群體如何融入社會、適應數字化生存;四是時代給予老年傳播怎樣的影響;五是老年群體的社會效能問題。
(一)聚焦“健康養老”,如何更加長壽
疾病是影響老年群體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21世紀以來,中國全面高速發展,有關養老的基本保障也得到解決,人們在思想上更加關注健康老齡、科學老齡等問題。筆者曾于阜新市新福托管中心、阜新鎮中心敬老院拍攝紀實影像《我和我的養老院》,其中半數以上老人每日都會服用藥物,在他們口中,“健康”是最常聽到的詞語,不少老人也擁有自己獨特的“長壽秘方”。以中文紀錄片《長壽密碼:食以養生》為例,該紀錄片以“壽命的長短是吃出來的”為主線,梳理長壽的定義及發展脈絡,呈現世界各地長壽老年群體的生活現狀以及如何以科學的方式長壽,并探究影響長壽的相關因素。相類似的紀錄片還有中文紀錄片《走遍中國·長壽之鄉》,BBC紀錄片《永葆年輕指南》以激活人類大腦的視角,延緩大腦的衰老從而達到長壽的目的。紀錄片《長生不老:地平線衰老指南》,探究在科學高速發展的社會,“長生不老”是否是可以實現的夢想。日本紀錄片《如何預防老年癡呆癥》從紀錄片創作角度出發,以老年人長壽、科學健康養老問題和如何預防老年疾病為切入點,探究以科學的方式保持身體健康,在宣傳科學養老服務建設中起了重要作用。此外,如埃里希·弗洛姆所說:這不是一個老年的問題,而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要面臨的人的生存問題。近些年,關注此類老年問題的人群年齡呈現下降趨勢,老年病也出現低齡化現象,拍攝對象及覆蓋受眾群體面積也應呈現縱向拓展的趨勢。
(二)聚焦“活力養老”,如何度過晚年
家庭養老或機構養老,是傳統養老模式下,老年群體面對的不同選擇。在紀錄片《人生第一次·養老》中,向我們展示了兩種不同的選擇方式下的生活,戴華奶奶走出家門是如此艱難的選擇,但養老院的生活讓她再遇了年輕時的朋友,也在這里找到了更加愉快的生活方式。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生理年齡不再是劃分世代的唯一標準,心理年齡——尤其是對新鮮事物的接受程度—成為重要的輔助尺度。所謂“活力養老”并不是選擇在哪里養老所決定或影響的,真正禁錮人的是一成不變日復一日的生活,是失去對未來期待的心靈枯萎,影片的二位老人雖選取了不同的度過晚年方式,但是他們都找到了生活的樂趣與希望,也因此不再孤獨。曾有研究對老年人收看電視心理展開探討與分析,參與訪談的15位老年人中,10人表示平常看電視娛樂放松,在未來我們期待紀錄片可展現智能化養老、智慧化養老模式,積極引導老年群體以多樣化、多元化的方式擺脫孤獨,豐富多元地度過晚年,提升晚年幸福感。何為幸福?在筆者拍攝的《我和我的養老院》中,養老院每周都要手寫黑板報,但不管板報內容怎么更改,下面總有不變的一行字:什么是幸福?您怎樣認為?老人們在書寫幸福時,仿佛已經得到了幸福。影像中的普通個體對幸福的理解和想象,既是對現實社會中個人“幸福觀”的折射,也是鼓勵個人追求幸福之天賦權利的啟蒙,更是在整個社會層面建構超越個體的“幸福觀”的有益嘗試。[2]
(三)聚焦“積極老齡”,如何融入社會
在智能化媒體時代,老年群體由于缺乏科技設備、具有“科技恐懼”、缺失媒介素養等問題迅速邊緣化,逐漸成為新媒體浪潮中的弱勢群體,“老年群體數字化生存”問題顯著。“積極老齡化”最重要的變化在于強調老年群體的社會參與權利,并致力于將老齡化的壓力轉變為可持續發展的動力。[3]紀錄片《銀發洶涌》中,邵愛麗發微信與遠在國外的兩個小外孫交流。筆者拍攝的紀錄片《愿你我所愿》中,住在光榮院中的齊寶榮爺爺常常要拿起手機和藍牙音響給遠在南方上學的孫子唱上一曲。在紀錄片中呈現出的老年人對于數字設備和新媒體的好奇程度,應當引起我們的反思。老年群體的孤單源于不能快速融入高度發展的社會生態和他們所熟悉的環境正在消失帶來無措感,面對如今陌生的社會環境他們不知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處在怎樣的位置,是老年群體無法在短時間內完成社會融入問題的關鍵。在新的數字媒介中的他們像極了“新生兒”,一切都是等待被架構的新的認知,等待建成的新的世界觀、價值觀。歷史的潮流不會逆向發展,他們所熟悉的媒介環境逐漸消失是無可避免的,也許他們并沒有準備好也沒有想好自己是否想要融入一個全新的世界,但他們的本能是好奇的,他們正在期待著接觸一個新的媒介生態。
(四)聚焦代際差異,如何相互理解
在紀錄片《人生第一次·養老》中,王意仁的女兒教父親使用手機軟件。王意仁也學會呼叫天貓精靈為自己放一首鄧麗君的歌曲。在筆者拍攝紀錄片《井上明燈》中,礦區的現在并非是中老年人的主場,出現更多與青年大學生接軌的前沿科技崗位。席明就是這樣一位年輕人,在黑龍江科技大學畢業后,投身煤礦行業,現已成為單位一名技術骨干。這里存在著老年群體與青年群體的身份對調,青年群體往往擔任著更加先進的科學技術工作。青年群體與老年群體兩者生長于完全不同的社會環境和文化背景中,兩個代際呈現著怎樣的關系與對照,是紀錄片所聚焦的熱點問題。相較于親代面對新媒介環境的無所適從,子代往往持有更自如的適應性、更開放的心態和更靈活的接納與使用能力,并具備向親代反向輸出新媒體使用技能、知識以及與之相關的流行文化和價值觀念的能力,即數字反哺能力。[4]《人生第一次·養老》中,王意仁選擇居家養老,清明節當天他眼含熱淚翻看已故妻子的相冊,深深悼念,而后又戴起軍功章唱歌,懷念過世的戰友。筆者拍攝的紀錄片《愿你我所愿》,光榮院中李振生爺爺常抱著一把“槍”,雖然是玩具槍,卻展現一名軍人刻在骨子里的魂。從米德“主我”與“客我”的概念來看,我們應當思考老年群體在社會化的過程中是否由于媒介生態的變化,而被動積極地想象著自己可以融入一個全新的數字化媒介,但“主我”的部分也許并不是如此,這種微妙的、被動產生的、想要融入一個與“主我”情緒相違背的社會的情緒產生也許他們自己也并未察覺到。作為紀錄片的創作者應同時感受到對于老年傳播問題不應只反映“數字反哺”“代際鴻溝”下老年群體的落后,也要呈現不融入數字化媒介的老年群體,享受慢節奏,體會從前慢式情感的晚年生活。紀實影像應盡可能多元化展現現實,并積極引導社會共識的建構,沒有哪種老年生活是被定義為“幸福”,最重要是找到適合自己的媒介環境和生活節奏。
(五)聚焦老年群體的社會效能
世界衛生組織2018年公布的數據顯示,65歲以上老年人群抑郁癥的患病率,保守估計在10%-15%。盡管老年抑郁癥已成為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卻鮮被輿論關注,老年抑郁患者這一群體也處于“失語”狀態,更有嚴重者具有自殺傾向。老年群體的抑郁癥狀的出現一定程度上與社會效能的消失相關,對于進入衰老時期的人們來說,勞動并不是最可怕的,不能勞動才是,不能付出勞動對社會作出貢獻,似乎象征著生理與心理上的同時衰老。“我會慢慢地做,不會太操勞,只有到我死了,我才會停止干活,我活一天就要做一天,直到死為止。”這是紀錄片《牛鈴之聲》中的臺詞。一個年邁的老人固執地拖著一頭同樣年邁的老牛,日復一日下地干活,這樣的場景看起來也許心酸,也許殘忍,但影片的主人公自己不這么覺得,在他的世界中,辛苦勞作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筆者拍攝的紀錄片《井上明燈》中,礦廠工作的老人大多是退休返聘回來的,他們選擇回來這個他們曾經熟悉的領域,為自己熱愛的事業作出一份貢獻,李明就是這樣一位老人,他說只要身體還能堅持,會一直工作下去。
三、老年群體紀錄片的未來發展
(一)立足紀實影像藝術價值,以獨特美學視角呈現對于老年群體的思考
筆者對比了《銀發洶涌》第一集(2013年)與《人生第一次·養老》(2020年)兩部紀錄片,均以兩位老人為主線展開敘事,但不同的鏡頭語言,呈現了完全不同的敘事視角。(詳見表1)
在《銀發洶涌》第一集中,多采用中景或全景鏡頭,以更加客觀和理性的鏡頭語言展示老年群體的生活。在《人生第一次·養老》中,更多采用特寫鏡頭,更能夠引起觀看者共鳴。
在空鏡頭的表達上,前者堆疊了大量的現代化工業城市與花草靜物的對比,試圖激發起受眾的更多思考,后者則更傾向于展示老年群體所處環境,在思辨意味的同時多了一些溫暖的意向。在拍攝手法選擇上,前者多使用跟拍鏡頭、手持鏡頭,著重以背影象征老年群體的困境,整體色調也更加偏向冷色調和暗調。
兩部紀錄片均使用了框式構圖,將老年主人公在視覺中放入狹小閉塞的空間中,以暗喻老年群體面對的生活的暗淡與狹窄。從整體來看,《銀發洶涌》第一集中的視聽語言和暗喻更加消極,傾向于引導受眾關注老年群體面臨問題,并探討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影片最后在黑暗的窗簾縫隙透進來的光中,一個老人的手迎接著太陽,象征著老年群體終將擺脫困境走向希望。《人生第一次·養老》也包含引導受眾思辨的試聽語言,如戴華奶奶家中鐘表的空鏡,隨著戴華奶奶決定去養老院到離開家,鏡頭的景別逐漸拉近收緊,最終在戴華奶奶的一句“這是人生的最后一條道路”后,收至特寫,時針的聲音逐漸停止,但紀錄片整體傾向于引導受眾關注老年生活不同選擇下的美好生活,較前者更加溫馨和明朗。
老年題材的紀錄片中,在攝影機與老年群體之間更多的采用平視的關系,正視老年群體的數字化、社會化、情感等需求,同時尊重其對于老年生活的多樣化選擇。在鏡頭語言的使用中打造積極的攝影美學,形成獨特的遲暮影像美感,適當減少框式構圖、俯拍機位等消極鏡頭話語。為老年題材紀錄片打造獨特的攝影美學標簽,同時加入適當的商業元素,以吸引更加廣泛的受眾群體,達到次級文本的廣泛傳播效果。
(二)立足紀實影像人文價值,以貼近生活方式呈現對于老年群體思考
在紀錄片影像的呈現中,除真實記錄老年群體生活之外,應進一步挖掘老年群體的特征,探索其內在需求。對老年問題的思考不應只停留于表面,老年時期也是社會中每個人都要經歷的時期,老年問題的解決需要多方力量的介入,包括老人自身心態轉變、對于老年群體的媒介培養、不同代際之間的相互學習與彌補、數字化媒介與老年群體的接洽問題、社會和國家的積極導向等。
(三)立足紀實影像社會價值,以多元化發展呈現對于老年群體的思考
除傳統養老模式外,紀實影像應進一步展示與促進養老模式多元化發展,如“時間銀行”“老人會”“病友組織”“守門人制度”等新型的養老模式。積極引領輿論導向,打破大眾對于老年群體和養老院的刻板印象。
四、結語
目前老年相關紀錄片中存在展示內容單一、運營模式固化等問題,過于強調老年人面臨的困境,渲染悲情色彩,較少對老年群體當下所面對身心問題和傳播問題給予相關回應或引導。在影片運營模式角度,與智能媒體宣發脫節,相較于同類別人文紀錄片,未引起極其廣泛的關注和討論度。紀錄片應脫離單一的共情導向,轉而肩負起引導受眾聚焦老年問題的責任,推動國家對老年群體的關注與建設。
參考文獻:
[1] 王華.在攝影機與少數民族之間發現中國:中國少數民族題材紀錄片生產與傳播研究(1979至今)[J].新聞大學,2014(5):47-57.
[2] 張玲玲,張欣,張書成.紀實影像如何建構中國式“幸福觀”:對四部中外紀實影像作品的內容分析[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3,35(11):91-95.
[3] 方惠,曹璞.融入與“斷連”:老年群體ICT使用的學術話語框架分析[J].國際新聞界,2020,42(3):74-90.
[4] 王敏芝,李怡萱.數字反哺與反哺阻抗:家庭代際互動中的新媒體使用[J].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21(1): 77-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