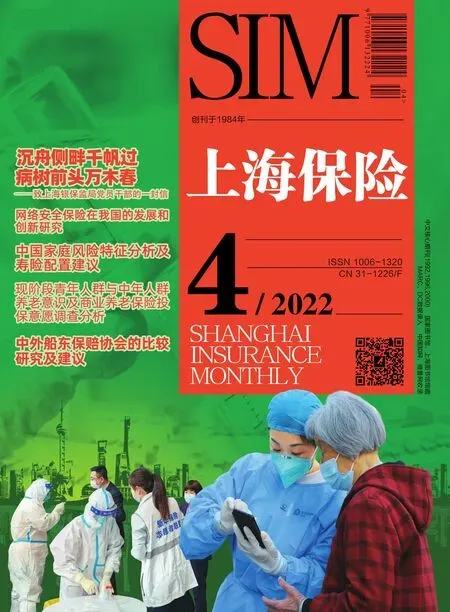簡評重疾險中重大疾病的認定條件
——以“肝豆狀核變性”判斷為例
陳禹彥 梁日升 上海蘭迪律師事務所
當今社會,越來越多的人出于防范風險的考慮,投保了重大疾病保險。對于重大疾病保險金給付的審核認定標準,保險公司一般通過保險合同中的疾病釋義條款予以約定。然而,保險公司所設置的標準往往與醫學標準有一定差別,這導致許多被保險人在被確診為保險合同承保的重大疾病后,在申請理賠時卻因“不符合合同約定的重大疾病保險金給付標準”而被拒賠。對于這種情況,保險消費者該如何維權?
本文以陳禹彥律師團隊親手經辦的案件為例,為同樣遭受此類拒賠情況的被保險人梳理出此類案件的基本維權思路,供各位讀者參考。
一、醫學介紹
肝豆狀核變性(或稱Wilson 病),是一種常染色體隱性遺傳的銅代謝障礙疾病,因致病基因ATP7B 編碼的銅轉運P 型ATP 酶功能缺陷或喪失,造成膽道排銅障礙,大量銅蓄積于肝、腦、腎、骨關節、角膜等組織和臟器,從而出現銅在各個器官的病理性沉積,最終導致大腦及肝臟等器官損害。
Wilson 病患者的發病年齡多見于5~35歲,但發病年齡不能作為診斷或排除Wilson病的依據,該病的臨床表現為肝臟損害、神經精神表現、腎臟損害、骨關節病及角膜色素環(K-F環)等。
Wilson 病的診斷標準包括:1.神經和(或)精神癥狀;2.原因不明的肝臟損害;3.血清銅藍蛋白降低和(或)24h尿銅升高;4.角膜色素環(K-F 環)陽性;5.經家系共分離及基因變異致病性分析確定患者的2條染色體均攜帶ATP7B 基因致病變異。符合(1 或2)+(3 和 4)或(1 或 2 或 3)+5 時,均可確診為Wilson 病。為診斷Wilson 病,原先醫療機構會要求進行肝穿刺活組織檢查,但隨著我國ATP7B基因檢測技術的普及,此項肝銅量檢測的重要性已降低,且肝穿刺是有創檢查,故國內專家一般不再推薦該項檢查。
Wilson病采用早期治療、終身治療、終身檢測的治療原則,由于Wilson病可能引起的臨床癥狀多變,故醫療機構往往需根據患者的臨床表現采取不同的治療策略。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懷疑患者罹患Wilson 病,患者應立即開始低銅飲食,以有效控制銅蓄積對靶器官的損害。
Wilson 病未經治療通常是致殘或致命的,患者病死率在5.0%~6.1%,但Wilson 病作為少數可治的神經遺傳病之一,經過長期規范的治療,可以大幅延長患者的壽命。在疾病早期,神經癥狀出現之前就進行干預,大部分患者可回歸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經過治療,癥狀穩定后,可正常結婚和生育,但需注意配偶也應進行ATP7B基因檢測,以免再次生育Wilson病患兒。
二、案情簡介
【投保】2017 年7 月20 日,白女士為其3歲的女兒琪琪(化名)在Y 保險公司投保了某款重疾險。
【確診】2019 年5 月,白女士注意到琪琪的發育明顯慢于同齡的小朋友,遂前往多家醫院進行檢查,發現血清銅藍蛋白和尿銅指標異常,最終被診斷為罕見的基因遺傳疾病“肝豆狀核變性”,需終身服藥治療。
【理賠】白女士以琪琪罹患“肝豆狀核變性”向Y保險公司申請理賠,Y保險公司卻以琪琪未達到合同約定的重大疾病相關條件而拒賠。Y 保險公司工作人員進一步指出,依照合同約定,只有滿足下列全部條件的“肝豆狀核變性”方可獲得理賠:1.典型癥狀;2.角膜色素環(K-F環)陽性;3.血清銅和血清銅藍蛋白降低,尿銅增加;4.經皮做肝臟活檢來定量分析肝臟銅的含量。琪琪未符合第2、第4項條件。
白女士多次溝通理賠事宜未果,決定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辦案結果】通過與法官的多輪溝通,白女士的律師團隊綜合運用專業醫學知識和法律規定,讓法官充分了解了“肝豆狀核變性”這一疾病的醫學診斷標準,成功突破保險公司在保險合同中設置的不合理門檻限制,幫助白女士全額獲得保險金。
三、法律分析
(一)琪琪已經確診保險合同約定的重大疾病,保險公司應當按約理賠
《健康保險管理辦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保險公司在健康保險產品條款中約定的疾病診斷標準應當符合通行的醫學診斷標準,并考慮到醫療技術條件發展的趨勢。健康保險合同生效后,被保險人根據通行的醫學診斷標準被確診疾病的,保險公司不得以該診斷標準與保險合同約定不符為理由拒絕給付保險金。”

琪琪雖未出現K-F 環癥狀,但K-F 環是“肝豆狀核變性”輔助檢測依據之一,并不是作為判斷該病嚴重程度的依據。依據醫療常識,并非所有臨床癥狀均會涵蓋病癥的所有典型癥狀。總的來看,琪琪已出現血清銅藍蛋白低于正常區間、尿銅含量高于正常區間等“肝豆狀核變性”的典型臨床癥狀,亦通過基因檢測確認其存在“肝豆狀核變性”的相關致病基因。醫院為此出具了《疾病診斷證明書》,確認琪琪已患有“肝豆狀核變性”。
因此,琪琪依據現有醫學診斷標準已經被確診為“肝豆狀核變性”,保險公司不得以琪琪未出現保險合同約定的全部典型癥狀為由拒絕給付保險金。
(二)保險公司不得在條款中設置不合理的或者違背一般醫學標準的要求作為給付保險金的條件
本案中,保險公司堅稱,根據保險條款要求,琪琪必須以肝臟活檢的方式確診為“肝豆狀核變性”,否則就不符合理賠條件。但是,琪琪年僅七歲,肝臟活檢作為一種有創檢查,顯然對其身體健康不利。相比之下,基因檢測對琪琪的身體損害更小,結果也更加精確。在醫生的建議下,白女士選擇了通過基因檢測進行診斷。
《健康保險管理辦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保險公司擬定醫療保險產品條款,應當尊重被保險人接受合理醫療服務的權利,不得在條款中設置不合理的或者違背一般醫學標準的要求作為給付保險金的條件。”事實上,隨著ATP7B 基因檢測技術的普及,肝臟活檢作為有創檢查,目前在醫療實踐中,醫生已經不再推薦患者采取該項檢查,保險公司的此項要求事實上已經遠遠落后于醫療實踐技術發展,明顯不合理。
(三)對重大疾病標準的解釋應符合普通人對合同締結目的的合理期待
鑒于重大疾病保險的專業性和特殊性,保險人與投保人、被保險人在保險業務的信息、經驗和知識方面存在嚴重不對等。《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三十條規定:“采用保險人提供的格式條款訂立的保險合同,保險人與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對合同條款有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合同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應當作出有利于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解釋。”因此,對重大疾病的認定應優先按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即以普通人對合同締結目的的合理期待為出發點,以現行合理科學的醫療診斷標準為依據。即使雙方對條款內容仍有不同解釋,也應依法采用有利于被保險人的解釋。
事實上,這一點也是目前司法實踐的主流觀點:被保險人依照通行的醫學標準確診保險合同范圍內的重大疾病,保險公司不得以不符合自身條款約定的疾病診斷標準為由拒絕理賠。
四、律師建議
(一)被保險人可以用疾病診斷作為申請理賠的依據
《健康保險管理辦法》第二十三條第二款規定:“健康保險合同生效后,被保險人根據通行的醫學診斷標準被確診疾病的,保險公司不得以該診斷標準與保險合同約定不符為理由拒絕給付保險金。”由此可見,重大疾病的認定標準并非唯一。除了保險合同中約定的重大疾病認定標準外,通行的醫學診斷標準同樣是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時可以援引的認定標準。
(二)雙方對合同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且無法得出通常理解的,應作出有利于被保險人的解釋
保險公司與投保人訂立的保險合同多為保險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投保人很難就保險合同的相關條款與保險人進行商榷。尤其是在健康保險領域,條款更具特殊性和專業性,保險人與投保人、被保險人在保險業務的信息、經驗和知識方面存在嚴重不對等。因此,如雙方對條款存在兩種以上的解釋而又無法得出通常理解,則應當作出有利于被保險人的解釋。
(三)保險公司應當尊重被保險人接受合理醫療服務的權利
根據《健康保險管理辦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保險公司擬定醫療保險產品條款“應當尊重被保險人接受合理醫療服務的權利”。即,保險公司應當尊重被保險人具有根據自己的病情、身體情況、醫生專業建議等因素綜合選擇自身診療方式的權利。保險公司一味僵化地堅持自身訂立的條款標準,不僅違反一般醫學標準,更有悖投保人和被保險人投保時的初衷,對保險消費者有失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