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藝術學在新時代的理論方向
——馬克思藝術思想的必然性及其與中國傳統藝術思想的統一性
尹德輝
(臨沂大學美術學院,山東 臨沂 276000)
習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做好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要善于從三個方面融通古今中外的各種資源。“一是馬克思主義的資源,這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主體內容,也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最大增量。二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資源,這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十分寶貴、不可多得的資源。三是國外哲學社會科學的資源,包括世界所有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取得的積極成果,這可以成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有益滋養。”(2016年5月17日)藝術學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藝術學理論作為藝術學中的基礎理論學科,同樣要遵循習總書記所指明的這個發展目標和研究方法。
藝術,在中西方文化史中,始終都是一個受關注的對象。從孔子的“興觀群怨”到劉熙載的《藝概》,從柏拉圖對詩的矛盾立場到康德的“美的技藝”,中西歷代思想家在自己的文化傳承中,以不同方式做出了各自的探索。到19世紀中期,這種相對平行的發展格局,開始向一種新的關系模式發生轉換。一方面,西方藝術理論加快了自身的邏輯演變,在巴托、康德的“美的技藝”之后,出現了謝林、黑格爾的“藝術哲學”,費德勒、德索等人的“藝術學”,以及風靡近一個世紀的現代藝術運動;另一方面,中國傳統藝術理論在這些西方藝術思潮的強勢影響下,處在了一個與之交匯、融通的復雜糾葛局面之中。迄今,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藝術學在我國學科體制中的穩步確立,包括藝術理論在內,這種以中西方對立、融合為主要傾向的文化交流方式,也到了一個漸趨統一、明朗發展的新階段。這既是中國傳統藝術理論現代轉型并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也符合西方藝術理論發展的內在邏輯訴求。中華文化是在對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先進外來文化的吸收基礎上,在面向未來的文化創造中不斷實現的,所以,中國藝術學如何繼續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方向指引,積極繼承中華傳統藝術理論和西方藝術理論兩個資源中的核心和精髓,是進一步確立自己的學科地位并走向世界的關鍵所在。
一、藝術的本質在西方藝術理論史中的歷時性呈現
當前,關于藝術的本質和藝術的定義等藝術學的核心問題,在西方現代藝術理論中已陷入循環論證的思維局限。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方面,藝術并非沒有本質,也并不是不可定義。早在柏拉圖對詩人的驅逐中,藝術的本質就以否定性的方式顯現出來了。另一方面,在從亞里士多德到康德,及其之后的現代藝術理論對藝術的各種肯定中,也存在不可克服的邏輯缺陷。藝術的本質和定義將生成于馬克思哲學對西方藝術理論缺陷的克服及重建之中。
第一,藝術的“感性、情感性、倫理性”本質在柏拉圖對詩和詩人的驅逐,也就是在對藝術的懷疑和否定中,得到了最初的顯現。
西方藝術理論的思想源頭是古希臘哲學。如在古希臘神話中就有掌管藝術的女神繆斯,在前蘇格拉底哲學中,恩培德克利、德謨克利特、高爾吉亞等人也都有關于藝術的論述。作為古希臘哲學的集大成者,柏拉圖不僅為西方哲學的后續發展奠定了基礎,而且作為核心的部分之一,那些被我們今天稱為藝術的詩歌、音樂、繪畫、雕塑、建筑等,盡管是以一種矛盾悖論的方式,也受到了柏拉圖的特別關注。
一般認為,柏拉圖是藝術的反對者,或是哲學和藝術之爭的哲學捍衛者。但是,柏拉圖只是對藝術有所反對,而不是全面地否定藝術。比如,他一方面反對詩人進入理想國。“我們終于可以說,不讓詩人進入治理良好的城邦是正確的,因為它會把靈魂的低劣成分激發、培育起來,而靈魂低劣成分的強化會導致理性的毀滅,就好比把一個城邦的權力交給壞人,就會顛覆城邦,危害城邦里的好人。”(國家篇 605B)但另一方面,他也對詩人有所挽留。“要是消遣的、悅耳的詩歌能夠證明它在一個管理良好的城邦里有存在的理由,那么我們非常樂意接納它,因為我們自己也能感受到它的迷人,……當詩歌用抒情詩或用別的什么格律為自己作了辯護之后,它難道不可以公正地從流放中回來嗎?”(國家篇607CD)柏拉圖之所以驅逐詩人,是因為有些詩可以通過感性和情感去“訴諸靈魂的低劣成分,以至毀滅理性”;而之所以又對詩人有所挽留,則是因為詩歌既可以對道德有所助益,也是令人愉快的,具有迷人的魅力。顯然,柏拉圖不是完全地反對詩和其他藝術,而是也肯定詩歌等對人的積極作用。這樣,兩個方面就構成了一個對藝術既否定也肯定的矛盾關系,成為柏拉圖留給后人的“藝術悖論”。
柏拉圖之所以對藝術持一個相對負面的消極態度,與柏拉圖哲學的邏輯特征有關。柏拉圖哲學是一個以理性為主導的自上而下的“理式”哲學。首先,對理性來說,由于詩歌、音樂、繪畫等作為人的技藝,和理式的距離較遠,比如在作為“模仿的模仿”的繪畫中,就存在由于理式的退化而具有欺騙性的可能。同時,以感性和情感為特質的藝術,不僅處在邏輯和理性的范疇之外,而且作為理性的異質對象,藝術所喚起的感性和情感也無法在理性中做出是否符合理式的邏輯判斷。其次,對感性來說,由于感性永遠無法感知到那個“始終同一的、非被造的、不可毀滅的”的理式(蒂邁歐篇52A,B),所以感性在邏輯上就是不可靠的;而詩歌、音樂等又恰恰是只作用于人的感性且喚起人的情感的技藝,所以藝術就更成為一個非邏輯的不可靠對象。在柏拉圖自上而下的理式哲學中,不僅從理性和感性方面,藝術都不是一個被積極肯定的對象,而且理性和人本身都處在一個相對于理式、神的次要地位上,尤其是,作為一種感性和情感的技藝,藝術還潛在地對理式、神、倫理、理性具有可能的危害性,所以必然在柏拉圖哲學中受到懷疑甚至完全的否定。
但是,即便在對藝術的這種否定中,柏拉圖還是揭示了藝術不同于其他技藝的基本特征,即“感性、情感性、倫理性”。作為一種人的技藝:首先,藝術的對象不是人的理性,而是人的感性;其次,藝術具有情感功能,并可以通過情感作用于人的理性;再次,藝術具有倫理道德功能,可以助益或者破壞人的理性。比如,詩、音樂、繪畫、雕塑、建筑等作為藝術,就在于它們都是作用于人的感性,并為人帶來愉快的情感,而在它們的倫理性方面,則或有害或有利于人的理性,故而成為不確定的必須懷疑的對象。我們看到,正是由于藝術的這三個基本特征,主要是其倫理性的不確定性,不僅不是必然地有利于理想國,而且還具有潛在的危害性,所以柏拉圖才堅決地反對藝術。通俗地說,在柏拉圖哲學中,由于人不僅具有理性,還具有感性,且是一種情感的動物,對由感性而產生的情感,如高興、憤怒、哀傷、愉快等,我們無法在理性和邏輯中對它們本身做出是否道德、善惡、美丑的倫理判斷,所以,藝術就因其感性、情感的倫理不確定性而處在一個兩難的哲學困境中。但是,僅就柏拉圖對藝術的否定而言,柏拉圖否定的只是其中的倫理性的不確定一面,而不是對作為藝術特征的“感性、情感、倫理性”的全面否定。其中,柏拉圖既不否定藝術的感性和情感特征,也不否認藝術可以對人的理性具有積極的倫理作用,甚至還可以通過辯護讓藝術“公正地從流放中回來。”(國家篇607CD)。所以,在柏拉圖對藝術的驅逐和他的兩難悖論中,藝術的本質特征已經得到了基本呈現。這是柏拉圖哲學之所以成為西方藝術理論起點的根源所在。
之后的亞里士多德試圖改造柏拉圖的哲學,但是,在他的“詩學”中,不僅柏拉圖的藝術悖論沒有得到解決,而且體現于其中的亞里士多德的藝術思想,與其形而上學、物理學、倫理學也不能形成統一的邏輯關聯。和柏拉圖哲學相比,由于亞里士多德的思想并不構成一個有機整體的邏輯體系,他的藝術思想就還不及柏拉圖更為集中和深刻。但是,對由人的感性而來的情感的倫理屬性,亞里士多德在“快樂”和“實現活動”的關系中還是做出了一個超出柏拉圖的邏輯推進。“既然實現活動有好壞的不同,有的值得欲求,有的應該避免,有的既不值得欲求也不需要避免,所以,實現活動是好的,其快樂也是好的,實現活動是壞的,其快樂也是壞的。”(尼各馬可倫理學 1075b 25)通過和實現活動的這種聯合,快樂便不再是一種孤立的情感,而是和實現活動聯系在一起的情感;這就將對情感的判斷轉換為對實現活動的判斷,反過來就等于實現了對快樂等情感的倫理判斷。如此,亞里士多德推進了古希臘哲學對詩歌等藝術的倫理判斷。
古希臘之后的新柏拉圖主義和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大體上都沿襲了柏拉圖的藝術觀念。從古羅馬到文藝復興,詩、音樂、繪畫、雕塑、建筑等,始終都與其他的各種技藝混雜在一起,在“自由技藝”和“機械技藝、粗俗技藝”的劃分中,藝術的基本特征并未得到進一步地揭示,甚至還達不到柏拉圖的思想水平。實際上,“自由技藝”和“機械技藝、粗俗技藝”的劃分都是一些和藝術的本質完全無關的分類。
第二,康德對“美的技藝”的闡明,在西方哲學史中積極肯定了藝術的“感性、情感性、倫理性”本質。
文藝復興既是古希臘藝術的復興,也是對人的感性、情感的解放。從詩和文學開始,繪畫、雕塑、建筑、音樂等各種藝術形式都得到了極大的繁榮和發展。到了18世紀,法國的夏爾·巴托神父將“音樂、繪畫、舞蹈、雕塑和詩”這五種技藝集合在一起,統稱為“美的技藝”。但是,雖然巴托準確劃定了藝術的范圍,卻并未正確闡明藝術的分類原則。他延用了古希臘以來的傳統觀念,依舊將“模仿”作為這些藝術的本質,只不過附加了一個條件“美的”,即:“美的技藝模仿美的自然”。顯然,巴托只是在亞里士多德“技藝模仿自然”(物理學199a 10)的基礎上,在技藝、自然之前各加了一個定語“美的”。這并沒有擺脫古代哲學的局限,“模仿”并不是藝術的本質。
早在古希臘的柏拉圖哲學中,藝術已被大致確定在“感性、情感性、倫理性”的范圍之內,只是由于理式和感性、情感的不兼容性,藝術才成為一個消極而悖論的哲學對象。進入近代,包括巴托和鮑姆嘉通在內,康德之前的思想家不僅在美學、藝術問題上,而且在哲學上都還處在一種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思想雜糅階段。雖然他們試圖從感性和現實的人出發,應用近代的科學、藝術的最新成果,去實現亞里士多德對柏拉圖哲學的翻轉性重建,以建構起一個人的哲學,但這個任務的初步完成是在康德哲學中。
在感性(審美)判斷力批判中,康德以一個相對獨立的部分討論“技藝”(Kunst)。這既是康德思想視野的全面性之所及,也是他承繼西方哲學的結構性之所限。本來,始自古希臘的哲學術語“技藝”,已經在近代科學、技術和藝術的興起中被逐步替代了。在康德的“純粹理性——形而上學、實踐理性——倫理學、判斷力——感性和目的”的三重批判架構中,技藝及其中的美的技藝(藝術)也沒有直接的邏輯位置,但康德仍然從“技藝”到“美的技藝”做了詳實的分類,其目的就在于在對“美的技藝”的確立中:一方面,以近代哲學自下而上的方式,翻轉自上而下的古代哲學中的技藝思想,并解決柏拉圖遺留的藝術悖論;另一方面,在“技藝——美的技藝(藝術)”這個特殊領域中,確立人的感性和情感的倫理正當性,以全面地完成他對人的感性和情感的哲學確立。
康德在感性(審美)判斷力批判,也就是在感性(鑒賞)判斷的四個契機和對崇高的分析中,確立了人的感性、情感和美的必然關系。這就掃清了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未能克服的邏輯障礙,為解決藝術問題開辟了理論路徑。在完成了對感性判斷力的批判之后,康德在總注釋的§43~§53中,首先沿用了亞里士多德的方式,將技藝和自然分開;然后,再和科學、手藝相互區分;繼而,將之前的“自由技藝”和“機械技藝”的關系置換為“感性(審美)的技藝”和“機械的技藝”的關系;最后,將“感性的技藝”區分為“快適的技藝”和“美的技藝”。“感性的技藝要么是快適的技藝,要么是美的技藝。它是前者,如果技藝的目的是使愉快去伴隨作為單純感覺的那些表象,它是后者,如果技藝的目的是使愉快去伴隨作為認識方式的那些表象。”這樣,康德就既接受了巴托等人對藝術分類的近代事實,也以肯定性的方式繼承了柏拉圖早在古代哲學中即已揭示的藝術的感性、情感本質,尤其是在“快適的技藝”和“美的技藝”的區分中,又對藝術的倫理和道德屬性給予了肯定。康德通過對自然、科學、手藝,機械的技藝,快適的技藝的逐次排除的方式,同時超越了柏拉圖和巴托的藝術思想,在對“感性、情感性、倫理性”的肯定中,確立了美的技藝(藝術)的哲學地位。
更具體而言,康德在他的技藝分類中,既繼承了技藝在之前古代哲學中的基本分類,比如亞里士多德對“技藝與自然”的區分,對古羅馬、中世紀的“粗俗技藝、機械技藝”的沿用;也做出了他的推進,比如以“感性的技藝”和“機械的技藝”置換了“自由技藝”和“機械技藝”的關系;尤其是,康德在技藝分類中,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完成了對柏拉圖自上而下的藝術觀念的翻轉,實現了近代藝術思想對古代藝術思想的哲學超越。首先,康德在“機械的技藝”和“感性的技藝”的劃分中,完全肯定了藝術所獨具的感性和情感本質。雖然在“手藝、機械的技藝”中未必沒有感性和情感的存在,但康德將只以“感性、情感”為目的的技藝從所有的技藝中區分出來,并在美的技藝中予以完全的肯定;這和柏拉圖對“感性、情感”本身的懷疑、以至對以“感性、情感”為目的的詩、音樂、繪畫、雕塑、建筑等的懷疑和否定相比,是一個截然相反的完全肯定。其次,盡管康德并未直接肯定美的技藝的倫理性,但一方面,由于和美的技藝的愉快相伴隨的是“作為認識方式的那些表象”,這決定了美的技藝與人的知性的必然關系,而康德哲學中的知性(關于認識的純粹理性)和理性(關于倫理的實踐理性)是統一的同一個理性;另一方面,由于康德哲學中的“美、善”是相互對應的關系,即“美是德性-善的象征”,所以,“美的技藝”就是“作為德性-善的象征的技藝”,美的技藝(藝術)就直接象征了倫理和道德。這兩個方面內在地決定了,在美的技藝中先天地包涵著倫理和道德屬性。(在藝術的倫理性方面,之后的西方現代主義者們徹底無視了這里的康德。)因此,在技藝的分類中,康德對“美的技藝”(藝術)的哲學屬性的闡明,即對藝術的“感性、情感性、倫理性(美、善)”這個本質特征的哲學肯定,已不只是對巴托的“美的技藝”的再次確認,或是對其分類原則的某種修正,而是在哲學上終于解決了產生于柏拉圖哲學的藝術悖論,并標志性地推進了始于古希臘的西方藝術理論,具有歷史轉折性的思想史意義。
在由柏拉圖開辟的西方藝術思想史中,撇開“技藝和自然”的關系這個有待完善的邏輯前提,康德全面地繼承和超越了在他之前的西方藝術思想。然而,在黑格爾用“藝術哲學”替代“美的藝術哲學”之后,“藝術”(Kunst)就取代了康德所確立的“美的技藝”(sch?nen Kunst)。自此,“藝術”概念就完全失去了始自古希臘的技藝涵義,現代的“藝術”(Art)觀念確立起來了;但在這個過程中,康德所確立的“美的技藝”的分類原則和哲學屬性(感性、情感性、倫理性)卻受到了忽視,藝術分類的結果,也就是具體的藝術種類,反到成了西方藝術理論的核心對象。在之后,對某種事物是否屬于藝術的判斷,并不是根據康德所確立的“美的技藝”的原則,即其是否具有“感性、情感性、倫理性(美、善)”的本質特征,而是反之,現代藝術理論只去考察具體的藝術,試圖再從中抽象出某種共性作為藝術的本質。顯然,這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虛幻命題,放棄了“感性、情感性、倫理性(美、善)”的本質特征,不管是堅持或是反對將“模仿”作為藝術的本質,還是在藝術體制中抽象出“自律、無功利”等其他特征,都不是藝術的本質屬性。
柏拉圖和康德都實質性地觸及了藝術的本質,但是,由于他們各自的哲學特征,即,柏拉圖的哲學不是一個以人為主體的哲學,康德的哲學是一個否定性的批判哲學,所以,藝術的本質在他們的哲學中不能以一個積極肯定的方式呈現出來。只有在之后的馬克思對以黑格爾哲學為集大成的西方哲學的徹底批判中,當馬克思整體翻轉了西方哲學,將思辨的、抽象的、理論的西方哲學轉變為一個實踐的、具體的、現實的人的哲學之時,其中的藝術思想才獲得了不同于以往西方藝術理論的實踐本質;或者說,雖然柏拉圖、康德在不同的時代,以不同的方式揭示了藝術的本質,但這個本質只有在馬克思哲學中才能得到肯定性的呈現。
二、馬克思哲學的真理性及其對藝術本質的科學揭示
西方現代藝術發展迄今的歷史事實證明,作為其理論支撐,康德之后的現代藝術理論并不具有指導實踐的真理性;藝術的真理性只能產生在西方哲學對康德哲學的進一步推進,即對西方哲學的整體批判與邏輯翻轉的馬克思哲學中。
在西方哲學從古代以神為主體向近代以人為主體的邏輯轉換中,藝術的地位也要發生改變。在以柏拉圖哲學為核心的古代哲學中,感性、情感的藝術必然處在一個相對消極的地位上;只有在以人為主體的近代哲學中,隨著人的感性、情感在近代感性哲學(感性學/美學)中的確立,藝術才可能在哲學中得到積極的肯定。從柏拉圖對詩的驅逐,到康德對美的技藝的肯定,就是這樣一個逐步轉換的演變過程。然而,雖然康德在哲學上肯定了藝術,但由于他的哲學是一個否定性的批判哲學,只是在人的哲學建構中以否定的方式清理了其中獨斷論和經驗論的各種邏輯障礙,所以,在康德對藝術的肯定性和他的整個哲學的否定性之間就出現了邏輯齟齬。因此,當其后的西方藝術理論直接接受了康德對藝術的肯定,但并未將其置入他的哲學整體之中予以關聯性地對待之時,“美的技藝——藝術”便從之前的關系語境中被孤立出來。事實上,當現代主義藝術理論及其影響下的藝術實踐,在一個有限且孤立的范圍內的各種邏輯可能性都被推演過一遍之后,現代藝術就要不可避免地走向終結。這從歷史來說,是康德之后的西方藝術理論片面地對待了康德藝術思想的結果;從康德本人來說,則是其哲學的內在局限后續發展的必然后果。對康德哲學這種邏輯缺陷的批判與糾正,只能在以每一個現實的人為哲學主體的馬克思哲學中才能實現和完成。
藝術作為人的一種技藝,不同于其他各種技藝的特殊性是其感性和情感特征。一方面,感性和情感只能以人為主體,所以,藝術只能是人的技藝,繼而,哲學對藝術的肯定,也只能建立在人的哲學基礎上;另一方面,感性和情感的時間性特征決定了它們的現實性才是其存在的真理性,藝術不能存在于概念或理論性的觀念之中,而只能存在于時間性的直接現實當中。就是說,藝術只能存在于現實性的人及其哲學之中。康德之后,這種現實性的哲學和現實性的人,就是馬克思哲學及其中的人。馬克思哲學是對西方近代人的哲學的繼續推進,是包括笛卡爾、康德、黑格爾等在內的近代哲學的最后完成,是實現了人的現實性的哲學。馬克思哲學,既不同于康德批判哲學是一個否定性且抽象的人的哲學,也不同于黑格爾哲學是一個對神學的恢復,更不是之后的其他各種在思想邏輯上產生退化的西方現代哲學,而是從“現實的人(人的個別性、特殊性)出發,到“人的實現(人的普遍性、一般性)的真正的人的哲學。所以,對藝術的哲學肯定,只能在馬克思對康德哲學的繼續推進,也就是在對全部西方哲學的整體批判基礎上,在現實的人的哲學建構中才能實現。
西方思想發展的內在邏輯決定了從康德哲學向馬克思哲學轉換的必然性。在這個必然的思想轉換中,康德的“美的技藝”思想中的邏輯缺陷得到了克服,馬克思的藝術思想成為西方藝術理論發展的必然歸宿和新的起點。
康德對藝術(美的技藝)的哲學肯定,實際上是通過排除法,確立了藝術的相對邊界;即,藝術不是自然、科學、手藝,不是機械的技藝,不是快適的技藝,而是那個與認識的表象相伴隨的、令人愉快的、感性的技藝。這個排除法雖然和康德的感性(審美)判斷力批判是邏輯一致的,(即在對感性的鑒賞和崇高判斷中,在對理性的善和概念的排除、對感性所喚起情感的經驗性快感的排除中,確立了人的純粹感性和美的必然聯系。)但是,在“美的技藝”的邏輯起點,康德直接挪用了亞里士多德關于技藝和自然相互對立的思想。其問題在于,在亞里士多德哲學中,技藝和自然的關系原本就是一個有待明確的基礎關系。一方面,亞里士多德認為:“關于創生的事物,有些是自然所成,有些是技術所成,有些是自發所成。……自然事物為自然所創造;……自然產物是這樣生成的,其它產物則稱為‘制品’。一切制品或出于技術,或出于機能,或出于思想。”(形而上學 1032a 15)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事物之創成為實是或由技術(人工)或由自然,或出機遇或出自發。技術之為動變原理出于被動變事物以外之另一事物,自然之為動變原理則出于事物本身(如人生人),其它的原因則為兩者之闕失。”(形而上學 1070a 5)就是說,在亞里士多德哲學中,自然和技藝之間的界限或對立并不是絕對的,其間還模糊地存在著“兩者之闕失”或“自發所成”的其他事物。因此,康德所建構的包括“美的技藝”(藝術)在內的“技藝”體系,在哲學上就存在著先天的邏輯疏漏。“美的技藝”能否建立在技藝和自然的對立關系基礎之上,還有待深入細查和推究。這既體現為康德對美的技藝的闡明(§43~§54)在判斷力批判中稍顯突兀的結構性關系,也在康德之后的現代藝術理論和現代主義藝術中得到了實際的驗證。盡管現代藝術理論中存在著對康德的理解偏差,但這種偏差的根源是來自康德自己的這種有待完善的論證基礎。
相對而言,技藝和自然的關系,對任何以人為主體的哲學來說,不管是在亞里士多德還是康德哲學中,都不可能得出邏輯完善的闡明。這是因為,技藝和自然在理論上的對立統一,只能實現在自上而下的柏拉圖式哲學中,至高無上的理式、或神的創造,先天地保證了技藝和自然的統一性;反之,在人的哲學中,由于失去了神或理式的最高統一性,一方面,人的技藝,另一方面,與人相互對立的自然,再一方面,作為自然的一部分的人(人的自然),三者(技藝、自然、人)的關系既不可能在技藝中,也不可能在自然中得到統一,而只能在作為自然的人或人的自然中獲得統一性。這是說,技藝、自然、人,這三個方面的統一性,不可能實現在技藝和自然的抽象的理論關系中,而只能實現在以人為主體的技藝和自然的現實關系中。技藝、自然、人的對立統一關系,即這三個方面的現實性關系,就是馬克思哲學中的“勞動”。繼而,對藝術(美的技藝)而言,那個在柏拉圖和康德哲學中以否定性的方式呈現的藝術的本質,即藝術的“感性、情感性、倫理性(美、善)”特征,也將隨著從柏拉圖、康德哲學到馬克思哲學的轉換,即從柏拉圖、康德的藝術思想向馬克思藝術思想的歷史轉換中得到肯定性的積極呈現。
柏拉圖、康德哲學中的藝術都是建立在技藝(或與自然相對立的技藝)的基礎之上,藝術也隨之具有了技藝的各種哲學屬性;同樣,建立在馬克思的“勞動”基礎上的藝術,自然也將隨之擁有勞動所具有的各種哲學屬性。因此,柏拉圖、康德的藝術思想和馬克思的藝術思想的關系,也就成為建立在技藝基礎上的藝術和建立在勞動基礎上的藝術的關系。因此,技藝和勞動的關系,就成為理解柏拉圖、康德和馬克思的藝術思想,以至整個西方藝術思想演變的關鍵所在。
在馬克思哲學中,勞動不只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學術語,而首先是一個最重要的哲學術語,人的本質就建立在勞動的基礎上,即“勞動創造人”。在西方哲學中,勞動并不是突然出現在馬克思哲學中,而是早在古希臘神話這個源頭上就已存在。在西方哲學中,馬克思的“勞動創造人”是一個貫通性的思想翻轉,是以神為核心的古代哲學轉換為以人為中心的現代哲學的必然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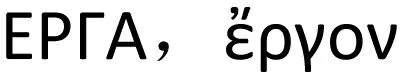
顯然,兩千多年之后,當馬克思將人的哲學建立在“勞動”基礎上時,這并不是他個人的突發奇想或靈感閃現,除了亞當·斯密和黑格爾的直接影響之外,這是由西方思想源頭中潛在的文化基因所決定的。馬克思的哲學和藝術思想并不是西方近代思想發展的偶然結果,而是作為一個邏輯整體的全部西方思想發展的必然結果。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曾對勞動與人的本質關系做出了在他全部著作中一個最經典的闡明。
“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引起、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人自身作為一種自然力與自然物質相對立。為了在對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質,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頭和手運動起來。當他通過這種運動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變自然時,也就同時改變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著的潛力發揮出來,并且使這種力的活動受他自己控制。……蜘蛛的活動與織工的活動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多建筑師感到慚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筑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著,即已經觀念地存在著。他不僅使自然物發生形式變化,同時他還在自然物中實現自己的目的,這個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為規律決定著他的活動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須使他的意志服從這個目的。”
在神話或有神論哲學中,人作為神的創造物,勞動是神指派給人類的神圣義務,那么在馬克思哲學中,這種被創造性和義務的神圣性已經翻轉為一種體現人的本質的自然創造性。就是說,勞動已經不再是人的神圣義務,而直接就是人的自然本質。在馬克思的勞動中,人類生存所必需的各種技藝,都將建立勞動的基礎上,存在于之前哲學中的技藝和自然的矛盾,就將在勞動的基礎上自然化解,技藝和自然成為一個既統一且同一的相互關系。在現實性的勞動關系中,從亞里士多德、康德那里的技藝和自然的邏輯齟齬已經化解,自然和技藝的關系得到了全面的澄明。
當然,限于馬克思本人的研究范圍,他并未對藝術展開充分的研究,如他指出:“撇開真正的藝術作品不說(按問題的性質來說,這種藝術作品的考察不屬于我們討論的問題之內)”。但在技藝與自然相互統一的“勞動”基礎上,由于勞動的現實性和倫理價值的先天性,即便馬克思在他的哲學中并未直言藝術的本質,但作為技藝中的一個特殊部分,在馬克思的尚未展開的藝術思想中,還是將不僅全面地繼承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康德等人建立在技藝基礎上的藝術本質,即“感性、情感性、倫理性”本質,而且藝術的這些本質特征,也將在馬克思哲學中得到肯定性的全面呈現。如,馬克思曾舉例說:“一個歌唱家為我提供的服務,滿足了我的審美的需要(?sthetisches Bedürfni?),但是,我所享受的,只是同歌唱家本身分不開的活動,他的勞動即歌唱一停止,我的享受也就結束;我所享受的是活動本身是它引起的我的聽覺的反應。”一方面,馬克思肯定了歌唱藝術的感性和情感特征,在其中的“歌唱家的活動、歌唱一停止、聽覺的反應,活動本身、享受”這些描述和概念中,無不體現了歌唱藝術的感性和情感性的現實性特征。另一方面,馬克思在此并未使用具有倫理確定性的概念“美”(Sch?nheit),而是用了不確定性的概念“感性、審美”(?sthetisches),這正是由于感性的歌唱是“美的”還是“快適的”,恰恰是一個有待做出藝術批評(審美—倫理)判斷的對象。總之,雖然馬克思哲學的未完成性,決定了馬克思的藝術思想是一個有待展開的嶄新領域,但在馬克思關于藝術的各個零星而分散的論述中,藝術的“感性、情感性、倫理性”本質已經邏輯地內在于其中了。
在馬克思哲學的基礎上,我們可以繼續推進馬克思的藝術思想:藝術隨著勞動的產生,也就是人類的產生,就在感性的方面并以感性和情感的形式,自然地內化在創造了人類的勞動之中;在勞動和人類的誕生中,具有感性和情感特征的藝術也同時性地起源了。在這個前提下,柏拉圖和康德等人以技藝為基礎所揭示出的藝術本質,即“感性、情感性、倫理性”就將得到肯定性的確立。一方面,在柏拉圖哲學中,處在驅逐和挽留之間的藝術,隨著奠基于勞動的基礎之上,那些存在于藝術中的消極后果,就被先天地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在康德哲學中,藝術(美的技藝)中被間接地肯定的倫理屬性,也隨著奠基在勞動的基礎上,以前提的方式成為感性和情感愉悅的基礎條件。馬克思不僅完全繼承了自柏拉圖以來的西方藝術思想,而且其思想的基礎和內涵已經全面超越了在他之前的所有西方藝術思想。
在馬克思哲學的勞動基礎上,由于藝術的感性、情感性和倫理性直接統一在現實的同一性之中,所以,在柏拉圖、康德哲學中得到初步揭示的藝術的本質,也就轉換為以情感為表征的人的勞動本質的感性呈現。簡而言之,在馬克思哲學中,藝術的本質就是以情感為表征的人的勞動本質的感性呈現。這個闡明了的藝術本質,是馬克思主義藝術學的基礎,與之相關的諸如藝術的定義、藝術美、藝術作品、藝術史、藝術家等相關問題,都將隨之具有嶄新而可靠的邏輯起點。
三、中國傳統藝術思想和馬克思藝術思想的邏輯統一性
西方藝術理論的雛形雖然早在古希臘的柏拉圖哲學中即已形成,但以肯定的方式確立起來,則是到了馬克思哲學中才得以初步的實現,且仍處在一個不斷建構的進程之中。與之相比,中國古代的藝術思想則呈現為一個大致相反的方式。
首先,中國傳統藝術理論從最初就肯定了藝術的“感性、情感性、倫理性”特征,而且尤其強調了其正面的倫理功能。如,在《尚書·堯典》中記載了最早的樂論。“帝曰:夔!命女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尚書·堯典)其中,“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是指音樂的感性和情感方式;“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強調的就是其倫理要求。再如,《周禮·春宮宗伯》記載了周代官制中的樂教體系。樂教由大司樂負責掌管,樂教的對象是作為國家接班人的貴族青少年,樂教的內容為黃帝以來的歷代祭祀鬼、神、袛的合樂舞蹈,在不同的場合、時節、儀節使用不同的樂舞,等。顯然,和柏拉圖側重于關注詩歌、音樂、繪畫等對人的理性的潛在破壞性相比,中國古代藝術理論更傾向于看到藝術在感性、情感方面對社會關系和倫理的積極作用。
其次,在中國古代藝術理論中,與古希臘的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的關系一樣,在對藝術的積極肯定之外,同樣也有對藝術的感性、情感特征的批判和規制。如在《國語》中:“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國語·周語下)感官的“聽、視”不能到達“震、炫”的程度,而是必須要“和、正”,才能有益于“心”。再如,老子指出:“五色使人目盲,馳騁田獵使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使人之行仿(妨),五味使人之口爽,五音使人之耳聾。——是以圣人之治也,為腹而不為目,故去彼而取此。”(道德經·第十二章)就是說,“五色、五味、五音”等感官的過度刺激會使人失去本心,和民眾的溫飽相比是應該放棄的對象。
同時,與柏拉圖對詩歌、詩人的盡管矛盾但仍是完全的驅逐不同,中國古代思想家們對藝術的消極作用有一個更為積極的辯證方式。如,在《墨子》中:“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為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以為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為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為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墨子·非樂上)墨子既肯定了音樂能給人的感官、感性帶來“安、甘、美、樂”的滿足感,也指出了它們不符合于“王之事、民之利”的倫理弊端,然后才表明自己“為樂非也”的藝術立場。與之相反,荀子提出了一個和墨子完全對立的觀點。“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望道,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道樂也,金石絲竹,所以道德也。樂行而民鄉方矣。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荀子·樂論)荀子認為,音樂的功能利弊完全在于人的取舍,“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只要能以“道”制“欲”,音樂就能發揮倫理教化的功能,成為“治人之盛”的藝術。再如,在中庸的儒家思想中,與墨家側重于對音樂的否定和法家側重于對音樂的肯定都不相同,孔子認為,好的藝術作品不僅是“美”的,而且是“善”的。如:“《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論語·八佾)就是說,好的藝術作品既可以給人以感官、情感的享受,也不逾越倫理和道德的規范,是“盡善盡美”的作品。
可見,中國古代藝術理論既重視如何利用藝術的感性、情感特征實現藝術的倫理功能,又注重如何通過倫理規范來制約藝術的感性、情感效果不至于無度。這種既肯定藝術的感情和情感屬性,但也同時強調其倫理正當性的思想特色,在中國古代藝術理論中是一個普遍性的歷史特征。藝術中的感性、情感及其倫理性,二者以對立統一的辯證方式構成了中國傳統藝術理論的邏輯核心。
最后,與西方藝術理論相比,中國傳統藝術理論還有一個更突出的特色,就是以“樂政相通”為基礎的“與民同樂”思想。“樂”與“政”的關系,大約最早出現在《國語·周語下》:“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國語·周語下)就是說,政治要像音樂一樣,要“和”而“平”。這雖然有比喻的成分,但考慮到先秦時期的樂教傳統,其中就包含了以“樂”之“和、平”帶動“政”之“和、平”的更深刻的現實涵義。再如,在《孟子》中:“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孟子·梁惠王下)“民貴君輕”是孟子仁政學說的思想核心,而從藝術的方面來看,這就是在“王、民”對立的視角中,以“獨、少”和“人、眾”的對比,表明了孟子對待“樂、政”關系的藝術立場。之后,荀子又提出:“樂者,圣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移俗,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荀子·樂論)荀子認為,以禮樂的方式達到“民和睦”的善治目的,其優勢正在于“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通俗地說就是,樂教具有“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潛移默化的政治和倫理功能。又如,在孔子關于詩(藝術)的“興觀群怨”,即“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論語·陽貨)思想中,這種“樂(藝)政相通”和“與民同樂”的政治和倫理功能,更是被明確地凸顯出來。
中國古代這種“樂政相通、與民同樂”的藝術思想,實際上就是進入現代社會之后藝術與社會、政治的關系。顯然,這和西方近代藝術理論中的“藝術自律、藝術體制”是直接對立的,而從西方藝術理論的發展整體來說,這種“與民同樂”“樂政相通”的中國古代藝術思想卻與馬克思的藝術思想具有一種內在的邏輯親和性;就是說,當西方藝術理論發展到近代,馬克思以現實的方式將西方傳統藝術理論建立在勞動的基礎上之后,西方藝術思想就和中國古代的傳統藝術理論具有了一種內在的邏輯統一性。
如果我們將馬克思哲學及其中的藝術思想作為西方思想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在其與中國古代藝術理論的比較中(以先秦藝術思想為例)可以發現,二者存在一種相互補充的邏輯對映性。一方面,中國古代藝術理論具有全面的思想內涵,但尚未建在一個邏輯嚴謹的理論基礎之上;另一方面,馬克思的藝術思想雖然具有一個邏輯嚴謹的思想內核,但由于歷史原因,馬克思并未對這個邏輯內核予以系統和深入的全方位展開。——具體而言,首先,從中西藝術理論對比的角度來說,西方藝術理論各個時期的歷史成果,還有待在馬克思哲學的基礎上接受批判并繼續推進;同時,中國傳統藝術理論也需要在馬克思哲學的基礎上進行全面梳理和系統性重建。其次,從中西藝術理論統一的角度來說,中國和西方的藝術理論不僅可以、而且理應得到系統而整體的邏輯統一;同時,實現這種統一的思想前提和邏輯基礎就是馬克思哲學及其中的藝術思想。
中國傳統藝術理論和西方藝術理論都需要在馬克思哲學的基礎上經歷一次全面的檢驗和整體重構,這是中西方藝術理論發展迄今所面臨的一個共同時代課題。正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的,“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一種關于“世界的文學”的藝術理論將在這個時代課題的完成中得以實現。
結語:新時代中國藝術學的理論路徑
藝術學從西方19世紀開始出現,歷經一百多年的興衰沉浮,在21世紀的中國確立起學科地位,從其產生、發展、確立的各種社會條件來說,有其內在的必然性。這首先是來自藝術本身的原因。進入19世紀之后,在康德、馬克思等人的揭示中,藝術作為人的一種把握世界的方式,終于顯現出其不同于政治、經濟、科學、宗教等的特殊本質。這也是費德勒等人倡導藝術學的思想基礎所在。其次,雖然藝術的本質得到了西方思想家們的基本揭示,但由于現實的社會原因,在私有制的資本主義條件下,藝術的本質不可能直接體現為現實存在中的本質。西方思想家雖然確立了理論中的藝術學,但不可能建成學科建制中的現實的藝術學。最后,藝術學之所以在21世紀的中國得以確立,雖然有西方藝術學的歷史影響,但根本原因還是在于,藝術學在中國具有產生和發展的現實土壤。
中國藝術學的現實性來自兩個方面。其一,從傳統的方面,中國古代藝術理論和作為西方藝術理論歷史結晶的馬克思藝術思想具有內在的邏輯統一性;或反之來說,馬克思哲學及其中的藝術思想為中國古代文化及其中的藝術思想開創了走向現代的邏輯路徑,并為準確把握其思想內涵提供了可靠的理論支持。只有在馬克思哲學的基礎上,中國古代藝術理論才能科學有效地完成去粗取精、條分縷析、系統完善的現代性轉化。其二,從當下的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發展,是藝術學經由西方傳播到當代中國并得以復興和發展的現實條件。在中國共產黨對國內文藝事業的正確引領下,當代中國的藝術,不論是傳統的還是現代的、本土的還是外來的,都得到了有效的保護、傳承和發展。這是藝術學的學科地位得以確立并得到持續發展的最主要的現實條件。
站在世界歷史的宏觀視角,在西方的古希臘和中國的先秦時代,藝術理論以不同的方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初步面貌,歷經各自二千余年的漸次發展,當整個人類社會進入到一個全球化的時代,藝術學所需要承擔的文化和歷史使命,已不再是只滿足某種地域性的藝術需求,而是具有了更加宏大的關系到全部人類未來的文化使命。至此,不管是西方藝術理論還是中國傳統藝術理論,就都要在這個新的時代需求面前做出歷史性的自我革命。對中國藝術學來說,這個發端于19世紀西方,形成于21世紀的嶄新學科,其學科建設就必須以馬克思哲學及其藝術思想為基礎,樹立起“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意識,從中西藝術理論的基本共性出發,積極實現中國傳統藝術思想的現代性轉化,以一種可以被全人類所共享的理論和話語形態,在新發展階段中實現其在世界范圍內的傳播與弘揚,在實踐中開創人類“世界藝術”的嶄新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