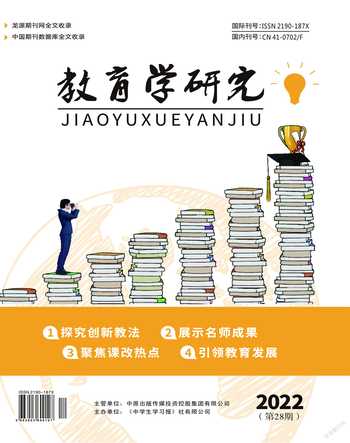正確處理孩子的憤怒 孩子的未來才能旗開得勝
武彩玲
提及“憤怒”,想到這樣一個故事:一位媽媽給家庭教育專家尹建莉老師的來信中說道,某天晚上,她的孩子用積木搭好三架創(chuàng)意十足的“小飛機”,并邀請媽媽前去欣賞。媽媽的贊不絕口讓孩子高興地手舞足蹈。活蹦亂跳中碰翻了“小飛機”,徒留雜亂無章的積木。瞬間,這個小小的人兒勃然大怒,順手拿起枕頭扔起來,不斷地扔,不停地哭。媽媽面對怒火中燒的孩子,不知所措;面對小小的身軀爆發(fā)的熊熊烈火,一片茫然。
尹建莉老師是這樣建議的:孩子把枕頭扔過來,你就把枕頭扔過去,且笑著告訴孩子:“你不用過來撿了,來來回回跑得累,媽媽幫你扔回去。”在枕頭的你來我往中,不知不覺進入一輪新游戲,孩子保準破涕而笑。
我瞬間被尹建莉老師的智慧和通透所折服。
相信,類似的場景在很多家庭隔三岔五地上演。
面對“怒火中燒”的孩子,很多父母會跟孩子一起急,氣急敗壞地威脅孩子“你再扔枕頭,我揍你”;少數(shù)父母一刻也不能忍受孩子的“憤怒”,直接拳腳相加;只有極少數(shù)的父母能像尹建莉老師這樣坦然接納孩子的“憤怒”,優(yōu)雅而從容地消解了孩子的憤怒情緒。
②
有的父母感覺不可思議:不就是幾件玩具嗎?有必要發(fā)那么大的火嗎?
試想想:很多成年人抱著游戲的態(tài)度過人生,而孩子卻抱著嚴肅的態(tài)度做游戲,所以,事關孩子的事情沒小事。幾個小時的勞動成果瞬間被打回原形,是個正常孩子,必然要憤怒。若孩子不憤怒,我們就要考慮這個孩子是否正常了。對于成年人,每個人的感受,也許并不總是表現(xiàn)出來,但卻是一直存在著。
就像快樂、悲傷、憐閔、羞恥、恐懼、無助、絕望和愛一樣,憤怒也是人類正常情感的一部分。每個人一生都在體驗著情緒,從出生到死亡。我們的情緒傳遞著生命的能量。我們通過情緒與家人、與社會保持聯(lián)系。
所以我們要坦然接納孩子的憤怒情緒,就像接納孩子的小鼻子、小腦袋一樣接納他們。
如果你對孩子的憤怒加以壓制:“再鬧,小心我揍你!”這本身是對孩子的一種消極暗示:你不接受來自他的憤怒情緒。這也是對孩子自身價值的一種否定,外界的負面反饋使孩子的形成了消極的自我概念,進而引發(fā)了孩子的低自尊。低自尊的孩子掌握不了主導權,無緣于幸福和成功。
所以,我們要勇敢地接納孩子的憤怒情緒,接納孩子的一切。
③
孩子憤怒的情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憤怒情緒的錯誤消解方式。
幾年前,有個村落發(fā)生的全家滅門案,晚上十點多,丈夫揮起菜刀砍向妻子、一雙二女、以及年過七旬的老父親,最后自殺身亡。只有老父親撿回一條命。究竟那個夜晚全家發(fā)生了怎樣的爭執(zhí)與矛盾,我們不得而知。
但顯然,那天夜里,男人是怒不可遏的,殺人成了他憤怒情緒的極端訴求方式。據(jù)鄰居說,男人平日里不愛說話,不善交流,不茍言笑。他平日里不可能沒有遇到過令他極為惱怒的情況,而通過他平日的表現(xiàn)只能說明他做了很多成年人被期待的事――將憤懣壓抑進心底。
情緒是一種能量,人體是不會消滅能量的。壓抑進心中的憤怒日積月累,能量與日俱增。終有一日,會如火山一樣爆發(fā),以一種扭曲的方式表達心中苦悶。
有些人的憤怒掩埋到地下,在自己的身體里面搞破壞,最終患上高血壓或心肌梗塞等疾病。
以上兩種憤怒的消解方式都不是我們所愿的,更不希望發(fā)生在孩子身上。顯然,壓制孩子的憤怒情緒百害無利。平素,我們要節(jié)制對孩子的話語:不許哭、不許鬧、不許發(fā)火、不許扔東西。孩子傷心地為死去的小貓哭泣,我們就抱著孩子陪他一起流淚;孩子為不翼而飛的玩具吵鬧,我們在一旁溫和地守候著孩子,直到他停止;
既然憤怒是一種能量,無法消滅,我們只能想辦法正確轉移能量,例如跑步、寫日記、發(fā)微博、自我暗示、自我激勵等。孩子在憤怒時不會主動運用以上策略,我們做好表率即可。正所謂正人先正己,傳道先有道。
④
記得作家趙星當年剛到外企上班,面對英語流利得跟母語一般的同事,她無比苦悶。后來她安慰自己:“下再多的功夫,英語怎么可能跟母語一樣,比不過英語,我們就來比母語!”后來,每日下班后無論多累多晚,都要寫作1500字,雷打不動。幾年后,她成為暢銷書作家。
就如作家趙星,接納孩子的憤怒,讓孩子肯定自身的價值,才能讓孩子的暴力傾向轉化為建設性的力量。我們要竭盡所能不要在孩子成長路上留下難以愈合的傷口,只留下成長的紋理。
沒有人天生完美,脆弱的情感是需要的,粗暴的情感也是需要的。我們要尊重孩子的憤怒,接納孩子的憤怒。
沒有完美的人,只有接納不完美后向上地成長,孩子的未來才能旗開得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