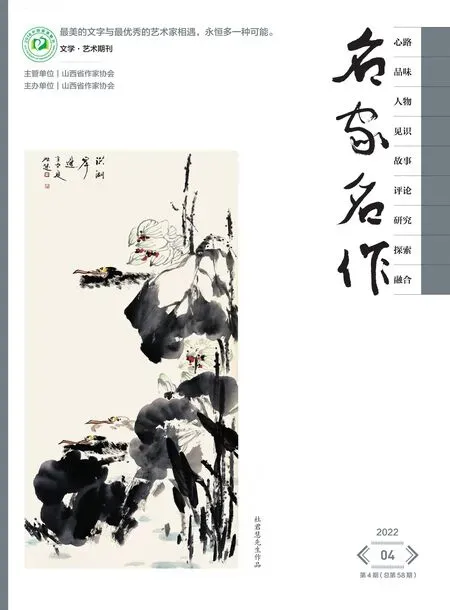美學內外:形質與意境
張 玥
書法作為一門視覺藝術,以漢字作為表現對象,從外部特征而言,它是以點畫線條組合成書體規定的字形結構;從內部特征而言,書法又是借漢字點線的運動完成結體造型來表達書者內心對宇宙萬物和社會生活的審美情感。這內外二者,也便是書法美學中形質與意境的體現。形質美與意境美之于書法藝術家們來說,如何將這兩者有機地結合是千百年來的一個經典命題。書家們各執己見,眾說紛紜。不可否認的是,二者缺一不可。
形質美,顧名思義,“形”是外形、結體的意思,而“質”含義較多,有“內質”“線質”等理解,“內質”較于“線質”更加抽象,所以我更加傾向于“線質”這一解讀。下面就先從這兩方面講起。
先從“結體”上來說,字形的收斂、對稱、開張等都叫結體美,這種結體美,在真、草、篆、隸中表現也不相同,如篆書、隸書及楷書的字體要遵循重心平穩、比例適當、參差錯落等原則,行書草書則追求不規則的排布、筆斷意連等原則。一個字的造型除黑色的筆畫之外還有空白的地方,清代大書家鄧石如曾提出“計白當黑”,這些字的疏密揖讓和虛實相生的排布,規律和無規律的統一都是中國書法藝術充滿魅力的原因,都能給人以美學的感受。包世臣在《藝舟雙楫》中說:“形質成而性情成。”也就是說,形質是書法家用來表達感情的基礎和要素,也就是一種要有可讀性的文字符號。如懷素《自敘帖》(如圖1),它打破了一般結體的平正、方整以及縱有行、豎有列的布白方式,在字與字、行與行之間,上下參差,大小錯落,以險絕取勝,并且懷素的狂草,還打破了方塊的外形,趨于圓轉,巧妙的改變給人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

圖1 《自敘帖》(局部)
從“線質”上來說,要表現線條點畫美,必須通過用筆,鐘繇提出:“筆跡者界也,流美者人也……見萬象接類之。”宗白華先生《中國書法里的美學思想》中曾對鐘繇此話做了最好的注解:“從這一畫之筆跡,流出萬象之美,也就是人心內之美。沒有人,就感受不到這美,沒有人,也就畫不出、表不出這美。”一幅作品中筆畫與筆畫之間映帶與分離,字與字之間的揖讓與協調,都是通過一支毛筆所寫出來的線條來表現的,這線條還流露出書家氣質修養和對書法的審美理解,所以謂之“人心內之美”和“萬象之美”。如張旭的《古詩四帖》(如圖2),整幅作品行筆婉轉自如,跌宕起伏,奔放豪逸,線條之間欲斷意連,其筆畫連綿不斷,像云煙繚繞,便是典型的以書法線條表現美的體現,他以自然萬象表達情感,同時情感又暗示著自然萬象。對書法線條的形象美,古代書家也多有論述,如“錐畫沙”“折釵股”“屋漏痕”和“點如高峰墜石”“橫若千里之陣云”等。

圖2 《古詩四帖》(局部)
中國書法歸為美學范疇最重要的還是意境美,美學大師鄧以蟄曾在《書法之欣賞》中提出:“吾國書法不獨為美術之一種,而且為純美術,為藝術之最高境。”
早在東晉王羲之時期,他的書論中就出現了晉人尚意韻的藝術傾向,《論書》中說:“須得書意轉深,點畫之間,皆有意,自有言所不盡,得其妙者,事事皆然。”《全晉文》中說:“而筆至惡,殊不稱意。”這些書論中所提到的“意”便是指書者在書寫中有了表現人們心理意愿、情感、心態的作用,這便是“意境”的雛形。我們從王羲之的作品中便能感受到這種“意境”的高深之處,天下第一行書《蘭亭序》,此作品的動態之美、變化錯落之美,一些橫與波挑又帶有隸書遺意,妍美的行書中又帶有楷書的骨力,晉人特有的超然玄遠的深情與意韻書文并美,以及作者的氣度、風神、襟懷、情愫在這件作品中得到了充分體現。這也是它成為王羲之書法藝術最高境界的原因。衛夫人《筆陣圖》中說:“夫欲書者,先乾研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抑,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后作字。”這里的“意”也充分肯定了它的重要作用。“意在筆前”,胸有成竹地表現作品的意趣和變化。
陳振濂老師在《書法美學》中將意境內涵分為神采、韻趣、詩情三個部分。關于神采,南朝書論家王僧虔在《筆意贊》中首次提出這組“神形”觀點:“書之妙道,神采為上,形質次之,兼之者方可紹于古人。”此處王僧虔所用的“神采”二字,也就是主體的精神境界、生命體驗與審美經驗等多重主觀元素在一幅書法作品中外化所呈現的風采美感,這種風采美感便是構成書法意境美的重要部分,但是王僧虔的“形質次之”并未表現出形質不重要的想法,而是說“兼之者方可紹于古人”,所以這種神采之美的表現也始終要以形象為依托。另外,書法意境內涵的韻趣美、詩情美便是集中表現在書法的語境美上,若是書法作品在造型上無論被表現得如何優美,但書寫內容與美相違背的話,“意境”蕩然無存,便不能稱之為藝術,更不具有藝術價值了。上文中提到的《蘭亭序》,文人雅集,吟詩作賦,談笑風生的藝術氣息躍然紙上,這使它的藝術價值無形之中又提升了。
從當代書壇來看,意境與神采之爭似乎表現得十分激烈,在近幾年來,隨著中西文化的交流,西方現代派、日本前衛派沖擊著傳統書界,一批“丑書”家興起,當然也并不能說“丑書”就沒有形質依托,只是打破了傳統漢字結構,以奇特、怪異的字形來表現自己的創新精神和審美價值,這種作品的“意境”與傳統書法作品的或高深、或奔放、或豪逸的“意境”大不相同。在近幾年的全國各地展覽中,胡涂亂抹、墨汁四濺、非字非畫、非技非法的作品屢見不鮮,這種作品既沒有形質的依托和意境的追求,更談不上高雅的意境,完全無法與古人相媲美。此種書壇亂象對當代學院派學習的風氣來說也有一定的影響,書法初學者本應該好好鉆研古法,取法古人,做好“形質”的安排和“意境”的營造,卻因獵奇的影響偏向于某一方面,過分強調所謂的情感而全然不顧字形,甚至一度出現了“盲書”等荒謬的做法。
在書法創作中,形質和意境二者均是書家畢生追求的至高境界。書法中意境的表現,一方面依賴于創作技巧的精熟,這是前提和基礎;另一方面,要達到書法形質與意境的完美結合,心態是一大因素,蔡邕《筆論》中說:“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后書之。”故習書時,只有我們的心態恬淡自如,創作中心手雙暢,融入自己的知識修養和審美趣味,才能寫出真情至性的作品。我作為一名專業的書法學習者,在以后日常的書寫創作中,應該辯證地看待形質與意境的關系:意境美蘊含于形式美之中,形式美又是意境美產生的基礎,也就是不能一味描摹字形而忽略了情感的表達:當然也不能因為過度地想要表現情感而喪失了基礎字形的依托。我們在學習創新的時候,一定要分清好壞,吸收借鑒絕不是融化混雜,或者替代。
總之,中國書法以其內在意境和外在形質成為造型藝術和表現藝術的靈魂,沈尹默先生曾說:“世人公認中國書法是最高藝術,就是因為它能顯示出驚人奇跡。無色而具圖畫之燦爛,無聲而有音樂之和諧,引人欣賞,心暢神怡。”愿吾國書法長立于世界藝術之林,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