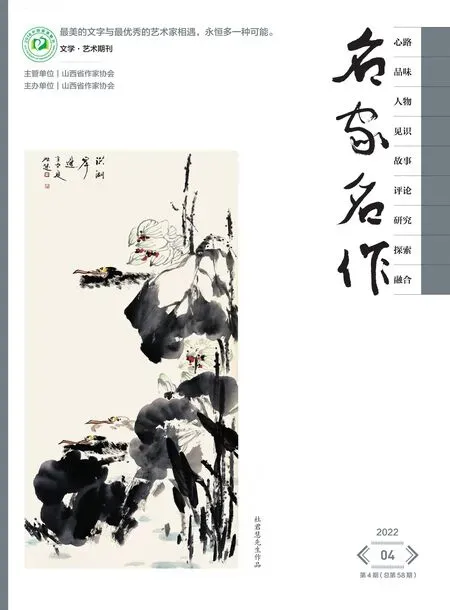禪宗與文人畫的精神交互方式
任 晏
早期文人畫的發展與禪宗結合,“意氣”和“修心”是文人畫的精神內核所在。隨著禪宗“無念”說與中國文人的達退觀的融合,文人和士大夫在內心中獲得了平衡。禪宗的“意境說”和禪定狀態下的文人對時間的理解也是推動文人畫發展的重要階段,而后到了明代中葉,禪宗與心學的相互滲透對傳統觀念造成了沖擊,掀起了追求個性解放的思潮,由于當時時代背景下情感表現的迫切要求,明末文人畫家產生了強烈的自我表現意識。
王維是最早以詩入畫,并將南禪的“頓悟”與山水畫相結合的藝術家。到了明代,董其昌等人從風格、流派等很多方面探討了王維的藝術成就。王維一生都與禪宗有密切的聯系,他所生活的唐代道佛合流,高僧輩出,崇佛風氣盛行,而且他出生在一個信奉佛教的家庭,自身也虔誠踐行禪法。后來,他因仕途不順且不愿同流合污,想要尋求解脫,萌生了強烈的隱遁思想。他在自然山水之中,與天地宇宙融合在一起,恍若無我之境,這使他內心獲得了真正的平靜。禪宗認為“心空心靜,視萬物性空也”。只有精神的淡然,才會帶來空靈澄凈的藝術境界。禪宗“物我兩忘”的境界也在他的畫中得到體現。王維一直將禪宗思想與山水畫論一起討論,主張“以禪喻畫”,在禪理中妙悟。在宋代之前,文人畫家與其他宮廷畫家還沒有在身份上作區分,但是宋代之后,文人畫家獲得了很高的地位。蘇軾也曾說道:“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許便倦。漢杰真士人畫也。”由此可見,蘇軾認為文人畫與畫工畫的區別在于意氣,由“意”入畫是繪畫的精神所在。比如著名的《古木怪石圖》,畫面流露出的氣息是簡淡、清散,畫面中逸筆草草,不求形似,看起來就像草稿一般,畫中的枯木與怪石也不僅僅是自然界中的物象,那些糾結的樹結象征的是其“心中郁結”,這正是文人意氣的體現。

《古木怪石圖》 (北宋)蘇軾
蘇軾對參禪有濃厚的興趣,而且能超然物外、游于物外,強調書畫“自娛”的作用。米芾也是典型的為抒發情感、不為了繪事而作畫的文人畫家、書法家。他們都為從南北朝開始的一個重要轉變做出了重要的努力,即從對物象的客觀描繪到借物喻情,也可以說是從外到內的一個轉變。這與禪宗中的“即心即佛”是不可分割的,禪宗起到了內在指引的作用,文人借助它找到真正適應時代的審美、適應人們心理本質的審美特質。
在他們之后,元代的趙孟頫是當時非常少有的漢族文人,他沿著宋人開辟的繪畫思路,在宋人的基礎之上,山水的題材變多了,因為寄情山水貼近元人的實際生活。其次,由宋人的重視“意”而更加轉向“修心”。因為禪宗主張現實生活和修行為一體,山水給人以空間感,人們在空間里能感受到心靈與山水的相互交融。另外,趙孟頫還提出了“以書入畫”。在唐宋文人追求寫意而不講究形似之后,以書入畫讓文人畫的氣息變得更為簡潔,以抒發胸中志氣之美為宗旨,書寫的方式更加凸顯了文人創作中的直覺性,直達事物本質,也能直接讓觀者體驗到在書寫中蘊含的超越物象之外的精神氣,這與禪宗的“頓悟”論有相同的內涵。禪宗在這個過程中密切參與文人士大夫出世入世的心理建構,融入文人的繪畫思考,改變了文人畫的審美特征。
歷代文人士大夫都有過在社會中的困境,陷于兩難,在進與退中,他們心中的憂慮便是一直在徘徊著的選擇基調。儒教和禪學的影響下形成了中國文人的達退觀,傳統儒學入世的正統哲學在意識層面引導著文人士大夫們,他們遵循著自己想要建功立業的想法,但是內心的潛意識層面,禪宗的人生哲學引領著文人的審美特征,在他們的內心深處,依然向往寧靜悠閑的生活,尋求平和的內心世界。因而,他們在自己營造的幻境中寄予了自己的人生追求和感情。
晚明的董其昌延續了之前的一些繪畫思想并且創立了南北分宗論。對董其昌來說,南宗畫可以體現他的人生追求。他以禪喻畫,認為南宗畫就像南宗禪的頓悟說,只有最有大智的人可以頓悟成佛,凡夫俗子無法完成頓悟,只能通過漸修。他特別欣賞米氏父子,可以“一超直入如來地”。雖然身居高位,但是他內心里非常向往平靜自由的生活,居廟堂而思江湖。禪宗所講求的是“無念為宗”,“無念”即是不讓自己的心被雜念束縛,人也不能什么都不念,這樣連呼吸都會是一種包袱。所以在這樣的禪宗思想的引導下,文人既想兼濟天下,又希望自己可以獨善其身,這樣矛盾的心理使其進退兩難。禪宗中講到“無住為本”,“無住”就是不讓自己的心被束縛,不被束縛就會“無念”,就可以得到解脫。所以從根本上說禪宗并不是需要坐禪苦修,而是不計較外在形式,只要“無所住心”便可,這么一來,禪僧們在士大夫化的同時,文人們也在世俗與隱遁中找到了平衡。
禪宗改變了藝術家的思維方式,改變了他們的創作思想、審美精神。禪宗的“意境說”應該是對文人畫影響最為深遠的。南北朝提出了“意象”,但到了中唐時期才從“意象”轉化到“意境”。這里所說的“意境”中的境是游于象外的,與禪宗思想更為貼近當時的時代風氣。意境是由心而造,是心在一定界限內游走,沒有固定的方向也沒有目的,是當時禪宗藝術精神的體現。
王維的“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中透露的禪意就是一種“淡”,這種“淡”在倪瓚的繪畫中也能感受到。而相較于倪瓚荒寒的意境,董其昌則突出了“凈”,是一種悄然無聲之感,是靜謐平和的自然。“淡”包含的是道家的自然觀,由實到虛,從有到無,慢慢向禪學的平常心演變。唐宋以后,文人畫家追求以簡勝繁。在宋元時期,文人畫的審美傾向是以“簡淡”為主的風格,也是受到了禪宗的影響。南宋時的禪僧畫家都陷于其中。梁楷的“簡筆”畫是代表,法常受梁楷的影響并將其“草草”的風格發揮到了極致。
文人畫家們往往會通過筆墨來表現“淡”的意境,但是“遠”卻需要由構圖、形式等來體現。不過筆者認為,這只是一種作品本身內容的“遠”,而不是一種“遠”的境界。觀者在畫面中也可以直接感受到這種遠的感覺,不需要去刻意營造或者建構。“遠”即是所謂象外之象,超出了界限之外。這種遠與玄學相通,玄有時候就會讓人覺得遠,這是一種理解上的疏離感,會讓人有撥云見霧之感,卻不會過于脫離人們的理解范圍。
道家通過“遠”去追求一種無限,這是一種沒有盡頭的目標。而禪宗則是以“心”傳心,通過“遠”的無限延伸,周而復始,最終還是回歸到內心,即人的本心。在無限延伸中體悟永恒的生命感,這就是禪宗崇尚的在藝術創作中的最高追求“自然”,一種趨于平淡天真的感覺。
在中國的哲學觀里,人類實在渺小,身觀所限,在有限和狹小中徘徊。宇宙宏闊,人類克服局限和渺小,很大程度上在于“遠”。遠是一種距離,但中國藝術中強調的遠也非自然距離之遠,應該是對自然距離的一種超越,是境界之遠、心靈之遠。藝術家以詩意的眼光感受萬物,精心構筑虛靈時空,和一般對待萬物的態度形成一種距離,這種距離感是一種遠意,因“遠”而真,流露自然本性。
而禪定狀態下的文人對時間的理解也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榮格說:“藝術創造以及藝術的效果的秘密要在返回到參禪狀態中去找。”參禪入定,以達到藝術創造所需要的內心體驗,在這種狀態里,物我同化,仿佛都變得融合,情感和心靈也得到了慰藉。禪宗尋求內心的解脫,會用一種豁達的心態去感受時間的變化。禪宗所說的“悟”全在“一念”之間,“一念”即“無念”。在《壇經》中,“無念”不是什么都不念,“念”可謂人的本性,但人的見聞覺知是自性,而非六根,所以只要不被束縛,即是無念。慧能所說的“無念”也并不是什么都不想地靜坐,而是不過多迷戀于現實中的事物,不論世事如何,都能安然看待所有。慧能還提道:“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這種對時間的感受來源于人們的主觀感受。人們對同樣長度的時間所產生的感受天差地別,稍縱即逝抑或是漫漫長夜,都在人們的感覺之間。所以時間的流逝與解脫的自我意識相互聯系,在這瞬間感覺會突然消失,而人生的意義便也在瞬間和永恒中消弭。根據現代心理學的研究,當人處在凝神狀態之時,潛意識會異常活躍,思維會四處發散,能產生各種奇思妙想。而在以禪定狀態下進行的直覺觀照中,人們會下意識地拋掉理性的制約和思維的限制,與自己的心靈相互融合。在這個過程中,直覺所產生的效果看似是不合理的,但是對審美創造而言是極其珍貴的體驗。人們在其中感受到的時間流動和最直觀的感受,是取決于內容的意蘊和深度。
在魏晉時期,玄學喚醒了人們的自覺感知方式,人能真正地感受到自然的無往不復。但其實中華文化中一直都存在著時空合一的宇宙觀,就是一種所謂的心理時空,它是會根據人們的經驗發生變化。特別是在進行藝術創作的時候,中華文化中更注重以時間引領空間。在圖式空間中,人的主觀意識統領空間,空間完全取決于人們自我,人們甚至可以在空間改造時間和再造生命。中國有很多藝術中都融入了這種時空觀。
禪宗一直在討論生死的問題,禪宗本質也是追求自由的精神彼岸。而達到這種境界需要開悟在這種自由的時間里,悟禪者往往能實現詩性的棲居,在自然中悟禪,忘卻了時間。其中這個過程也是人“本來面目”顯現的過程,在存在中發現真理,頓悟后達到“澄明”的境界。
明代中后期的禪宗在心學的影響下以個性解放以及對自心自性的肯定促進著人文思潮,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宋元時期,文人遭到打擊時往往是通過山水將自己消融在自然之中,做到心平氣和,也是為了尋求解脫,徹底達到物我兩忘的境界。但是在人們都意識到自我意識的存在,即自我覺醒的時候,又無法得到認可,所以會導致因為自我價值被否定而造成的強烈的反抗情緒,這種反抗的精神作用于藝術創作,并影響著藝術風格的變化。在明代以前,文人畫的基調大體是脫離不了對靜寂、清冷的表達。而明代文人的覺醒給文人畫注入了新的生機,在清醒和智慧帶來痛苦的同時,也真正能體會生命的快樂。明清追求個性解放的時代特征,使文人畫家萌發了強烈的自我表現意識。他們迫切地想要表達自己的情感,并把這當成表現繪畫的目的。
明末文人在各個領域都表達了那個時期的思想,他們對人的本體表示了更多尊重。王艮所提出的“淮南格物”在明代思想史中占據重要地位,它的核心是“安身之本”論,這里“安身”是以解放身體、重視身體為前提,從而達到對心靈的解放。對人性的尊重在這里不僅體現了經世思想,也激發了藝術家在創作中自我意識的表達。石濤提出“我自用我法”的理論,他自己在實踐中也師古人,但不一味崇古,風格多變且富有創造性,不同時期充滿矛盾。何心隱的“育欲”論在明末清初推動了藝術家欲望和情感的釋放,反對扼制“人欲”。許多畫家在這一時期借物喻情,借繪畫抒發內心的滿腔憤怒。八大山人的畫中就通過各種意象抒發了對清王朝的譏諷。這一時期的畫家在藝術實踐中都不再追求華美、流暢的美感,而去接近生澀、自然的氣息。
葛兆光在研究中提到,禪學興起初期“狂禪”就已經形成,但是并沒有達到個性解放的程度。所以禪宗其實在明初并不興盛,到了明末,“狂禪”之風漸漸走向縱欲,對封建正統儒學是一種異端的存在,且對當時社會藐視禮法、放縱等社會風氣也起到了直接的推動作用。明末的反中和的風氣也呼之欲出,文人畫家已經難以在傳統的禪學中獲得內心平靜的處世之道。遺民畫家也都用各自的方式抒發他們的沉痛心情。這種強烈的悲痛已經無法再以“傷感”去表達,他們中有一群人的情緒已經帶著憤怒的一面,傅山就擁有批判儒家的激烈態度,幾乎是與中和之美勢不兩立了。他指出:“寧拙毋巧,寧丑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直率毋安排,足以回臨池既倒之狂瀾矣。”石濤在畫論中提到作畫“盤礴睥睨,乃是翰墨家所養之氣”。八大山人的悲痛不例外地也是以一種悲憤的姿態出現,他畫面中的奇怪魚鳥白眼向人,人生憂憤更是躍然紙上。對中和之美的討論一直完善和推動著中國審美的發展,但也泯滅了人的個性的一面,鉗制了人們的思想,既然反對封建主義,那么“中和之美”就是對藝術中審美的反叛。畫家們盛行“狂肆”,強烈的情感宣泄加強了藝術表現中的雄肆之美,個性意識也凸顯了出來。
本文通過時代思潮和畫家內在生命力的表現深入討論了禪宗對藝術創作中的審美經驗的影響。文人們將自己的想法和以禪修身的內在素質融入實踐,在作品里寄托情感,對當時以及后世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們將個人的主觀精神融入藝術創作,對當代繪畫的發展有著很大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