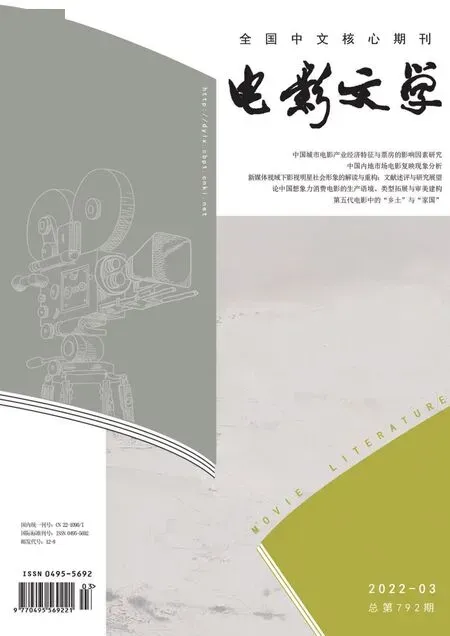女性主義視野下近十年中國女性題材電影觀察(2010—2020)
余克東 王 健
(福建師范大學傳播學院,福建 福州 350117)
近十年來女權運動不斷發展與高漲,席卷美國的“Me Too”事件再次將女權問題推至全球輿論的風口浪尖。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的家庭結構、女性地位、思想觀念都悄然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反物化、反父權、性別歧視等議題的女性主義逐漸從“邊緣”走到“主流”,從“幕后”走到“臺前”,從“失語”走到“疾呼”,并通過影像來表達女性立場,逐漸形成女性電影傳統,即“由女性執導,以女性話題為創作視角的并帶有明確女性意識的電影、錄像、DV 和多媒體實驗作品”。中國女性題材電影從黃蜀芹導演對女性身份、女性困境的關注到李玉導演對女性命運的傷痛關注,女性導演始終有著別樣的細膩、敏銳。然而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電影女性導演卻屈指可數,女性題材的電影更是長期缺席中國電影市場。可喜的是,近十年來,一大批青年女性導演如雨后春筍般登上電影舞臺,她們攜帶著獨特體驗與個性思考的女性題材電影開始在各大電影節涌現并頻繁獲獎,成為近幾十年來難得一見的女性導演創作熱潮。(具體片單見表1)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批女性導演的創作中涌現出諸如《剩者為王》《嘉年華》《過春天》《送我上青云》《春潮》《喜寶》《少女佳禾》等基于女性主義視角創作的佳片,在探討女性困境、女權意識以及對社會癥候的影像關切方面均體現出一致的創作趨向,成為中國電影創作的一道亮麗風景線,值得給予深入的探討。

表1 近十年中國電影女性新銳導演作品一覽表(不完全統計)

(續表)
一、批判:“失范”的原生家庭
家庭是社會的最基本單位,同時也是每個個體性格形成的重要“土壤”。在中國傳統觀念中,家庭亦是以父權為主導的“體現男尊女卑文化惰性的一項重要的意識形態”,家庭成為女性主義電影重要表現對象,從《嘉年華》到《少女佳禾》這一系列的女性主義電影無一例外地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了原生家庭,通過對“失范”原生家庭的控訴來強化“反父權”的女性主義藝術主張。
(一)父性的“缺席”
在世俗傳統中,家庭是建構于父權制下的一種組織形態,在文化層面上,“父親”亦代表著權威與秩序的維護者,是家庭的主宰。勞拉·穆爾維在其代表作《視覺快感與敘事性電影》中認為,在傳統好萊塢電影模式中,“支持男人的角色作為主動推動故事向前發展,造成事件的人”。電影總是以男性視角為敘事主線,以男性為中心的角色設定引導觀眾與男性目光認同,形成了以男性為主導的父權意識形態電影,男性成為凝視的主體,而女性則是被凝視的客體。而作為女性主義電影,對以男性為敘事主體,女性為被凝視的對象的男權意識電影批判與驅逐不失為反父權,樹立女性意識電影傳統的一種常見方式。
縱觀這一時期的女性主義電影,如《過春天》《嘉年華》《柔情史》《送我上青云》《春潮》《喜寶》《少女佳禾》,電影中無不對父性角色輕描淡寫,抑或置于“失語”狀態。“父”不僅指代父親,在廣義上更代表男性,如男朋友、丈夫等角色。這些電影在父性角色體現出鮮明的趨同性:第一,敘述主體的變換上。男性不再是影片的主角,取而代之的則是女性,女性成為敘事的主體并與觀眾形成目光的認同,如《嘉年華》的小米(文淇飾)、《柔情史》的小霧(楊明明飾)、《送我上青云》的盛男(姚晨飾)、《春潮》里的郭建波(郝蕾飾)等,當然導演亦全為女性。第二,父性的“缺席”,并以一種模糊化處理來強化女性意識。在電影《過春天》中,主角佩佩(黃堯飾)出生在一個由香港父親與內地母親結合的離異家庭。父親被塑造為一個香港底層中年男性,他既無法從經濟上維護一個家庭的秩序,亦無法從文化上成為家庭的精神主宰者,呈現出的是一種頹勢“閹割”的父親形象。這與《喜寶》中相類似,姜喜寶(郭采潔飾)亦出生于一個經濟拮據的單親家庭,一直與母親生活的她,從小沒有父親的關愛,母親至死的執念就是等待姜喜寶的父親,可最后父親出現的時候卻是為了母親保險金而來,被塑造的是一個“貪財自私”的男性形象,這里父親不僅缺席了女兒的成長、教育、關愛,甚至在最后為了錢跪在姜喜寶面前放棄男人的尊嚴,影片用這種“弒父”的形式來完成女性主義書寫。同樣在電影《春潮》中,“郭建波的父親一方面是母親口中風流成性的流氓;另一方面又是女兒記憶中引導她進入女性世界,給她鼓勵的完美慈父。通過在場人物的言說和夾雜于敘事中的回憶,他成為典型的‘缺席的在場’人物,甚至是一個映射歷史的符號”。在《送我上青云》中,罹患卵巢癌的盛男欲向父親借錢看病,未等開口父親卻向盛男借錢,“自私貧窮”的父親設定成為女性電影的共性,在《少女佳禾》中的夫妻形象亦如此,導演通過對父親性格的“貶謫”以及經濟權的剝奪來完成對父親角色的“閹割”,使得父親失去了男性權威,進而完成對男權的批判。
(二)母性的“異化”
除卻對男性“缺席”化的塑造,對母親的塑造則采用“異化”處理方式完成女性主義書寫。在西蒙·伏波娃《第二性》中指出,女性“被兩種異化的方式異化——裝成男人是她失敗的根源,可裝成女人也意味著欺騙。做女人就將成為客體和他者”。在傳統家庭結構中,“賢妻良母”成為母親標準,在某種程度上亦是男權的附庸的表現,在電影上,在勞拉·穆爾維看來男權附庸的女性被視為是被動凝視的客體。而且母親與孩子的關系,尤其是對待女孩上,其教育的終極目的也是將其培養成男權意識下“賢妻良母”的標準,正如拉康提出的“鏡像”理論那樣,“嬰兒在六到十八個月這段期間,由他以為自己的鏡像是另一個兒童,發展到認出那鏡像就是自己”,母親與我(女性)互為鏡像,鏡子中是此時的母親,未來我將成為此時的母親,“也就是說,鏡像中的‘我’成為被誤認的對象,成為‘理想自我’,一個外化的主體,同時這個主體又重新內化為‘自我理想’,為以后與他人認同打下基礎”。所以“賢妻良母”般的母親形象成為女性主義批判的對象,而這種批判的方式則是采用“異化”方式來實現的。
其一,男性化即伏波娃所謂的“裝成男人”。這里的男性化并不是說從外形上男性化,而是一種精神形態的男性化。例如在《春潮》中,郭建波的母親紀明嵐(金燕玲飾)熱衷社區活動,在社區扮演著秩序的維護者身份,在家庭中,無論從經濟上還是從精神上亦是家庭的權威,在某種程度上充當了新的“父權”,男權與女權完成了置換,類似的情況同樣出現在《柔情史》中,強勢甚至有些神經質的母親一直試圖主宰女兒的人生,都是一種“異化”形態。其二,“裝成女人”,即男權社會標準的“賢妻良母”。在《送我上青云》中,盛男的母親梁美枝(吳玉芳飾)溫柔賢惠,19歲就嫁為人婦淪為家庭婦女,但換來的是丈夫出軌另組家庭的悲劇下場;與之類似的則是在《喜寶》中,喜寶母親至死都在盼望著丈夫的消息,而丈夫早就知道她們的住所一直不現身,直至逝世,丈夫為了保險金才現身葬禮。成為男權社會的犧牲品,導演通過這兩類女性形象的異化處理來鞭撻男權強化女權意識。
二、困境:生育、家庭與自我價值的女性意識
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觀認為,女性的地位是根據生產技術發展而變化的,在原始社會,受制于生產條件,男女在原始分工中并無多大差距,男女身份達到一定的平衡。但隨著生產技術的提高,農業需要集約勞動,柔弱的女性在新一輪分工中敗下陣來,私有制的產生導致女性從屬男性的新局面,所以“女人的自我意識不是取決于她的性征,實際取決于社會經濟環境,這一環境又反映了人類所達到的技術發展水平”。在互聯網經濟環境下的今天,女性早已同男性站在同一經濟起跑線上,傳統的經濟關系、家庭結構、兩性觀念都在發生著重要的變化,正是這樣的新經濟環境為女權意識的生成與表達提供了沃土。
(一)經濟獨立與女性精神獨立之困
自我獨立不僅意味著精神獨立,更為重要的還是經濟獨立,在相當程度上經濟的獨立成為女性主義意識的核心與根源。在電影《送我上青云》中,主人公盛男(姚晨飾)具有堅定的新聞理想,始終以獨立甚至“俠義”的姿態對待生活,但突如其來的疾病——卵巢癌所需要的醫療費不得不讓盛男低下高傲的女性尊嚴,尋求經濟支持。死亡與尊嚴的困境歸根結底是經濟困境,在求助于家庭未果,只能屈尊幫助一個富商父親撰寫傳記,成為經濟的“俘虜”,在經濟獨立與女性意識兩難困境中游弋。在電影《過春天》中,佩佩(黃堯飾)為了滿足去日本看雪的愿望,無法在家庭中獲取經濟支持的她走上一條鋌而走險的“水客”路,經濟的制約,亦使其步入了自我認同的困境,包括深港身份以及對家庭關愛與關注的渴求心理。此類情況還在《喜寶》中體現,經濟困頓的喜寶為使學業得以繼續,在愛情與經濟困境中選擇了老富翁勖存姿,這也使其女性尊嚴飽受周遭質疑與非議,均強調了經濟獨立對于女性意識的重要性,可以看出經濟獨立成為女性自我獨立的第一塊絆腳石。
(二)生育權之困
第二個困境則在于對于生育權的掌控。生育分為“生”和“育”,“生”包含女性性的欲望及選擇配偶的權利;“育”則是面對孩子的態度。在電影《送我上青云》中,獨立好強的盛男目睹19歲就嫁為人婦母親的不幸婚姻,拒絕像母親一樣被“凝視”,淪為男權的附庸,所以她不修邊幅,干練獨立,甚至不需要男性乃至婚姻。但面對卵巢癌——這一引以為傲的女性性征病變時,不免流露出對女性欲望以及生育權的留戀,進而當遇見中意的劉光明時,“劉光明的出現喚醒了她作為女性的被觀看的需求:她開始化妝,搭配服飾,甚至向劉光明求愛,而劉光明的逃跑則再一次使她陷入性別的定位困境”。盛男在對劉光明懦弱的性格失望后,進而向男性好友毛毳索求“性愛”,以彌補在喪失女性生理特征的愉悅體驗后亦遭受挫折,在“生”權困境中掙扎。在《春潮》中,郭建波面對刻薄母親不斷的“責備”現狀,本可以逃離,除卻經濟因素制約外,另一原因不乏女兒郭婉婷的養育問題。單身好強的郭建波住在單位宿舍無法為女兒提供一個良好的養育環境,再加上工作原因使其不得已將女兒寄送母親處撫養,對女兒的養育之困為祖孫三代女性撕扯提供了場域。
(三)傳統倫理的抗爭
其一,母女矛盾往往成為家庭抗爭的焦點。《柔情史》中偏執的母親與落魄的小霧在家庭的瑣碎中不斷角力撕扯。母親常常以家長式的權威干預女兒小霧的生活、工作乃至情感,而小霧不以為然地抗爭著,稍有不慎便會陷入“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貧,你連狗都不如”的道德困境;《春潮》中的郭建波的母親,一邊是對社區的“慈眉善目”,一邊卻是對家人的“尖酸刻薄”,對待女兒掛在嘴邊的常是:“吃著我的喝著我的,還想我笑著服侍你?”“我養你,還要你罵我?”常常借助母愛與孝道倫理之名,數落女兒的種種不是,以發泄對其父親的不滿的扭曲心理,母與女的家庭倫理抗爭與代際沖突成為這一類題材女性困境的重要表征之一。其二,便是對男權傳統世俗觀念的抗爭。“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在電影《嘉年華》中,小文和新新在遭受性侵后,小文的媽媽將事件歸罪于小文穿著打扮上,而新新的父母以小孩的清白和聲譽為準則放棄對施暴者的制裁與法律的公正。“新新父母的偽善與男權社會對‘性侵’事件的態度不謀而合,這也導致了類似新新的女性被‘性侵’后不是去尋求正義,而是自欺欺人,以無知或麻木的精神狀態承受這一切”,強烈地諷刺了男權社會下的虛偽與罪惡。在電影《喜寶》中,姜喜寶沖破世俗觀念與倫理束縛委身于年長而富有的勖存姿,在金錢與愛情中不斷飽受非議,在相互利用還是真愛中掙扎;電影《過春天》中為了實現自我價值而以身試法無不是對失衡家庭的抗爭的表現。
三、思辨:女性主義與時代癥候折射
近十年來這批青年女性導演均不約而同地采用了現實主義敘述方式,從影像刻畫到主題表達都具鮮明的貼近性與時代性,“現實主義題材電影是時代圖景的‘木乃伊’,也是社會矛盾的‘晴雨表’”,這一時期的女性主義題材電影在相當程度上反映著當下社會思想變革與時代癥候。
(一)“綏靖”之女性主義態度
女性主義伴隨著中國經濟的變革以及思想的開放對社會影響日益加大,作為新銳導演將女性題材作為自己的處女作搬上銀幕,并受到市場一定的關注,不可否認其鮮明的典型性與概括性。但也不可忽視的是,不同于西方女性題材電影的冷峻與犀利,中國女性題材電影在女性主義表達上凸顯出獨有的妥協、折中與“綏靖”態度。
無論是《春潮》中的郭建波、《柔情史》的小霧,還是《送我上青云》中的盛男,在這一類女性題材電影中女性均走出了男權意識下“被看”窠臼,消解了女性的身體修辭,甚至將男性置換為“被看”的敘事位置,但女性主義不僅限于走出男權“凝視”。“女權主義電影批評家們認為,以往的電影語言是男性的產兒,要想建立更接近婦女情感體驗的新電影,就必須首先破壞語言,摧毀大男子主義的傳播方式。”相較于西方女性主義對性的超越(同性戀電影),對父權形態的顛覆激越,中國女性電影一方面試圖跳出男性凝視,批判父權;另一方面卻又無法擺脫男權規則與評價體系,如《送我上青云》中,不施粉黛的盛男在面對心儀對象約會時,也不得不做出取悅男性的行為來。在另外一種程度上思考,無論是《春潮》《送我上青云》,還是《柔情史》,以母女結構為主的家庭的失衡歸根結底是父親的缺失,男性成為自我救贖的方式,如《柔情史》中在母女關系緊張到不可調和時用戀愛來緩解和轉移矛盾壓力;《春潮》中母女的焦點始終在缺席父親的評價上;《送我上青云》中女性最后的性快感必不可少的男性等,表面上來看,這批電影均有女性主義電影特征,但其對男性的“革命”以及對男權社會的倫理的抗爭仍然具有很大的妥協性,以及《嘉年華》結尾的開放性與模糊性都體現了中國女性主義電影的“綏靖”色彩。
(二)時代癥候之多元折射
有關女性的困境,囿于約定俗成的男性主導的社會傳統一直容易被忽視。伴隨著近十年女性題材電影的井噴,其體現出來的不僅是女性個體對于女性困境的表達,在更高層面亦反映出當下時代語境下的多種社會癥候,這些癥候在女性影像細膩的表達中,柔中帶剛,發人深省。
改革開放后,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跨越式發展,中國社會發生著廣泛而深刻的變革,伴隨經濟與社會變革的則是各類時代新問題的產生,新思想的碰撞。首先,則是對家庭結構的沖擊。近十年,中國城市化進程迅猛,大批勞動力從鄉村涌入城市,不僅催生出了“房價高”問題與“留守兒童”問題,更為重要的是拉平了男女兩性分工的差距,女性在經濟地位上逐漸趨于男性,甚至高于男性,且在互聯網信息革命的推波助瀾下,人與人之間的聯系便捷而直接,面對無時不在的誘惑,傳統的家庭結構在經濟與誘惑的雙重沖擊下愈加脆弱。婚外情、離婚率不斷攀升,衍生出愈加嚴重的“原生家庭”問題、單親家庭問題,重組家庭越發普遍,故而影片中母女代際問題、拜金主義、剩女問題成為一個時代的癥候。
此外,《嘉年華》中雖然反映的是當下社會灰色地帶少女性侵問題,但更讓人咋舌的則是在面對少女性侵問題中,基于所謂“利益”“名譽”下成人不當處理的方式,這不僅是社會法律問題,甚至是一個倫理悖論以及社會畸形的表現;《過春天》中表面貌似是一個少女犯罪問題,但其體現出當下社會深港身份認同問題、家庭教育問題、兒童心理問題均具有普遍性;其他如關于少女題材的《悲傷逆流成河》《少年的你》中校園暴力問題,《剩者為王》中“剩女”問題以及《番薯澆米》中老年女性生存問題等有鮮明的時代性,在相當程度上折射出這個時代女性所面臨的種種困境,暗合了當下中國社會存在的諸多典型癥候,其體現出的思辨性、反思性在女性主義表達之外增抹一層理性色彩。
結 語
“在時代轉型的現實語境下,隨著社會進步,女性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影響力不斷提升,女性作為中國電影新勢力的中堅力量和重要電影消費群體,深刻影響著電影界的結構性調整和優化。”女性題材電影飽含女性導演獨特的情感體驗,堅韌而細膩,反父權的藝術主張與對時代問題的反思,理性而深刻,隨著越來越多女性導演的涌現,女性主義電影將在未來愈加普遍與成熟,為多元而繁榮的中國電影增抹一道獨特而亮麗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