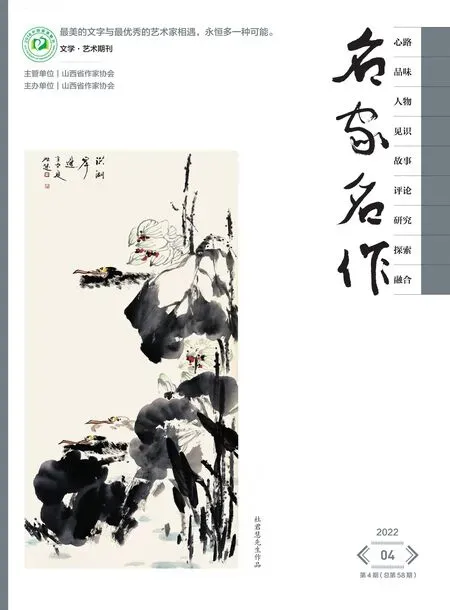試論弘一的書法境界
柳 坡
弘一法師,俗名李叔同,清光緒六年(1880)生于天津,1942年圓寂于泉州。他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前驅,卓越的藝術家、教育家、思想家、革新家,是將中華傳統文化與佛教文化相結合的優秀代表人物,是中國近現代佛教史上最杰出的一位高僧,又是國際上聲譽甚高的知名人士。弘一法師的一生具有很濃烈的傳奇色彩,譜寫了很多傳奇的故事,出家前的他鮮衣怒馬、才華橫溢,出家后的他恪守戒律、慈悲為懷,念佛卻不忘愛國,從濁世公子到日本留學生到藝術文學家再到人民教師,直到最后做了一名和尚,可以說,半生繁華半世僧,他的人生是典型的絢爛至極到歸于平淡寧靜,他的每一步都走得非常精彩。對很多愛好藝術的人來說,弘一法師似乎有一種獨特的魅力和莫名的吸引力,他在美術、書法、篆刻、戲劇、音樂、佛學、繪畫、文學等很多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尤其是他的書法,出家之前給人一種行云流水的感覺,出家之后一筆一畫不會連筆,給人一種親近、平和、悠然自在、灑脫的感覺,最后自成一體,后人難以企及,用“大道至簡”來形容弘一法師是最妥帖不過的。很多文化藝術界的名人以得到他的一幅字為人生之幸和無上榮耀。
一、擺脫世俗,獲得自在
作為高僧,弘一法師與歷史上的一些僧人藝術家存在差異,如智永和懷素,盡管身披袈裟,但他們的一生似乎并未以堅定的佛教信仰和懇切實際的佛教修行為目的,他們不過是寄身于禪院的藝術家,“狂來輕世界,醉里得真知”,這完全是藝術家的氣質與浪漫。八大山人筆下的白眼八哥形象,諷刺的意味是顯而易見的,他的畫作實在是一種發泄,是入世的,并未超然。比之他們,弘一法師逃禪來得徹底,他皈依本心,超然塵外,要為律宗即修為佛而獻身,是一名純粹的佛教大家。而他的書法被人譽為“佛書”還有一段緣起:弘一法師初寫經書,深受印光大法師“寫經不同寫字屏,取其神趣,不必工整。若寫經,宜如進士寫策,一筆不容茍簡,其體須依正式體,若座下書札體格斷不可用。古今人多有以行草體寫經者,光絕不贊成”這一席話的啟發,自此后,一絲不茍寫經,得到了印光“接手書,見其字體工整,可依此寫經”的贊語。弘一法師的書法蛻變無疑與其皈依佛法不無關聯,他把自己的佛學思想體系歸納為以華嚴為境、四律為行、導歸凈土為果,在南普陀講學的時候,他總結稱:“如果佛法學得好,字也可以寫得好。最上乘的字或最上乘的藝術,在于從學佛中得來,要從佛法中研究出來,才能達到最上乘的地步。”弘一法師曾借用佛法來講書法,稱“是字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從哲學思辨上看,不去思量、沒有分別心,才有對世間萬物的平等對待,也才會真正對人與自然予以充分尊重和理解。在《我出家二十年的感悟》一文中,大師稱:“看來作為一個學道的人,只要心中有春意,就不用世俗的享受來愉悅自己,倒是世間的一切,均可以是自己感到快樂。更何況是為解脫世間眾多受苦人的事業而努力,只要有一點成績和希望,我們都應感到欣喜!”由此可見,弘一法師從佛法修行中逐漸得以擺脫世俗的約束,實現對自我的超越,得到真正的大自在。
技進乎道,這是中國文藝的核心思想。書法藝術創作是藝術家的思想情感流露以及對中華文化的理解和表達,換言之,中華文化和哲學思想就是書道的根本,而書法的氣息、格調則是書道的外在呈現。高明的書法家不僅要掌握過人的書寫技巧,還應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和非凡的思想高度。從藝術格局來看,弘一法師的字簡遠、通透,內涵豐富,氣象博大,這也能從側面反映出大師非同尋常的文化涵養和思想高度。弘一法師的字之所以簡遠,首先在于其用筆從容自在,內涵豐富,能讓人從中感受到時間的悠長。高水平的書法家,用筆看似簡單,卻極為精練,孫過庭《書譜》說:“一畫之間,變起伏于鋒杪,一點之內,殊衄挫于毫芒。”鑒賞一件書法作品,實際上從一個筆畫、一根線條就能看出這個作者的水平和境界,一個筆畫就能體現俯仰向背、陰陽變化,一根線條就能看出氣息的強與弱、長與短,石濤所說的“一畫論”實際上也是在講這個道理。宗白華在《美學散步》中提道:“自然、樸素的白賁的美才是最高的境界。”賁本身是一種斑紋華采的絢爛之美,白賁則是絢爛之極復歸平淡,縱觀歷史長河,能達到這一境界的可以說屈指可數。要想進入最高境地,必然要經歷由“小我”到“大我”、由“有我”到“無我”的蛻變和超越,所有的思考揣摩、情感起伏,都將一一放下,一切的外象、執著都將歸于空無。
二、從不卑不亢到淡泊寧靜
從書法作品來看,弘一法師是典型的碑帖結合的路子,這也是晚清民國諸多大家普遍選擇的方式,沈曾植、馬一浮、于右任等人都是碑帖融合的典范。從現存的資料可以看出,弘一法師在出家前臨摹的碑帖包括石鼓文和《始平公造像記》《楊大眼造像記》《張猛龍碑》《爨寶子碑》《松風閣帖》等經典碑帖,其《臨古法書》中所臨摹的碑帖更是幾乎可以亂真。對絕大多數的學書者來說,以某一兩種碑帖為主要依托是較為穩妥的路徑,經過長時間的臨習能寫出某一家某一派的味道,這已經相當不錯了。但書法史上一流的大家皆不滿足于此,無論是“二王”、顏柳還是蘇、黃、米、蔡,他們都提倡博采眾長,力求做到以最大的功力打進去,以最大的勇氣打出來,最終形成自身的藝術語言。
此外,需要強調的是,中國書畫藝術特別看重“金石氣”“金石味”,推崇那種古拙蒼茫的格調,朱良志認為“金石氣”有兩個特點:一是它歷時久遠,二是它的恒定性。弘一法師晚年的書法,減弱方筆、直線的運用,加強方圓結合、虛實相間的協調處理,雖然減少了早期那種硬朗甚至剛猛的視覺沖擊力,但從容、祥和、溫潤的韻味卻從作品中自然流露出來,以靜制動、以柔克剛,神定氣閑、從心所欲,隱然蘊含一種力量和氣場。書法從技術表現到意境的營造,與古詩詞中渲染的畫面感頗為相似,弘一法師營造出一種淡遠而深邃的畫面,有一種讓時間凝固而永恒的魅力。
弘一法師晚年的書法多用較為空靈的篇章布局。通常來說,字間距小的作品顯得茂密、充實,例如《開通褒斜道碑》《楊淮表記》和龍門二十品,以及顏真卿的《麻姑仙壇記》《顏家廟碑》等,密不透風、氣勢磅礴,視覺上給人以震撼甚至是壓迫感,從美學上可以歸為壯美的范疇。而字間距大的作品顯得空靈、優雅,例如《曹全碑》、楊凝式《韭花帖》、董其昌的行書詩軸等。弘一法師晚年的書法也多用這類方式,但與之不同的是,弘一法師的字采取了更為沉穩、平靜的用筆方式,配合相對空靈的章法布局,呈現出一種“充實至極虛靜生”的效果。從單字的書寫來看,弘一法師晚年的書法也非常講究留白、透氣,尤其是單個字的搭接方式,跟早期相比增加了虛實相間的意味。正是通過虛實相生的表達,讓人感覺到時空是流動的、變化的,虛實之間的相互滲透使得我們能感受到空故納萬物的深遠意境。弘一法師的書法得到不少人的精辟論述。葉圣陶作為弘一法師的友人,曾說過:“……就全幅看,好比一個溫良謙恭的君子人。不卑不亢,和顏悅色,在那里從容論道。就一個字看,疏處不嫌其疏,密處不嫌其密,只覺得每一筆都落在最適當的位置上,不容移動一絲一毫。再就一筆一畫看,無不使人起充實之感、立體之感,有時候有點兒像小孩子所寫那樣天真。但是一面是原始的,一面是成熟的,那分別又顯然可見。總結以上的話,就是所謂蘊藉,毫不矜才使氣。功夫在筆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結合這一評語,再觀弘一法師50歲以后的作品,或可反觀弘一法師書法前期雄而強健、中期秀而雅致、晚年淡而清遠的整個演變過程。
弘一法師的尺牘之書與其書法之作一樣,也是富有變化,且與其不同時期的書法風格一脈相承、同頻共振。從時段上講,弘一法師尺牘的書風之變,正是以其悉心于經文書寫之前后作為轉折點。如,弘一法師1918年出家前后至1921年數年中所書的若干手札,遺筆老到而熟稔,行文自然而順暢,似信手拈來。盡管如此,此時期依然隨處可見弘一法師借鑒六朝書風的影響。彼時弘一法師書法正處于碑帖書風的融合調整時期,此類書風隨著帖學日益被重視、被采納,隨之數年便發生了變化。而之后的相當一段時間內,弘一法師的大多數書牘寫經的烙印顯而易見:皆結體整肅而筆道分明。當然,書信與寫經畢竟不同,人們在弘一法師的書牘中見到不少不甚經意之作,多是其性情所致。有人曾對弘一法師寫經結字的特點進行評述認,為其早年偏扁,到中年偏方,而到晚年則是偏長。這實際上是有一定道理的,而這個特點自然反映到弘一法師的書牘中。比較弘一法師出家前后、45~55歲之前和此后直至圓寂這三個階段的書牘,可清晰看出這一規律。弘一法師進修梵行的精深,使得他的書牘愈至晚年,愈字字清正、狹瘦,既有不食人間煙火的空靈之感,也有由此而生的天籟境界之曠遠。弘一法師的晚年之作《行書金剛經偈軸》等,看似下筆遲緩、結字狹瘦,與硬筆書相近,但從中映現的正是一種白賁之美——淡泊寧靜、不惹塵埃,這種精邃玄微的道之境界,非書法大家無法表現。弘一法師不愧是我國近代書壇中“我手寫我心”的曠世高人。
三、追根溯源,無我無它
“弘一法師”是人們因為其杰出貢獻而給予的尊稱。弘一法師可謂“通才”,不僅是書法家,同樣也是近現代音樂家、美術教育家、戲劇家以及現代話劇的開拓人之一,最早將鋼琴、油畫等引入我國,詩詞歌賦、丹青金石樣樣精通。從弘一法師對書法方面的獨到貢獻,以及其書法對人們學習書法的影響中可以看出,弘一法師的書法更是寫出了真性情,寫出了本我,淋漓盡致地表現了書法的本質意義,弘一法師由此成為人們不斷追求書法藝術性的楷模。也有學習書法的人,對學習弘一法師的書法作品覺得難度較大,甚至無從下手。那么,追根溯源,學會對弘一法師的書法作品進行欣賞,首先要了解弘一法師的書法源泉來自何方。學習書法要師法于古人,弘一法師也不例外,他將更多精力投入魏碑書法的學習上。魏碑書法屬于楷書的一種,筆力雄強而且健朗遒勁,練習書法增強筆力,魏碑書法則是一定要學的書體。弘一法師在學習魏碑書法中,不僅能深得其行,也為其日后書寫筆力奠定了基礎。另外,弘一法師博學多才,無論是閱歷、學養還是修養,都與其他藝術相融,自成一體,自成一家,形成了弘一法師個性鮮明的書法藝術境界。他的書法既體現了其高超的技法水平,而且也將文學、音樂、美學、哲學等內容融入作品中,實際上也正是寫出了“本我”。而這也就是書法中所講究的“勢”,即韻。“無我無它”,成為弘一法師的書法境界,更是眾多書法人的畢生追求。有的人寫了一輩子的書法,也無法達到“無我無它”的境界。弘一法師的書法正是受到佛學影響,排除外界的任何干擾,看似干巴巴的筆畫,也正是一種無情與無欲的體現。在這其中,沒有摻雜任何的情感以及物念,無欲無求,自在自得。
總的來說,弘一法師在書法藝術上的成就為世人所矚目,令人嘖嘖稱贊。潘天壽曾說:“吾師弘一法師云:‘應以文藝以人傳,不可人以文藝傳。’可與唐書‘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一語相證印。”藝術家若想要達到一定的高度,必須全方位提升自己的能力,著力培養自己的品位,堅持不懈錘煉自己的修養,如果只是專注如何去寫、如何去畫,只關心所謂的技法研習,就容易陷入形而下的桎梏。只有當心態、品格、性情達到成熟或是超脫的境地,創作出來的作品才有了靈魂,有了氣韻,有了深度,有了高度。弘一法師反復強調“先器識而后文藝”,他說:“某人所寫之字或刻印,多能表現作者之性格。體現朽人之字者:平淡、恬靜,中逸之致是也。”這便是古人所講的“字如其人”,從藝術創作中獲得對自身的認識甚至是覺醒,這就是藝術最微妙、最有魅力的地方。他的書法閑雅沖逸、富有樂感,樸拙中見風骨,以無態備萬態,將儒家的謙恭、道家的自然、釋家的靜穆蘊含書藝之中,聞字猶聞佛法。早期脫胎魏碑,筆勢開張。書法可謂大氣磅礴、挺拔剛健、果斷用筆,且多用方筆。后期自成一體,沖淡樸野。出家后的作品則充滿了超凡的寧靜和云鶴般的淡遠,具有著絢爛至極的平淡之美和老成之后的稚樸純真。而這其中也反映出弘一法師的人生境遇與心路歷程。出家后,弘一法師的性格與追求有了根本變化,進一步反映到書法上。他的書法變得厚重、圓潤,沒有了斬釘截鐵的方筆,筆畫變得柔和、平易近人,這與弘一法師在佛教上的修為有極大的關系。弘一法師書法的線條所呈現的瀟灑之境,令人神往,從魏碑化古蛻變而來,如同一例圭表,是后世書法家出帖與寫我的典范。尤其是弘一法師的絕筆之作“悲欣交集”,瀟灑之氣達到極致,為其一生的修行畫上圓滿的句號。
四、結語
書法作為一種藝術門類,不是簡單模仿、再現客觀事物的形象,而是表現書法家的審美感受,表達書法家的個人觀點,傳遞書法家的情緒和情感,強調對整個宇宙自然結構形式及其生命運動規律的整體把握。書法家對生命形式的體悟、感受,構成了書法審美意味的一個重要方面。弘一法師書法藝術中的獨特個性,是在簡潔樸素中尋求微妙的變化和豐饒的內美,從而表現出樸茂而空靈的氣韻,給人一種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而又平淡、超脫的感覺,恰如他自我表白的那樣:“朽人之字所示者,平淡、恬靜、沖逸之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