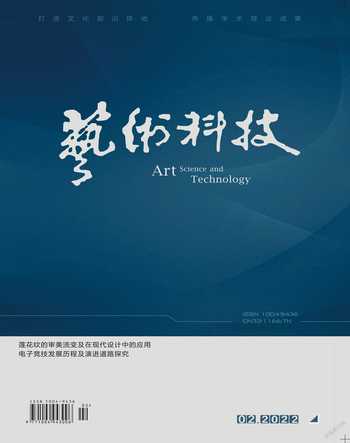空間生產與本土表達:空間理論視域下當代中國的黑色風格電影
摘要:文章在空間理論的視域下探究當代中國黑色風格電影的空間敘事脈絡和其背后的文化表征。黑色電影由于其視覺風格上特有的空間性,與空間敘事之間有一種天然的姻親性。中國當代的黑色風格電影表征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化與全球化變革之中的空間生產脈絡,而在“無地域空間”無限擴張的全球化時代,其本土性表達顯得尤為可貴。
關鍵詞:空間理論;黑色電影;本土表達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2)02-00-04
2014年,刁亦男導演的《白日焰火》斬獲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之后,國內電影界興起了一股黑色電影的制作、研究熱潮。《白日焰火》也被當作中國黑色電影開始破冰的標志。《烈日灼心》(2015)、《心迷宮》(2015)、《暴裂無聲》(2017)、《暴雪將至》(2017)、《風中有朵雨做的云》(2018)等一系列兼具藝術性和商業性的國產黑色電影漸漸進入公眾的視野。
近年來,我國一系列帶有黑色風格的電影是在好萊塢經典黑色電影和新好萊塢背景下新黑色電影的雙重影響之下誕生的。
經典黑色電影,主要拍攝于20世紀四五十年代,一般在視覺風格上體現為低照度、高反差、傾斜感等;在人物上表現為偵探、警察、罪犯、蛇蝎女人;在敘事上體現為主觀視角、復雜敘事等;在主題上體現為關于社會“幽暗意識”的表達,關涉人性和社會中陰暗的背面,表達著對人類理性的懷疑,甚至絕望的拒絕態度,以及對現存秩序和法制的帶根本性的失望和詛咒[1]。筆者認為,黑色電影最重要的特征不是視覺上的,而是其主題上的“幽暗意識”和其中的存在主義色彩。
20世紀70年代的好萊塢興起的一批新黑色電影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對經典黑色電影的翻拍和戲仿,這種新實質上是一種“舊”;另一類則體現為對血腥畫面的使用、更復雜的敘事、彩色的黑色等。后者破壞了經典黑色電影在視覺風格、人物形象上的慣例,導致部分批評者認為這些電影只是偽黑色電影[2]。
如何界定黑色電影,目前仍然眾說紛紜。文章基于空間理論探究這一類型影片的形式風格和背后的文化心理,故暫時將其命名為較寬泛的黑色風格電影,判定的核心在于影片是否體現了一種“幽暗意識”。中國當代的黑色風格電影既有明顯借鑒經典黑色電影的影片,如《白日焰火》《風中有朵雨做的云》等,又有一些吸收新黑色電影特征的影片,如《心迷宮》《灰燼重生》等,其中包含一批在中國黑色電影風潮出現之前,已經帶有黑色風格的影片,如《無人區》《天注定》等。
1 黑色電影與空間敘事的天然關聯
1974年,列斐伏爾《空間的生產》的出版標志著學術界的空間轉向。福柯在其學術生涯的末期也刻意強調了空間的意義,他宣稱:“我們這個時代的焦慮,與空間有著根本的聯系,其甚至超越了與時間的聯系。”空間,作為一種方法,是診斷時代癥候和文化表征的關鍵元素[3]。
需要說明的是,后現代主義對空間的理解不是傳統“第一空間認識論”下的物質空間,而是列斐伏爾所定義的一種社會空間。列斐伏爾的空間概念強調,生產的社會關系是一種空間的存在,社會關系將自身投射到空間里,在其中留下烙印,同時又生產著空間。社會空間既不是物質空間,又不是精神空間,而是二者的綜合與超越。愛德華·索亞高度評價列斐伏爾的空間觀念,認為這一空間既是客觀的,又是主觀的;既是實在的,又是隱喻的。
而以空間作為方法研究黑色電影,是因為黑色電影與生俱來的空間性。它在布景上對于城市和街道的迷戀,在布光上對于陰影和反差的偏愛,都彰顯了黑色電影不同于其他類型電影的強烈的視覺空間感。加州大學學者愛德華·蒂門伯格認為類型或者風格的定義中沒有空間的概念,而空間性很適合歸于黑色電影的特征之中。受列斐伏爾等后現代空間社會學家的影響,他在其著作《黑色電影和現代性的空間》中專門剖析了黑色電影的空間演變。他認為,“黑色電影系列展示了再現空間和居住空間的實踐,揭示了文化自身是如何被理解為一種再現和空間實踐的符碼”[4]。
黑色電影的空間形式本身包含著內容,這與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不謀而合。黑色電影通過其特殊的影像語言,將城市與疏離、無情、危險的情感聯系起來,同時還會通過部分隱喻將社會關系予以空間之中。例如,霍華德·霍克斯的《夜長夢多》(1946)就細致區分了洛杉磯的幾代人,將他們和城市發展的不同階段聯系起來。生于舊洛杉磯的斯登伍德享受朋友之間的親密關系,而他的兩個女兒在新的城市里長大,花著父輩的錢,沉迷于毒品和賭博,體現出一種齊美爾在《大都會與精神生活》中所描述的厭世態度——無限地追求快樂使人變得厭世,因為它刺激神經長時間處于最強烈的反應中,以至于對什么都沒了反應[5]。
當代中國的黑色風格電影也會通過影像語言將社會關系投射到空間之中,如電影《暴裂無聲》對色彩的運用。農村空間是暖調的黃土地,城市空間則是冷調的現代辦公空間。煤礦老板昌萬年用餐的空間出現了兩次,輔以紅色的燈光。第一次是昌萬年通過非法和暴力的手段收購了金泉礦業公司,第二次是昌萬年氣憤于手下辦事不力,而憤怒地毆打,這里的紅色象征著一種暴力。
電影《浮城謎事》則通過建筑結構與布景隱喻社會階層的分化。喬永照和妻子居住在一個復式結構的房子內,他們擁有一個可愛的女兒,家中還有長期保姆和家庭教師,是一個典型的中產階層家庭。但是這個家庭空間卻因過于整齊干凈而缺少了人情味。喬永照的情人桑棋居住在一個破舊的筒子樓內,屋內擁擠雜亂,但充滿了生活的煙火氣。電影還通過鋼琴這一物品,表現了兩個家庭的貧富差距。妻子的女兒可以聘請家庭教師教她彈鋼琴,而情人的兒子卻還只能彈著玩具鋼琴。桑棋不顧一切地想要擠掉正房陸潔的位置,不僅是出于對喬永照畸形的愛,也是出于其想要擺脫階層困境的訴求。在這些電影中,創作者都有意識地利用空間的層級隱喻社會階層的層級關系。
2 從城市化到全球化的空間生產脈絡
列斐伏爾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的生產重心正在從物質資料的生產轉移到空間本身的生產。在全球化的今天,這種空間的生產不僅表現為大城市的擴張和普遍的城市化,還體現為資本依靠全球化的銀行、機場、高速公路,整合能源、原材料和信息,對所有空間進行抽象。“環境的組構、城鎮和區域的分布,都是根據空間生產和再生產中所扮演的角色來進行。”[6]
如果對近年來的國產黑色風格電影進行一番梳理,可以發現其中隱藏著一條關于改革開放幾十年來中國發展從城市化到全球化整合的脈絡。不同于西方緩慢線性的城市化進程,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后進入了一個急速城市化擴張的時代。這是一個十分混雜、不均衡的過程,總體上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三個階段既是先后發生的,又常常是同時發生的。
第一個階段是城市化的早期,農村勞動力流向城市,而城市對農村的空間進行整合。典型影片如《暴裂無聲》中,現代公司通過對農村土地進行征用補償,得以開采礦業,《天注定》中農村的煤礦也被富豪侵占。這一部分影片都或隱或顯地將城市作為鄉村的對立,城市代表的罪惡入侵鄉村,導致傳統鄉土社會的土崩瓦解,這一類電影延續了中國傳統的城鄉二元對立主題。
《天注定》中的大海對于富豪侵占煤礦一事感到十分憤怒,試圖寫信狀告中南海,卻因為不知道中紀委的地址而無法寄信。這個段落其實表征了以空間為維度的城市化對以時間為維度的鄉村的擠壓。大海仍舊停留在傳統的鄉土社會,對于鄉村之外的空間沒有概念,他無力解決家鄉的突變,只能訴諸暴力。
第二個階段是城市空間的重新整合,表現為城中村的拆遷和城郊犯罪。城郊的發展是城市向心結構朝離心結構轉變的結果。這一類影片有《風中有朵雨做的云》和《風平浪靜》。城中村拆遷是當代中國長期以來的背景和主題。電影《風平浪靜》就指涉了釘子戶強拆的社會事件。李唐為了GDP(搞地皮)不惜撞死釘子戶。資本操縱之下的城市空間生產與重建可以任意碾壓人的生命。而電影《浮城謎事》則在無意之間表述了城郊犯罪。陸潔跟蹤丈夫的出軌對象一直來到了城市郊區,也是高速公路的沿線地帶。女孩和她的父母居住在這一片城郊地區,在女孩死后,她的家人接受了官二代的賠款,用女兒的命換來了城市中的一套居所。空間碾壓著生命,生命交換著空間。
第三個階段是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婁燁最新的兩部電影《浮城謎事》和《風中有朵雨做的云》,雖然一個聚焦于中產階層,一個聚焦于城市拆遷,但其背后都浮現著全球化時代風雨欲來的信息。《浮城謎事》的開頭是一個以喬永照在飛機上的視角俯瞰武漢的全景,從生態良好的高速公路平移至城市的邊緣,最后來到城市的重工業區,高聳入云的煙囪排放著廢氣。鏡頭下移之后,城市之中原有的煙囪已經倒塌,這其實表征著武漢這座傳統重工業城市的轉型。喬永照從飛機上下來之后,驅車回家,他一邊開車一邊接聽生意上的電話。“現在,我們在為普田電子做ECU,量很大。”這一句話,表明了喬永照的身份。ECU,電子控制單元,又稱“車載電腦”,代表著高科技。喬永照作為一家高科技公司的負責人,顯然是這個城市轉型之際新興中產階層的代表。
而《風中有朵雨做的云》則完整記錄了姜紫成的紫金置業從貿易公司到房地產公司再到在香港成功上市的發家過程。姜紫成2000年從臺灣回到內地,此時正是中國房地產業的興起階段。2006年,中國金融行業全面開放,外資、熱錢大量涌入房地產行業。2007年,紫金置業集團成功在香港上市。姜紫成的發家史正是那個時代房地產業迅速崛起的寫照。
寧浩導演的《無人區》雖然聚焦于西部荒野的無人區,但其盜獵的野生動物的去向是阿拉伯,這一行為實質上是全球化時代的跨國犯罪。2011年,英國《獨立報》經過長達一個月的調查,發布了全球動物走私報告,動物走私成為僅次于毒品和武器貿易的全球第三大犯罪產業[7]。無獨有偶,科恩兄弟于2007年拍攝的《老無所依》的故事空間也是美國中部腹地荒無人煙的鄉村。這實際上是全球化時代空間擴張的一種表征,資本的無限擴張正在侵蝕地球上為數不多的凈土。
3 全球化時代的本土書寫
全球化時代,本土的重要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放大。全球化使城市逐漸被可移植的“無地域空間”覆蓋,城市為了維持其本土特色,需要保留其具有強烈地域色彩的空間。所謂“無地域空間”,指的是某些超越文化和地域特質,或被抽去原地域、文化因素的空間符號,此類空間的突出特征乃是其可移植性 [8]。
當代中國電影中,出現了一大批以“無地域空間”作為城市背景的影片,以《杜拉拉升職記》《失戀33天》等電影為代表。這類電影可以概括為“新都市電影”[9],通常以表現現代都市青年的情感與趣味為宗旨,以明亮、快節奏的清新風格表征現代化都市,與曾經著重表現城鄉二元對立的都市電影走向了截然相反的空間建構路徑。這實際上表征著中國新興中產階層的興起,他們迫切需要自我的身份認同,確認城市生活與奮斗的合法性。而這些影片的故事空間基本都位于北京、上海等一線大都市,同時也為二、三線城市的觀眾兜售著關于國際大都市的幻想。
但這些影片中充斥著都市烏托邦和都市景觀,屏蔽了城市中的真實生活和陰暗的角落。當曾經的都市電影、地下電影走向末路之后,令人欣喜的是,這一批具有黑色風格的國產影片仍然在以現實主義的方式記錄著城市的本土空間,在“無地域空間”無限擴張的今天,做到了極為可貴的本土表達。
說到黑色電影,因為其受德國表現主義布光的影響,由此很少聯想到現實主義,但實際上好萊塢黑色電影還繼承了德國魏瑪電影的新客觀主義。新客觀主義是一種中立、嚴肅、實事求是的客觀方法,倡導功能主義、實用性、去除雕飾[10]。這種新客觀主義發展到新黑色電影之中,則演變為一種紐約派攝影風格。紐約派攝影風格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整個紐約市制作電影的特點,受制于經費和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的影響,他們的電影一般采用實景拍攝,不加修飾地表現紐約街頭的骯臟,常用手持攝影,以《午夜牛郎》《法國販毒網》《出租車司機》為代表。這些電影常常將紐約這個危險、衰敗和分裂的地方的形象建構得更加牢固。
當代中國黑色風格電影對于西方黑色電影在視覺風格上的吸收少部分表現為德國表現主義的布光方式,更多體現為對新客觀主義的繼承,即對空間不加修飾地記錄,運用現實主義的手法描繪城市,因而成功做到了對本土性的表達。
《南方車站的聚會》很好地實現了表現主義布光和現實主義布景的融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對于城中村內筒子樓的再現:破損的墻皮、雜亂的電線、懸掛的毛巾、墻上的涂鴉、立式電風扇等,都在召喚著關于底層空間的記憶。而表現主義式的燈光和暴力場景的呈現又為這個底層空間增添了怪誕、陌生的風格。
其他的黑色風格電影很少采用極端布光,但一般會以現實主義手法再現城市的本土空間,如工廠、夜總會、筒子樓、城中村、廣場等極具中國特色的空間,同時還會保留這些空間的現實肌理與煙火氣息。《白日焰火》中,雪地中的黑色污漬、冬天車窗上結塊的冰霜、路邊餐廳臟亂的桌面,都是對城市空間不加修飾的記錄。
4 結語
中國當代黑色風格電影常受限于客觀原因,需要在電影結尾處加一個光明的尾巴,但其整體上還是呈現出一種對于時代和社會的絕望態度和“幽暗意識”,以一種曖昧的方式呈現暴力和法律。在當下這樣一個飛速發展又整體穩定的時代,風平浪靜之下是暗潮洶涌。黑色電影之于創作者而言,是使電影兼具商業性和作者性的一種載體,也是他們保留時代記憶、表征社會變革的一種表達。對于觀眾而言,則是一種時代焦慮的宣泄和對記憶衰退的抵抗。在空間視域下研究當代中國的黑色風格電影,可以為當下中國日新月異的空間變革提供一種輔助性的線索和歷史記憶。
參考文獻:
[1] 郝建.類型電影教程[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184.
[2] [美]約翰·貝爾頓.美國電影美國文化[M].米靜,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33.
[3] 吳紅濤.作為方法的空間[J].自然辯證法研究,2014,30(11):86-91.
[4] [美]愛德華·蒂門伯格.黑色電影與現代性空間[M].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2004:11.
[5] 汪民安,陳永國,馬海良.城市文化讀本[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135.
[6] 陸揚.社會空間的生產:析列斐伏爾《空間的生產》[J].甘肅社會科學,2008(5):133-136.
[7] 沈姝華.動物走私成全球第三大犯罪產業 年產值達60億美元[EB/OL].鳳凰網,http://news.ifeng.com/c/7fZPlsvoGNG,2011-03-07.
[8] 孫紹誼.“無地域空間”與懷舊政治:“后九七”香港電影的上海想象[J].文藝研究,2007(11):32-38.
[9] 陳犀禾,程功.“新都市電影”的崛起[J].社會觀察,2013(6):64-66.
[10] [美]芭芭拉·門奈爾.城市與電影[M].陸曉,譯.南京: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2016:41.
作者簡介:張斯迪(1997—),女,湖北襄陽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電影理論與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