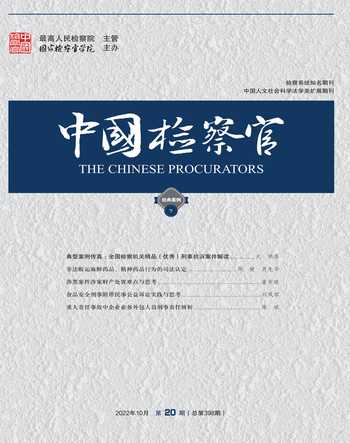推進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訴源治理的檢察路徑
佟齊 張靜 張珂
摘 要: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案件易發多發,與現有執法力量不足,網絡及寄遞行業存在漏洞,普法宣傳不到位,民眾法律責任認識不足等密切相關。檢察機關應樹立治罪與治理并重理念,以依法能動履職促進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訴源治理。在辦案過程中,要合理發揮刑事追訴職責和民事公益訴訟檢察職能辦理個案,并加大類案研究,監督協同行政主管機關齊抓共管、督促相關行業完善服務、落實普法責任促進公眾提高法治意識,形成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社會治理格局。
關鍵詞:類案監督 行刑銜接 訴源治理
一、問題的提出
[案例一]2016年5月,陸某某為買寵物,找到犯罪嫌疑人張某某,后張某某向其出售了一只非洲灰鸚鵡(時為國家二級保護動物,經鑒定價值人民幣1萬元,現為國家一級保護動物)。2021年6月,民警在陸某某家中將非洲灰鸚鵡起獲,并對張某某以危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案立案偵查,于2021年8月移送S區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檢察人員發現,張某某家中還飼養了20只箭毒蛙和2只青藍柳趾虎(均為國家二級保護動物),而張某某辯稱其為朋友贈送或個人人工繁育所得。檢察人員引導公安機關查找上游犯罪,后通過審查微信記錄發現張某某兩次從河南某微商(被當地刑事處罰)處購買7只箭毒蛙(經鑒定價值共計人民幣3500元)的事實。2021年9月,S區人民檢察院以張某某犯非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提起公訴,并于同年11月補充起訴其涉嫌非法收購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兩起事實均于2022年1月獲法院判決支持。[1]
[案例二] 2021年10月1日、10月7日、10月8日(禁獵期)早晨,犯罪嫌疑人景某某于B市S區某山坡(禁獵區)使用金屬桿2根、粘網1個、國家二級保護動物紅脅繡眼鳥3只誘捕野生鳥類,共捕獲三有動物沼澤山雀2只、黃雀1只,經鑒定價值共計人民幣900元。10月8日早晨,某野生動物公益保護組織人員發現后報警,景某某被民警查獲。當日S區公安分局以景某某涉嫌非法狩獵罪立案偵查,后移送審查起訴。最終,法院判處景某某拘役5個月,緩刑5個月。
實踐中,檢察機關辦理包括案例一、案例二在內的多起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時,發現這些案件主要呈現以下特點:一是犯罪手段集中,突出表現為收購、販賣、獵捕等,如案例一張某某非法出售、收購行為,案例二景某某非法誘捕行為;二是犯罪對象以萌寵類活物以及動物制品為主,如案例一陸某某購買非洲灰鸚鵡當作寵物;三是犯罪隱蔽性、機動性高,網絡交易盛行,如案例一張某某從微商處購買野生動物等。
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易發多發,不僅嚴重危及生物資源、破壞生態平衡,還會給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帶來威脅。檢察機關作為政治性極強的業務機關,應當積極踐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依法能動履職,打擊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活動,梳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易發原因,有針對性提出解決舉措,凝聚打擊合力,積極推進訴源治理,促進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二、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易發原因
(一)普法宣傳不到位,民眾認識不足
有不少行為人對保護野生動物資源的重要性和法律責任的認識和理解不正確、不深入。一類行為人能夠認識到行為有錯,可能會被給予行政處罰,但是不能意識到該行為具有刑事違法性。如案例二中,景某某認為自己誘捕野生鳥類的行為最多會被處以罰款或者沒收作案工具,并沒有想到會觸犯刑法。另一類行為人能夠認識到其可能會承擔刑事責任,但是錯誤認為只是在對動物生命權造成嚴重危害后果的情況下才會被追責,沒有意識到生態平衡遭到破壞亦是嚴重后果。如案例一中,張某某的下家陸某某認為,自己只買了一只非洲灰鸚鵡,且一直善待它,并沒有危害其生存,故雖然自己的行為觸犯法律,但是只要動物沒有受傷或者死亡,就達不到要判刑的程度。
上述現象的出現,一方面,有行為人受利益誘惑的原因,但另一方面,也與對應的行政法規較為繁雜,相關部門普法宣傳不到位有關。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屬于法定犯,與自然犯系行為本身明顯違反公共秩序、善良風俗和人類倫理而自然蘊含著罪惡性不同,法定犯是行為本身并無罪惡性,而是基于公共管理的目的,為適應社會形勢的需要而規定的犯罪[2],其構成犯罪的前提是違反行政法規中的禁止性規范。這些行政法規既有國家層面的原則性規定,還有各級地方政府根據本行政區域作出的細化規定,還有法規本身隨著社會發展變化進行的調整,使得“知法”門檻提高。比如案例二中,景某某購買的紅脅繡眼鳥,是2021年新修改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增加的517種(類)物種之一,而在此之前其只是《國家保護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經濟、科學研究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名錄》中的物種。名錄的變化導致入罪標準的變化,加之相關部門普法能力與水平不能適應現實需要,導致群眾觸法風險加大。
(二)執法力量不足
當前野生動物保護執法力量較為薄弱,執法監管體系存在短板,給不法分子帶來可乘之機,滋生其不易被查處的僥幸心理,進而以身試法。一是狩獵類案件的作案方式十分隱蔽,現有專業執法力量在人力配備上明顯不足。案例二中,景某某非法獵捕野生鳥類行為發生在清晨人跡罕至、樹木茂密的山林中,其利用竹竿、捕鳥網捕鳥,短時間得手后便撤離現場,執法人員難以及時精準到達獵捕地點。二是非法交易手段多樣且隱蔽,查處難度較大。線上交易通常采取使用虛假交易信息、偽裝郵遞等方式,而線下交易則依托正規花鳥魚蟲、工藝美術市場中的隱蔽場所和地下黑市,均較難被執法人員發覺。三是野生動物保護有“獵捕、販賣、運輸、收購、食用”五個關鍵環節,涉及農業、林草、市場監管、網信、城管等諸多行政管理部門,實際工作中存在職能分散交叉、工作銜接不暢等問題[3]。
(三)商務、社交等網絡平臺及寄遞服務存在監管漏洞
借助于現代互聯網及便捷物流,跨域交易頻繁。賣家利用貼吧、朋友圈、微信群等各種網絡渠道發布信息,或者利用淘寶等第三方商務平臺進行交易,之后再采用快遞寄遞運輸。案例一中,張某某位于河南的上家便是通過微信朋友圈等平臺發布廣告,之后與有購買意向的買家添加微信好友點對點洽談,最后借助快遞向全國各地運輸,形成了固定的運作模式。
筆者還發現,網絡運營商在履行防范網絡違法犯罪的法律義務和保護野生動物的社會責任方面存在不足:一是有的電商平臺在商業利益驅動和監管成本考量下態度消極被動,有的甚至在接到舉報后仍然不予處理、監管明顯缺位;二是電商平臺審核人員專業能力不能完全滿足現實需要,難以及時正確評判舉報內容是否違規。而寄遞環節同樣有漏洞,開箱驗視、過機安檢機制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如案例一中,張某某的上家多次通過將箭毒蛙隱藏在茶葉盒中發送快遞,均未被發現。
三、檢察機關推進相關犯罪訴源治理的路徑
(一)打擊與治理并重,完善對犯罪嫌疑人的懲治體系
第一,堅持全鏈條打擊,依法追捕漏犯、追訴漏罪,織牢法網。在辦理某一環節的案件時,應注意從口供、證言、交易記錄、聊天記錄、現場勘查等證據中發現關聯的上下游犯罪線索,全鏈條打擊犯罪。如案例一中,民警因張某某販賣非洲灰鸚鵡一案對其居住地進行搜查,發現其在家中飼養其他國家保護動物。檢察機關通過督促公安機關調取證人證言、恢復其手機聊天記錄發現其收購的事實,破除其脫罪僥幸心理。
第二,落實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把好案件“入口關”。[4]檢察機關應注重發揮在刑事追訴職責中的“程序中樞”作用,合理追訴犯罪,把控好捕訴審查關口。根據現行法律規定把握好定罪量刑標準,既要考量價值,也要兼顧其他情節,做到具體靈活、綜合裁量、寬嚴相濟,讓人民群眾切實感受到公平正義。應綜合評估社會危害性,如是否造成動物死亡或者動物、動物制品無法追回等危害后果,是否有退賠退贓、悔罪表現等從輕情節,或者涉案動物是否系人工繁育等,準確認定是否構成犯罪,發揮好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對犯罪嫌疑人的教育轉化作用,減少短期集中羈押帶來的在押人員交叉感染弊端,減少犯罪嫌疑人的社會對抗負面情緒,推動其順利回歸社會。對于作出相對不起訴處理的案件,應根據刑法第37條的規定,適用非刑罰處理措施,避免出現處罰真空。
第三,發揮檢察一體化機制優勢,及時移送案件線索,助推被侵害的生態環境及時恢復。刑事檢察部門發現可能損害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情形的,應當及時將相關案件線索移送公益訴訟檢察部門。后者可通過訴前公告等手段督促法律規定的機關或建議符合法律規定條件的組織提起民事公益訴訟,或者適時啟動(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程序,向侵權人主張賠償損失、承擔替代性修復責任等訴訟請求,促進生態環境的恢復。
(二)發揮法律監督作用,豐富外部協作機制,增強訴源治理合力
2021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關于加強訴源治理推動矛盾糾紛源頭化解的意見》強調,要推動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導和疏導端用力。野生動物資源保護是個系統工程,涉及到多個監管和執法部門,例如農業農村部門、林業部門、市場監管部門等。[5]檢察機關應發揮法律監督職能作用,協同行政主管機關共同提高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在雙贏多贏共贏理念中合力解決治理難題。
第一,充分發揮行刑雙向銜接機制作用,促進行政、司法機關發揮各自職能優勢,合力打擊違法犯罪活動。打破數據“壁壘”,與森林公安等行政職能部門建立并完善行政與刑事案件信息共享機制、重大疑難復雜案件溝通協調機制、情況通報機制,暢通案件線索移送渠道。強化類案分析研判,如對于哪些屬于人工繁育技術成熟、已成規模,作為寵物買賣、運輸的野生動物,以及非法狩獵未遂是否構罪等立案標準等方面達成共識,構成犯罪的,督促及時移送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對于被不起訴或者免予刑事處罰的行為人,依法應給予罰款、沒收犯罪工具和違法所得、吊銷狩獵證、記入社會誠信檔案等行政處罰或其他處分的,移送相關部門處理。
第二,對行政監管執法問題開展法律監督。檢察機關針對履職過程中發現的行政監管漏洞或者執法不到位、不嚴格等問題,可采取磋商提醒、督促其通過強化聯合執法質效等方式解決,必要時向相應級別行政主管機關發出訴前檢察建議、提起公益訴訟,促進專項治理。
第三,建立交流會商和研判機制,共同解決野生動物保護執法中的突出問題。檢察機關通過向地方黨委政府、人大政協報告情況,爭取支持,促進野生動物保護的法治化、規范化、制度化發展;通過聯席會議、同堂培訓等機制,就證據收集和固定、司法鑒定、法律適用標準、野生動物救助等重點難點問題達成共識;通過聘請行政人員兼任檢察官助理、行政機關派員參與臨時檢察辦案組、檢察人員赴相關職能部門交流鍛煉等雙向交流機制[6],助推專業領域案件辦理質效的提升。
(三)制發檢察建議,督促網絡平臺、寄遞企業強化監管意識和能力
通過制發檢察建議,督促相關企業履行法律責任和社會責任,打好“網絡無野”“寄遞無野”阻擊戰:網絡平臺切實提高技防人防水平,不斷更新相關技術,提高平臺自動攔截、屏蔽違法信息的能力,從源頭阻攔違法犯罪信息;強化后臺人員審核意識和甄別能力,科學準確判斷違法犯罪信息和正常商務活動的界限,及時查封違規網店、賬號;建立完善的舉報線索反饋機制,及時回應公眾關切,建立違法犯罪線索甄別和移送執法機制,鼓勵形成社會公眾、公益組織、網絡平臺、政府機關多方共建共治格局。抓好“八號檢察建議”落實工作,督促寄遞企業提高從業人員安全意識、處置水平和設備技術識別能力,落實“實名收寄、開箱驗視、過機安檢”三項制度,強化同城閃送、智能快遞柜等寄遞新業態監管,多措并舉破解落實難題,打造寄遞行業清朗空間。
(四)貫徹“誰執法誰普法”責任制,引導民眾更新野生動物保護理念和法律意識
積極引導民眾更新和轉變思想觀念,提高其法律意識,既能加強源頭預防,也有利于彌補執法力量不足,使人民群眾成為野生動物受害案件的“舉報人”,共同形成保護野生動物的合力。
第一,開展個案釋法說理,精準普法。深入了解涉案行為人犯罪動機、行為方式,在辦案過程中達到法治教育、特殊預防的目的。
第二,以案說法,增強宣傳活動的直觀化、多樣化、鮮活性。通過檢察公開聽證等形式深入群眾,以鮮活案例釋法說理;利用電視、廣播、報紙、網絡新聞媒體等多種渠道拓寬普法廣度。打造野生動物保護主題精品課程,送法進校園、單位、社區,切實提高人民群眾野生動物保護意識。
第三,定期定向普法宣傳,加強宣傳活動的本土化、精細化、時效性。通過研判本區域案發特點,針對重點對象、重點手段、重點區域、重點人群制定宣傳策略和方案,如在花鳥魚蟲、工藝品市場等重點線下交易區域做經常性的普法宣傳,在鳥類遷徙季的淺山區、流動黑市附近宣傳當地野生鳥類知識、常見違法手段、市民舉報方式等,或者在重要節日節點,如世界野生動植物日、國際珍稀動物保護日或者專項行動中予以集中宣傳。
*北京市石景山區人民檢察院黨組成員、副檢察長、三級高級檢察官[100043]
**北京市石景山區人民檢察院第一檢察部四級高級檢察官[100043]
***北京市石景山區人民檢察院第一檢察部三級檢察官助理[100043]
[1] 根據辦案當時適用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已失效),陸某某危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達到了立案追訴標準。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施行,其規定收購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的入罪標準是價值人民幣2萬元,因該案未達到此犯罪數額,故公安機關最后作出了撤銷案件處理。
[2] 參見曲新久主編:《刑法學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61-62頁。
[3] 參見《保護成效怎樣?仍有哪些漏洞?短板如何補上?—透視執法檢查報告中的野生動物保護現狀》,新華網www.xinhuanet.com/2020-08/12/c_1126358111.htm,最后訪問日期:2022年8月4日。
[4] 參見苗生明、劉辰:《刑事檢察能動履職促進訴源治理機制的構建與運行》,《人民檢察》2022年第8期。
[5] 參見劉炫麟:《我國野生動物法律保護的體系、缺陷與完善路徑》,《法學雜志》2021 年第 8 期。
[6] 參見彭玉:《行政人員與司法人員交流協作的域外做法及借鑒》,《人民檢察》202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