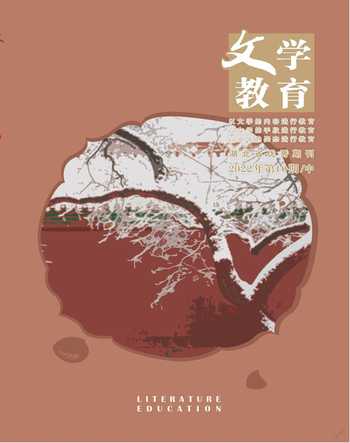《盲刺客》:多個空間下的女性救贖之路
許陳丹
內容摘要:《盲刺客》被稱為是一部回憶錄,它以現實空間為主線,創造出第二空間,即“勞拉”的《盲刺客》,由此再建立了第三空間“盲刺客”的敘事線。在這三個空間里,“我”即艾麗絲蔡斯是多個空間下的聯結者,她借三個空間里的人物建立起自我對話。每個空間里的女主人公都是本體敘事者艾麗絲隱藏的另外兩面,同時分別隱喻了男權制時代下女性共同的命運。從三個空間的隔空對話、多重身份的多種含義、救贖之路三個方面來分析艾麗絲是如何在多個空間中建立起對話并進行救贖的,以此來探討女性在男權社會下的生存之路。
關鍵詞:《盲刺客》 空間敘事 女性主義 象征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是當代極富代表性的女性作家、詩人、評論家。她的作品《可以吃的女人》《別名格蕾絲》《盲刺客》等都很有影響力。《盲刺客》(The Blind Assassin,2000)是她第十部長篇小說,出版于2000年,并獲得了該年英國布克獎。無論是從敘事學、后現代、還是女權主義等方向,國內外學者對《盲刺客》從不同的研究角度進行了解讀,然而在眾多學者的文章中,最后都只是揭示了女性遭受困境的原因,卻未能提出解救女性的生存困境之法。例如柯倩婷的文章中探討了小說的記憶與空間敘事,并揭示了作者利用這種敘事方式來寫作的隱含目的。但是在這篇文章中并沒有對空間敘事進行非常清晰的梳理,也沒有對小說所揭示的女性困境提出救贖方法。本文重新對文本所呈現的多個空間進行了清晰地邏輯劃分,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條女性救贖之路。
一.多空間對話
《盲刺客》是部結構十分復雜的作品,故事里套著故事。這種復雜的結構一方面得于作者的敘事技巧,另一方面也得于作者寫作的隱含目的。阿特伍德運用其超強的敘事能力在作品中為讀者建立起了三個空間。首先文本一開始就將讀者帶入了第一空間——現實空間。在現實空間的基礎上,作者又虛構出了第二空間,在第二空間里又虛擬了第三空間。每個空間里都以不同的人稱講述著不同的故事,而這些故事中的人物之間又建立起了一種交流關系。
1.“隱忍與困惑”的現實空間
現實空間在小說中指的是以第一人稱“我”展開的敘事空間,是高齡82歲的女主人公艾麗絲·蔡斯以記憶敘事方法來回憶過去和講述當下生活的故事。
在現實空間里,由女主人公的妹妹勞拉的死來引出作品的第一個故事,也是整個作品的主題故事。文中開篇寫道:“大戰結束后的第十天,我妹妹勞拉開車墜下了橋。”在這里阿特伍德運用了倒敘手法,為整個故事制造了懸念:勞拉為什么墜下了橋?是意外還是自殺?在故意宣告勞拉死亡和引起的種種疑問之下,“我”開始回憶與勞拉的成長過程。首先在現實空間的回憶當中,整個線索都是由從小照看艾麗絲姐妹的女傭瑞尼來提供的。作為本體故事的主要線索提供者,將艾麗絲、勞拉以及蔡斯家族的發展歷程完美地串聯在了一起。在艾麗絲的回憶中,還穿插了許多則新聞報道,為艾麗絲的“回憶之旅”提供了時間框架。但是這些新聞記錄的只是生活的表面,小說通過最后揭示的真相中來顛覆了各種新聞報道的事實。在此使用新聞報道不僅體現了作者本人對新聞報道存在質疑的觀點,同時也將小說里現實空間里的本體故事的真實性提高到了一定高度。現實空間里除了回憶的故事情節外,還穿插著艾麗絲當下的生活片段。小說中描寫到了年老的艾麗絲受著身體、心理上帶來的雙重痛苦,進一步暗示了艾麗絲對自己妹妹勞拉的愧疚之情。
2.“放縱與反叛”的第二空間
主人公艾麗絲假借勞拉之名發表了文本——《盲刺客》。《盲刺客》在“我”的回憶中,套入了“他”和“她”的故事,是在現實空間的基礎上以第三人稱為敘述視角建立起來的第二空間。在這個空間里主人公分別為“他”和“她”。作者借用這兩個人稱代詞來指代左派激進青年亞歷克斯和艾麗絲。華萊士·馬丁在《當代敘事學》中指出:“第三人稱一般是指其中根本不提及寫作的‘我的虛構作品。”看似為讀者營造出了一個虛構的空間,但卻是暗示了艾麗絲婚外情的真實故事。
整個第二空間是由“他”和“她”進行約會而展開的。作者通過塑造不同約會場景、場所、環境的好壞和變換來暗示艾麗絲與亞歷克斯約會的不易。比如文本中“路面只有犁溝那么寬。到處是餐巾紙、口香糖的包裝紙,以及魚鰾似的用過的安全套。瓶子、鵝卵石和泥路上的一道道車轍,一切都亂糟糟的”。然而即使是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下約會,艾麗絲表現出來的卻是愉悅、興奮之感,她與亞歷克斯的每場約會都是其釋放內心被婚姻束縛住了的情感的地方。
3.“無法擺脫厄運”的第三空間
在小說塑造的第二空間里《盲刺客》中作者又虛構了第三空間——“他”給“她”講述了發生在塞克隆星球的盲刺客故事。塞克隆星球上的薩基諾城曾是一座美麗繁華的城市,后來毀滅于部落戰爭。在國王統治下,那里的居民信仰眾多之神,以少女的血祭奠神靈,同時把這些當祭品的女孩割去舌頭,成為獻身啞女。在故事中盲刺客致盲的原因以及他的身世是這樣描述的:“這座城市還以編織品而聞名——這種地毯總是由奴隸中的兒童來編織的——由于長時間不斷地把眼睛湊近織物勞作,他們一般到八九歲時就全都瞎了。而地毯的價值是賣主根據它完工后瞎了多少個孩子來衡量叫賣的”;“這個年輕人小時候曾經織過地毯,后來淪為了童妓,逃脫后就以他的無聲無息、行動詭秘以及無情的殺人手腕而名聲大噪。”
啞女和盲刺客的愛情是處在一個危險境遇的,猶如第二空間里的艾麗絲和亞歷克斯。四個人雖扮演著不同的身份,但是所面臨的愛情與殘酷現實之間的問題是有所相似的。他們有結實的愛情、有雙方的信任,也有惡劣的環境、有不能公眾于世的苦楚。
4.三個空間的嵌套
阿特伍德在現實世界里創造出第二空間,再由第二空間里的人物虛構出第三空間。讀者可以在現實世界里的艾麗絲、勞拉的成長過程中發現,勞拉的死與其從小生長的環境而形成的性格分離不開。性格倔強、孤傲的勞拉身上有種不同于姐姐艾麗絲的強烈反叛特征。反之,艾麗絲卻是個‘保守、‘任人擺弄的舊女性。在現實空間里的“我”是壓抑的、失去自由的、肉體與靈魂是相斥的。也正因為這樣,得不到情緒釋放的艾麗絲以勞拉的名義發表了《盲刺客》,在現實空間里創造了第二空間。因此,第二空間里的艾麗絲與現實空間里的“我”產生了強大的反差感。“我”通過第二空間里的艾麗絲,與之對話,把隱藏在身上的自由放蕩、叛逆之情全部投射到第二空間里的“她”身上。
在當現實空間與第二空間完成一組對話后,第二空間里的艾麗絲與第三空間的啞女也建立起了對話。她將自己與亞歷克斯實現雙宿雙飛的愿望寄托在啞女身上。雖然啞女自身也遭受著所屬空間里的困境,但她終究是與之相愛的盲刺客時刻在一起的。而這正是第二空間里的艾麗絲所不能做到的。這三個空間以這種嵌套式的結構向讀者展現了以艾麗絲所代表的女性是極其復雜的。
二.多重身份的象征
多個空間的對話使得艾麗絲這個人物變得更加立體,也使艾麗絲在現實世界里實現不了的情感通過隔空對話傳達給第二、第三空間里的“她”和“啞女”。阿特伍德不僅是在敘事上運用了空間嵌套的技巧,而且在這些構造的不同空間里,所塑造的人物:“我”“她”“啞女”都帶有不同的象征性,她們象征著男權社會中各類女性所面臨的共同命運。
1.“我”即敘事者身份的象征
為了擺脫工廠困境,父親把“我”許配給了富有的中年實業家理查德。然而此時的艾麗絲已愛上亞歷克斯,但由于她從小所受的教育造就了她順從的性格,無奈之下只好同意成為理查德妻子。在后來的生活中,始終被理查德的一家掌控于手掌之中。即便是自己的妹妹被丈夫送去了精神病院也無可奈何、無計于施。在《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雜志的一篇論文中寫道:“無論是由于艾麗絲的個性,還是由于她母親早逝而強加給她作為姐姐的責任,艾麗絲對自己有自決能力的信念已經被埋葬在虛假的自我之下,她構建了這個自我,以獲得她情感上依賴的男人的愛和認可。”可見在男權制社會下,大部分女性即便是貴族小姐或是富家夫人,都是生活在她們的父親和丈夫的掌控下。
然而不可忽視的是在小說中也寫到了“我”在接受來自家族的安排和丈夫支配下,內心充滿著無盡的叛逆。例如“我”在小時候會故意地將妹妹推倒在草坪上,或是在小說后半部分講述到“我”出于妒嫉而告訴妹妹自己與亞歷克斯的戀愛關系。以上這些都暗示著“我”這類女性在自身欲望中有著覺醒意識。阿特伍德用極為豐富的思想內涵和強大的藝術張力將“我”身份賦予了這一層象征意義。現實空間里的“我”是處于困境中帶有覺醒意識的女性,雖然沒有自由、沒有權力,但是在她們的意識中往往有著微弱的反抗意識,也是一種無聲的掙扎。
2.“她”者身份的象征
位于第二空間里的“她”者身份又有著另一層象征意義。在這個空間里,艾麗絲與亞歷克斯的歷次約會被描寫成一場場偵探情色片。上流社會的貴族夫人穿越在大街小巷,隱藏自己的面目,去公園、去列車風格的咖啡館、去五金店樓上的小房間,作者將這些約會變成了一種主人公的冒探險經歷。然而這對于生活在枯燥乏味中的艾麗絲來說,這種約會形式對她來說具有極大的感官體驗,比如其中描寫道:“她需要一件在大甩賣時的買的外套,塞入手提箱,進一個飯店的參觀,把自己的外套留在前臺,溜進化妝間換衣服,然后再弄亂頭發,擦去口紅,出來時就成了另外一個女人……她可以揚起雙眉,那種坦然真誠的目光只有雙重間諜才能裝出來。”
艾麗絲在緊張的時間、狹窄的空間里,享受著每一次的自我釋放。他們的約會是緊張與激情的二重奏。阿特伍德將戲劇性的約會布景賦予了艾麗絲一種“逃離”浪漫色彩。因此,“她”者身份其實是象征著敢于反叛現實困境、追求自我空間與自由愛情的女性。
3.啞女的身份象征
啞女是帶著“失語癥”的特征出現的一類女性。她的身份是一種對自由的失望和無奈的象征。在啞女這個故事里女性是物化的、可以被操控的祭品,是與鎖鏈相伴的受害者。在這虛構的星球里,啞女處于被摧殘的生存境遇中。原本以為盲刺客與啞女在逃離后會在無人認識的一片凈土里開始自由生活,但故事的結局是盲刺客帶著啞女逃出了薩基諾城,在幾經磨難后戲劇性地被“狼”吃掉了。阿特伍德并沒有簡單地抨擊社會對女性的壓抑,而是運用了一種歐亨利式——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結局模式。正是以這樣的一個悲慘結局,從一個角度折射出女性的悲慘命運。
阿特伍德用啞女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他者地位形象,一方面揭示了對男權統治的反抗意識,另一方面表示女性在男權制社會中經歷著沒有自由、沒有權力、沒有自我的困境。值得注意的是以這類啞女為代表的女性仍未有覺醒意識,或者說她們在這樣的困境中充斥著無限的恐懼和孤獨。
三.女性救贖之路
作者從多方位的、虛擬的、現實的空間,再到不同空間里人物的隱射,向讀者揭示了女性在面對困境時的不同選擇,以及女性在特定時代下所遭受的共同命運。當然作者并沒有到此截然而止,而是針對這些女性命運問題之后,向讀者傳達出女性該如何在困境中開創出一條救贖之路的信息。從現實空間到第二空間再到第三空間,多個空間結合在一起后呈現出來的是一條女性救贖之路。這條救贖之路從艾麗絲的成長軌跡到虛構的故事空間中,顯現出來的是由“他救”“互救”“自救”三種模式相組合而成。
“他救”在這里是指來自異性間的救贖。文本中對艾麗絲來說亞歷克斯是“他救”者。生活于婚姻牢籠中的艾麗絲在亞歷克斯的愛情催發下,不顧一切地放下身段去各種地方進行約會。可以說如果沒有亞歷克斯的愛情與那份敢于偷情的勇氣,艾麗絲的自我意識、自由意識不會得到釋放,從而就會導致她在婚姻牢籠中逐漸迷失自我。她在與亞歷克斯的愛情中找回了真實的自己,這是一種來自異性者的“他救”之路。
“互救”在這里指的是同性間的互相救贖。小說中艾麗絲摧毀了勞拉,這個事實無可更改。比如勞拉對亞歷克斯在戰爭中身亡的事實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她面對姐姐的坦白卻難以接受。艾麗斯原本可以選擇撒謊,繼續維持勞拉的幻想,但卻因為嫉妒,她撕破了一切,把妹妹推向了死亡。如果艾麗絲能夠在理查德決定把勞拉帶回家中時就提出反對意見,或者當得知勞拉被理查德送去精神病院后能及時把妹妹救出來,那么勞拉或許也不會自殺,同樣艾麗絲在晚年也不會過得如此凄涼。如果艾麗絲能與勞拉攜手抵抗理查德家族,那么悲劇或許就不會發生。在男權社會里,同性間的互相救贖是不可或缺的。
“自救”是除了“他救”和“互救”之外小說想體現的更為至關重要的一個途徑。每一位女性無論身處怎樣的困境,個體的自我救贖是除肉體之外靈魂得到重生的重要途徑。阿特伍德用三個故事,以小說中大故事的敘事者“我”作為主體,通過回憶敘事、塑造第二、三空間來暗示這是女主人公艾麗絲的一場自我救贖。例如在小說的最后一份新聞報道里寫著:“她坐在她家的后花園里,十分平靜地離開了我們”。這里的“十分平靜”可見艾麗絲在走之前不是痛苦的,所展現的是一種對過往的釋然、對自己的諒解。
《盲刺客》的故事套故事的結構固然復雜,卻看到了以艾麗斯為代表的女性在對自己的人生處境上是如何經歷困境、覺醒、反叛的過程。艾麗絲在三個空間中建立起了自我的隔空對話,在這對話中含有的三種不同身份又各自代表了女性三種意識形態。在此基礎上,構建出了一條女性在男權社會下的生存之路。
參考文獻
[1]阿特伍德.2003.盲刺客[M].韓忠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2]柯倩婷.《盲刺客》:一部關于記憶的小說[J].外國文學評論,2007(01):104- 110.
[3]黃向輝.論《盲刺客》的結構藝術[J].當代外國文學,2007(04):76-81.
[4]何瑛.《盲刺客》:女性的敘述欲望與生存地圖[J].上海文化,2015(07):113- 119.
[5]饒靜.盲目與洞見——讀《盲刺客》[J].世界文學評論,2008(01):181-183.
[6]王嵐.《盲刺客》:一部加拿大后現代女性主義的杰作[J].外國文學,2005(01):75-79.
[7]“Alias Laura”: Representations of the past in Margaret Atwood's “The Blind Assassin”[J]. 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2006,101(2).
[8]Laura Flores. Tres caras en el espejo A propósito de The Blind Assassin de Margaret Atwood[J]. Revista de Culturas y Literaturas Comparadas,2008,2(0).
(作者單位:浙江工商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