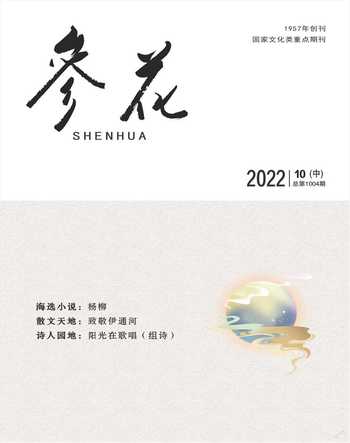中印美學中的“味”“韻”和物我合一
中印美學范疇中存在著三組極為相似的概念。婆羅多的“味論”與鐘嶸的“滋味說”都強調讀者接受過程中的超越性藝術審美體驗,歡增的“韻論”與王士禛的“神韻說”皆認為,詩人應當創作具有言外之意的作品,新護所推崇的“梵我合一”的“喜”與莊子追求的與道合一的“逍遙”,在本體論意義上達成了一致。對這些概念的對比研究有助于明晰中印兩國的美學特質,為東方詩學提供更多更有意義的內容,同時,在與西方文論進行對比研究時,更有理論自信。
一、中印接受理論概念——“味”
(一)印度美學的“味”
“味”這一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古籍中記載了四類“味”。到了公元前700年左右,精神的味取代了物質的味,其中“這是味,得味者歡喜”對文學理論的影響很深。作為文學理論的“味”形成于公元前3世紀左右,之后經過發展,約公元2世紀左右,婆羅多牟尼作《舞論》標志著“味論”正式成熟。
《舞論》系統地總結和闡釋了“味論”,具體論述了戲劇的艷情、滑稽、悲憫、暴戾、英勇、恐怖、厭惡和奇異八種味,這些味產生于別情、隨情與不定情的結合,各味又有各常情。“情使這些與種種表演相聯系的味出現”,由情生味,情與味相輔相成,“正如善于品嘗食物的人們吃著有許多物品與許多佐料在一起的食物,嘗到味一樣。智者心中嘗到與情的表演相聯系的常情的味。因此,這些常情相傳是戲劇的味……有正常心情的觀眾嘗到一些不同的情的表演所顯現的,具備語言、形體和內心的表演的常情,就獲得了快樂等戲劇的味”。[1]《舞論》中論述的“味”是藝術之生命,美之本質,“沒有任何(詞的)意義能脫離味而進行”,[2]這種“味”指向創作、表演與鑒賞中的感情,更傾向于審美體驗。
之后,大約10至11世紀,新護的《舞論注》在前人基礎上,創造性地闡釋了婆羅多的味論,成為梵語詩學家大多采納的理論,并為現代人所推崇。新護在洛羅吒“強化展示論”、商古伽“模仿推理論”、那耶伽“品嘗論”三種味論的基礎之上,[3]提出具有鑒賞力的觀眾在觀賞戲劇時,通過演員表演等各種藝術手段,戲劇內容與真實存在互相抵消,觀眾形成一致性感知,被戲劇中普遍化的情由、情態和不定情喚醒心中潛伏的常情,由此產生一種超越文字和語言的感知,就是味。觀眾品嘗到的味由常情產生,但常情有快樂,也有痛苦,而味永遠是愉快的,因為味是超越世俗束縛的審美體驗。并且,新護還在婆羅多八味說的基礎上增加了第九味——寂靜味。至此,印度美學對味論的研究達到最高成就,“味論”也形成了全面體系,成為占據核心地位的美學思想。
(二)中國美學的“味”
中國的“味論”從先秦就開始了,不過主要是以“味”論政或論樂。《左傳·昭公·昭公二十年》記載“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以“五味”喻政德,將味的概念限制在政治領域。而《論語·述而篇》有“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禮記·樂記》有云,“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4]都將味與樂聯系了起來,使味的概念進入審美領域。
到了南北朝時期,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以味論詩。陸機的《文賦》以味品詩文偏重文采,劉勰的《文心雕龍》直接將味與情采聯系,但只是旁及,未將味視為獨立概念,理論價值不高。真正建立詩味說的是齊梁時期的鐘嶸,他第一個明確提出并全面論述了詩之味。鐘嶸建立的“滋味說”的核心內容有兩點:一是好詩須有滋味,這種滋味來自內容與形式的完美結合。其《詩品序》謂五言詩當為“眾作之有滋味者”,原因就在于其“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而不似玄言詩的“理過其詞”和宮體詩的“詞繁意少”。將情真意切與文采華茂結合,才能產生有滋味的好詩。二是把“味”當作評判詩歌好壞的藝術標準,有滋味的好詩才能“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心動”,引起讀者的審美愉悅感。由此,鐘嶸建立的“滋味說”開始作為重要概念影響后世美學,晚唐司空圖進一步將滋味說發展為“韻味”說,將滋味說引向了更高的審美領域。
綜上所述,中印美學中的“味”都指能產生審美愉悅感的接受心理,形成與感知流程基本一致:先是作品提供引起藝術感知的前提,然后通過作者的表述或演員的表演,使接受者獲得普遍的情感體驗,由此,接受者達到超越性的藝術審美境界。在這一過程中,“情”非常重要,中印美學都強調以情感味,由情生味,但“情”的含義不大相同。印度味論中明確規定了“情”的各種類型,含義廣泛且不固定。中國味論所說的“情”即為感情,只強調真實性而不進行詳細劃分。印度的味論更偏重戲劇這一舞臺表演形式,而中國的味論主要限制在詩文領域,受不同傳播媒介的影響,接受者所感之“情”也不太相同。然后,中印美學的“味論”都趨向了更為復雜的審美和哲學境界,如新護以“喜”解味,中國的滋味說經由司空圖發展為“味外之味”,最后在王士禛那里發展為“神韻說”,之后進一步發展為代表中國美學核心的意境說。印度的味更多地走向了宗教領域,而中國則將其限制在藝術審美領域。
二、中印創作理論概念——“韻”
(一)印度美學中的“韻”
提出“韻”這一術語的是公元八九世紀的歡增,在此之前,“韻”是一個語言學概念,是指通過語音展示詞義的一系列發音過程。歡增的《韻光》將“韻”從語言學領域轉換到詩學領域,容納莊嚴論、風格論和味論,構成了“韻論”完備堅實的體系。
《韻光》中指出詩的意義有表示義和暗示義或領會義兩類,詩的本質是后一種,暗示義“不能為僅僅具有詞和義的學問(一方面)知識的(人)所知曉,而只能為懂得詩的意義的真義的(人)所知曉”,[5]因而這是由暗示和超越所得的詩的靈魂——“韻”。在歡增的論述中,韻既指具有暗示意義的詩,也指在詩中起暗示作用的因素和所暗示的意義,其“實質是詞(以及由詞組成的句和由句組成的篇)的暗示功能和由此產生的暗示義”。[6]同時,歡增將韻分為“非旨在表示義”和“旨在依靠表示義暗示另一義”兩大類,兩類之下,又有“味韻”“情韻”和“莊嚴韻”等若干小類,建立起細致全面的體系。此外,歡增還將詩分為韻詩、畫詩和以韻為輔的詩三類。他推崇韻詩,認為詩人通過巧妙刻畫別情、隨情和不定情形成暗示義,將事物的本質和靈魂隱藏在外在形式之下,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可以透過事物的表面領悟真理,這種領悟是與梵我合一極為相似的境界。歡增所建立起的這套以“韻”為中心的詩歌藝術理論,將詩歌視為一個有機體,走出了語言學的桎梏,為印度詩歌理論的發展帶來了新思路。之后,大約10至11世紀,新護的《韻光注》進一步發揮了歡增的“韻論”,同時,曼摩吒的《詩光》也談及了詞的字面義、內含義、暗示義和韻的分類等,使“韻論”成為印度美學的核心理論之一。
(二)中國美學中的“韻”
與印度美學相稱的中國美學中的“韻論”為“神韻說”,其來源與莊子的“得意忘言”論密切相關。莊子認為道無形,故不可言,所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但他也認為言可間接“渡”意。對于這種間接性,王弼給了通達的解釋:“立言以造象,立象以傳意”,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因此,莊子的“得意忘言”之論強調了言語作為象征性工具的作用,但同時也涵蘊了形象大于語言文辭的意思,這就可以悟出形與神的問題。在這之后,鐘嶸提出“文已盡而意有余”,皎然論說“意中之靜,意中之遠”就順其自然了。這些理論都是在莊子“得意忘言”基礎上的進一步闡發,在此之上,司空圖提出了“韻外之致”“味外之旨”,形成了神韻論的雛形。
司空圖的《與李生論詩書》以飲食為喻,主張詩歌應寫得含蓄蘊藉,做到“近而不浮。遠而不盡”,具有“韻外之致”“味外之旨”,這一論說直接啟示了王士禛。王士禛繼承了司空圖“X外之X”的結構和“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理論,認為象外之象的組織結構促成了味外之味的藝術效果,正式確定了“神韻論”這一概念。“神韻論”即詩人以簡易筆墨、虛實之意象和含蓄蘊藉之語言,造既富生機又表意深遠的意境,借此含蓄表達作者的真摯情感和幽深意緒,以促使讀者從中體會“言有盡而意無窮”的審美意蘊。
梳理中印韻論可以發現,兩者都將“韻”的暗示性和超越性作為核心特點進行理論建構。印度韻論轉借語言學概念,強調語言的言外之意,以為這才是詩之靈魂,中國的神韻說同樣強調要用有限的語言表達無限深遠的意境。中印韻論都是對詩人創作的規定,認為詩人應通過一系列技巧和手法創作出具有韻的詩,這樣的詩才算好詩。但兩者的體系卻完全不同:歡增詳細規定了韻論的含義及分類,建構了一套邏輯嚴密的理論體系;中國韻論的建立和發展都很隨性,概念模糊,理論凌亂,對于這一點,中國文論應合理揚棄。
三、中印藝術境界:物我合一
(一)印度美學——“喜”
10至11世紀,新護在《韻光注》和《舞論注》中提出了“喜”,指藝術品的“味”“韻”必須達到“物我雙亡”、主客合一的“喜”的境界,即“梵我合一”。這一概念與印度一貫的美學追求相符合。古代印度把世界分為現實的物質生活領域和超驗的精神生活領域,這種靈肉二元的觀點貫穿印度美學的始終,使印度人不僅積極享受人生的欲樂悲苦,同時,又充滿了對現實的超越之情。“梵”即是這種靈肉二元合一的最高境界。新護所提出的強調梵我合一的“喜”,就是要求人們透過物質現實領域的美去領悟精神世界梵的真,這種經驗美和超驗美的和諧統一,是印度獨特的靈肉雙美的藝術風格。
同時,新護受印度吠檀多“不二論”影響很深。吠檀多“不二論”分“不二一元論”派、“制限不二論”派以及“二元論”派,三派中的“不二一元論”派是主流學派,主要觀點為“梵我不二”,即梵與“個我”合一。新護認為,好的藝術作品可以使讀者實現“梵我合一”的境界,很明顯與“不二一元論”相符合。可見,在美學層面,印度始終貫穿靈肉雙美的思想追求。由此,“喜”作為融合了傳統美學思想的核心概念,強調“不受阻礙的藝術感知”,能使欣賞者“不厭倦和不間斷地沉浸在享受中”,始終追求一種在有限之中達到愉悅的無限境界。
(二)中國美學——“逍遙”
吠檀多派將世界的本源和終極都歸于“梵”,道家則認為世界的根基是“道”。在本體論上,二者達成了一致。新護以“不二一元論”為核心,認為藝術的最高境界乃是“梵我合一”的“喜”。在道家思想中,同樣強調與道合一的是“逍遙”。莊子提出逍遙的核心是“無己、無功、無名”之后的“無所待而游于無窮”,這是一種與道合一,精神與身體都絕對自由的境界,要達到這一境界,須“心齋”“坐忘”。
莊子所謂的“心齋”即“虛靜”,是認識和審美的心理要求和狀態,指排除內心雜念之后的大清明。“坐忘”即忘卻外物,忘卻自我,心物無二,物我合一。“心齋”“坐忘”的實質都是擺脫身心欲求,保持心靈自由,通過主客一體的渾融進入審美狀態,這是創作者和欣賞者都應該具備的審美態度或修養方式。如此之后,“物物而不物于物”“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最終實現有限人生的無限自由。中印美學在物我合一這一概念上達成的一致令人贊嘆,他們皆看到人生活中物質與精神的二元存在,也共同強調對二元世界的融合,既肯定現實美,同時,又追求精神的超越,這種和諧之美是中印兩國共同追尋的美學精神。但印度走向了神秘的超驗世界,而中國走向了現實的藝術。
四、結語
印度文藝思想成就很高,但探討印度文化或美學所能依據的文獻資料斷續不全,集成的著作一出,零散的前驅就散失。因此,無法對印度美學做全面系統的了解。但本文選取的這三個美學概念,作為印度美學的核心概念,資料相對豐富,因而筆者才能與中國文論對照,在彼此關照中,發現中印兩國不同又相似的美學特質,為東方詩學提供一些有意義的內容,豐富東方文論的研究。同時,在與西方文論進行對比研究時,也能更好地找準定位,樹立理論自信,建立東方文論體系。
參考文獻:
[1][2][5]曹順慶,主編.東方文論選[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3]尹錫南.梵語文藝理論家新護對《舞論》戲劇論與樂舞論的闡發[J].南亞研究季刊,2020(02):62-68+100+5.
[4][元]陳澔,注.金曉東,校點.禮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6]黃寶生.印度古典詩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作者簡介:張明月,女,碩士研究生在讀,天水師范學院,研究方向:文藝學)
(責任編輯 劉月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