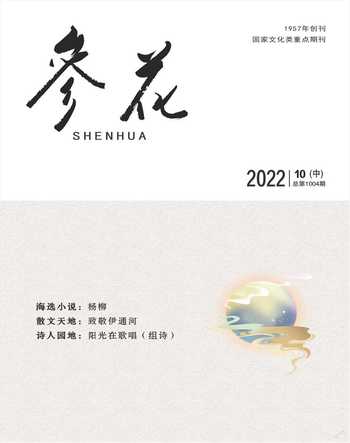論小說《紅高粱》的跨媒介改編
“媒”,《說文解字》認為,“媒,謀也。謀合二姓”,后引申為事物發展的誘因。“介”在甲骨文中指鎧甲,后演變為介于兩者之間。“媒介”一詞,魏晉經學家杜預為《春秋左傳正義·桓公三年》中“會于嬴,成昏于齊也”作注時,提出了“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指使雙方發生關系的人或事物。后在《舊唐書·張行成傳》中再次出現,含義與之前一致。可見,“媒介”即是訊息送達受播者途中的工具或方法。“跨媒介”又稱跨平臺,跨平臺是實現跨媒介敘事的基礎,它能為敘事提供不同的呈現方式,也能為受眾提供更多的討論空間。跨媒介敘事由亨利·詹金斯在《融合文化》一書中提出,經多年的補充完善,逐步發展成一套成熟的敘事理論體系。跨媒介敘事是一個故事橫跨多種平臺的展現,每一個媒介都對整個故事進行創新,使故事具有更加立體、多元的討論空間。
《紅高粱》是莫言的代表作品,這篇小說蘊含多種紅色意象,而“紅高粱”作為小說中的典型意象,是地域文化符號的表現。小說采用意識流敘事手法,跳躍式地呈現一個一個的魔幻現實主義場景,強烈刺激了讀者的感官,為訴諸視聽的多種媒介改編提供了創作空間。隨著大眾媒體的發展,電影、電視劇、戲劇等版本的《紅高粱》逐漸出現,使文本解讀更加多樣。《紅高粱》作為文學文本,經過不同媒介的改編使其成為莫言作品中跨媒介制作和傳播的經典文本,就傳播廣度、發掘深度和藝術高度而言,此作品的跨媒介改編值得深入探究。
一、電影版《紅高粱》
電影《紅高粱》改編自莫言的同名小說,糅合了《高粱酒》中的部分情節,由張藝謀執導,姜文和鞏俐擔任男女主角,榮獲了金熊獎。張藝謀導演的《紅高粱》呈現出了“純、簡、極致”的影像風格。“純”:將男女主角復雜的愛情提純為美麗童話。“簡”:簡化時代背景,刪減次要人物。“極致”:將情感發揮到極致。影片以“中國紅”為特色,具有強烈的象征性,象征民間的喜慶熱鬧和中華民族蓬勃的生命力。影片中的紅嫁衣、紅花轎等物化符號建構出一個被紅色暈染的空間場景,身處這一空間下的人物心理狀態也被凸顯出來,紅色高粱和紅色火焰將人物的歡快、躁動和悲憤情緒外化,表現了人物與命運抗爭的殘酷性,給觀眾造成強烈的視覺沖擊,具有民俗審美趣味。在這一片由紅色高粱浸染的場景之中,老百姓旺盛的生命力得以迸發,張藝謀由此譜寫了一首張力十足的生命贊歌。影片《紅高粱》作為首次對小說進行再創作的作品,直接影響了后來的戲劇和影視改編。
二、電視劇版《紅高粱》
2014年10月,《紅高粱》電視劇登上了影視舞臺,宏大的故事情節、復雜的人物關系等使導演以《紅高粱家族》為參照進行改編,重點選取《高粱殯》來擴充情節,將小說的寫意敘事轉換為抗日敘事,將男主戲轉化為以九兒為主的女主戲,“紅高粱精神”由男性的雄渾遒勁轉變為女性的柔韌剛強,九兒與余占鰲的愛情被調整為兩個個體間的相互征服。此改編作品塑造了“女主角”九兒,情節緊湊,滿足了觀眾對影視劇充滿戲劇性的審美需求。此外,電視劇將故事場景由影片中的黃土地置換為小說中的高密東北鄉,搭建了古色古香的單家大院、單家酒窖等場景,增加了代表傳統的單家大奶奶這一角色,其與九兒展開了一系列明爭暗斗的故事。兩院之間的空間對峙,使九兒與大少奶奶的性格凸顯出來,并形成強烈對比,更具商業性。
可見,電視劇《紅高粱》的改編策略是符合跨媒介改編特質的成功演繹的,但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俗化改編,譬如九兒與大少奶奶的宅斗內容過多,占全劇的五分之三,削弱了文本的藝術性。
三、紀錄片《高粱紅了》
紀錄片《高粱紅了》記錄了電視劇從拍攝到殺青的所有事情的經過,如購買版權、拍攝過程等,記錄了電視劇詳細的制作過程。它與尋常紀錄片的不同之處在于,其對真實發生事件的戲劇化安排,既滿足了觀眾的需求,又達到了解構電視劇的效果;它又不同于拍攝花絮,《高粱紅了》具有完整的敘事單元,超出了花絮的敘事容量;它還不同于宣傳片,宣傳片是在影視劇播出前,制作方用來造勢、吸引觀眾的短片,包括重點情節、故事懸念等,不涉及過多的幕后制作的細節。這種嶄新的影視類型,更適合依托于中長篇的歷史題材電視劇,或是擁有龐大粉絲群的大IP改編作品。這樣,紀錄片節目就有了眾多可解密的內容,能夠引起觀眾強烈的興趣。《高粱紅了》作為國內電視劇史上第一個真人實際紀錄片,具有特殊的審美娛樂價值,它既發掘了電視劇敘事文本的娛樂功能,又滿足了觀眾二次觀看的喜好,豐富了觀眾在觀看電視劇外的娛樂體驗。但其作為一種新興的影視樣式,還有待成熟,可以視為紀錄片與真人節目的粗糙結合,因此,其價值有待考量。
四、戲劇版《紅高粱》
(一)舞劇
由小說《紅高粱》改編而來的舞劇共兩部:1988年王舉的《高粱魂》和2013年王舸、許銳的《紅高粱》。
王舉的舞劇分為顛轎、野合、祭酒神、序和尾聲五塊,每一塊均為獨立的“意象單元”,呈現出大跨度跳躍的“組舞式”結構,從人的生命欲望出發,交織著“人”“神”“魂”三個生命主題,“既有強烈的現代意識又有濃郁的民族風格和北方地域文化的特色”。王舸、許銳的舞劇比王舉的舞劇多了三個場景,正是這多出的場景,融入了歷史背景,使劇作主題由個人“小義”升華為民族“大義”,歷史感更為厚重。全劇最具視覺沖擊力的當屬群像之舞,融合了山東鼓子秧歌、膠州秧歌和生活基本體態,是舞劇最突出的“表意”機制。但舞劇作為戲劇的一種,還要完成寫意之外的故事敘述,王舸和許銳在“大表意”的群像中穿插了一些生活化的“細寫實”,如性格化的造型、“跑驢”等民俗細節,這種“大表意”與“細寫實”的交融,使舞劇《紅高粱》成為一部優秀作品。但舞臺表演也有其弊端,如對復雜情緒的牽強呈現、浮夸的肢體動作等,反而限制了舞劇的表現力。
(二)晉劇
晉劇《紅高粱》不再將小說文本中的倫理感情作為敘事核心,劇作將余占鰲、羅漢、九兒定為青梅竹馬的三角關系。晉劇《紅高粱》吸收了民間舞蹈的表現體態、蒲劇和梆子戲等表演程式,如九兒的“站椅子”、用“踩轎”表現“跑驢”,雙人舞展現男女主的野合等,既推動了情節發展,又突出了人物形象。劇院采用三維技術,用LED屏打造出漫山遍野的紅高粱和奔騰直下的黃河水的場景,舞臺極具現代特色,滿足了觀眾的視覺審美期待。以上融合了多種藝術門類的全新表現手法,使現代戲劇取得了創造性的突破,為傳統戲曲的現代化轉換提供了一個新的方向。晉劇對《紅高粱》的二次創作,可謂大醇小疵,雖有創新,但削弱了九兒和余占鰲之間充滿野性的叛逆精神和生命張力。
(三)豫劇
豫劇《紅高粱》開場以抗日為大背景,以男女主角的愛恨情仇為故事發展的主線,敘述了農民英雄反抗侵略者的事跡。為適應豫劇的藝術表現形式,導演將故事發生地改為豫西地區,將余占鰲更名為“十八刀”,身份設置為草莽英雄。九兒的身份變為草臺戲班的女演員,并融入扈三娘的扮相。在劇中,九兒被賣給麻風病人單扁郎,經十八刀解救后互生愛慕之情,結為連理。抗日戰爭爆發后,二人義無反顧地帶領全體鄉親抗日,最終犧牲。其中,二人互訴衷腸和壯烈犧牲的場面感人至深,呈現出了震撼的藝術效果,尤其是九兒著扈三娘戲服演唱“靠山吼”的場面,象征著人物對悲劇命運的強烈反抗。劇中血海似的高粱地、酣暢淋漓地喝酒的場面等呈現了一場豐富的視覺盛宴,再加上豫腔特有的唱法,使劇作更具感染力。
(四)評劇
評劇《紅高粱》采用倒敘手法,開場就將抗日英雄們慷慨赴死的悲壯畫面呈現了出來,奠定了戲劇的格調。整部劇以鮮艷的紅色大色塊鋪呈開來,動態的紅高粱、紅嫁衣等紅色道具構建出具有生命力的色彩世界,紅色意象被運用到了極致,“接通了文本、地域、民族與戲曲審美的通道,在當代戲曲舞臺上成為無可替代的唯一”。化用舊程式,創造新程式,塑造了剛烈嫵媚、充滿野性的新女性形象。評劇還糅合了《檀香刑》中的行刑場面,將劉羅漢被行刑這一場景進行立體呈現,成為戲劇化特色舞臺的一個重要呈現途徑。導演熟練運用“小仔兒”這一串場人,為整部評劇無序的“意識流”結構建立情感邏輯秩序,使文本與舞臺的“碎片”和“定格”在情感緯度上得到統一。這使觀眾獲得了強烈的審美體驗,也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文本的戲劇化特色。此評劇是文本、舞臺和表演效果的有效統一,是《紅高粱》小說戲劇改編的絢爛樂章。美中不足的是,評劇中男性旁白語調怪異,紅高粱地和法場的舞臺場景布置奇巧不足,笨重有余,這與舞臺的固定、有限性有關,顯得拖泥帶水。
(五)茂腔戲
茂腔戲《紅高粱》以茂腔為主,既采用高密方言,曲調質樸自然,又融合京劇、話劇等多種劇種,具有多樣化性。全戲共八場,如抗婚守身、心心相印、羅漢救友、復仇烈火等,集中展現九兒、余占鰲和劉羅漢之間的三角戀關系及眾人的抗戰故事。劇作采用茂腔特有的表演技巧和傳統的唱腔風格,運用原板、搖板等多種板式,加入山東快板、順口溜、現代音樂等,極具舞臺效果,戲劇演員優美的身段和融入現代音樂的唱腔,帶給觀眾極強的視聽沖擊力,建構出更為立體的戲劇空間。不足之處在于導演為迎合觀眾的審美期待,將厚重的《紅高粱》變成了通俗的愛情戲,淡化了戲劇原有的表現力。簡而言之,以上五種戲劇對《紅高粱》的再創作,各有特色,豐富了小說文本,但白玉微瑕,也頗需注意,在當下,更要警惕戲劇向市場過度靠攏的趨勢。
五、戲劇電影版《紅高粱》
劇作改編自《紅高粱家族》,全劇自始至終貫穿著茂腔戲,包括九兒被顛轎前后的哀怨無助、洞房前后的無可奈何、回門路上的為愛吶喊和為羅漢報仇之際的聲嘶力竭,演員們以婉轉幽怨、質樸自然的高密茂腔進行演唱,極具感染力。同時,還融合了多種現代流行音樂、童謠的唱法,為傳統茂腔唱腔增添了不少色彩。并介入電影技術,呈現了單家大院、十八里坡民俗村等場景,打破了戲劇原有的舞臺限制,擴充了戲劇的敘事時空,增強了演員的語言表達能力,將“戲”與“影”的美學風格相貫通,使影片的趣味性和觀賞性有所增強。與珠玉版的電影《紅高粱》相比,茂腔版的《紅高粱》將高密市兩大瑰寶“茂腔”和“紅高粱”糅合在一起,洋溢著濃郁的本土氣息。茂腔戲作為一種小眾的藝術形式,對觀眾本身的品位、藝術感知能力有著較高的要求,觀眾需要具備一定的藝術鑒賞能力,此電影打破了這種限制,促進了傳統戲劇的傳播。可見,這是創作者在茂腔戲和電影《紅高粱》基礎之上的再創新,吸收了二者為觀眾所樂道的長處,不失為一部優秀的改編作品。此外,戲劇電影版《紅高粱》雖是一部創新之作,但影片將余占鰲和九兒曲折的愛情故事作為核心,占據全劇情的四分之三,對部分細節處理得不夠細致,尤其是顛轎這一情節,淡化了抗日大背景,不免落入了俗套之中。
六、結語
小說《紅高粱》作為一部經典作品,自發表至今,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劇、紀錄片、戲劇、戲劇電影等多種作品,這些改編作品將小說文本引向了多種媒介領域,每一次闡釋,既是對原著的再解讀,又是藝術的再創造,呈現出了不同的敘事特征,使《紅高粱》這一作品愈加趨向立體化。通過梳理和比較不同媒介對《紅高粱》的改編,發現在當前的市場和技術水平下,其改編質量參差不齊,也做出了一些突破性嘗試,既有對小說文本的呈現、創新,也有對其的遮蔽。這樣的跨媒介敘事理論實踐,彰顯了優勢,也暴露了不足。隨著這一理論的發展,未來將會出現更多經典作品的跨媒介改編,《紅高粱》不失為一個可借鑒的先例。此外,跨媒介敘事理論的發展領先于實踐,文學作品的跨媒介改編仍有很長的道路要走。
注釋:
①周詩蓉:“魂”驚四座,舞蹈,1988年,第11期。
②彭維:“濃墨重彩”推動場面變形與結構流動——以評劇《紅高粱》為例,戲曲研究,2019年(02),第79頁。
參考文獻:
[1]莫言.紅高粱家族[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
[2][挪威]雅各布·盧特.申丹,校.小說與電影中的敘事[M].徐強,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3]張智華.電視劇敘事藝術研究[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1.
[4]戴錦華.電影理論與批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
[5]劉晶.敘事學視野下《紅高粱》的改編研究[D].中國藝術研究院,2016.
[6]周詩蓉.“魂”驚四座[J].舞蹈,1988(11):45-
47.
[7]彭維.“濃墨重彩”推動場面變形與結構流動——以評劇《紅高粱》為例[J].戲曲研究,2019(02):73-87.
[8]周安華.論當代中國戲劇的電影化傾向[J].文藝研究,2002(05):92-100.
★基金項目:本文系天水師范學院2021年
研究生創新引導項目(項目編號:TYCX2143)
的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豆盼盼,女,碩士研究生在讀,天水師范學院,研究方向:文藝學)
(責任編輯 劉月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