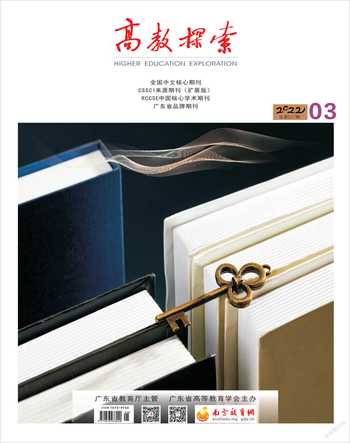祛魅與治庸:博導“放羊”現象治理路徑研究
林靖云 劉亞敏 杜學元
摘 要:在博士生教育生態系統中,博士生導師是博士生教育質量的重要供給者和關鍵性影響因素。然而,囿于制度、權力與熟人社會,源于封建官僚體系的懶政、尋租和庸治歷史鏡像般投射到博士生教育領域時,便生成了博士生導師的“放羊”行為。當個體行為成現象級呈現,必將造成重大公共影響,不僅會引發博士生教育質量下降、國家教育資源浪費的原生危害,還會演化出諸如學校管理壓力、師生關系異化、博士生精神健康風險等次生危害。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應從博士生導師制度著手,制度祛魅與程序治庸雙管齊下,改革和創新博士生導師制度,以制度規塑博士生導師的指導行為。
關鍵詞:博士生導師;“放羊”現象;博士生導師制度;治理
一、問題的提出
博士生教育關乎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博士生教育質量不僅是評估一個高校、一個學科建設水平的重要指標,更是衡量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質量及國家競爭力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在博士生教育生態系統中,博士生導師是博士生教育質量的重要供給者和關鍵性影響因素[1]。博士生需要經過嚴格和系統的學術訓練以獲得從事學術研究所需的基本素養和技能,完成從學生到研究者的角色轉換和專業社會化。在這個過程中,博士生的讀博體驗、學術能力的提升以及是否能順利完成學業等都與博士生導師的指導行為密切相關。導師的指導行為具有教育、生產、支持以及管理功能,一個導師能夠培養出一個博士,也能毀掉一個博士。[2]博士生導師對博士生的影響如此直接而強烈,因此,要檢討博士生教育質量,除了要考慮誰來辦博士生教育、誰有資格攻讀博士學位,還必須考慮誰有資格指導博士生。[3]《關于開展博士研究生教育綜合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2017年)、《關于加強博士生導師崗位管理的若干意見》(2020年)和《關于加快新時代研究生教育改革發展的意見》(2020年)從嚴格規范質量管理、加強博士生導師崗位管理、全面落實育人職責三個維度對博士生導師提出了要求,博士生導師隊伍治理已然成為國家行動。在這一改革指向中,博士生導師不僅是新一輪博士生教育改革政策的具體執行者,同時也是改革的推動者和保障博士生教育質量的中間力量,這注定他們無可避免地將扮演有著內生矛盾性的雙重角色。一方面,博士生導師的身份決定了其必然成為新一輪博士生教育改革的重要參與者,具體執行旨在提高博士生教育質量的相關政策,并參與嚴格規范質量管理的全過程;另一方面,博士生教育屬于尖端精英教育,在博士生教育治理中,被遮蔽的部分博士生導師指導行為的懶政、博士生導師管理中的庸治和現有博士生導師制度的缺陷日益凸顯并亟待治理,這使得博士生導師也應然成為新一輪博士生教育改革的重點對象。
伴隨著博士生教育改革的深化,博士生導師的指導行為日益受到學界的關注。現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博士生導師的指導模式[4][5]、指導行為的內容[6]、指導行為的分類[7][8][9][10]以及導師指導頻率對博士生培養質量的影響[11]。博士生導師的指導行為,不僅是“良心活”,更應該是專業化的“技術活”。然而,在博士生教育實踐中,有部分博士生導師對博士生采取“放羊型”指導,使得博士生入學即開始處于無序的“放養”狀態,博士生因得不到有效指導,學術能力難以提升,專業社會化實現之路異常艱難。這種“放羊型”的指導行為讓博士生反感,卻又囿于導師的學術權力和深植于心底的尊師重教的道統以及申訴救濟機制的不健全而無力反抗,成為沉默的“羔羊”。現有研究文獻中只有一篇論文對博導與博士生之間的“放羊型”互動進行了簡單描述:師生終年難得見一面,倘若學生不主動聯系導師,彼此交流機會就非常少,由于導師忙于自己的事務,來去匆匆,學生很難找到與其面對面互動的機會,即使交流,也只是短暫的寒暄,缺乏實質性指導內容。[12]該論文并未對這一具體指導行為類型進行深入探究,而在百度和知乎社區輸入“博導‘放羊’”“博士生被‘放養’”,卻出現了數以千計的討論貼和回答。關于博士生導師指導中的“放羊”行為,出現了社會普遍關懷而學術研究爆冷的局面。為了提高博士生教育質量,各個博士生培養單位在嚴把博士生招生“入口關”和“出口關”的同時,紛紛實行博士生中途分流機制。但若只在博士生一方著力,而不把握博士生教育質量的關鍵點,放任博士生導師的“放羊”行為,不僅有失教育公平,而且勢必催生“劣幣驅逐良幣”的畸像,寒了天下學子的心。聚焦博士生導師指導行為中的“放羊”現象、探索其治理路徑,對深度回應社會關懷、推進新一輪研究生教育改革和提升博士生教育質量具有重要意義。
二、從“行為”到“現象”:博導“放羊”的公共影響
博士生導師指導中的“放羊”行為看似是博士生導師的個體行為。然而,當這種“放羊型”博導達到一定的數量,個體行為成現象級呈現,必將造成重大的公共影響,這是由博士生教育自身的公共性所決定的。博士生教育位于國民教育體系最頂端,博士生導師是博士生培養質量的第一責任人,肩負著培養國家急需的各種高精尖人才的重任,責任不可謂不重大。所以,博士生導師的指導行為,并非一己私事。博士生導師指導中的“放羊”行為,其本質是失職行為,是一種極端不負責任的表現。博導“放羊”不僅會引發博士生教育質量下降、國家教育資源浪費的原生危害,還會演化出諸如學校管理壓力、師生關系異化、博士生精神健康風險等次生危害。
(一)原生危害
1.博士生教育質量的下降
博士生導師是影響博士生教育質量的關鍵因素。國家對全國博士生教育改革實施權威性的、政策性的宏觀調控,各高校則循序漸進地推進、實踐和反饋,保障政策的良性運行。在此過程中,政府和高校為教育利益而博弈。博士生導師是學校與博士生之間的中間力量,是政策的踐行者和推動者,其“放羊”行為會直接影響博士生的專業社會化過程。博導的責任,是根據博士生的個性特征和研究興趣為其制定培養方案,有計劃有步驟地把博士生培養成高、專、精、尖的人才。博士生需要在導師的指導和幫助下,掌握研究問題的思路和方法,找到研究問題,創造出新知識、新理論。“放羊”型博導忘記了自己的責任擔當,扭曲了博士生的培養邏輯和原則,使博士生的學術能力難以得到應有的提升。此種“放羊”行為實質是一種消極怠工和教育責任感缺失的表現,是性質惡劣的行為失范,破壞了博士生教育的學術環境,損毀了博士生教育的精神基礎。博士生有權利接受公平而有質量的博士生教育,而這種極端不負責的“放羊”行為,恰恰破壞了教育公平,導致博士生教育質量的下降。
2.國家教育資源的浪費
導師指導也是影響博士生的修業年限和流失率的重要因素。獲得導師良好指導的博士生能夠獲得更高水平的個人專業發展。反之,博士生導師的“放羊”行為會消解博士生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術熱情和繼續從事學術職業的信心。有的博士生對導師的學術水平和指導能力感到失望,但由于制度的缺失或不健全無法或不敢更換導師,又沒有足夠的自信能夠獨自摸索完成學業,感覺前路迷茫,產生自我放棄的想法,申請退學以便及時止損或等著修業年限到了被學校自動清退。還有的博士生入學時躊躇滿志,但因為得不到導師的有效指導和幫助,學術能力長期得不到提升,自信心受挫,論文寫作陷入困境,無法如期畢業。據測算,2019年我國博士生分流退出人數已上升至0.79萬人,而博士生學業延期的人數達到13.67萬人。[13]分流與延期,是提升博士生培養質量的有效手段,但占比過多,會造成辦學資源的占用和教育成本的增加,導致國家教育資源的浪費。
(二)次生危害
1.學校管理壓力的增加
進行系統的學術訓練是博士生專業社會化過程中必不可少的環節,博士生需要通過適當的學術訓練來為學業的順利完成做準備,科研任務過重或學術訓練的缺失都有可能會阻礙博士生的學業完成。[14]“放羊”型導師對博士生的科研訓練與管理的缺失,直接影響博士生的專業社會化。按學制預測,2017年全國應畢業的博士生數15.8萬人,實際畢業人數為5.6萬人,未正常畢業者占64.6%;2019年博士應畢業生數177884人,但實際畢業的博士生僅占到35.18%。[15]延期不僅對博士生個人來說是巨大的損失,逐年累積的延期博士生,對博士生培養單位也是一種考驗和壓力,在培養成本增加的同時,也面臨著管理工作增加的壓力,延期博士生在校學習需要宿舍、圖書館、食堂等公共資源,造成了某種程度上的對正常學制內學生的資源的擠占,為了協調其間的矛盾,學校需要投入更多的資金、設施和人力資源。
2.師生關系的異化
博士生導師與博士生之間的指導關系實質上是一種權力關系。福柯(Michel Foucault) 認為,知識即權力,兩者的融合使“話語”的作用得以凸顯,從而形成話語權力。在教育的表層權力網絡中,教師是規訓者,學生是被規訓者[16],在規訓機制中,教師通過規范化、可視性、懲戒與獎勵等途徑進行權力實踐,權力關系塑造著師生互動,影響著師生之間的關系。博士生導師和博士生之間事實上也存在著這種權力與身份的差異。博士生從導師這里傳承學術思想和促進導師的學術流派的形成。亦所謂“從我學者為我學生,不從我學者不是我的學生”。[17]在博士生的學術社會化過程中,博士生導師應當扮演學術顧問、信息提供者和研究合作者的角色,給與學生學業上的指導,這是對博士生導師這一角色的最本質性定義。[18]從博士生的角度出發,他們會希望導師在自己的研究領域有著較好的研究基礎、提供資助參加高級別的學術會議以了解本領域的前沿研究動態、定期召開組會以便及時交流溝通大家的研究進展、能夠有時間指導自己并在討論之前認真閱讀自己的研究計劃或學位論文以便提出實質性的建議。但是“放羊型”導師往往無法滿足博士生的這些需求,他們采取放任不管的態度,不對博士生選題的可行性進行把關,也不對博士生提出的問題給予及時反饋,更不提供必要的經濟資助,沒有在博士生的學術進階之路上發揮應有的引導性作用。博士生會因為博導沒有給予指導和提供開展研究所需的支持而對博導心有怨言,但囿于制度的缺失或不完善,不能或不敢更換導師。師生關系陷入異化困境,導致師生之間信任度低,關系疏離甚或對立。
3.博士生精神健康風險
Baker和Lattuca曾對博士生專業社會化的支持主體進行研究,并利用發展網絡理論(Development Network Theory)對之進行分析,認為學術組織中的導師、合作者與學術組織外的家庭、朋友共同構成了博士生的發展網絡,影響著博士生的專業社會化。[19]基于《自然》公布的2019年博士生調查數據,我國博士生曾因焦慮或抑郁尋求幫助的比例高達40%。[20]與其他博士生相比,被“放羊”的博士生的社會支持系統缺乏關鍵性的一環——導師的支持,在片面強調發表的學術文化影響下,他們面臨著更嚴酷的學術處境。長期處于無序的被“放養”狀態的博士生們,由于缺乏正確的指導和系統的學術訓練,學術能力得不到應有的提升,在論文寫作和發表方面會面臨著更大的困難,導致自信心不足、自我評價低、學業進展緩慢。學業壓力是被“放養”博士生的關鍵性壓力,并且是引發抑郁的危險因素。壓力累積到一定程度,會出現情緒衰竭和個人目標成就降低等癥狀,自信心不足,容易自我否定、自我懷疑,加之對未來不確定性的焦慮,他們面臨著高抑郁風險,時有輕生、自殘等極端事件發生。
三、制度、權力與熟人社會:博導“放羊”行為的生成機理
博士生導師的“放羊”行為是多種因素交織的產物,但本質上都可歸因為缺乏職業敬畏感、濫用學術指導權力,而權力濫用的根源,除卻個體因素外,更多在于培養單位現有的制度缺失或不能有效制約。[21]當有人將博士生導師資格視為一種教授級別中的至高榮譽而忘卻了這稱謂背后的責任的時候,制度性“不失去”遮蔽下的“懶政”、學術“官本位”下的權力尋租與熟人社會文化生態中的庸治成了博導“放羊”行為產生的溫床,當個體行為成現象級呈現,便生成了博導指導行為中的“放羊”現象,并日益成為當前博士生教育質量治理中的突出問題。
(一)制度性“不失去”遮蔽下的“懶政”
博士生導師制度是一項為了開展博士生培養工作、確保博士生教育質量而專門設立的基本制度,主要包括博士生導師的選聘、責權與考核,與博士生教育質量的高低密切相關。我國自1961年制定“高教60條”,并開始實行指導教師負責制。1981年我國恢復了學位制度,但很少有教師具備擔任博士生導師的資格,遂決定在教授中選拔一批博導,由國家統一評審,以國務院的名義任命,享受學部委員的待遇(介于教授和院士之間)。此后,雖然審批權下放了,但從教授中遴選博導以及享有高于教授的地位和待遇卻被當做慣例而一直沿用。如無特殊情況,一般終身聘任直至退休。博導在眾人眼里成為一種層次和榮譽的象征,成為許多大學教師終其一生努力追求的最高職業目標,但由于沒有明確的退出機制,博導隊伍缺乏良性競爭,問題也日益凸顯:有的教師自從選聘上博導,覺得已經站在了“山頂”,沒有奮斗目標了,加之缺乏競爭機制,動力不足,不再學習新理論、新方法,不關注前沿熱點,知識結構得不到及時更新,學術水平停滯不前,無法為博士生提供有效的指導,影響博士生的培養質量;有些博導因為沒有競爭的壓力,沒有被“下崗”的風險,逐漸喪失了進取心,不申請課題,不寫論文,淪為“三無”博導(無課題、無經費、無成果),無法為博士生提供必需的學術資源,不利于博士生的學術進階之路。我國大多數高校缺乏博導退出機制,在大家的意識里,博導資格是終身制,是一頂摘不掉的“帽子”,能上不能下,導致一些學術創新能力強的年輕學者因為資歷和職稱所限被阻擋在博導隊伍之外。這不僅導致博士生導師隊伍的結構老齡化,還引起了部分博士生導師指導行為的“懶政”,成為“放羊者”。
(二)學術“官本位”下的權力尋租
“官本位”觀念,即以官員的價值訴求和利益需要為衡量標準和行為取向,唯官是重,唯官是大,具有天然的優越感,這是源自封建社會官僚體系的文化傳統和社會慣習。當它以一種歷史鏡像投射到高等教育領域時,這種功利性價值追求便催生出學術界僵化的分等定級和愈演愈烈的大學“官本位”趨勢。
教授和博士生導師質量的高低是衡量一所高校學術水平高低的一個重要指標。他們本應該是學科建設的領頭羊、高精尖人才的培養者、優良學風和校風的建設者和示范者、大學學術聲譽的創造者和傳播者。但是博導頭銜被作為一種利益,成為了權力的博弈對象,引發了行政權力對學術權力的僭越,滋生了學術腐敗行為,出現了“搭車”當“博導”的亂象。一些行政管理者把持學術資源,壟斷關鍵信息,在博導遴選過程中按照人際和利益上的差序格局分配資源,利用權力進行利益交換和尋租。[22]還有些高校用“博導”資格取悅一些政府官員和企業領導,使“博導”資格赤裸裸地政治化、商品化,出現了權力博導、關系博導、商品博導的現象。[23]沒有博士點的高校、院系的教授,想方設法(時常用的都是不正常手段)到外校、外系搞一個博導頭銜。[24]一些官員“仕而優則學”,通過在職學習的方式,獲得了本科、碩士甚至博士學位,在國家選拔干部高學歷化的趨勢下,他們的官位獲得升級。其中有些高級官員好為人師,想把自己打扮成學者型的領導,高校也想利用官員的權力為學校謀取經濟利益或政治利益,如此,便有了權力的尋租,有的高校把兼職教授送給了高級官員,緊接著,又把博導頭銜送給了他們。[25]為了自己的利益意圖,行政官員通過權力系統進行權力的擴張,通過強勢的權力控制攫取最大化的利益。權力與利益的勾結使高校這一學術重地淪為權力和利益導演的名利場。[26]以官謀學、官學不分,大學的學術組織屬性被侵蝕,尊嚴被踐踏,教學與學術的本真邏輯被扭曲。
導師有相對穩定的科研方向是培養博士生的關鍵。當博士生的研究課題與導師的研究領域相符并形成良好合作時,進步較大并對導師的指導行為感到滿意。但這些通過權學交易、權權交易而獲得博導頭銜的博導們的學術素養和能力參差不齊,加之政務繁忙,無心也無力潛心學術,只把博導這一頭銜當做炫耀的資本、榮譽與地位的象征。博士生的研究領域便是他們的研究領域,博士生的研究成果也自然成為了他們的研究成果。他們因為自身尷尬的學術水平無力指導博士生的學業,或者隨意給出錯誤的指導反而人為地阻礙了學生的學業進程,對學位論文的把關作用更是無從談起。在這種情形之下,誰有信仰和威望引領新人,誰有水平或才情激勵后生,誰有資格或能力指導博士?誰有精力或時間溝通弟子?也就不言自明了。[27]
對官位與權力的推崇,也扭曲著大學內部的價值取向,行政權力尤其是行政官員的作用被過度強調,而教授及其群體的學術權力則經常處于失語或半失語狀態。有一些教授“學而優則仕”,主動或被動地登上了領導崗位,從政之后能者多勞,繼續做教授、當博導。更有些領導在調往其他高校后,繼續在原高校當博導,博士生一年最多見自己的導師兩次:自己的開題或師兄師姐的預答辯/答辯會場,甚至有的導師見面認不出自己學生。雖然頭頂博導的頭銜,但忙碌于行政工作,他們與學術漸行漸遠,也沒有多余的時間和精力用以指導學生,不得不對博士生實行“放養”,博士生的專業社會化以及讀博體驗嚴重受影響。有些滿懷夢想與激情的博士生因為被“放養”而漸漸泯滅了學術熱情。
(三)熟人社會文化生態中的庸治
熟人社會是一種以自我為中心、以關系為紐帶形成的差序格局的社會結構,人們憑借關系的親疏遠近賦予彼此權利與義務,以禮治秩序維護彼此關系。[28]格蘭諾維特提出的測量關系強度的四個維度(互動頻率、感情力量、親密程度和互惠交換)[29]對熟人社會有著強大的解釋力。人與人之間互動頻率高、感情力量強、關系親密、互惠交換多、同質性較高,是熟人社會的典型特征。傳統熟人社會追求人際和諧,強調交往中的差序格局和心領神會,漠視正式規則,默會知識和非正式規則盛行,其組織管理以血緣、親情、地緣關系為依據,以宗法禮教和傳統權威為手段。
現代組織理論強調組織中人的因素,認為組織不單純只是理性系統,同時也是自然系統,組織的運行并非完全依照理性的原則。[30]人性需求需要出口,會以人際關系形成一個自然系統,并以非正式規則將理性系統的部分正式規則儀式化、空心化。現代熟人社會組織既通過各種規章要求來維系等級化的秩序,同時隱性的規范規則又在實際上主導著組織運行,并形成了不同的利益團體[31]。
由于編制問題,大多數高校教師都會在某個高校一直工作直至退休。我國的高校行政管理隊伍沒有像西方一樣實現職業化和專業化,中層管理人員基本只在校內流動輪崗。很多中層管理人員都是本科留校或者入校工作后繼續在本校讀研讀博獲得相應的學位,與本校的學緣關系非常緊密。“工作穩定性”“學緣關系”,構成了中國高校內人與人之間復雜的網絡紐帶關系,高校是典型的熟人社會,與科層組織相融共生。
高校既具有很強的熟人社會的氣質,在治理結構上又呈現出專門化、等級制、規則化和非人格化的科層制特點。科層制的管理模式以明確的正式規則為載體、以追求效率為原則,同時,熟人社會的存在也使大學治理呈現出講人情的特點。熟人社會的本質是人治,通過關系交換和道德制約達到組織和諧。
高校的熟人社會這一組織特征使博士生導師處于立體化的社會網絡中,作為博士生教育體系結構中的重要節點人物,博導擁有多維人際關系。他們往往以朋友、地緣、學緣等關系為聯結進行利益結盟,來保障自己在選聘和考核等方面的利益訴求。被置于高校熟人社會網絡節點中的博導在擁有更多的資源和利益的同時,也要背負更多的人情義務以及維護高校熟人社會的責任。對漸進式的改革范式的認同、以和為貴的大眾心理及大學的熟人生態、根深蒂固的計劃體制思維、深厚的民主傳統、知識分子群體的強烈自尊及崇尚獨立的大學精神、學術本位的大學邏輯等,共同表征為高校熟人社會文化。[32]圈子文化、近親繁殖、學術尋租盛行,易使正式規則儀式化、潛規則盛行、科層制的核心價值被瓦解。一些掌握學術話語權的學者在學術評價上不講規則和原則,反而受利益驅使大搞近親繁殖、發展裙帶關系,形成學術資源壟斷和幫派。在進行導師考核時,因為是單位內部評價考核,被考核者或者是同事,或者是領導,又或者彼此間關系親密,考核時抹不開情面、不敢得罪或有意幫忙,使得博導考核成為人情與面子下的“走過場”約束機制。不完善的導師考核制度,催生了高校熟人社會文化生態中的庸治。庸治的存在,使得有的博士生導師感受不到約束和壓力,放肆地“放羊”。
四、祛魅與治庸:消解博導“放羊”現象的治理路徑
要消解博導“放羊”現象,需從博士生導師制度著手,祛魅與治庸雙管齊下,改革與創新博士生導師制度,以制度規塑博士生導師指導行為,解決因博導“放羊”行為造成的博士生教育質量問題,有效提升博士生培養質量。
(一)制度祛魅
1.實施博導崗位制度,實行動態管理機制
博士生導師制度,其本質應該是一項教育工作崗位制度。長期以來,我國形成了一套嚴格的、較為完善的博士生導師遴選制度,其中與“職稱”的捆綁關系較為固定,一般要求博導必須具備教授職稱。弊端顯而易見:博士生導師資格終身制的制度缺陷,導致優秀的人才“上”不來,能力不足的人又“下”不去,造成博士生導師隊伍的“積庸”流弊。一些高校率先開始進行博士生導師制度改革。2003年,武漢大學“三無”博導“下崗待業”;同年,華東師范大學打破博導終身制;2005年,北京大學以博導崗位的競爭制取代遴選制;2011年,清華大學全面取消博導評聘制度,博導在清華大學不再是榮譽與地位的象征,只是一個工作崗位,從事教學科研工作的副高職稱以上的教師都有資格指導博士生。[33]這些高校改革試點結果證明:放開博導資質,解綁職稱關聯,看起來似乎是放寬了導師的評定資格,實際上競爭越來越激烈了,博士生導師為了搶占爭奪優質生源的先機,盡力提高自身的科研優勢和教學水平。改革博導終身制,破格啟用中青年教師,不僅使導師梯隊的年齡結構更合理,還因此而提高了博士生教育質量。
隨后,不少高校效仿,參考哈佛大學的博士生導師制度,實行博士生導師崗位制度,以便吸納真正優秀的人才到博士生導師隊伍服務于博士生教育事業,并有多所高校在博士生導師動態管理機制方面邁出了實質性的步伐。西南政法大學在2019年和2020年的導師招生資格審查中,分別有20名和10名博士生導師被暫停當年的招生資格。2020年7月31日,華南理工大學啟動第9次導師年度招生資格審核工作。2020年7月29日,首次全國研究生教育會議召開,提出要打造一流的導師隊伍,要深化導師管理的機制體制改革,探索打破導師身份“終身制”。[34]高校的試點,加之國家高度重視博士生教育質量,使得博士生導師改革的問題進入政策議程,最終促成了相關政策的出臺。2020年9月24日,教育部發布《關于加強博士生導師崗位管理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提出健全崗位選聘制度,建立導師招生資格定期審核和動態調整制度。[35]
為了構建結構合理的博士生導師隊伍,各大高校應徹底廢除博士生導師“終身制”,實施聘任制,邁向導師崗位制。此外,為了有效激發博士生導師的工作動能,還可以從以下兩方面著手。一是構建招生資格年審制度。博士生導師的年度招生數量不再固定分配,實行年度申請和審定。由導師提出招收博士生的申請,學校相關部門依據導師的學術水平、研究成果、科研項目、課題經費進行科學評估、審定并確定導師當年的招生數量。這樣不僅能夠使博士生導師保持旺盛的學術熱情,持續地專注于科研,也能夠確保博士生入學后能得到導師提供的學術支持,擁有充分的學術訓練機會和充足的學術資源。二是實行動態調整制度。被選聘為博導后,并不是進了保險箱,仍需定期對博士生導師的教學、科研和指導博士生的效果等進行階段性評審。可以設定5年為一個周期。當博士生導師聘期滿了5年,必須對其是否勝任博士生導師工作再次進行評審。博士生導師的勝任特征由師德與特質、教學與指導、學術與科研、管理與合作等要素構成。[36]一名合格的博導必須師德高尚、學術水平高、指導能力強。評審未通過者,不得繼續擔任博士生導師。這種嚴格的定期反饋可以有效避免博士生導師的“躺平”和“放羊”行為,有助于促進博士生導師的終身學習,實現專業化發展,使導師們始終保持較高的學術水準。
2.構建聯合指導制度,同時堅持主導師責任
除了導師的個體因素,學術指導質量還受導師指導制度安排的影響。到底是單一導師指導有利于博士生的專業社會化,還是接受兩個或兩個以上導師的集體指導更有助于博士生專業社會化的成功?審視全球博士生教育的“從獨立培養到團隊指導”、“從導師主導到多方參與”[37]的變革歷程,聯合指導制度已成為國際趨勢,被公認為博士生學術指導制度的理想類型。
聯合指導制度主要有兩種形式,分別是以美國為代表的以主導師為主的指導委員會制度和以英國、澳大利亞為代表的主導師加副導師制度。在美國,學生通過博士資格考試后,由3-7人組成的論文指導委員會進行管理。博士生的主導師擔任指導委員會的主席,指導委員會的成員中至少要有一位是來自相鄰學科。指導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聽取學習進展匯報,主持綜合考試和論文開題,提供必要的學位論文寫作指導,閱讀論文并給出修改意見,并決定論文是否通過。[38]指導委員會成員在博士論文指導過程中扮演著指導者、評審者、把關人三種角色,主導師負主要責任,論文無需其他同行的評閱。在英國和澳大利亞,學生的博士論文由主、副導師聯合指導,但論文質量需交由其他同行評閱和認定,主導師和副導師并不參與其中。
我國的博士生培養長期以來以單一導師制為主。單一導師制有利于強化導師的指導責任,但這種個人化、封閉性的指導方式日益凸顯出局限性,與博士生培養的開放性與跨學科趨勢相悖[39],對于學生視野的開拓和創新思維的培養顯然是不利的。20世紀80年代后,有些高校開展聯合導師制的改革探索,嘗試采用導師個別指導結合教研室集體培養的方式。2013年,三部委頒發《關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見》,提出要重視發揮導師團隊的作用。高校紛紛響應,開展聯合指導改革試點。到2018年,35.8%的博士生有副導師或第二導師,理工農醫學科的博士生,聯合指導所占比例分別為37.4%、44.8%、38.9%、41.6%。[40]聯合指導制已然成為這些學科重要的博士生指導實踐方式。在人文學科,有些高校強調導師個人指導結合集體指導的方式,但事實上,集體指導形同虛設,博士生的所有科研活動都由導師單獨負責。
實行聯合指導制度,既是我國深化博士生教育改革的應然需要,也是實現立德樹人目標的必然途徑。聯合指導制當前急需解決的是制度化和規范化的問題,需要進行制度設計以便明確導師之間的權責劃分,以及通過相應的培訓來規范聯合指導的形式。要以博士生為中心,以促進博士生學術能力提升和學業完成為目標,構建聯合導師制度。在博士招生環節,當年所有招生名額收歸導師組,不具體分配到各位導師名下。博士入學后,可以在課程學習或實驗室輪轉中了解各位博導的研究領域,發掘自己的研究興趣和研究課題,找尋與自己的志趣和研究方向相匹配的博士生導師,經過博士生與導師之間的雙向選擇,確定主導師。在完成博士課程學習并通過博士中期考核后,學院為每個博士生建立以主導師為主的導師指導小組,對博士生的學習和論文寫作進行監督和管理。導師組應由不少于3位一級學科的博導組成,成員中至少應有一位來自跨學科門類,以使導師組的知識結構更趨合理,不同學術專長者之間形成優勢互補。導師指導小組的職責主要有:每學期開一次會,對博士生的研究進展進行監督;博士生有優先權就課題研究和論文寫作向導師組成員尋求幫助,導師組成員要閱讀博士生的論文并提供必要的指導;主持博士生的開題、預答辯和答辯。
以博士生為中心的聯合指導制度,通過導師組成員共同承擔指導學生的責任和義務,不僅能夠杜絕博導“放羊”行為的發生,還克服了單一指導的弊端,擴大了師生的交流范圍,指導模式由“一對一”變為“多對一”,博士生博采眾長,更易成長為復合型、創新型人才。博士生與導師組成員之間的這種多向接觸,能充分發揮導師團隊在培養博士生中的整體優勢,推動跨學科博士生的培養。但聯合指導制度并非完美無瑕的,存在的潛在問題之一是易造成“責任分散效應”,因責任的不確定性,在聯合指導過程中,導師可能會因為有其他導師的存在而放松自身的指導責任,造成“旁觀者效應”[41];另一個潛在問題是可能會由于多位導師的指導意見存在分歧,使得指導關系緊張。與此同時,博士生也可能會因為要滿足導師組所有成員的指導要求而導致時間上的延誤,給自己帶來困擾和壓力。因此,在實行聯合指導的同時,博士生還必須有一位主導師,堅持主導師責任,明確界定主導師的權責邊界,由主導師在博士生的指導中發揮主要作用。當導師組成員之間意見相左的時候,由主導師根據博士生課題研究的需要,權衡利弊,以最有利于博士生的利益、服務學業完成為目標,做出最終決定。此外,還要構建有利于推廣聯合指導制度的聯合指導文化。博士生指導方式的變革實質上是師生之間關系的重構和導師權力的再分配。博士生與導師之間基于學術興趣的一致性形成聯合的意識,導師之間構建基于學術共治的平等合作關系,這是建立聯合指導文化的關鍵。
(二)程序治庸
1.嚴格選聘制度,遴選合格博導
一流大學離不開一流的博士生教育,一流的博士生教育需要優秀的博士生導師。博士生導師是決定博士生教育質量的關鍵要素。合格的博士生導師是有效指導的前提。《意見》指出,要制定完善的博士生導師選聘辦法,讓更多有責任心、有能力的優秀教師參與到博士生教育中來[42],讓最優秀的人來培養更優秀的人。嚴格博士生導師選聘標準,明晰遴選標準的科學性與合理性,這是構建優秀博士生導師隊伍的基本前提。
師德高尚為首要原則。2018年,教育部頒布《關于全面落實研究生導師立德樹人職責的意見》,明確了導師隊伍的 “高線”和“紅線”,嚴禁師德失范。2020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公布《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以下簡稱《方案》),強調要堅持把師德師風作為教師評價的第一標準,把師德表現作為評聘的首要要求 [43],要“發揮導師言傳身教作用,激勵導師做研究生成才成長的引路人”。[44]2020年10月30日,教育部印發《研究生導師指導行為準則》(以下簡稱《準則》),強調導師要引導研究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增強使命感、責任感,既做學業導師又做人生導師。[45]博士生導師是博士生培養第一責任人。師德高尚的博士生導師會有強烈的內在道德感,并內化為自身的精神需求,率先垂范,以德立身、以德立學、以德施教,注重在日常教學與指導中以自身優良的品德和人格魅力感染博士生,對他們形成潛移默化的熏陶,營造良好的學風,引導博士生們恪守學術道德和規范。師德優良的博士生導師會有強烈的思想引領使命感,并自覺地將之轉化為責任感,以博士生的成才成長為己任,明確自己的職責,以道德來規范自身的指導行為,投入時間和精力于博士生指導工作。師德優良的博士生導師會有明顯的邊界感和秩序感,嚴于律己,不會隨意去觸碰師德禁區、侵害博士生的正當權益。
學術水平是硬指標。在遴選導師過程中,要嚴格堅持學術標準。一個學術水平高的博導的最基本特征是能夠提出好問題,并解決問題。這個可以通過查驗博導是否在有影響力的期刊上持續發表論文以及H指數(所發表最有影響力的論文的引用次數)來進行判斷。除此之外,還應考慮導師的指導能力、指導條件和指導熱情等因素。博導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幫助博士生提出一個有價值且可操作的問題,并啟發他如何進行研究設計,最終有信心獨立地解決這個問題。讀博時間有限,好的博導不會讓學生浪費時間去研究不重要的問題,他會花費足夠長的時間和博士生討論研究問題,幫助他們進行研究設計、分析和解釋數據,指導他們的論文寫作和會議展示,并為博士生的職業生涯發展提出建議。目前的博士生導師遴選制度是以“科研能力”為標準的選拔。毋庸置疑,對于培養學歷金字塔最頂端拔尖創新型人才的博士生導師的遴選,在堅持師德高尚的原則下,以科研成果為重要參照物進行遴選,是一種簡單、高效且相對公平、公正的遴選博士生導師的基礎手段。
2.引入導師培訓制度,提升導師指導能力
好學者未必就是好導師。正如馬克斯·韋伯所言:“具備學者的資格與成為合格的教師,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事情。一個人可以是杰出學者,與此同時也有可能是糟糕透頂的老師。” [46]由于有些高校的博士生導師選聘制度在遴選階段過于注重學術能力,一些初次擔任博士生導師的學者自身理論功底扎實、科研能力很強但由于缺乏指導經驗而指導能力不足,造成無法很好地適應博士生導師角色身份、順利開展指導和管理博士生工作的局面。博士生導師的指導能力,是需要發掘和培養的。英國、瑞典、芬蘭、丹麥等國家,為了提升導師指導能力、保障學術指導的質量,紛紛引入導師培訓制度,初級學者在正式入職前必須參加導師培訓。英國生物工程和生物科學理事會啟動了全國性的導師培訓和認證 (Training and Accreditation Programme for Postgraduate Supervisors, TAPPS) 項目,為導師提供招生、指導技巧、考試評價等方面的培訓。[47]大學還通過舉辦研討會,資深導師分享學術指導的經驗,探討提高指導質量的辦法。
我國也應該引入導師培訓制度,由博士生培養單位對博士生導師開展制度化的專門培訓。通過多種形式,加強博士生導師崗位培訓,提升導師指導能力。培訓內容方面,主要是進行師德培訓和領導力(培養、育人)訓練,使導師了解作為一名博士生導師的角色和責任、行為邊界及違規后果,從而在日后的指導實踐中有所為、有所不為。培訓實施方面,培養單位應該構建常態化、制度化、形式多樣的導師培訓機制。一是要對新聘博導進行崗前培訓。對《準則》等相關制度文件進行政策解讀,輔以博士生教育實踐中的具體問題、典型案例,讓博士生導師明晰指導行為的可為與不可為。二要定期舉辦學院內部的博導論壇。由年度考核優秀的博士生導師現身說法,起到榜樣示范作用,組織本院系的博士生導師們就指導實踐中遇到的困難和具體問題展開研討交流,提升指導實效。三要不定期邀請校內外指導效果佳、反饋較好的優秀博士生導師分享指導故事,傳授有效指導的經驗,發揮傳幫帶作用。四要實施崗位交流培訓。鼓勵理、工、農、醫、法律、經濟、管理等實踐性較強的學科的博士生導師以崗位交流的形式到相關單位部門任職,以便導師們在實踐中提升自己的協同創新能力和指導能力。
3.完善考核評價制度,建立競爭激勵機制
僅憑以崗位制代替終身制的權力“瘦身”對博士生導師進行管理,效果不一定顯著,這種單向的制度“剝奪”會使博士生導師對博士生指導工作產生心理上的抵觸情緒,無法從根本上消除“放羊”現象,還可能會使“放羊”行為以新的更隱匿的形式出現。因此,完善博士生導師考核評價制度、建立有效的競爭激勵機制對于預防和抑制博士生導師“放羊”行為的滋生和變異至關重要。
首先,完善考核評價制度,強化指導有效性。博士生導師考核評價制度具有外在的促進作用,能促使導師重視博士生培養,激發其指導工作的主觀能動性。當前對博士生導師的考核評價,大多數高校都把科研作為考核的側重點,對指導博士生情況的考核,要么沒有,即便有,也是流于形式。故而有的博士生導師并未將指導博士生當做自己的主要職責,導致對博士生的指導不夠。《方案》提出要改革教師評價,推進踐行教書育人使命,堅持把立德樹人的成效作為根本標準,克服重科研輕教學、重教書輕育人等現象,全力構建潛心教學、全心育人的制度。[48]《意見》提出要“將政治表現、師德師風、學術水平、指導精力投入等納入導師評價考核體系。”[49]這些改革風向標,不斷將博士生導師的評價體系要求推上了新高度。因此,有必要構建多元考核體系并完善考核標準。一方面,考核范疇除了課題項目的等級和數量、科研成果的水平和多寡等指標外,指導博士生情況也應該作為一個重要的考核指標,具體包括三個方面:指導工作量(指導學生數、指導次數、指導頻率)、指導過程(交流方式、溝通內容)和指導效果(博士生發表的論文、成果的水平,博士生的精神成長、博士生對指導行為的滿意度)。例如,將博士生學位論文盲審和抽檢結果以及延期畢業生數納入博導的考核體系,將博士生的畢業結果與博導的績效考評、職稱評定、來年的博士生招生名額等掛鉤。另一方面,給學生賦權,通過開展匿名評導師活動,以及畢業生評價導師制度,既能避免當下矛盾又能解決長遠沖突,使導師不敢“放羊”。將對博導的考核評價制度化和規范化,不僅可以促使博士生導師努力提高指導水平、提供有效指導,還可以促進良好導生關系的構建。
其次,建立有效的競爭激勵機制,激發內生動力。實行優勝劣汰的競爭制度,這是構建結構合理的博士生導師隊伍的關鍵。培養單位應建立一系列合理、清晰的規章制度,幫助導師實現自我規范,從而降低博士生導師不作為的可能性。任何制度都具有一定的預防性,制定制度的目的不是為了懲戒而在于預防。制訂相關制度時,主要以指導過程中導師的指導行為表現為依據。如實行博士生指導獎勵制度、優秀博導評選制度等,并根據考核結果獎優懲劣。同時,輔以合理的競爭制度,如招生資格年度審核制度,將在讀博士生數、指導條件、指導效果與博導的當年招生資格掛鉤。《意見》提出,要建立招生資格定期審核和動態調整制度,對于未能有效履行崗位職責、不適合繼續指導博士生的導師,要求及時退出導師崗位。[50]培養單位要強化政策的引領和導向功能,對考核獲得優秀者給予表彰或津貼獎勵,招生指標要向指導水平高、科研條件優、培養質量好的博士生導師傾斜,對考核不合格的博士生導師施行中途退出機制,使導師內心形成一種緊迫感,不敢敷衍,用心指導,從而提高博士生培養質量。
4.建立合理的監督問責制度,保障博士生的合法權益
首先,培養單位缺少規范導師的具體指導行為的管理制約機制,這是博導“放羊”行為孳生的重要誘因。博士生是博導“放羊”行為的被侵害者。當學術不端事件、博士生論文盲審或抽檢不合格、博士生延期等事件發生后,到底應該追誰之責?以往有的博導明哲保身,“甩鍋”學生,撇清自己,輿論也往往一邊倒地將追責對象指向博士生,而忘了博士生導師才是博士生培養的第一責任人。崇尚權威、尊師重道的思想深植于東方文明,在師生關系中,博士生是相對弱勢的一方,為了不影響畢業,博士生通常放棄抗爭而選擇沉默隱忍。只要學生不投訴和舉報,培養單位往往也對這種現象采取容忍態度。忍讓和容忍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縱容,變相地加劇了博士生導師“放羊”行為的發生,嚴重影響博士生的科研生活,最終的結果就有可能是毀掉一個博士生的學術職業生涯。
《準則》強調導師要精心盡力投入指導,確保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提供指導,要對學生的學業進程進行監督,對學生面臨的學業問題進行指導,對于導師的指導違規行為要強化監督問責,依法處置。[51]這為約束導師的指導行為、建立相應的程序性管理機制指明了方向。為了有效預防和治理“放羊”行為,博士生培養單位應建立合理的問責制度,依法依規對博士生導師指導中的違規行為進行責任認定和追究,以便事前警示、事后追責,而后警世。現代法治理念中,只要有可問責之事實,人人皆可問責。因此,有必要構建面向社會的信息公開制度,明確社會力量問責的主體地位,建立多元主體參與的教育問責機制,加強社會監督,充分發揮社會主體在教育治理中的作用[52],只要博士生導師的指導行為中具有與自己的角色相悖的過失而無正當的免責理由,就應當依法依規追究其責任,并進行信息公開,讓社會公眾、學術共同體和全校師生一起形成合力,共同監督,使得“放羊”行為沒有滋生的土壤。
其次,還應健全博士生的權益保障制度。當導師濫用指導權,對博士生的合法權益造成侵害后,博士生要有相應的申訴途徑和權利救濟方式。[53]博士生作為教育利益的多元主體之一,理應參與到學校的博士生教育治理中,充分發揮監督作用。作為博士生導師指導活動中的相對人,身為親歷者,博士生對博士生導師的指導行為有著最為真實的體驗,感受也最為深刻,由他們來監督,對于規范博士生導師的指導行為,不僅必要,效果也將更加顯著。但囿于倫理、經濟、話語的不對等地位,博士生即便遭遇了“放羊”,也不敢表露心中的不滿。因此,博士生培養單位需要完善申訴渠道,當博士生遭遇“放羊”、教育權益被侵犯時,能通過正當的渠道理性地發聲、捍衛自己的合法權益。
再次,培養單位還要為遭遇“放羊”行為的博士生提供必要的權利救濟方式,幫助博士生擺脫困境,使博士生沒有后顧之憂,敢于發聲。在這方面,MIT于2021年3月8日起實施的“過渡資金”(RISE)計劃或可資借鑒。該計劃適用于受到導師的虐待、疏忽或錯誤指導的學生,通過給學生賦權,來拒絕不公正。MIT通過向學生提供相應的過渡性資助來幫助學生離開“不健康”的指導關系,以改善現狀、實現更好的學術自由。MIT在推動此項計劃時,強調了四個核心原則:為學生提供廣泛的資格與財務保障,通過0GE集中項目管理,提供非資助住宿,與有問題的導師共同解決問題。如果博士生導師的“放羊”行為一經查實,博士生培養單位應該盡快公正合理地解決博士生反映的問題,保護其合法權益,如協助博士生更換導師、提供過渡階段所需的資金資助。
參考文獻:
[1]PAGLIS L, GREEN S, BAUER T. Does Advisor Mentoring Add Value?A Longitudinal Study of Mentoring and Doctoral Student Outcomes[J].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2006, 47(4): 451-476.
[2]LEE A. How Are Doctoral Students Supervised? Concepts of Doctoral Research Supervision[J].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2008, 33 (3) :267-281.
[3][27]董云川.文科博士生教育之省思[J].高教探索,2020(4):5-10.
[4]范皚皚,沈文欽.什么是好的博士生學術指導模式:基于中國博士質量調查數據的實證分析[J].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13(3):45-51.
[5]古繼寶,王茜,吳劍琳.導師指導模式對研究生創造力的影響研究:基于內部—外部動機理論的分析[J].中國高教研究,2013(1):45-50.
[6]吳東姣,鄭浩,馬永紅.博士生導師指導行為的內容與類型:基于人文社科博士生培養的質性研究[J].高教探索,2020(7):35-44.
[7]龍立榮,楊英.研究生指導行為的評價與分類[J].高等教育研究,2005(6):50-53.
[8][12]毛如雁,江瑩.導師類型與師生互動分析[J].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07(9):26-29.
[9]蔡翔,呂芬芬.研究生導師類型及“導師—研究生”互動模式分析[J].現代教育管理,2010(10):66-68.
[10]杜嬙.導師指導與博士生專業素養的發展:自主性的調節作用[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9(3):36-43.
[11]陳珊,王建梁.導師指導頻率對博士生培養質量的影響:基于博士生視角的分析和探討[J].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06(3):61-64.
[13]張煒.博士研究生退出和延期的數據測算與討論[J].研究生教育研究,2021(1):1-6.
[14]HUWE M, JOHNSON B. On Being an Excellent Protege: What Graduate Students Need to Know[J].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Psychotherapy,2003,17(3):41-57.
[15]蔡芬,曹延飛,顧曄,謝鑫.教育博士生延期畢業影響因素的質性研究[J].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20(3):46-52.
[16]劉云杉.師生互動中的權力關系[J].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報,2008(1):55-57.
[17]陸健東.陳寅恪先生的最后二十年[M].北京:三聯書店,1995:103.
[18][47]趙世奎,沈文欽.博士生導師制度的比較分析[J].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11(9):71-77.
[19]BAKER L, LATTUCA R. Developmental Networks and Learning: Toward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on Identity Development during Doctoral Study[J].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2010, 35(7):807-827.
[20]WOOLSTON, CHRIS, O’ MEARA, et al. China’s PhD Students Give Their Reasons for Misery[J]. Nature, 2019(575):711-713.
[21]李海生.導師指導中不當行為的主要表征及防范對策:基于對4521名研究生導師的問卷調查[J].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19(4):12-20.
[22][26]胡娟.熟人社會、科層制與大學治理[J].高等教育研究,2019,40(2):10-17.
[23]王長樂.對人文學科博士生培養單位及博導遴選方式改革的思考[J].現代大學教育,2010(6):52-58+111.
[24]顧海兵.莫把“博導”作頭銜[J].中國高等教育,2003(12):31-32.
[25]顧海兵.中國研究生教育制度:批評與建設[J].學術界,2002(3):76-94.
[28]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9.
[29]GRANOVETTER M.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8(78):1360-1380.
[30]W·理查德·斯各特.組織理論:理性、自然和開放系統[M].黃洋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52-56.
[31]王尚銀,康志亮.中國熟人社會的“類社會資本”:關于中國傳統社會社會資本儲量的考究[J].社會科學戰線,2012(1):165-170.
[32]張繼明,余敏.論現代大學制度建設中的大學文化治理:基于社會學新制度主義的視角[J].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17(5):149-157.
[33]楊晨光.清華研究生院副院長解讀:為何取消博導評聘制度[N].中國教育報, 2011-02-28.
[34]中國教育報.全方位打造一流的研究生導師隊伍[EB/OL].(2020-08-01)[2021-05-30]. 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jyzt_2020n/2020_zt15/baodao/pinglun/202008/t20200813_477868.html.
[35][42][50]教育部.關于加強博士生導師崗位管理的若干意見[EB/OL].(2020-09-29)[2021-05-30].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s7065/202009/t20200927_491838.html.
[36]彭蘭,潘午麗.高校博士生導師勝任特征模型構成要素研究[J].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12(8):19-22.
[37]王傳毅,趙世奎.21世紀全球博士教育改革的八大趨勢[J].教育研究,2017(2).
[38]International Affairs Offic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Structure of the U.S. Education System: Research Doctorate Degrees[R/OL]. (2008-02-09)[2021-05-30].https://www2.ed.gov/about/offices/list/ous/international/usnei/us/doctorate.doc.
[39]劉亞敏,王聲平,關荊晶.美國一流大學博士生培養過程管理:特征與啟示[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9(3):93-97.
[40]中國博士質量分析課題組.中國博士質量報告(2018)[R].北京大學教育研究院,2018.
[41]沈文欽,金帷.博士生聯合指導制度的全球擴散: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分析[J].中國高教研究,2020(12):89-95.
[43][48]中共中央,國務院.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EB/OL].(2020-10-13)[2021-03-09].http://www.gov.cn/zhengce/2020-10/13/content_5551032.htm.
[44][49]教育部,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關于加快新時代研究生教育改革發展的意見[EB/OL].(2020-09-04)[2021-03-09].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s7065/202009/t20200921_489271.html.
[45][51]教育部.關于印發《研究生導師指導行為準則》的通知[EB/OL].(2020-10-13)[2021-03-10].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s7065/202011/t20201111_499442.html.
[46]馬克斯·韋伯.學術與政治[M].馮克利,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21.
[52]林靖云,劉亞敏.我國教育治理中的社會參與:困境與出路[J].現代教育管理,2020(11):44-50.
[53]林靖云,劉亞敏,杜學元.教育懲戒權再審思:內涵、邊界與落地[J].教育科學研究,2021(5):40-46.
(責任編輯 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