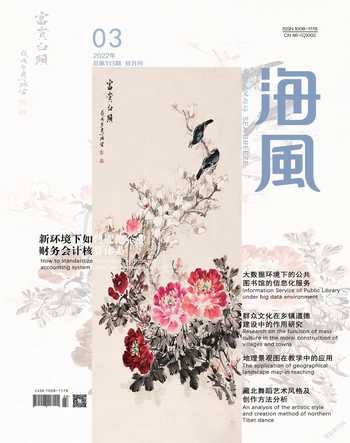中國傳統雕塑中馬的藝術造型演變
馬的形象在藝術作品中廣泛出現始于秦代,并在秦、漢、唐三代不斷發展。本文主要對中國秦漢時期傳統雕塑中馬的形象進行分析,一方面馬成為藝術創作對象集中在秦代;另一方面,這一時期馬作為雕塑藝術創作對象有了較大的發展,能以點帶面梳理出馬雕塑藝術在造型上的演變。
馬作為雕塑創作的主題內容,在秦朝以前就已出現。先秦馬的雕塑的體量較小,馬的整體形態上多采用圓滑的線條以表現馬的整體形象,細節刻畫不多,主要集中在馬頭上,對馬身的刻畫不深入,在創作手法上,已經有了將圓雕和浮雕相結合的方式,刻畫馬的生動形象,但略顯粗糙。這一時期的馬的形象體型憨態,卻無神駿氣態,加之體量小,細節刻畫有限,與秦以后馬的雕塑形象存在差異性。但先秦時期的馬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寫實性,如山西曲沃晉侯墓地發現的玉馬,就已經對馬休息時的狀態進行了刻畫,馬前蹄直立,后蹄微曲,脖子略低,做休息狀,馬目平視前方,雖沒有對肌肉細節進行刻畫,但在整體上有所塑造,能看出馬身肌肉豐盈之態。
一、秦代馬的雕塑造型
(一)秦代馬的雕塑造型影響因素
秦統一六國依靠的是全國尚武的風氣、獎勵軍功政策和強大的軍事實力,而馬在古代戰爭中是重要軍事裝備組成部分。秦國依托良好的地理位置,聚集了眾多野馬,因此秦國自上而下有養馬的傳統,這使得馬在秦代相較于其他牲畜地位相對而言更為重要,這些因素的疊加造成秦代尚馬的傳統,也為秦國統一六朝奠定軍事基礎和馬成為藝術形象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奠定基礎[1]。
秦代雕塑中馬的形象塑造受《相馬經》影響較大,《相馬經》是秦穆公時期孫陽善所著,指導人如何判斷馬的優劣的書籍。秦穆公時期正是秦國瘋狂擴張領土時期,由于馬在戰爭中的重要地位,選擇優質戰馬顯得尤為重要。孫陽善指出,優質馬額寬,眼鼻大,耳形短小硬直相攏不散,上嘴唇緊密有力,下嘴唇方正發達,頸部長而彎,胸廓寬厚,背部平而廣,腹部充實,股部厚重,尾根高,肘腋欲開,膝骨圓大,四蹄欲厚且大。《相馬經》能夠通過馬的外形推測腹部臟器健康與否和馬的耐久力等,并綜合各方面分析馬是否能夠達到戰爭所需,書中提及,鼻大則肺大,眼大則可斷定心大,思維敏捷,在戰爭中能適應長途征伐,且反應迅猛。《相馬經》對民間甄別馬的經驗進行了總結,在秦代成為選馬的即行標準,書中對優質馬特征的描寫直接影響了秦代雕塑,秦代諸多以馬為題材的雕塑中都可以看到《相馬經》中優質馬的特征。
秦代雖然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廢除了分封制,但在喪葬文化上沿襲了西周以來的習俗,陪葬品成為顯示墓主身份高低的憑證,在現今已搶救性發掘保護墓葬文物中,以馬為創作對象的雕塑陪葬品也是屢見不鮮的。以馬作為陪葬品是為了顯示墓主的自衛能力和強大的軍事力量,寓意即使往生,仍有軍隊對自己的“人身安全”進行保護,護衛自己的靈魂到達靈魂凈土。雕塑馬的功能屬性促使其在造型上與現實的馬匹有一定共通性,對馬的體態等方面都做出了新的要求,而不僅僅像先秦時期只要求初具馬形即可[2]。
(二)秦代馬的藝術造型特征
秦代馬雕塑造型集大成者就是秦始皇兵馬俑中的陶馬與銅馬,秦代馬的雕塑形象以寫實為主。由于秦代治國理論采用法家思想,功利主義盛行,因此在雕塑上,無論是使用者還是創作者都希望作品具有功能屬性,這促使創作者在創作過程中追求寫實,馬雕塑形象與生活中的馬相契合。
以秦始皇兵馬俑為例,秦始皇兵馬俑創作初衷是顯示秦朝雄厚的軍事力量,讓秦始皇在死后仍舊能夠統領千軍萬馬。所有有關馬的雕塑都是盡量還原實體,如兵馬俑中的馬匹四蹄觸地,馬頭呈前傾狀,通過肢體塑造出蓄勢待發之感。同時,細節刻畫十分細致,利用圓滑的曲線對馬的頸脊,馬腹、馬臀三處線條的深入刻畫,勾勒出馬身的肌肉線條,凸顯出馬的強健雄偉之態。在馬的五官刻畫上,創作者運用多種技巧,體現雕塑馬栩栩如生之感。創作者在進行創作時,應用了商周以來刻陰陽線的方式,勾畫五官,利用陰線雕刻眼部,利用陽線,刻畫鼻孔,使得五官從平面變得更為立體,與創作實體越發接近[3]。
寫實是秦代馬的雕塑最大的特征,注重體量感,追求力量感,但也不可避免地使雕塑具有笨拙、粗狂,整體上馬身采用圓線條勾勒外形,整體渾圓,給人厚重結實的感覺;局部上方圓相結合,局部上形成方與圓的對比關系。除了方圓對比和線面對比明顯外,創作上更有層次感,層次最多、變化最豐富的莫過于馬頭,馬頭臉頰為半圓外輪廓,臉部則較為平面,線條與面的交疊促使馬頭成為秦代雕塑最具有研究價值的部分,也是整個馬的雕塑具有神韻的地方。
二、漢代馬的雕塑造型
(一)漢代馬的雕塑造型影響因素
漢代馬的雕塑是在秦代基礎之上發展的,在諸多方面都對前代的藝術成果進行了吸收借鑒,但漢代以儒家學說作為治國指導思想,這促使漢代馬雕塑與秦代在造型上略有不同。同時,漢代存在的時間比秦代長,在經濟各個方面比秦代更為穩定,漢代早期休養生息政策也為經濟增長提供條件,物質條件的變化為藝術發展提供了經濟基礎。
漢代雕塑創作也受到了楚文化的影響,尤其是西漢初期馬的雕塑造型,既有前朝的嚴謹寫實特征,又具有楚文化神秘古樸之意,在兩種文化的影響下,早期漢代雕塑藝術在整體風格上呈現了靜穆古樸的風范。以馬踏匈奴為例,在體量上繼承了秦代,創作技巧上也是大量使用圓雕手法,整體造型呈現莊重威嚴,但對細節刻畫較少,著重體現雕塑的體量感,并且對馬蹄下的匈奴刻畫沒做鏤空處理,而是將匈奴士兵填充在馬腹之下,整個雕塑渾然一體,在一定程度上為觀賞者留下想象空間,創作者將美好的希望寄托在作品之中,體現著楚文化的浪漫。
(二)漢代馬的雕塑造型特征
不同于秦寫實主義下的馬的雕塑藝術,漢代馬的雕塑對神韻有一定追求,細節刻畫上沒有秦代馬的雕塑刻畫深入,強調雕塑的整體傳神,在創作過程中融入了創作者的思想,而不再是單單追去對實物的極致寫實。
漢代雕塑中的馬的藝術造型多為動態,造型上整體有清晰的線條勾勒外形,對體型感塑造到位,頭部重點內容塑造上繼承秦代寫實風格,但同時,也注入了創作者的創作思想,對馬的動態性重點刻畫。如《躍馬》這一雕塑,馬首上昂,微斜,眼睛目視前方,口微張,鼻子呈運動狀,頸部前傾,后肢臥于地面,前肢向前彎曲,呈現準備奔走狀,使觀賞者即使看到是身體臥于地面的馬,但明顯能夠從這些局部塑造中感受到馬即將要一躍而起的動態。技法上,圓雕與浮雕的相互配合,圓雕突出整體形象,浮雕起強調作用,以此凸顯馬的雕塑動感。漢代的雕刻家們擅長利用石材的原有形態,利用石材本身的形態進行構圖,真正達到“藏其形,為其神”的效果,這與秦代有著較大的區別[4]。
除了傳神性之外,漢代馬的雕塑創作內容上更具有想象性。東漢時,《銅奔馬》成為了雕塑藝術杰出作品之一,造像上寫實技巧更加精湛,圓雕技術更加成熟,無論是在局部還是整體上對比前代都有所發展。《銅奔馬》描繪的是馬的疾馳形象,創作者采用夸張手法,在馬蹄下附加一只飛燕表現馬的速度,除此之外,馬頭鬃毛飛揚,馬口呈嘶吼狀,馬耳也在風力作用下微微向后;頸部略彎,腰身與腹部緊湊,馬蹄三蹄懸空,一蹄落于雨燕背部。既描繪出了馬的奔跑狀,又突出了馬的莊嚴凝重。這也與秦代馬的雕塑形象相差較大的地方。
三、總結
馬的雕塑藝術發展取決于不同社會藝術審美的發展程度、經濟發展狀況和技法等多個方面。秦代由于其特殊的社會背景、尚馬傳統習俗和現實的需要等多方面因素,促使馬的雕塑藝術得到長足的發展。但秦代馬的造型藝術上注重實用性,追求寫實性,雕塑的創作者們的思想不能夠得到更好的表達,雕塑更多為統治者、雇主所服務。但這也促進了雕塑家們創作技巧的提升,創作方式的優化。
漢代,創作者們繼承發展了秦代關于馬的雕塑藝術,技巧應用更加嫻熟,同時,由于漢代統治思想的變化,為馬的雕塑藝術發展提供了表達空間,馬雕塑的創作者們不再拘泥于實用的功能性,而將自己的創作想法融于雕塑之中,既應用了秦代雕塑技巧,又善于應用多種藝術表達技巧,促使漢代的馬的雕塑形象神大于形。
正是有秦代對馬雕塑藝術造型的創新和漢代的繼承與發展,才促使在唐代馬雕塑藝術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將秦漢兩代優勢集中于一體。研究馬的雕塑藝術造型單看某一朝代馬的雕塑藝術,而應該聯系起來,用發展的眼光去分析,才能從中分析出各個朝代的特點,對于馬的雕塑藝術發展有重要意義。馬的雕塑藝術在我國歷史悠久且具有代表性,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更是要在傳統文化中汲取養分,將馬的雕塑藝術進一步發展。
參考文獻:
[1]郭維陽.對秦代動物雕塑中馬的藝術特點的分析[J].藝術科技,2013(12):56.
[2]郭維陽.秦漢馬雕塑造型風格比較[J].新疆藝術學院學報,2014(2):67.
[3]薛文杰.秦、漢、唐馬形象雕塑的藝術表現以及對當代藝術的啟示[D].西安:西安美術學院,2016.
[4]莊鵬.論秦漢時期的馬藝術[J].科技信息,2009(19):122.
作者簡介:程俊杰(1996-),男,漢族,湖南長沙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美術與國際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