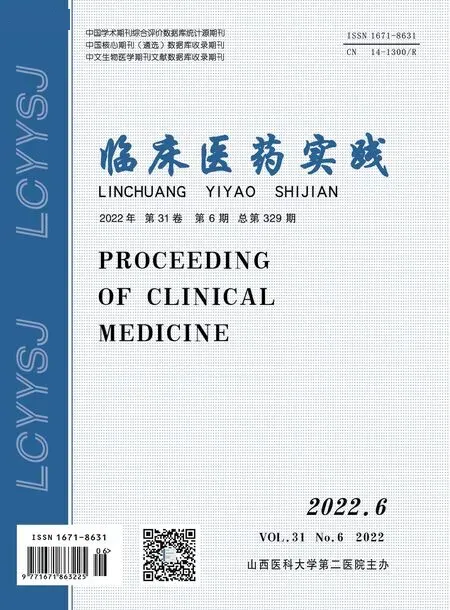巨大腘動脈瘤血管腔內修復1 例報告并文獻復習
張寧,田宇,蔡漢鑫,黃智勇
(深圳大學第三附屬醫院,廣東 深圳 518000)
腘動脈是外周動脈瘤形成最常見的部位[1],而巨大腘動脈瘤(PAAs)比較罕見。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2]在出現癥狀時腘動脈瘤破裂的發生率約為2.2%,所以早期診斷與治療是保證患者生命安全及減少患肢進一步損傷的關鍵。開放手術一直被認為是PAAs修復的金標準[3]。近年來,血管腔內修復(EVR)方法在PAAs治療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已得到廣泛證實[4]。然而,對于巨大的腘動脈瘤,目前還沒有確定的治療標準。本文報告1 例罕見的合并右腘動脈巨大動脈瘤及腹主動脈瘤(AAA)的多發外周動脈瘤患者,通過血管腔內修復安全有效。結合此病例,對近年腘動脈瘤治療方式文獻進行回顧分析,報告如下。
1 臨床資料
患者,男性,44 歲,因右下肢疼痛3 d入院。患者入院前3天無明顯誘因出現右下肢疼痛,坐立位和站立位加重。既往史:20 余年前因右上肢肱動脈瘤行手術切除。長期吸煙史,否認家族遺傳病史;高血壓病史20 年,未規律口服降壓藥物治療。入院體檢:右側腘窩可觸及搏動性腫塊,左上肢肘窩可觸及搏動性腫塊。實驗室檢查:白細胞計數10.08×109/L,中性粒細胞比值81.4%,C反應蛋白34 mg/L,纖維蛋白原3.79 g/L,栓溶二聚體定量2.87 mg/L;免疫指標檢查:抗核抗體、抗雙鏈DNA抗體、抗ENA譜、抗中性粒細胞胞漿抗體、抗腎小球基底膜抗體均為陰性;乙肝表面抗體陰性;梅毒螺旋體抗體陰性。腹主動脈及下肢動脈CT血管造影(CTA)檢查:腹主動脈瘤(40.80 mm×25.89 mm);雙下肢髂外動脈、髂內動脈多發動脈瘤;右下肢腘動脈瘤(54.53 mm×45.15 mm);左下肢腘動脈瘤;未見明顯鈣化斑塊形成。入院后,考慮患者既往史、體檢,結合下肢CTA影像學表現,考慮患者存在多系統受累表現,遂接受全身其他臟器血管檢查。頭顱CTA:椎動脈瘤、頸內動脈瘤;胸主動脈CTA:腸系膜動脈瘤;上肢血管彩超顯示:左上肢肱動脈瘤。
診治經過:患者,中年男性,考慮多發動脈瘤形成,其中腹主動脈瘤囊性擴張,直徑較遠端明顯變大,且目前右下肢腘動脈瘤較大并伴隨繼發血栓形成,遠端流出道未見,處于急性缺血邊緣。經過團隊討論,為提供良好的膝下流出道,先經左側股動脈入路行右側腘動脈置管溶栓術;置管溶栓24 h后再次行腘動脈造影,可見腘動脈遠端流出道顯影良好,遂行右腘動脈瘤腔內隔絕術,術后造影示支架位置良好,腘動脈瘤隔絕良好,未見內漏(見圖1);再次行腹主動脈造影,可見腹主動脈囊性擴張,遂行腹主動脈腔內隔絕術,術后造影顯示支架位置良好,腹主動脈瘤隔絕良好,未見內漏(見圖2)。建議患者術后開始服用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3 個月,然后終身服用阿司匹林。

(a):右腘動脈瘤樣擴張;(b):置管溶栓術后瘤體遠端顯影較前好轉;(c):覆膜支架腔內隔絕術后瘤體消失

(a):腹主動脈囊性擴張;(b):腹主動脈瘤腔內隔絕術后
2 結 果
術后患者右側脛后動脈和足背動脈搏動良好,腘動脈動脈瘤搏動消失。術后1 周患者出現右側腘窩處酸脹不適及右側足趾麻木,給予持續1 個月的康復訓練,患者感覺良好,酸脹及麻木消失。術后3 個月行腹部及下肢動脈CTA檢查示:腹主動脈及右腘動脈支架通暢,未見內漏,瘤腔大小無明顯縮小(腹主動脈:38.45 mm×25.68 mm;腘動脈51.53 mm×42.93 mm),實驗室各項指標均正常。同期,我們對左肱動脈瘤行切除重建術。標本病理檢查表現為內彈性板破裂,膠原蛋白增生,無炎癥細胞浸潤,診斷為肌纖維發育不良(FMD)。
術后18 個月患者因出現右下肢乏力再次就診我科,復查腹部及下肢CTA示:腹主動脈支架通暢,未見內漏,瘤腔較前明顯縮小(28.90 mm×23.21 mm),右側腘動脈支架內血栓形成,瘤腔明顯縮小(25.89 mm×19.55 mm)。患者訴未規律口服抗血小板藥物,遂行右腘動脈置管溶栓及球囊擴張術,術后可見腘動脈支架遠端血流通暢,未見明顯血栓殘留(見圖3);出院后再次囑咐患者規律服用抗血小板藥物治療,定期隨診,切勿自行停藥。

(a):支架內血栓形成;(b):術后支架血流恢復
3 討 論
PAAs是最常見的周圍動脈瘤,發生率為0.1%~2.8%[5]。PAAs最常見的原因是動脈粥樣硬化,但也可由創傷、醫源性損傷、梅毒、肌纖維發育不良、先天性腘動脈瘤、真菌性動脈瘤以及Behcet病引起。
本研究中,患者雖然有長期吸煙史及高血壓病史,但CTA示患者無明顯動脈粥樣硬化斑塊,而病理結果顯示肌纖維發育不良是此患者的發病基礎。同時,該患者還合并其他動脈瘤,特別是腹主動脈瘤。研究顯示[6],超過20%的PAAs患者也同時存在AAA,這可能與這些疾病之間有共同的心血管危險因素和病因機制相關。因此,PAAs患者篩查其他動脈瘤是必要的。一旦確診,應該重視PAAs,因為腘動脈血栓栓塞可導致下肢急性缺血,從而導致截肢[7]。研究表明[8],對于無癥狀的PAAs,當腘動脈瘤直徑超過20 mm或瘤腔內有附壁血栓時,應當予以積極干預;而對于存在臨床癥狀的PAAs,則必須予以修復。為了獲得良好的流出道,我們對本病例進行了動脈內溶栓,獲得良好的流出道后建立手術通路并行腘動脈瘤腔內隔絕術,同期行腹主動脈瘤腔內隔絕術,術后予抗血小板治療,患者18 個月后出現腘動脈支架內血栓形成,可能與患者停止抗血小板治療有關。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開放手術(OR)一直被認為是PAAs修復的金標準[9]。EVR自1994年首次報道以來,因其創傷小、失血量少、手術時間短、麻醉風險低等優勢,已被證明是一種很有前途的PAAs治療方式[10]。為了比較兩種術式的安全性及有效性,我們納入17 篇文獻[11-27]進行回顧分析。通過OR治療的患者1 年的初級通暢率明顯高于通過EVR治療的患者,而次級通暢率無明顯差異,兩者3 年初級通暢率及次級通暢率均無統計學差異。與通過OR治療相比,通過EVR治療的患者在30 d內移植物閉塞和再干預率更高,而截肢或死亡率沒有明顯差異。盡管患者術后接受抗血小板或抗凝藥物治療,支架閉塞仍比靜脈旁路移植更多[28]。
綜上所述,本病例報告及文獻回顧說明了腔內修復巨大腘動脈瘤是安全有效的,然而,盡管這是一種有價值的替代方法,但開放手術仍是目前的首選[29]。期待隨著具有良好通暢度、靈活度和徑向剛度的新設備的發展,血管內修復可以被認為是治療巨大PAAs和復雜PAAs的可靠治療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