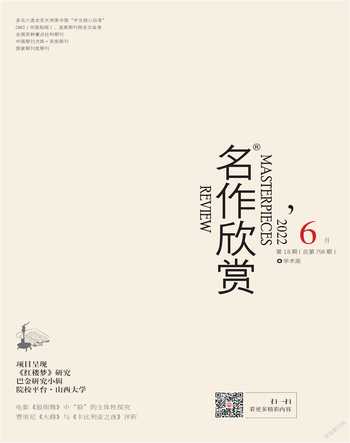論楊絳散文中的知識分子寫作立場
李天然
關鍵詞:知識分子 文化融合 邊緣化 楊絳 散文
本文從四個方面展開論述:一是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和歷史事實,將《楊絳全集》中的散文集進行充分的融合整理,借此分析“隱身”立場在文本中的呈現和影響;二是從《楊絳全集》中的散文集探究其本身的“隱身”這一創作立場,探究其獨到的作品風格與楊絳獨有的文學視角;三是回歸到《楊絳全集》中的散文部分,通過楊絳先生的個人書寫與思考探究該作品的思想內核和人文情懷,體驗作者當時悲涼之情的外射與物化對廣大讀者產生的“隱身”思考;四是以楊絳先生一生的生活經驗和閱歷為研究點,分析文藝理論家對楊絳散文“隱身”立場的評價。
一、楊絳散文中的隱身立場
(一)智慧的隱身衣——邊緣化的創作立場
作為一名出色的學者型作家,楊絳邊緣的創作姿態和豐厚的文學作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回顧楊絳艱苦繁重的文學創作歷程,其邊緣化的寫作姿態無疑是對傷痕文學的平靜化處理。從寫作立場而言,楊絳的文學創作是自發性的,是較少功利性的,是一種文化傳承的藝術沉淀。
以知識分子的寫作姿態對“隱身”的內涵進行多維度解讀,即三個推論:冷看、流亡、委婉的批判與含蓄的幽默,這同時也是楊絳語言中“萬人如海一身藏”的中國式哲學,當不朽的文學巨著和隱身的文學創作不期而遇,這是對“文學回歸本身”的指向性詮釋。
法國文藝家丹納在《藝術哲學》中肯定了環境對文藝所造成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不僅體現在楊絳對其文學作品中“小市民形象”的合理建構,同時也側面體現了淡化歷史的時空創作觀。
楊絳隱身的文學創作不僅可以反映時代嬗變的政治風云,還可以記錄作者真實的心靈世界。從其自身的文化視野來看,邊緣化的文學創作背后是對唯英雄論的委婉批判與諷刺,莊子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這為楊絳“隱身的靈魂”和對唯英雄論的批判提供了雙重論據。
這種隱身的創作姿態是“冷看”,標志著其作品意義指向性的迥然不同。這里的“冷看”并不是居高臨下或默不作聲的,與魯迅筆下的旁觀者形象截然不同,楊絳的“冷看”是一種對自我的超脫,即對心靈敏感具有“本我、自我、超我”的情緒化體驗。
哀而不傷、怒而不怨,愧怍中夾雜著一點私心,這是楊絳文學作品中所獨有的雍容感。作為一名多重角色的學者型知識分子,楊絳總是游離于文學創作和時代的主流之外,這也與其自身的流亡生活形成了自身的心靈敏感。楊絳的旁觀姿態也使得“我”在作品中的旁觀體驗感濃厚,知識分子眼中的小市民是帶有功利性和競爭性的,這也使得楊絳的作品中自帶一些“諷刺的幽默感”,即在憐憫的關懷和批判的幽默中追求諷刺與詼諧的統一。
將楊絳的文學生涯進行橫縱分析,從桃李年華的文壇初創到九十高齡的再綻光芒,這一生涯跨度的時空歷史無疑是對個人記憶書寫者與社會歷史回憶者的雙重感悟。而對散文、小說、文論、翻譯等多方面的體裁理解,則從側面體現了楊絳厚重的文學功底和邊緣化的創作姿態。
(二)“隱身”風格的產生原因
以流亡者和知識分子的雙重身份所進行的文學創作,是楊絳自身文化基因交融碰撞、互相輝映的最終結果。作為流亡者,她的語言孤獨而犀利,既游離于時代的浪潮又緊扣歷史的記憶;作為知識分子,她既批判“別人”的同時又譴責“自己”的私心,這也使得其游離于時代的孤獨感被悄然隱退,直至無聲。
作為一名智慧的知識女性,楊絳對自身文化姿態的建構中蘊含著地域性文學的“和而不同”和“懸置不信”,包含著江南士風的耳濡目染與學院精神的言傳身教,以及傳統女性的蘭質蕙心和西方人文的獨立自主。這使得楊絳能從多種文學視角中形成一種多元的創作體系和文化體驗,更能在隱身的創作姿態中“冷看”,形成獨特的文學世界。
首先,受父親楊蔭杭和母親唐須嫈的影響,幼時的楊絳自發萌生了自身的理想追求,其父親的形象與楊絳所翻譯的《堂吉訶德》里的“瘋騎士”形象不謀而合;而母親唐須嫈的“不爭”姿態則為楊絳知識分子的創作理論提供了自我與他者的留存。其次,學院精神的言傳身教為楊絳提供了厚重的文學素養和深厚的藝術功底,而她本身對學術的無限探討使她逐漸形成了執著堅定的文化性格。20 世紀30 年代就讀清華時的國學老師大多是“京派”的文化大師。堅持學術無政治,文學應該服務于自身,這也使得楊絳的散文呈現出一種邊緣化的寫作特征。再次,作為一名傳統的智慧女性,其身上所獨有的知性美為“不爭”提供了睿智超脫的人生態度。無論是母親唐須嫈所具有的賢惠文靜,還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體悟,都造就了楊絳文學的婉而多怨。而這種流亡形象的書寫也使得淡化歷史的個人記憶得到充分的留存。
最后,西方精神世界的獨立自主是楊絳多重角色與多種體裁的充分展示和獨特表現。從傳統文化與西方思想的水乳交融,再到學院精神的言傳身教和江南士風的耳濡目染,楊絳以驚人的創作實績和低調的人生態度構成了一種“中間狀態”的時空體書寫,形成了一種真實與夢境的空間組合體。
二、“隱身”立場在文本中的呈現
(一)《干校六記》和《雜憶與雜寫》
和楊絳的戲劇作品不同,其散文作品《干校六記》拋棄了所謂第三人稱的全知全能視角,以第一人稱敘事為主,以補敘進行遺憾化處理,使得文學作品中的“我”具有一種獨特的個人反思,這與當時的傷痕文學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反差感,使得作品中的“我”實現了情感上的更高觀照。
“年逾七旬的老人了,還像學齡兒童那樣排著隊伍,遠赴干校上學,我看著心中不忍,抽身先退;一路回去,發現許多人缺乏歡送的熱情,也紛紛回去上班。
大家臉上都漠無表情。”a作者將不幸的年華進行了自身的平靜化處理,使得其文學語言中蘊藏著悲情的鈍感力。從似乎沒有悲憫的體驗,再到愧怍情感的觀照與反思,作者以外圍于空間和時間的視角作為其克制而冷靜的筆觸。
這與傳統文學中盛大的離別場面與生死場面不同,楊絳以邊緣化的創作態度和“隱身”的創作筆調使得作者的參與感降到了極低的閾值,這種以微知著、不露鋒芒的文字則讓人更感悲其苦,流露憫意。
知識分子的自由精神使得楊絳的散文更注重讀者的閱讀感受,她從不隨波逐流,保持著“大隱隱于市”的創作獨立與情感體驗。而《雜憶與雜寫》則從側面體現了其以文養身的情緒抒發,而無功利性的客觀娛樂體驗和文字的平靜化藝術處理也使得楊絳的文學創作在傷痕與反思的浪潮中獨樹一幟,特色鮮明。
甘于邊緣的自由創作使得楊絳處于一種流亡的“中間狀態”,而悲憫寬厚的文學語言則使得她生命中的痛苦黯然消隱,只留平靜。作者一邊以個人記憶書寫歷史,一邊則以寫實的虛化作為其現實主義文學的主要特色。
(二)《我們仨》
巴赫金認為,時空體在文學中有著重大的體裁意義。“不同觀念的人們通過不同的時間、空間組合體來理解并訴說外部現實。”b《我們仨》以時間中的非歷史性淡化和消解了讀者對于死亡的疏離感。而對于散文中的“我”,則是超而不脫的知識分子對于世事的情感化體驗。
《我們仨》中的夢境使得淡化時空的歷史觀蘊含著一種情感朦朧,而這種外圍視角與西方傳統理論中的“移情說”和而不同。巴赫金認為移情更多的是價值方面的審視,即運用他的位置去構建他的框架,這使得文學作品中的“我”既能陶醉其中也能超凡脫俗,形成其獨有的“冷看”思維。
“這是一個萬里長夢,夢境歷歷如真,醒來還如在夢中。但夢畢竟是夢,徹頭徹尾完全是夢。”c楊絳運用虛實相生的筆法使得個人書寫的悲痛感得到了平淡化處理,讓人陷入了一種旁觀的思緒。當主觀的悲傷與客觀的超脫在同一主體中得到交融,自然而然會形成一種流于“中間狀態”的冷看。
悲傷中蘊含著虛妄,溫情中隱藏著淡然。楊絳在《我們仨》的創作中,以自我的更高觀照使得歷史事件變得客觀,體現了散文作品中所獨有的歷史敘事性。而這種淡化時空的歷史觀也使得巴赫金的時空體理論得到了充分體現,使得楊絳的文學作品在經歷了時間的考驗后依然可以熠熠生輝。
三、 對“隱身”立場的評價
(一)游離于主流話語方式之外
“隱身”立場中自帶客觀的形式使得楊絳的散文被自覺排斥于20世紀60年代所形成的“革命現實主義”的洪流之外,而這種無功利性的文學審美意識形態又使得楊絳散文中的批判與幽默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留,看似與人民群眾審美情趣的矛盾也轉化為楊絳自娛自樂的文化消遣,達到了讓文學回歸本身的意義。
作為一個翻譯家、學者、作家,楊絳在早期創作中更多以自身審美情趣為導向。她橫跨七十多年的創作生涯,知識分子的寫作狀態并沒有改變,反倒是在“純文學”的道路上愈走愈遠。而這種多樣化的創作方式和語言也使得楊絳在創作散文時筆耕不輟、游刃有余。這種崇尚自由的創作方式使得楊絳不再緊跟時事,而是通過時間和歷史讓文學成為其獨特的娛樂方式。
這種留存散文的歷史敘事性,不置一評,以個人記憶客觀地還原歷史,于平靜中揭露無聲,從側面反映出楊絳本人對于文學“冷看”的態度。作為一名知識分子,其獨特的創作立場從客觀上使得楊絳與主流的話語方式難以融入,同時又體現了一種“超而不脫”的人生態度。
(二)冷看與隱身
這種“隱身”和“冷看”思維使得楊絳散文具有一種平靜的語言流向和轉折藝術,無論是“陸沉”或是“書遁”,都是為了知識分子獨立于自身的人文自由。楊絳的文學創作盡可能地保持著流浪的“中間態度”,獨立于主流文學之外,形成了一種嚴肅的現實主義文學觀。
以文隱身,以文養身,以文娛身,在少功利性的文學中追憶樂觀向上的文學姿態,以冷靜的筆觸反思自己的私心,而這種邊緣化的創作態度使得其獨立于重功利性的文學天地之外,回歸到“文學應該關注本身”的文化意義,使得獨立自主的學院精神得到充分留存,創造了一片文化學術氛圍較濃厚的本真天地。
“冷看”作為楊絳文學創作的最核心的文學特色之一,依據其“隱身”的文學姿態自然形成了文化疏離的話語流向。避免自己投入主觀的體驗情緒,以委婉的諷刺和低調的詼諧作為“純文學”的語言回流,這是作為一個自由知識分子最好的“中間狀態”。
四、結語
本文以知識分子的創作立場為筆,將冷看、旁觀、委婉的批判與含蓄的幽默作為對“隱身”立場的最好詮釋,楊絳與同時期的其他作家相比,永遠有其獨立的閃光點。她作為一名秉持自由主義創作觀的知識分子,其“隱身”的創作姿態使得她在時代文學外獨有自己的學術天地。從桃李年華的文壇初創到九十高齡的重放光華,楊絳以平靜化的文字處理與客觀的精神姿態獨放光芒。她以謙卑為姿態,用冷靜作筆鋒,實現了“我”的更高觀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