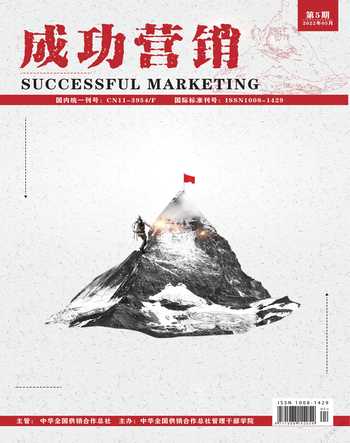淺談農村土地三權分置對鄉村振興的影響

作者簡介:余濤,(1991.8-),男,湖北黃岡,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技術經濟及管理專業,本科,初級工程師,農村土地與產業振興。
摘要:三權分置是農村深化改革中土地要素改革的關鍵一環,這種獨特的三權分置,為農村土地高效利用和鄉村振興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農村土地制度伴隨著經濟發展不斷改革,先后經歷了“單一產權”、“兩權分離”,直至當下的“三權分置”,在當前經濟發展背景下,三權分置為工商資本下鄉和個體農戶經營土地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為農村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但三權分置落地執行中仍存在土地碎片化、基層組織不完善、制度模糊性、城鄉發展不平衡等問題,導致真正實現鄉村振興仍存在一定困境,仍需要不斷試點和摸索。
關鍵詞:土地改革;農村;三權分置;鄉村振興
我國是農業大國,土地制度直接影響著農民的生活和利益,也對社會的穩定安定和農村經濟發展帶來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社會經濟持續發展,農村土地先后經歷了“單一產權”、“兩權分離”、“三權分置”的發展過程。2018年12月,全國人大第七次會議通過了修改農村土地承包法的決議,為農村地區土地的三權分置的施行提供了法律政策支持,本文所指農村土地是指農民使用的用于農業勞動生產的土地。
在土地改革的推動下,農村土地的經營權得到了釋放,農村閑置撂荒地問題有所改善,農民經營的意識也在逐漸提高,隨之而來,農民收益有所增加。然而,由于一些客觀原因,諸如土地碎片化、基層組織不完善、制度模糊性、城鄉發展不平衡等原因,使得三權分置的政策目標實現必然存在一定阻礙。本文著力于分析農村土地變革歷史以及農村土地三權分置對鄉村振興的影響和改進建議。
1農村土地變革歷史
土地資源,作為經濟發展的生產要素資源,土地制度也伴隨經濟發展不斷變遷。中國農村土地改革也是順應國家經濟發展和農村經濟發展而不斷變革。
新中國成立前夕,1949年9月29日頒布的《共同綱領》指出,“農民已經取得的土地的所有權必須得到保護”,由此說明此時推行的是“農村土地私有制”,為新中國成立的穩定和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1951年起,中共中央公布系列文件,鼓勵生產互助提高農業生產效率,通過教育和啟示,不斷發展推動個體經濟逐漸走向集體經濟,也是為了從小生產的個體經濟到大規模機械化的集體經濟的發展,以迅速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1951年,中共中央發文提出了“土地合作社”的概念。隨著生產互助模式的發展和完善,1958年,黨中央明確要求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這是時代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人民公社的建立完成了農村土地私有制向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轉變,這種轉變確立了農村土地“單一產權”的產權制度,為一定時期內經濟的快速發展做出了貢獻。
土地集體所有制的轉變在一定時期內為農業生產穩定發展奠定了基礎,也為工業化的大發展做出了奉獻。由于整體工業化程度不高,我國又面臨人多地少的現實窘境,人民公社領導下的集體組織發展經濟效益較差;土地集體所有制消滅了私有產權,也意味著中國農民喪失了獨立自主經營權,在“大鍋飯”的現實背景下,社員自主勞動積極性不高,繼而反向妨礙了集體經濟的發展。新中國成立后,近三十年的傳統經濟體制在保證我國工業化低水平資本原始積累的同時,也讓農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農業反哺工業的政策,使得生產力極其有限的集體經濟更是捉襟見肘。
實踐經驗表明,發展中國家需要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農業部門健康發展是基礎,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創新促進了農業的高速增長,家庭聯產承包制這一制度創新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聯產承包制改革遵循比較優勢原則,通過增加微觀主體的自主權,激勵其積極性,從而提高經濟績效。
1978年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標志著改革開放成為國家發展的重心,經濟發展成為國家發展第一要務。安徽鳳陽小崗村率先開展了土地承包到戶經營,為農村土地改革做出了示范。1983年1月2日,中央政府對農村經濟發展的政策方向明確提出,聯產承包制成為農村生產組織的主要形式。聯產承包制的政策落地,標志著我國農村地區土地的集體所有權與農民承包經營權的分離,極大地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為農業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化建設奠定了基礎。隨著家庭聯產承包制的推廣和實施,廣大勞動人民激情大漲,糧食產量也不段攀升。具體數據見表1。
1984年農業生產總值比1978年相比增長147.57%,遠高于工農業生長總值48.65%的增長率,說明家庭聯產承包制極大的調動的勞動人民的熱情,農業生產得到較快增長,同時也佐證了在人民公社領導下的集體經濟中,農村農業生產活力被極大程度壓制。同期,糧食產量增長比例達到33.59%,生豬產量增長1.6%,說明這一時期內,農民集中力量全力發展農業生產,最終全國糧食產量大幅攀升。反觀生豬產量增長僅為1.6%,說明解決溫飽問題是當期人民群眾第一要務。同期在人口增加6.24%的基礎上,人均糧增加25.76%,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糧食增產、解決溫飽問題奠定了基礎。
西奧多·舒爾茨曾評價我國農村經濟改革,聯產承包制帶來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但是改革開放以來農業經濟組織一直沒有改變家庭經營的形式。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城市化的不斷發展,經濟的飛速增長,由于農業產業經濟價值低,農民收益較低,致使許多農村選擇進城務工,以增加收入。2020年全國農民工數量達到28650萬人,城鎮化率達到60%。大量農民進城引發了“農村空心化”、“農地撂荒”、“農民老齡化”等社會問題。
農村出現了“地無人耕”和“人無地耕”的問題,為了深入挖掘農村土地資源的生產要素價值,保證農民穩步增收、糧食安全以及社會穩定的大局,2014年中央提出“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2016年國家發布政策文件,把土地所有權、土地承包權和土地經營權分開。“三權分置”相關政策辦法的頒布施行,是農村深化改革的內在需求,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是符合經濟規律的,奠定了鄉村振興的資源基礎。2018年12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七次會議通過了修改農村土地承包法的決議,為農村土地的三權分置的施行提供了法律支持。至此,農村土地三權分置的改革發展正式鋪開。
2三權分置的現實意義
農村土地的“三權”為土地的所有權、承包權及經營權。農村土地的所有權屬于集體,農民對土地享有承包權和經營權。“三權分置”的核心是土地的承包權和經營權分離,并且確保在集體所有制和農民承包經營權不變的基礎上,進行經營權流轉。承包經營權的再次分離是對我國農村土地制度的完善和創新,“三權分置”促使更多資本投資于農業生產,滿足不同階層農民生產生活與發展的多層次需求,農民可以在土地上自主經營種植符合國家政策規定的農作物,也可將土地流轉給生產大戶或企業進行規模種植生產。三權分置它們既有整合的效用,又各自賦有各自的功能。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制,不僅可以抑制不合理的征地行為,而且可以維護農戶的合法權益;又可以對土地資源進行集約利用,避免出現農業用地作非農業行為使用,以保障國家耕地不遭到不法侵害。
土地三權分置的制度順應了農民想要自主經營土地的意愿,也適應了農業現代化適度規模發展的需要,將土地承包經營權進行分置,農民能夠獲得土地承包權,同時也獲得自主經營權。這一舉措最大的突破在于將經營權放活,讓農民有了土地自己經營權,且又讓經營權有了合法的地位和依據,以保障農民進行自主生產經營土地的合法利益。
農村土地三權分置政策的實施,這對我國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意義。從制度的角度來說,既落實了農民對土地的承包權,又能夠增強農民自主經營的積極性,同時也保障了我國耕地合理高效集約利用。從經濟的角度來說,該制度的施行,促進了農戶進行承包地的經營積極性,提高了土地資源利用率和農業生產率,推動了鄉村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
3三權分置的現狀和問題
三權分置的政策和相關法規的出臺,讓經營權有了合法依據。據統計,截止2020年11月上旬,農業農村部公布,全國農村承包地確權頒證率已經達到96%,為進一步放活土地經營權打下了基礎。截止2020年底,我國農村土地經營權的流轉面積達到5.32億畝,占農村土地確權頒證面積35.5%,當前土地流轉總量偏低,仍存在大量的撂荒地,究其原因主要有土地碎片化、基層組織不完善、制度模糊性、城鄉發展不平衡等。
3.1土地碎片化,規模化經營較為困難
按照土地確權原則,是按照占地地塊進行劃分,政府向農戶辦理土地承包經營權證。農戶能夠自行選擇承包經營或流轉,如農戶自行進行經營,一般難以形成規模化生產;農業企業一般通過從農戶手中獲取地塊的經營權,但由于土地劃分到每一農戶,無法確保所有農戶愿意進行經營權流轉,農業企業經營主體難以獲得較大規模成片土地進行經營,規模效益、現代化技術措施等無法發揮效用,從而導致土地經營價值難以提高,最終,將阻礙農業現代化的建設進程。
3.2基層組織不完善,協調功能較弱
當前土地流轉大多是農戶之間進行流轉、農戶流轉給企業、村委會集體流轉給企業或個人或以土地入股方式流轉。農戶之間流轉、農戶流轉給企業,存在土地碎片化問題。村委會集體流轉給企業或個人,按照流轉辦法可以采用招標或協商的方式進行,如僅采用協商,存在一定的灰色地帶,農戶的經濟利益無法保障。根據新修訂的農村土地承包法,發包人在承包期內不得調整承包土地,,針對不愿流轉的農戶,村委會的協調功能無法有效發揮。
3.3制度模糊性,配套管理制度不全
結合中國《民法通則》及新《土地管理法》關于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相關規定,現階段,集體土地所有權包括村內農民集體、鄉鎮農民集體、村內多重農民集體(如村民小組等)。在城市化進程中,許多農民集體經濟組織已經不復存在或名義上存在,這就極大影響了農民集體行使所有權。此外,農村土地的所有權和用益物權并未有相關法規、制度或規定對此作出明確的解釋,這就導致了產權關系存在模糊和不確定性。如果土地承包經營權屬于“用益物權”,則土地經營權的法律權限不明確。土地流轉而進行規模化經營往往前期需要投入大量資金,擔保或抵押土地經營權用于申請貸款或融資時,金融機構往往難以受理,資金不足往往又會影響土地生產率,從而導致企業參與程度不高。另外對土地經營權的定價機制、交易規則等還未完全建立起來,三權分置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如何分配,部分農戶的過高期望,都將直接影響著三權分置政策最終的落地效果。
3.4城鄉發展的不平衡導致了農村發展的局限性
在工業化和城鎮化優先經濟發展的安排下,人口和土地等主要生產要素從農村單向過度流向城市。鄉村振興的最終歸宿是農業穩產增產、農民穩步增收、農村穩定安寧,而這一切都需要建立在農村經濟發展的基礎上。農村土地三權分置的目標是促進農村經濟發展,以實現鄉村振興。由于制度安排,過多的人口、土地、資源以及政策均傾向城市建設發展,從而出現當前城鄉發展在經濟水平、人居環境、保障制度等方面差距較大。城市生活成本高居不下、大中城市房價令人無法觸及,農業產業本身收益性較低,進城農民務工的不確定性,政府規劃及政策缺位等問題的存在,導致農村的發展局限。土地承包經營權作為農戶個人或家庭的最后保障,一些農民不愿意轉讓土地經營權。
4建議和改進措施
4.1完善相關法律制度和程序,明晰土地權屬相關制度
在法律層面上,土地所有權、經營權、承包權的權屬關系需要明確。針對不同權屬方頒發相應證書,并明確其權屬類型。一方面要讓基層集體組織能合法合理行使土地所有權的權限,避免土地碎片化而導致的規模化經營阻礙;另一方面,也要讓農戶合理行使土地承包權的收益或使用權;最后,也需要賦予土地經營權獲得者對應的自主經營、市場化運營的權限。同時,對土地經營流轉程序需進一步明確規范,要避免暴力流轉、違規流轉等問題的發生,確保農戶取得合理化的最大價值。
4.2明確基層黨組織權責,加強基層經濟合作社建設
農村采用的是民主自治的方針,基層黨組織要充分貫徹黨中央的惠農便農利農政策,承擔起助農扶農興農的重擔,為農業農村發展發揮作用。同時,要在基層黨組織的領導下,成立相應的基層經濟合作社建設,提高基層經濟組織的自我造血能力,不斷提高基層經濟組織的經濟效應,與基層黨組織一同完善農村的基礎設施、社會保障的建設。
4.3規范農村土地規劃,適當傾斜資源
農村土地的高效集約利用,鄉村振興的優先實施,必須建立在規范的農村土地資源規劃的基礎上。在鄉鎮層面,要充分結合村鎮實際,合理編制鄉村規劃,在確保不減少基本農田的同時統籌村鎮建設用地、宅基地、農地指標,確保在鄉村振興的道路上不過度開發;在市縣級政府層面,要充分給予鄉鎮規劃指導和資源鏈接,根據鄉鎮實際,進行鄉鎮合理定位,避免千篇一律;在省級政府層面,要統籌區域發展,有效控制基本農田總量,扶持和支持特色鄉鎮、資源貧瘠小鎮的發展;在國家層面,要統籌基本農田指標總量,立法層面為三權分置各主體提供律法保證,同時要適當提高農產品價格,為鄉村振興注入更多經濟活力。
參考文獻
[1]喬榛,焦方義,李楠. 中國農村經濟制度變遷與農業增長——對1978- 2004年中國農業增長的實證分析[J]. 經濟研究,2006(7):73-82.
[2]林毅夫. 李約瑟之謎、韋伯疑問和中國的奇跡——自宋以來的長期經濟發展[J]. 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4):5-22.
[3]陳紀平. 組織視角的中國農業規模化問題分析[J]. 中國經濟問題,2012(6):40-46.
[4]Feder Gershon. The relation between farm size and farm productivity:The role of family labor,supervision and credit constraints[J]. Economics,1985(2):297-313.
[5]袁方成,靳永廣.深化農地改革推進鄉村振興:關鍵問題與優化路徑[J]理論與改革,2020.4:139-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