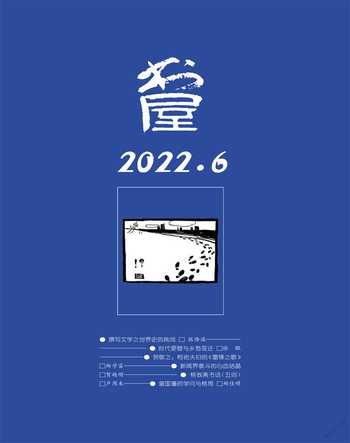時(shí)代更替與鄉(xiāng)愁變遷
徐鯤
鄉(xiāng)愁是人類的一種普遍情感,根植于故土家園和文化傳統(tǒng),連接人的生命來路,關(guān)乎人的心靈安放。有著安土重遷文化心理的中國人,鄉(xiāng)愁氣質(zhì)尤為濃厚。翻一翻中國古代文學(xué)作品便可發(fā)現(xiàn),作為古代文學(xué)主流的詩歌,鄉(xiāng)愁氣息撲面而來,兩千多年綿綿不絕。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無論詩歌、散文還是小說,鄉(xiāng)愁也是一個(gè)重要主題。文學(xué)是現(xiàn)實(shí)的折射,詩文反映的正是自古以來中國人揮之不去的鄉(xiāng)愁情結(jié)。隨著農(nóng)業(yè)文明向工業(yè)文明進(jìn)而向信息文明時(shí)代轉(zhuǎn)型,特別是進(jìn)入二十一世紀(jì)以后,城市化、網(wǎng)絡(luò)化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和國人的生活方式,古老的鄉(xiāng)愁也隨之發(fā)生巨大變遷。
中國自古就是一個(gè)農(nóng)業(yè)大國,中國文化植根于農(nóng)耕文化,如果說鄉(xiāng)土中國是中國的本色,那么農(nóng)耕文化則是中國文化的特質(zhì)。農(nóng)耕民族依賴并崇拜土地,并由此滋生對(duì)故土強(qiáng)烈的熱愛和依戀之情。農(nóng)耕文化崇尚安土重遷,除非不可抗拒的原因,如災(zāi)荒戰(zhàn)亂等。傳統(tǒng)的中國人不愿離鄉(xiāng)背井、漂泊異地。即便遠(yuǎn)走他鄉(xiāng),家鄉(xiāng)永遠(yuǎn)是心中的念想之地,到老也想著落葉歸根。哪怕在異鄉(xiāng)重新扎根、開枝散葉,族譜上也會(huì)記著祖祖輩輩的來龍去脈。如果后人有心,即使時(shí)光過去數(shù)百乃至上千年,還會(huì)跨越千山萬水尋根問祖。那些不得已漂泊在外的游子,如果是文人墨客,濃郁的鄉(xiāng)愁彌漫開來,化作文字便是一行行憂傷的詩句,一篇篇深情的文字。
早在中國文學(xué)的源頭《詩經(jīng)》和《楚辭》里,鄉(xiāng)愁就如長(zhǎng)江之水汩汩滔滔。“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這是對(duì)故鄉(xiāng)今昔變遷的感傷,也包含對(duì)漂泊人生的感嘆;屈原遠(yuǎn)離故鄉(xiāng)時(shí),憂傷彷徨,“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xiāng)。仆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李白的“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xiāng)”,已成中國人的鄉(xiāng)愁啟蒙詩句;杜甫的“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xiāng)明”,抒發(fā)的是人們對(duì)故鄉(xiāng)永恒的眷戀;“獨(dú)在異鄉(xiāng)為異客,每逢佳節(jié)倍思親”,表達(dá)了中國人最真切的思鄉(xiāng)思親情感;“共誰爭(zhēng)歲月,贏得鬢邊絲”,感慨離鄉(xiāng)太久,歲月無情;“故鄉(xiāng)今夜思千里,霜鬢明朝又一年”,既是對(duì)故鄉(xiāng)的思念,更是對(duì)親人的關(guān)切;“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bào)平安”,對(duì)于戍邊將士,平安是給故鄉(xiāng)親人最好的告慰;“不忍登高臨遠(yuǎn),望故鄉(xiāng)渺邈,歸思難收”,登高望鄉(xiāng)是游子思鄉(xiāng)最常見的行為表達(dá)方式,但有萬水千山阻隔,無限鄉(xiāng)愁像一杯烈酒只能自斟自飲,自飲自醉;“日暮鄉(xiāng)關(guān)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漂泊在外的游子迷茫時(shí),故鄉(xiāng)是溫暖的精神慰藉。翻開中國古代詩詞,鄉(xiāng)愁作品俯拾皆是,且歷代綿綿不絕,可謂鄉(xiāng)愁代代無窮已。不夸張地說,一部中國古代詩歌史,假如沒有鄉(xiāng)愁抒寫,思想和藝術(shù)將大為遜色。
中國古代盛產(chǎn)鄉(xiāng)愁詩歌,一方面源于中國的鄉(xiāng)土文化和最基本的思鄉(xiāng)戀家情結(jié);另一方面是基于古代比較落后的生產(chǎn)力,特別是落后的交通方式和通信方式。在古代交通不便,信息閉塞,人一旦離開故鄉(xiāng),基本和故鄉(xiāng)斷絕了聯(lián)系,故鄉(xiāng)發(fā)生的一切幾乎都難以知曉,即便知曉家園變故,但想要從遠(yuǎn)方回到故鄉(xiāng),也是路途漫漫、行程日久。因此,游子在外越久,鄉(xiāng)愁越濃。也因?yàn)楣枢l(xiāng)和異鄉(xiāng)之間音信不通,所以古人普遍會(huì)有“近鄉(xiāng)情怯”的微妙情緒,時(shí)間和空間的阻隔,讓故鄉(xiāng)變得“陌生”,返鄉(xiāng)的游子一旦走近故鄉(xiāng),不可預(yù)知的事總讓人內(nèi)心忐忑不安。個(gè)人認(rèn)為,古代中國人,除了主觀上對(duì)家鄉(xiāng)的思念之外,客觀上交通不便和信息不暢放大了思鄉(xiāng)之情,空間阻隔和信息閉塞極大地強(qiáng)化了鄉(xiāng)愁情結(jié)。
到了近現(xiàn)代,雖然交通條件不斷改善,以及通信聯(lián)絡(luò)方式逐漸進(jìn)步,客觀上緩解了思鄉(xiāng)之苦,但鄉(xiāng)愁作為一種深沉的情結(jié),依然沉淀在國人的血脈中。在文學(xué)及藝術(shù)作品里,書寫和歌唱故鄉(xiāng)仍然是一個(gè)重要的主題。現(xiàn)當(dāng)代作家以鄉(xiāng)愁為主題的作品不計(jì)其數(shù),例如魯迅的小說《故鄉(xiāng)》、周作人的散文《故鄉(xiāng)的野菜》、老舍的散文《想北平》、汪曾祺的《故鄉(xiāng)的食物》系列散文、張抗抗的散文《故鄉(xiāng)在遠(yuǎn)方》、黃河浪的散文《故鄉(xiāng)的榕樹》、余光中的詩歌《鄉(xiāng)愁》、司馬中原的散文《握一把蒼涼》等。至于歌唱故鄉(xiāng)的歌曲更是難以計(jì)數(shù),例如許多年前程琳演唱的《故鄉(xiāng)情》、費(fèi)玉清演唱的《夢(mèng)駝鈴》、費(fèi)翔演唱的《故鄉(xiāng)的云》、韓紅演唱的《家鄉(xiāng)》,以及近些年許巍創(chuàng)作并演唱的《故鄉(xiāng)》,都傳唱一時(shí),深入人心。這些文藝作品傳承古老的鄉(xiāng)愁情結(jié),書寫或歌唱永恒的鄉(xiāng)土鄉(xiāng)情。“一個(gè)士兵,要不戰(zhàn)死沙場(chǎng),便是回到故鄉(xiāng)。”這是沈從文墓碑上的碑文,不僅抒發(fā)了逝者對(duì)故鄉(xiāng)鳳凰的至深情感,同樣也表達(dá)了中國人深沉的故土情結(jié)。
二十世紀(jì)上半葉,中華民族內(nèi)憂外患,連綿不斷的戰(zhàn)爭(zhēng)造成了無數(shù)國人背井離鄉(xiāng)。他們中有的遠(yuǎn)走異國他鄉(xiāng),更多的走向海峽對(duì)岸。雖然臺(tái)灣海峽在現(xiàn)代算不上天塹,但它將兩岸中國人無情分離,在中國人心頭劃上一道深深的傷口,至今未能愈合。游子漂洋過海,因?yàn)楸娝苤脑颍屑也荒軞w,催生了海峽對(duì)岸同胞的另一種鄉(xiāng)愁,這種鄉(xiāng)愁除了延續(xù)千百年來的基本鄉(xiāng)情之外,還飽含民族情、骨肉情和歷史傷痛。遠(yuǎn)走臺(tái)島的同胞創(chuàng)作了大量懷念故鄉(xiāng)的文學(xué)和藝術(shù)作品,催生了一股不大不小的鄉(xiāng)愁文藝思潮,如上文提及的余光中的《鄉(xiāng)愁》,以及梁實(shí)秋的《北平的冬天》、林海音《城南舊事》、琦君的《水是故鄉(xiāng)甜》等,都是鄉(xiāng)愁文學(xué)的代表作品;《夢(mèng)駝鈴》《爸爸的草鞋》《鄉(xiāng)愁四韻》等是鄉(xiāng)愁歌曲的代表作。在諸多臺(tái)灣鄉(xiāng)愁作品中,國民黨元老于右任的《望大陸》最令人感動(dòng):“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xiāng);故鄉(xiāng)不可見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故鄉(xiāng)情、家國情和歷史的傷痛融于詩中,字里行間灑滿淚水,令人動(dòng)容。
中國傳統(tǒng)社會(huì)是一種“超穩(wěn)定結(jié)構(gòu)”,鄉(xiāng)土?xí)r代的中國,社會(huì)發(fā)展相對(duì)緩慢,人們生活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慢節(jié)奏的環(huán)境中,社會(huì)環(huán)境變化十分緩慢,因而鄉(xiāng)愁也相對(duì)單純穩(wěn)定。戰(zhàn)爭(zhēng)和自然災(zāi)害是鄉(xiāng)土社會(huì)最大的變數(shù),其破壞性和劇變性足以成為鄉(xiāng)愁的催化劑,能給人造成巨大的心靈創(chuàng)傷。
二十世紀(jì)七八十年代開啟的改革開放極大地加快了中國的發(fā)展進(jìn)程,中國逐漸由農(nóng)業(yè)大國走向工業(yè)大國(制造業(yè)大國),從農(nóng)業(yè)文明時(shí)代逐漸走向工業(yè)文明時(shí)代,進(jìn)而開始走向信息文明時(shí)代,鄉(xiāng)土中國正逐步轉(zhuǎn)型為城市中國。四十多年來,中國發(fā)生了前所未有的巨變,速度之快,變化之大,可謂翻天覆地。這種巨變其實(shí)就是一部鄉(xiāng)土社會(huì)快速城市化的歷史,是一部鄉(xiāng)下人大規(guī)模進(jìn)城的歷史——農(nóng)村人口不斷向城市流動(dòng),城市人口不斷增加,城市面積不斷膨脹,而代價(jià)是傳統(tǒng)鄉(xiāng)村的逐漸衰落,村落減少,人口外遷;同時(shí),城市自身也不斷“棄舊圖新”,大量傳統(tǒng)民居和舊街老巷消失。據(jù)統(tǒng)計(jì),1949—1978年的近三十年間,我國城市化率僅從百分之十點(diǎn)六提升至百分之十七點(diǎn)九,增長(zhǎng)非常緩慢;而1978—2020年四十余年里,城市化率從百分之十七點(diǎn)九增長(zhǎng)到百分之六十三點(diǎn)八九,增速遠(yuǎn)遠(yuǎn)超過前三十年。今天,城市化時(shí)代已然到來。
城市化是一個(gè)國家和地區(qū)走向現(xiàn)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國城市化的背后是數(shù)以億計(jì)的農(nóng)村人離開鄉(xiāng)土家園。他們主動(dòng)或被動(dòng)走向城市,交織著歡喜與憂愁、希望與失落。在巨大的城市化浪潮中,有無數(shù)鄉(xiāng)土村居和自然村落逐漸被冷落荒廢,田園大量廢棄荒蕪。著名作家馮驥才多年來致力于保護(hù)傳統(tǒng)文化,特別是傳統(tǒng)村落和民居。據(jù)他調(diào)查,在2000—2010年,我國自然村從大約三百六十萬個(gè)減少到二百七十萬個(gè),十年間就消失了近九十萬個(gè)自然村,數(shù)字令人觸目驚心。2010年至今,十多年過去了,自然村落減少的狀況仍在持續(xù)。無數(shù)自然村落的消失意味著承載家園的鄉(xiāng)土也隨之消失,族親、鄉(xiāng)親關(guān)系將漸漸消散,鄉(xiāng)土民俗也隨風(fēng)而去,曾經(jīng)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們,鄉(xiāng)愁已無處安放。那些尚未荒廢消失的村莊,也多是一片清冷,往日孩童滿村、人丁興旺的景象不復(fù)存在,曾經(jīng)的鄉(xiāng)村風(fēng)情多已凋零,即使到了一年中最熱鬧的春節(jié),也無法重現(xiàn)往日的熱鬧。平日里留守家園的基本都是空巢老人、留守兒童和部分中年婦女,這些弱勢(shì)群體駐守家園,更襯托出鄉(xiāng)村的落寞。伴隨鄉(xiāng)村的相對(duì)衰落,鄉(xiāng)土文化漸漸式微,鄉(xiāng)村根脈岌岌可危,鄉(xiāng)愁也越來越難以歸附。
對(duì)于數(shù)以億計(jì)進(jìn)城的鄉(xiāng)下人來說,城市既是生存機(jī)遇,也是生存壓力所在,城市文化和鄉(xiāng)土文化之間的矛盾與張力不是一時(shí)半會(huì)兒就能消失的。無數(shù)置身城市的鄉(xiāng)下人特別是年輕人,大體都有類似的感受:家鄉(xiāng)回不去,城市又留不下,或者詩意地說:家鄉(xiāng)容不下肉身,他鄉(xiāng)容不下靈魂。家鄉(xiāng)已經(jīng)巨變,父老鄉(xiāng)親有的已遷居城市,有的已衰老或離開人世;城市又沒有自己的根,他們儼然是漂著的群體,鄉(xiāng)愁即便是有也無處安放。第七屆魯迅文學(xué)獎(jiǎng)獲獎(jiǎng)作品中篇小說《儺面》(作者肖江虹)講述了這樣一個(gè)故事:年輕的山村女子顏素容,向往城市生活,離開家鄉(xiāng)去了省城貴陽,在繁華的都市迷失自我患上絕癥。抱著“葉落歸根”的心態(tài)回到家鄉(xiāng),在“等死”的日子里,她變得暴戾乖張,對(duì)父母和鄉(xiāng)親惡語相向,以此來尋求早日自絕于人世。顏素容還曾上吊自殺,但被傳統(tǒng)手藝人儺面制作師秦安順老人救下,而秦安順老人對(duì)幾近失傳的儺面手藝的堅(jiān)守,也讓顏素容獲得活下去的勇氣。秦安順去世后,她自覺保留老人的絕世作品“伏羲面具”。小說生動(dòng)地表現(xiàn)了城市文化與鄉(xiāng)土文化的根本矛盾,也反映了鄉(xiāng)下人在城市的尷尬處境。顏素容的肉體和精神被故鄉(xiāng)拯救,其實(shí)是被鄉(xiāng)愁拯救。
對(duì)于根在鄉(xiāng)村,寄居城市的人來說,慰藉鄉(xiāng)愁的最佳時(shí)機(jī)是傳統(tǒng)節(jié)日,最好的慰藉方式是回到故鄉(xiāng),盡管故鄉(xiāng)已經(jīng)物是人非,但那片土地還在,至少還可以勾起往日的回憶。所以,每到清明節(jié),無數(shù)身在外鄉(xiāng)的人手捧鮮花和祭品趕回故鄉(xiāng),在祖輩父輩的墳前表達(dá)追思。這追思表達(dá)的既是親情也是鄉(xiāng)愁,祖輩父輩們出生成長(zhǎng)的鄉(xiāng)土,正是鄉(xiāng)愁縈繞的地方。另一個(gè)重要的傳統(tǒng)節(jié)日中秋節(jié),以親人團(tuán)圓為旨?xì)w。遠(yuǎn)離故鄉(xiāng)的兒女們,只要時(shí)間允許都會(huì)趕回家鄉(xiāng)和親人團(tuán)聚。“但愿人長(zhǎng)久,千里共嬋娟”,無法回家團(tuán)聚的游子,只能用思念聊慰鄉(xiāng)愁。在中國傳統(tǒng)節(jié)日中,春節(jié)最為盛大隆重,也是萬家團(tuán)圓的喜慶日子,最能引發(fā)國人的鄉(xiāng)愁情緒。節(jié)前數(shù)以億計(jì)的中國人從城市返回鄉(xiāng)村,或者說從異鄉(xiāng)回到故鄉(xiāng),故鄉(xiāng)面貌的改變、家人的變故、童年的記憶、鄉(xiāng)村的現(xiàn)狀等,都會(huì)喚起全民性的集體鄉(xiāng)愁。前些年每到春節(jié)時(shí)期,各種返鄉(xiāng)筆記在網(wǎng)上熱傳一時(shí),例如《一個(gè)農(nóng)村兒媳眼中的鄉(xiāng)村圖景》(作者黃燈)、《一位博士生的返鄉(xiāng)筆記》(作者王磊光)。這種集體性的鄉(xiāng)愁回憶折射出鄉(xiāng)土社會(huì)走向城市化時(shí)代產(chǎn)生的諸多社會(huì)問題。
其實(shí),鄉(xiāng)愁并非只是遷居外地的農(nóng)村人的專利,城市人的心頭同樣縈繞著如煙似霧的鄉(xiāng)愁。快速城市化進(jìn)程讓中國城市日新月異,但巨變的背后是大量的舊城區(qū)、老街古巷和各種古老人文景觀的消失。老街古巷等承載著城市中老年人的許多美好記憶,如今它們大多被密密麻麻的高樓大廈取代。比鄉(xiāng)下人更尷尬的是,城里人想找個(gè)童年生活的老地方懷舊都不容易,而在農(nóng)村至少童年的那方水土基本還在,雖然面目已不復(fù)當(dāng)年。學(xué)者王曉明在談及他的博士生王磊光的返鄉(xiāng)筆記時(shí)說:“在思鄉(xiāng)這件事上,今日中國的城里人,是比鄉(xiāng)下人更可悲憫的。今日上海的本地人,有多少還有舊居老街可以回去探訪?十不存一吧!當(dāng)在電視上看到返鄉(xiāng)人風(fēng)塵仆仆的時(shí)候,像我這樣的上海本地人有沒有想過,自己其實(shí)更可憐,是連故鄉(xiāng)都蕩然無存、只能靠記憶摸索‘過去’的無根族!”(2015年6月10日《中國民航報(bào)》)。城市化時(shí)代,對(duì)于許多都市人來說,鄉(xiāng)愁薄如煙,輕如霧,若有若無,有些人已沒有了“故鄉(xiāng)”,沒有了歸屬感,也沒有了鄉(xiāng)愁,他們是人海中的浮萍。
進(jìn)入二十一世紀(jì),隨著信息技術(shù)的快速發(fā)展,中國和世界一起進(jìn)入互聯(lián)網(wǎng)時(shí)代。互聯(lián)網(wǎng)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狀態(tài),點(diǎn)擊鼠標(biāo),天涯海角近在眼前,地球已變成了“地球村”。電腦和智能手機(jī)的普及使“天涯若比鄰”成為現(xiàn)實(shí),路途遙遙曾經(jīng)只能夢(mèng)中思念的故鄉(xiāng),如今可以隨時(shí)“掌”握。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時(shí)代,人和世界的距離就是眼睛到屏幕的距離,故鄉(xiāng)、親友、過去的時(shí)光在屏幕中似乎觸手可及,鄉(xiāng)愁似乎在屏幕前就能得到釋放。近幾年,網(wǎng)紅女孩李子柒拍攝的有關(guān)鄉(xiāng)村生活的短視頻之所以大受追捧,就是因?yàn)樗高^屏幕讓人近距離感受到鄉(xiāng)村生活,滿足了人們對(duì)鄉(xiāng)村的美好回憶和想象,慰藉了鄉(xiāng)愁。與此同時(shí),快速的交通工具也改變了人們的出行方式。私家車已進(jìn)入尋常百姓家,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四通八達(dá),飛機(jī)更是風(fēng)馳電掣,遠(yuǎn)隔千里的故鄉(xiāng),今天可以“千里江陵一日還”,萬水千山已不再成為鄉(xiāng)愁的阻隔。
從表面上看,便捷的音頻、視頻和文字聯(lián)系一定程度上疏解了人們的鄉(xiāng)愁。家鄉(xiāng)的變化,親人的現(xiàn)狀,輕點(diǎn)手機(jī)屏幕就能了解。鄉(xiāng)土?xí)r代因時(shí)空隔閡造成的“近鄉(xiāng)情更怯”的心理,現(xiàn)在已不再具有普遍性。然而,互聯(lián)網(wǎng)時(shí)代溝通的便捷并不表明古老的鄉(xiāng)愁已經(jīng)消散,事情并沒有表面看起來那么簡(jiǎn)單。鄉(xiāng)愁雖然關(guān)涉物質(zhì)條件,但主要是精神層面的東西,與之緊密相關(guān)的是鄉(xiāng)土文化、傳統(tǒng)文化和往昔記憶。便捷的交通和信息可以拉近人和故鄉(xiāng)的空間距離,但無法讓已逝去的人和事的重現(xiàn),無法讓昔日重來。詩人流沙河認(rèn)為余光中的詩歌《鄉(xiāng)愁》抒發(fā)的是時(shí)間上的鄉(xiāng)愁,這種鄉(xiāng)愁可以回味,卻無法彌補(bǔ),而空間上的鄉(xiāng)愁可以通過返鄉(xiāng)來彌補(bǔ)。雖然手機(jī)和電腦可以有限彌補(bǔ)空間上的鄉(xiāng)愁,但對(duì)時(shí)間上的鄉(xiāng)愁基本無能為力。因此,從根本上講,無論網(wǎng)絡(luò)和交通如何發(fā)達(dá)便捷,都無法根本解除人類的鄉(xiāng)愁情結(jié)。
實(shí)際上,鄉(xiāng)愁與社會(huì)發(fā)展往往成反向關(guān)系,社會(huì)變化越劇烈越頻繁,縈繞在人們心頭的鄉(xiāng)愁越濃郁。這道理類似于科技提升了人的物質(zhì)生活水平,卻無法解決人的精神痛苦一樣。就全世界而言,雖然人類物質(zhì)生活已相當(dāng)豐富,但人類的幸福感并不一定同步提升,自殺率并沒有因此下降,有的國家甚至還有上升。這似乎是一個(gè)悖論。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時(shí)代,手機(jī)電腦可以讓我們和故鄉(xiāng)時(shí)刻保持在線,親人的一舉一動(dòng)、故鄉(xiāng)的一草一木都近在眼前,但快速變化的時(shí)代,那些烙印著人的生命記憶的東西最容易消逝,最容易讓人產(chǎn)生失落感和空虛感。對(duì)于敏感的個(gè)體,深層的鄉(xiāng)愁絕不會(huì)因物質(zhì)條件的改善而消逝,有時(shí)還可能相反。互聯(lián)網(wǎng)里的虛擬世界,可以帶給我們無盡的喜怒哀樂,但里面有許多是虛幻的泡沫,深層的鄉(xiāng)愁有時(shí)可能被娛樂化、庸俗化,嚴(yán)肅的感情也可能被消遣,變成一地雞毛。所以,手機(jī)電腦之于鄉(xiāng)愁是利弊互現(xiàn)的。屏幕太小,鄉(xiāng)愁太沉,“載不動(dòng),許多愁”。網(wǎng)絡(luò)時(shí)代,手機(jī)和電腦看似拉近了人和故鄉(xiāng)的空間距離,但歲月和生命依舊流逝,鄉(xiāng)愁依舊難解。
流沙河在《臺(tái)灣鄉(xiāng)愁詩歌選》序言中將鄉(xiāng)愁分為三種:第一種鄉(xiāng)愁,即是出于戀巢的本性,是起碼的鄉(xiāng)愁;加上對(duì)生命的敏感,悲歲月的流失,就產(chǎn)生了第二種鄉(xiāng)愁,深層的鄉(xiāng)愁;第三種鄉(xiāng)愁,就如余光中的《呼喚》,比前兩種更深的,是文化的鄉(xiāng)愁,這種鄉(xiāng)愁既是一種感情,又是一種覺悟,常人少有,智者或有之。我認(rèn)為,不管哪種鄉(xiāng)愁,都值得我們珍視。人之所以為人,鄉(xiāng)愁就是“今生今世的證據(jù)”之一。“胡馬依北風(fēng),越鳥巢南枝”,動(dòng)物尚且如此,何況萬物之靈的人類。
今天,不管是鄉(xiāng)村還是城市,發(fā)展變化是時(shí)代主流,不可阻擋。發(fā)展過程中,承載鄉(xiāng)愁的鄉(xiāng)土民俗、傳統(tǒng)文化(物質(zhì)的、非物質(zhì)的)等必然面臨著考驗(yàn)和挑戰(zhàn),但這并不表示我們只能空懷愁緒,無能為力。在物質(zhì)富足、科技發(fā)達(dá)的時(shí)代“留住”鄉(xiāng)愁,我們是能夠有所作為的。比如,在財(cái)力充足的條件下,可以較好地保護(hù)古城古鎮(zhèn)、古街老巷、傳統(tǒng)技藝等,建設(shè)紀(jì)念館、博物館等;先進(jìn)的數(shù)字技術(shù)可制作有關(guān)物質(zhì)和非物質(zhì)文化的視頻、音頻和圖片,留下珍貴的影像資料。事實(shí)上,近些年來為留住傳統(tǒng)文化、記住鄉(xiāng)愁,國家做了大量有價(jià)值的工作,例如自2015年起開始制作大型系列紀(jì)錄片《記住鄉(xiāng)愁》,每年一季,今年已是第八季,總共已播出了近五百集(每周一集)。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在當(dāng)下美麗鄉(xiāng)村建設(shè)中,一些地方也進(jìn)行了可貴的探索,如突出鄉(xiāng)村特色,保持田園風(fēng)貌,體現(xiàn)地域文化風(fēng)格,注重農(nóng)村文化傳承等。有的鄉(xiāng)村在建設(shè)過程中堅(jiān)持不砍樹、不填塘、不占田、慎拆房,盡可能避免大拆大建,保護(hù)好古樹、老屋、舊物件,最大程度地守住鄉(xiāng)村之魂。一些城市對(duì)古街老巷、民居民俗和傳統(tǒng)技藝的保護(hù)也頗有成效。
雖然快速發(fā)展的時(shí)代讓世界變動(dòng)不居,我們不可能將過去的一切全都完好地保留,然而當(dāng)所有的舊物都消失殆盡的時(shí)候,我們的鄉(xiāng)愁又何以安放?正如作家劉亮程在散文《今生今世的證據(jù)》里所言:“當(dāng)家園廢失,我知道所有回家的腳步都已踏踏實(shí)實(shí)地邁上了虛無之途。”所以,不管社會(huì)如何發(fā)展演變,我們的心中該有一條路,它通往故鄉(xiāng)、通往生命的過往。回望來路不僅僅為了緬懷,而是為了更好地面向前方。我們匆匆趕路,不能忘了當(dāng)初為什么出發(fā)。同時(shí),不管物質(zhì)生活如何富足,我們的身外該擁有一個(gè)地方:那里有我們美麗的家園,有傳統(tǒng)文化的根脈;那里望得見青山,看得見綠水,留得住鄉(xiāng)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