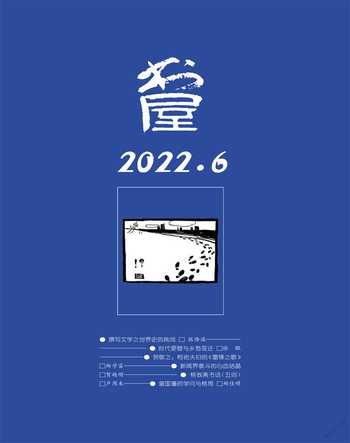“準(zhǔn)販東西洋”:晚明的海外貿(mào)易
齊悅
中華文明兼容并包,大量吸收外來文化。唐、宋時(shí)期,我國對(duì)外高度開放,陸上交通、海上絲綢之路,使得無論官方還是民間,對(duì)外交流都十分頻繁。元朝時(shí)期依舊遵循前朝舊制,對(duì)外政策一直較為寬松。
明朝開國伊始,沿襲宋、元方針,對(duì)外交流頻繁,載滿生絲、茶葉、香料、象牙、瓷器的中外商船穿梭于海洋之上,促進(jìn)中外文化和物資交流,后因沿海倭寇泛濫、海面不靖等政治軍事因素,開始實(shí)施“片板不許下海”的海禁政策,封鎖對(duì)外往來。永樂年間,朝廷將民間海船“悉改為平頭船”,使其無法遠(yuǎn)航;禁止近海人民建造三桅以上大船下海與外國貿(mào)易,違者照謀逆罪處斬。海禁政策作為祖訓(xùn)載入《大明律》,被后世子孫長期遵循,也為近代中國的自閉與落后埋下伏筆。
明朝在實(shí)行海禁的同時(shí)建立以明朝為中心的朝貢體系。朝貢制度是在民間海外貿(mào)易往來受阻的情況下,由中央制定的官方對(duì)外貿(mào)易管理制度。它滿足了明朝對(duì)海外物品的需求,也便于受理海外藩國的貢賦繳納之事。因此,明前期海洋管理政策是在政府強(qiáng)制實(shí)行的海禁之下,由官方主導(dǎo)開展實(shí)施朝貢制度,進(jìn)行中外貿(mào)易往來。
1370年,明廷在廣東廣州、福建泉州、浙江寧波設(shè)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諸國朝貢和貿(mào)易事務(wù)。1374年,由于倭寇問題嚴(yán)重,明朝停擺這三處市舶司。明成祖即位后,一改朱元璋保守的對(duì)外政策,1403年下令恢復(fù)了三市舶司。1408年,三市舶司分別建懷遠(yuǎn)驛、來遠(yuǎn)驛和安遠(yuǎn)驛,以更好地接待貢使,彰顯大明朝國威。1408年,朝廷設(shè)交趾云屯市舶司。市舶司主管朝貢貿(mào)易,負(fù)責(zé)查驗(yàn)貢使身份、安排食宿及抽分征稅等。與此同時(shí),明成祖組織了大規(guī)模的遣使海外外交活動(dòng),特別是鄭和七下西洋,開辟了經(jīng)印度洋到達(dá)西亞和非洲東海岸的遠(yuǎn)航航線,廣泛進(jìn)行友好交往,朝貢貿(mào)易盛極一時(shí)。
明朝初年,朝貢制度和海禁相輔相成,成為明朝處理對(duì)外關(guān)系的基本政策。朝貢貿(mào)易成本極高且不合經(jīng)濟(jì)規(guī)律,明中期以后,朝貢制度逐漸衰落,而后繼統(tǒng)治者仍嚴(yán)厲踐行著海禁政策。嘉靖年間,英國的都鐸王朝正極力推行拓海政策,中國的海禁卻達(dá)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嘉靖皇帝曾下令“一切違禁大船,盡數(shù)毀之”,“沿海軍民私與賊市,其鄰舍不舉者連坐”。
“海禁愈嚴(yán),賊伙愈盛”,沿海奸商滑民因商道不通,無以為生,在嚴(yán)苛法律與巨大利益的共同刺激下,私人海外貿(mào)易被迫畸形發(fā)展,從過去的合法商業(yè)活動(dòng)轉(zhuǎn)向走私乃至武裝走私,并出現(xiàn)了一些大的海上武裝走私集團(tuán)。沿海的農(nóng)民、漁民“資衣食于海”,也因“海禁太嚴(yán),漁樵不通”而生活艱難,迫于生計(jì)而投入倭寇的懷抱,形成了三分真倭,七分假倭的罕見歷史景象,且假倭的騷擾規(guī)模和次數(shù),遠(yuǎn)高于真倭。
嘉靖年間,最大的海賊頭目王直、徐海,都是從事海外貿(mào)易的徽州商人。王直擁眾數(shù)十萬,先稱“靖海王”,后稱“徽王”,“南面稱孤”,與大明王朝分庭抗禮。倭寇之亂,屢打不絕,王直之后,吳平繼之,吳平死后,曾一本興起,造成曠日持久的“倭寇之亂”。
世界的另一邊正在發(fā)生著驚天動(dòng)地的社會(huì)變革,新航路的開辟,大航海時(shí)代的到來,西方殖民者的東進(jìn),促使先進(jìn)的知識(shí)分子開始對(duì)海防及海禁政策進(jìn)行重新審視和思考。有識(shí)之士逐漸認(rèn)識(shí)到倭亂的根本原因在于商業(yè)問題,連年倭患皆因私通貿(mào)易而起,“市通則寇轉(zhuǎn)而為商,市禁則商轉(zhuǎn)而為寇”。血的教訓(xùn)表明,如果不想逼良為盜,只能調(diào)整海禁政策。他們認(rèn)為開海不僅可以消弭倭患,穩(wěn)定沿海社會(huì),也可富國裕民,充裕國庫和民眾收入。此外,開海貿(mào)易與海外各國交流往來,洞悉海外習(xí)聞動(dòng)靜,知己知彼,有備無患。
嘉靖年間,福建巡撫譚綸就在閩地放寬海禁,允許百姓近海捕魚、經(jīng)商,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沿海人民私通倭寇。繼任的巡撫涂澤民繼承譚綸的海防思想,隆慶初年,他毅然上疏請(qǐng)求開放海禁,允許沿海商民與外國商人開展貿(mào)易。
隆慶皇帝登基之初,銳意改革,內(nèi)閣輔臣高拱、趙貞吉、張居正皆治世之能臣,在內(nèi)政外交上做了大刀闊斧的改革,而困擾明帝國數(shù)十年之久的“南倭北虜”問題必然成為政治改革的重點(diǎn)。高拱、張居正等內(nèi)閣輔臣也意識(shí)到,沿海平倭戰(zhàn)爭(zhēng)源于貿(mào)易限制,無論是嘉靖年間的王直、徐海,還是曾一本、林鳳,曠日持久的“倭寇之亂”令政府消耗了大量財(cái)力物力,四處圍剿終究是治標(biāo)不治本的應(yīng)急之策,必須轉(zhuǎn)變思想,調(diào)整對(duì)外政策,以一種全新的方式維護(hù)地區(qū)和平。
隆慶皇帝聽從高拱、張居正之建議,起草詔書宣布“除販夷之律”,選擇東南隅的福建月港作為中外貿(mào)易的窗口,厲行二百年之久的海禁政策終于被打破,為海上貿(mào)易活動(dòng)開啟綠燈。這次開海無論在中國古代經(jīng)濟(jì)史上還是對(duì)外貿(mào)易史上都極為重要,史稱“隆慶開關(guān)”。
海澄月港位于漳州府城東南,地處沿海,“外通海潮,內(nèi)接山澗”,“其地之形水縈之如月然”,故而得名月港,唐、宋以降即稱“海濱一大聚落”。成、弘之際,月港已成為走私貿(mào)易的基地,“趁舶風(fēng)轉(zhuǎn),寶貨塞途,家家歌舞賽神,鐘鼓管弦,連飚響答。十方巨賈,競(jìng)鶩爭(zhēng)馳”,已有“小蘇杭”之稱。嘉靖年間葡萄牙人在福建海商的誘導(dǎo)下轉(zhuǎn)移到月港,夏來冬去,往來販易,月港成為福建走私貿(mào)易的重要據(jù)點(diǎn)。
明政府在月港開禁,準(zhǔn)許私人出海貿(mào)易。福建政府以月港為治所設(shè)立海澄縣,設(shè)立專門負(fù)責(zé)管理私人海外貿(mào)易的督餉館,并對(duì)其征收關(guān)稅。考慮到日本經(jīng)常侵犯沿海,對(duì)日貿(mào)易仍在禁止之列,所有出海船只均不得前往日本。若私自前往,則處以“通倭”之罪。
開海政策雖仍有諸多限制,開放的月港也只是一處小港口,但民間私人海外貿(mào)易畢竟已獲得朝廷的認(rèn)可,只要遵守政府的管制,民間私人海外貿(mào)易就被視為合法經(jīng)營。海外貿(mào)易政策的調(diào)整,突破了朝貢貿(mào)易的局限,帶動(dòng)了海外貿(mào)易的迅速發(fā)展,從月港進(jìn)出口的商品種類豐富,月港陸?zhàn)A收稅商品就多達(dá)上百種,有龜筒、西洋布、玻璃瓶等工藝品;胡椒、木香、丁香、蘇木、檀香、奇楠香、象牙等奢侈品;也有冰片、阿魏、沒藥等藥材;還有虎豹皮、獐皮、孔雀尾、紅銅等原料。
每年春夏之季,十余萬中國海商從月港揚(yáng)帆起航,盛況空前,出洋商船“大者,廣可三丈五六尺,長十余丈;小者,廣二丈,長約七八丈”,“澄商引船百余只,貨物億萬計(jì)”。當(dāng)時(shí)主要的海外貿(mào)易基地是菲律賓,菲律賓首府馬尼拉與月港的距離較近,更主要的是西班牙殖民者開辟了從馬尼拉至墨西哥阿卡普爾科的大帆船貿(mào)易航線,把墨西哥銀元載運(yùn)至馬尼拉,換取中國的手工業(yè)品。大量的福建商船載著中國商品從月港載運(yùn)至馬尼拉,然后由西班牙大帆船轉(zhuǎn)運(yùn)到拉美和歐洲各地,中國產(chǎn)品已成為拉美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時(shí),月港貿(mào)易也促進(jìn)了拉美地區(qū)的經(jīng)濟(jì)繁榮,作為大帆船貿(mào)易終點(diǎn)的阿卡普爾科隨著大帆船的到來而逐漸繁榮。荷蘭東印度公司將中國的生絲和絲織品,從月港轉(zhuǎn)販到日本及東南亞各地。
明朝的絲織品、瓷器、茶葉、鐵器等遠(yuǎn)銷海外,廣受世界各國歡迎,白銀大量流入明朝。據(jù)估計(jì),在此后的七十余年間,自葡萄牙、西班牙、日本等國輸入明朝的銀元,至少在一億元以上,有力地促進(jìn)了明朝國內(nèi)商品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促進(jìn)了民生改善和社會(huì)進(jìn)步。在世界形成一個(gè)整體的歷史進(jìn)程中,月港使中國市場(chǎng)與世界市場(chǎng)連接起來。
西方學(xué)者丹尼斯·弗萊恩和阿拉圖羅·熱拉爾德茲提出,世界貿(mào)易在1571年即明隆慶五年誕生。當(dāng)世界逐漸形成一個(gè)整體之時(shí),一個(gè)世界經(jīng)濟(jì)體系也隨之產(chǎn)生了。這個(gè)體系不是西方創(chuàng)造的,明代中國曾積極參與世界經(jīng)濟(jì)體系的初步建構(gòu),為整體世界的出現(xiàn)作出了重要貢獻(xiàn)。
誠然,從隆慶元年“準(zhǔn)販東西二洋”,到萬歷年間月港對(duì)外貿(mào)易長達(dá)半個(gè)世紀(jì),形成獨(dú)具地方特色的月港體制。福建商民利用這個(gè)通道,大規(guī)模出海經(jīng)商貿(mào)易,進(jìn)而移居南洋、日本,不僅在華商中一枝獨(dú)秀,而且成為南海貿(mào)易中強(qiáng)勁的海上勢(shì)力。海禁的解除,海外貿(mào)易的開展,增加了明朝廷的收入,也促進(jìn)了商品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然而,月港體制也有相當(dāng)?shù)木窒蓿粶?zhǔn)福建商人出海貿(mào)易,不許外國商人入境通商,可見月港模式并不是完全徹底的開放,而只是一種局部開放,這無疑限制了外貿(mào)的受惠面,影響著對(duì)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
廣東擁有漫長的海岸線,港口眾多,素有對(duì)外貿(mào)易傳統(tǒng)。與月港體制不同的是,廣東不準(zhǔn)私人出海貿(mào)易,只允許外商前來貿(mào)易。嘉靖年間,廣州每年定期舉辦貿(mào)易會(huì),允許葡萄牙人到廣州城買賣物品。“隆慶開關(guān)”鼓舞了廣東商人,地方政府雖明面禁止私人出海,可廣東出海人數(shù)也逐年增加。
隨著形勢(shì)的發(fā)展變革,廣東當(dāng)局也逐漸調(diào)整對(duì)外貿(mào)易政策。萬歷六年,兩廣總督凌云翼提請(qǐng)?jiān)谕咨铺幹煤=闆r下,準(zhǔn)許商人出海貿(mào)易。
這時(shí)的明王朝正值“江陵柄政”時(shí)期,內(nèi)閣首輔張居正勵(lì)精圖治,攘內(nèi)安外,基本平定了山賊海寇。張居正認(rèn)為廣東亦可仿效福建發(fā)展對(duì)外貿(mào)易,增加國庫收入,中央政府遂放寬對(duì)中國商人出洋貿(mào)易的限制。廣東繼福建之后,成為對(duì)外交流的又一個(gè)窗口,相對(duì)福建“有往無來”的單向開放,廣東則采取“互通有無”的全面開放模式,不僅允許外商前來經(jīng)商,而且也允許廣東商人出境貿(mào)易。廣東商人只要領(lǐng)取海道發(fā)放的證照,不夾帶違禁貨物,就能置貨出洋做生意。
自此,從廣東出海的中國商船絡(luò)繹于東西二洋,甚至遠(yuǎn)去月港模式所禁止前往的日本,廣州成為中國第一大港,東南沿海地區(qū)的私人海外貿(mào)易呈現(xiàn)出蓬勃發(fā)展的局面。
萬歷時(shí)人郭棐的《嶺海名勝記》附有一張廣州城與省河形勢(shì)圖:廣闊的江面上船只爭(zhēng)流,白鵝潭江面停泊著一艘五根桅桿的大船,海珠石江面停泊著一艘兩根桅桿的大船,旁邊標(biāo)有“烏艚”字樣,顯然屬于遠(yuǎn)洋海船。反映出晚明廣州商舶貿(mào)易的繁榮景象。
萬歷八年,朝廷選擇在省城廣州舉辦春夏兩季“交易會(huì)”,展銷來自世界各地的商品。廣州交易會(huì)規(guī)模空前,周期較長,進(jìn)出口商品結(jié)構(gòu)較為復(fù)雜。每次交易會(huì)展期長達(dá)二至四個(gè)月,春季在一月舉辦,主要展銷銷往馬尼拉、印度和歐洲等地的商品,夏季在六月份舉辦,主要銷售運(yùn)往日本的商品。各國商人懷著對(duì)東方大國的心馳神往,趁著東南季風(fēng)或東北季風(fēng)起航來到中國,云集在廣州這個(gè)華南重鎮(zhèn),在廣交會(huì)上不僅可以買到高質(zhì)量的好貨,而且可以根據(jù)海外市場(chǎng)需求訂制適銷商貨。
珠江三角洲西岸的澳門,北鄰珠海,原為香山縣南海中小島,后因珠江西江三角洲成陸加快,澳門島與香山縣連接。古代澳門有疍民、漁民等水上居民,直至明中葉,澳門并未設(shè)置行政性基層組織或軍事機(jī)構(gòu)。十五世紀(jì)以來,歐洲人開始在全球范圍內(nèi)開展海上探險(xiǎn)和殖民擴(kuò)張,東方大國自然是他們垂涎向往之地,歐洲霸主葡萄牙人首先登陸澳門,經(jīng)過一番周折,于1553年獲準(zhǔn)在澳門租住。澳門成為唯一允許外國人居住貿(mào)易的港口,吸引大批中外商人前來互市。
廣州以中國內(nèi)陸為依托,為海外貿(mào)易提供大量商品,澳門則成為西方國家在東方最大的轉(zhuǎn)折港和貿(mào)易基地,逐漸形成獨(dú)具特色的廣州-澳門二元中心的貿(mào)易體制。
外國商船進(jìn)入廣東沿海港口者日多,由廣東起航前往東、西洋的商舶也絡(luò)繹不絕于印度洋,廣州、澳門貿(mào)易遠(yuǎn)及南洋、印度、歐洲和美洲,沉寂二百年之久的海外貿(mào)易無論形式還是內(nèi)容,都開始和世界接軌。葡萄牙人克里斯托旺·維埃拉在廣州發(fā)信盛贊廣東是中國最好的省區(qū)之一:這里擁有不計(jì)其數(shù)的稻米和其他食糧,全國的商品都匯集在這里進(jìn)行交易,因?yàn)樗彺蠛#瑒e國的商品也運(yùn)到這里來貿(mào)易。這里的土地是世上最富饒的,世間的一切業(yè)績(jī)都是在廣東的地盤上創(chuàng)造出來的。
此時(shí)正值世界地理大發(fā)現(xiàn),地球的另一邊也在發(fā)生著驚天動(dòng)地的變革,歐洲人征服美洲后,在墨西哥發(fā)現(xiàn)巨型銀礦,日本本土也發(fā)現(xiàn)銀礦,而中國本土銀產(chǎn)量有限,不能滿足社會(huì)發(fā)展需求。福建、廣東的對(duì)外開放,使得中國的絲綢、茶葉等大量出口,中外貿(mào)易存在巨大順差,世界三分之一的白銀涌入中國。中國的市場(chǎng)上,充斥著來自西班牙的“本洋”、墨西哥的“鷹洋”和日本的“龍洋”。白銀的流入促進(jìn)了商品經(jīng)濟(jì)的繁榮,東南沿海城市發(fā)展欣欣向榮,一批新型城鎮(zhèn)興起,為晚明經(jīng)濟(jì)改革提供了物質(zhì)基礎(ch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