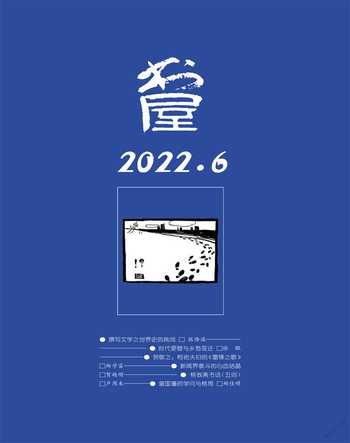方孝孺之死
趙映林
方孝孺是明初大儒、杰出思想家,然而在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隨著馬蹄聲碎,喇叭聲咽,“靖難之役”畫上了句號,建文帝出亡,一批臣子不甘臣服有違禮法、“犯上作亂”的燕王朱棣,紛紛遭誅戮,伴以“瓜蔓抄”,株連無辜。總計不下數(shù)千人被誅戮,流放充軍發(fā)配者約有數(shù)萬人之多,方孝孺拒絕為朱棣撰寫登基詔書,被誅十族。
究竟如何看待方孝孺的死,數(shù)百年來,莫衷一是,究其原因,則是在于論者所處的時代、地位不同,而論者的視野也有高下,見仁見智,實屬正常。
《皇明表忠記》的作者錢士升肯定方孝孺的忠:“孝孺十族之言(誅),有以激之也。愈激愈殺,愈殺愈激,至于斷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顧,而萬乘之威亦幾于殫矣。”
明后期著名思想家李贄,對孝孺的過激言論導致誅十族,也頗不以為然。他以山西清遠戍卒羅義為例,羅義曾上書燕王,“乞早息兵歸國”。燕王置之不理。他又赴京上書要求朝廷“息兵講和”,被逮入大獄。靖難之役后,朱棣提拔他為戶科給事中,不久擢為湖廣參政。李贄借此議道:“此衛(wèi)卒見識,勝方正學十倍,人亦何必多讀書哉?嗚呼!以全盛之天下,金湯之世界,付與講究《周禮》、精熟《大學衍義》之大學士,不四年而遂敗。可畏哉,書也!”把孝孺的以死抗爭僅僅歸結于讀書多了,這是一種偏激的看法。
民國著名通俗歷史小說家蔡東藩說:“方孝孺一迂儒耳,觀其為建文立謀,無一可用,亦無一成功。至拒絕草詔,猶不失為忠臣,然一死已足謝故主,何必激動燕王之怒,以致夷及十族,試問此十族之中,有何仇怨,而必令其同歸于盡乎?”對方孝孺激怒朱棣不以為然。
《皇明獻實》的作者袁帙說:“方孝孺之于文皇(明成祖),湯武之夷齊也。”充分肯定方孝孺之死的意義。
清軍機大臣張廷玉說:“帝王成事,蓋由天授。成祖之得天下,非人力所能御也。齊、黃、方、練之儔,抱謀國之忠,而乏制勝之策。然其忠憤激發(fā),視刀鋸鼎鑊甘之若飴,百世而下,凜凜猶有生氣。是豈泄然不恤國事而以一死自謝者所可同日道哉!由是觀之,固未可以成敗之常見論也。”張廷玉也肯定方孝孺視死如歸的精神,不以成敗論事論人。
到了現(xiàn)代最具代表性的人是胡適,他認為方孝孺是殺身殉道的了不起的人物。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沈剛伯在臺灣作學術報告,提出明成祖朱棣之所以要殺方孝孺,是“要毀滅方孝孺的政治思想”,并進一步提出,朱棣殺了方孝孺以后,“明朝二百年,再沒有政治思想家。我國政治思想在十四世紀以前,決不遜于歐洲,但近五百年來何以不振,這是由于方孝孺被殺的慘劇所造成的”。不過,胡適不贊同沈剛伯的這一說法,胡適修正說:“在方孝孺死后一百多年,王陽明不是明朝的大思想家嗎?”胡適接著又說:“明太祖刪節(jié)《孟子》失敗,明成祖要毀滅方孝孺的政治思想也失敗了。”
筆者認為方孝孺之以死抗爭而不屈,除與建文帝思想契合,以及報答建文帝的知遇之恩外,更為重要的深厚思想乃是他秉承儒家的一貫道統(tǒng),恪守儒家“正統(tǒng)”觀念,注重理氣修養(yǎng),承襲固有文化傳統(tǒng),這是他的價值理念。理學強調的君臣大義,“明王道,致太平”是孝孺矢志不渝的追求與價值觀。“事莫重于綱常,忠莫大于報主”“世間好事唯忠孝,臣報君恩子報親”,決定了方孝孺為維護傳統(tǒng)文化精神而為之殉道,殺身取義成仁。這在方孝孺的詩文中也有反映,他在緱城閑居時寫的《閑居感懷》十七首詩,其中一首:“我非今世人,空懷今世憂。所憂諒無他,慨想禹九州。商君以為秦,周公以為周。哀哉萬年后,誰為斯民謀?”明確透示出他要以商鞅為榜樣,不惜以身殉“道”,要像周公那樣服務朝廷:“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他還說:“圣人之道,離之為禮樂、政教、法度、文章,合之而為性命之原、仁義之統(tǒng)。其事業(yè)在《詩》《書》,其功用在天下。”圣人之道最終落實到人的性命上。方孝孺以身殉道并非心血來潮,而是有深厚的思想根源。所以,李贄說“使孝孺得用于太祖之時,則孝孺便成得一個好良臣,唯用于建文,故遂成一忠臣以死耳”。
朱棣無視“皇統(tǒng)”,以“奉天靖難”的名義武力奪取帝位,這不僅是破壞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皇統(tǒng)”,且影響后世,突出的事例就是在他孫子朱瞻基繼位(為明宣宗)后,其次子漢王朱高煦有樣學樣,如法炮制,也發(fā)動叛亂,試圖推翻侄兒奪取皇位,最后是明宣宗親征平叛才了結。而早在朱棣發(fā)動“靖難”的過程中,武官勛臣中大多數(shù)都主張以功能為標準,傾向廢嫡(朱棣嫡長子朱高熾,明宣宗之父)改立,但文臣們秉承“皇統(tǒng)”,堅持主張保留朱高熾的皇太子地位,并千方百計予以維護。明前期權力交替之際,為皇位繼承問題爆發(fā)的重大沖突或分歧,造成政局的動蕩,甚至流血,始作俑者,朱棣也。所以,方孝孺的殉道也不是孤立的,他是有一批同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