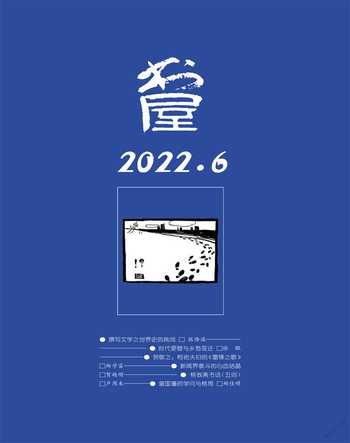《遠航尋蹤:近代文化史管窺》自序
章開沅
我一生與長江為伴,出生在蕪湖老宅,正好在長江下游支流青弋江畔。抗戰期間,流亡到長江上游四川,在江津(今屬重慶市)國立九中攻讀整整五年,湍急的川江與江心的沙灘成為課余假日的天然樂園。后來兩次被學校開除,先是浪跡于川江重慶瀘縣之間最為曲折艱險的那一段,隨后當兵于銅梁(如今也成為重慶的后花園)。抗戰勝利后又復回到蕪湖,并且在南京金陵大學就讀兩年多。而從1949年隨軍進入長江中游的武漢,至今已七十多年。難忘長江養育之恩,情如母子眷戀之深。所以,季羨林前輩晚年主編“長江文化研究文庫”,我一經征召就立即從命,參與編輯出版工作,并且更加深化了對長江歷史文化底蘊的理解和珍惜。直至年逾九十,我還極為關心武漢長江文明館的建設與發展,甚至為其舉辦的國際“大河對話”盛舉站臺助興。
因此,我把自己的學術生涯總結為“歷史是已經畫上句號的過去,史學是永無止境的遠航”。治學無非是求知,從已知到未知的探索就是學者畢生最大的樂趣。我出生于一個古老的移民宗族,一世祖從浙江紹興府地移到太湖邊的一塊蘆葦叢生的荒野——荻港。經過好幾代人血脈繁衍,人多地少為患,十二世祖節文公離鄉游幕并從政,先后移居于蘇、豫、晉,最終定居太原并病故于定州任內,其孫十四世維藩公兄弟兩人,出生于太原,成長于甘肅,此后又隨左宗棠西征軍進駐哈密,常年征戰于隴新邊陲大戈壁,直至1882年才隨左宗棠回到江南,并由軍功保奏,在安徽安慶、宣城等地任知縣及知州等職。甲午戰后,維藩公棄官從商,在蕪湖創辦益新面粉公司并定居于此地,晚年頗有落葉歸根情思,遂正式回荻港認祖歸宗。但由于兩處產業都在安徽,面粉廠在蕪湖,寶興鐵礦在馬鞍山,所以未能實現終老于荻港的夙愿,只留下一枚“苕溪漁隱”的印章記錄這個永恒的遺憾。古老的家族背景促成我自幼產生流浪的根性。
我的學術生涯充滿偶然,或多或少地帶有流浪色彩,仿佛是行走在沒有航標的江河之上,漂泊無定,隨遇而安。由于1948年參加革命,被組織上安排在武漢教書,所以就地取材,從研究辛亥革命起步,但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機緣巧合促使我癡迷于《張謇日記》《扶海垞未刊函電》,乃至收藏于原北京圖書館的《趙鳳昌藏札》等珍貴原始文獻。我的第一本學術專著《開拓者的足跡——張謇傳稿》,在寫成二十年后才被中華書局列入“中國近代文化史叢書”出版問世。狀元辦廠本來就是晚清過渡時代的一種特殊文化現象,或許可以說這就是我研究文化史的發端,但是卻與我當時承擔的“北洋軍閥”研究課題有所疏隔。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學術界有一股“文化熱”,我雖然忙迫于有關辛亥革命與孫中山的國際學術交流,但始終不能忘情于文化思想史的研究。作為辛亥革命研究重點的《辛亥革命與江浙資產階級》一文雖然側重于政治、經濟角度,但由于我力圖把整個社會作為研究視野,所以仍然有些文化思想史的副產品,如1903年前后的社會思潮、江浙新型知識分子群體的覺醒、章太炎與國粹學派等方面的研究。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普林斯頓大學宗教系熱情邀約,我參與了魯斯基金支持的中國教會大學史國際合作研究項目,在文化教育與基督教研究方面花費精力甚多,這在1990年赴美訪學三年多期間更成為治學主體。及至二十世紀末,由于受到湯因比與池田大作對話錄的深刻影響,我對人類命運以及嚴重文明危機深感憂慮,因此在新世紀到來之際,對文明危機與價值重建進行全面思考,并且通過與池田大作長達一年多的詳盡對話,向全世界表明自己的主要觀點與強烈呼吁。
晚年經常吟誦張維屏的一首詩:“滄桑易使乾坤老,風月難消千古愁。多情唯有是春草,年年新綠滿芳洲。”與宇宙乾坤及文化長河相較而言,吾輩普通學人豈不正如一株小草,渺小平凡之至。春草的多情也無非是自作多情,既缺耀目光華,更無國色天香。但小草作為具有生命的個體,亦自有其存在價值。“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其生命意志何等剛毅,何等充盈,它以億萬群體的蘇醒,萌發出漫山遍野的新綠,一片又一片增添了春天的顏色。詩人以春草自喻,既非故作謙抑,更非妄自菲薄,而是對世事人生已有更深沉的醒悟,其實也是徹底的自我超越與更高的精神追求。
天寒歲暮,文思枯滯,即以此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