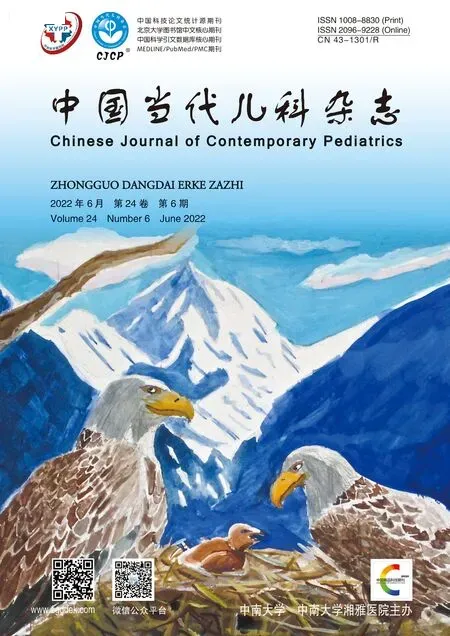胎糞污染羊水新生兒發生重度胎糞吸入綜合征的臨床特征及預警因素分析
何曉光 李金鳳 徐鳳丹 謝浩強 黃天麗
(廣東醫科大學附屬東莞兒童醫院新生兒科,廣東東莞 523325)
胎糞污染羊水(meconium-stained amniotic fluid,MSAF)是一種胎兒存在危險的警示信號,常常與不良的圍生期結局相關[1]。據估計,在所有分娩中,約8%~25%的羊水被發現含有胎糞,其中大約3%~12%的MSAF新生兒出現胎糞吸入綜合征(meconium aspiration syndrome,MAS)[2]。新生兒復蘇技術的進步降低了MAS的總體發生率,但嚴重程度并沒有顯著下降,重度MAS仍然是足月新生兒致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3-4]。
MAS的病因復雜,相關因素包括胎兒窘迫、胎心率不穩定、緊急剖宮產、Apgar評分低、胎兒宮內發育遲緩等[5]。少量的研究提示初產婦、新生兒出生體重>第90百分位數、臍動脈血氣分析pH<7.20等與重度MAS的發生相關[6-7]。目前MSAF新生兒發生MAS的病理生理機制未完全明確,相關致病因素包括氣道阻塞、炎癥、肺表面活性物質失活等。有研究顯示,胎糞暴露的時間、數量、性狀與MAS的發生和嚴重程度缺乏必然聯系,胎兒娩出后的氣管插管和胎糞吸引并不能預防所有MAS、特別是重度MAS的發生[8],推測MAS并不全是由于分娩過程誤吸胎糞導致,其他重要的上游因素也參與了其中的發生和發展過程,比如宮內窘迫、炎癥和感染等,尤其是重度MAS[9-10]。
目前基于臨床表現和影像學特征的MAS診斷方法未能及時提供足夠的信息來判斷嚴重呼吸衰竭的發生,因此重度MAS的診斷和治療仍然充滿挑戰[7,11]。本研究回顧性分析295例MSAF患兒的臨床資料,分析母親和新生兒臨床因素的差異,探討MSAF新生兒發生重度MAS的臨床特征及預警指標,以早期識別高危兒。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回顧性收集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入住廣東醫科大學附屬東莞兒童醫院新生兒科的Ⅲ°MSAF新生兒295例的臨床資料。納入標準:本院產科出生,Ⅲ°MSAF,單胎,胎齡>37周。Ⅲ°MSAF的診斷標準:羊水呈現棕黃色黏稠狀且量少,有顆粒狀胎糞,甚至臍帶及胎兒出現糞染[12]。排除標準:患先天性遺傳代謝性疾病或染色體病或先天畸形者。
根據病情嚴重程度分為無MAS組、輕度/中度MAS組和重度MAS組,MAS臨床診斷依據《實用新生兒學》第5版[13],包括臨床表現及胸片結果。MAS嚴重程度判斷依據參考文獻[14],即輕度:吸氧濃度<40%,時間<48 h;中度:吸氧濃度>40%,時間>48 h,無氣漏;重度:需機械通氣>48 h,常伴持續肺動脈高壓。機械通氣治療策略參考中華醫學會兒科學分會新生兒學組制定的《新生兒機械通氣常規》[15],有創通氣模式初始為同步間歇指令通氣,無創呼吸支持模式為鼻塞式持續氣道正壓通氣。
1.2 臨床資料收集
收集的臨床資料包括:(1)母親因素:年齡、是否羊水過少(羊水指數<5)、產前發熱≥38℃;(2)新生兒因素:入院年齡、胎齡、出生體重、出生方式、5 min Apgar評分、胎盤病理檢查(臍帶炎、絨毛膜羊膜炎)、出生是否有活力、是否行胎糞吸引術,臍動脈血氣分析結果(乳酸水平、pH值、BE值),出生1 h時動脈血氣分析結果(乳酸水平、pH值、BE值)及外周血白細胞(white blood cells,WBC)計數、C反應蛋白(C reactive protein,CRP)和白細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水平。
1.3 統計學分析
使用SPSS 19.0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s)表示,3組間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組間兩兩比較采用LSD-t檢驗;非正態分布計量資料用中位數(四分位數間距)[M(P25,P75)]表示,3組間比較采用Kruskal-Wallis one-way ANOVA(k samples)檢驗,組間兩兩比較采用All pairwise檢驗。計數資料用率(%)表示,多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組間兩兩比較采用卡方分割法。采用受試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線評價臍動脈血乳酸水平、出生1 h時外周血IL-6水平預測患兒發生重度MAS的效能。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采用All pairwise和卡方分割法行組間兩兩比較時,P<0.017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各組患兒一般臨床資料
本研究共納入295例MSAF新生兒,32.5%發生MAS(96/295),其中輕度/中度MAS占80%(77/96),重度MAS占20%(19/96)。兩兩比較結果顯示:輕度/中度MAS組男性構成比高于無MAS組(P<0.017);重度MAS組5 min Apgar評分低于輕度/中度MAS組及無MAS組(P<0.05);輕度/中度MAS組羊水過少發生率高于無MAS組(P<0.017);重度MAS組住院時間明顯長于輕度/中度MAS組及無MAS組,輕度/中度MAS組住院時間長于無MAS組(P<0.05);3組患兒胎齡、出生體重、剖宮產率、入院年齡、母親年齡、母親產前發熱情況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3組患兒均無死亡病例。見表1。

表1 各組患兒一般臨床資料比較
2.2 各組患兒實驗室檢查結果
兩兩比較結果顯示:輕度/中度MAS組臍動脈血BE值低于無MAS組(P<0.017);重度MAS組臍動脈血乳酸水平高于輕度/中度MAS組及無MAS組(P<0.05);重度MAS組和輕度/中度MAS組生后1 h動脈血pH值均低于無MAS組(P<0.05);重度MAS組生后1 h動脈血BE值低于無MAS組(P<0.017);重度MAS組生后1 h動脈血乳酸值高于輕度/中度MAS組及無MAS組(P<0.05),輕度/中度MAS組生后1 h動脈血乳酸值高于無MAS組(P<0.05);重度MAS組生后1 h外周血IL-6水平(P<0.017)和WBC計數(P<0.05)均高于無MAS組;輕度/中度MAS組臍帶炎發生率高于無MAS組(P<0.017)。見表2。

表2 各組患兒實驗室檢查結果比較

表2(續)
2.3 重度MAS診斷價值分析
根據上述單因素分析結果,納入臍動脈血BE值、乳酸水平及生后1 h動脈血pH值、BE值、乳酸水平、IL-6水平、WBC計數共7個指標,應用ROC曲線評價上述指標預測患兒發生重度MAS的效能,結果發現臍動脈血BE值、乳酸水平及生后1 h動脈血乳酸水平、外周血IL-6水平對重度MAS的診斷有預測價值(P<0.05)。見表3和圖1。

表3 ROC曲線評價相關檢驗指標預測患兒發生重度MAS的效能
2.4 重度MAS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根據單因素分析結果,以是否發生重度MAS為因變量,以臍動脈血BE值、乳酸水平及生后1 h動脈血pH值、BE值、乳酸水平、IL-6水平、WBC計數為自變量,進行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提示生后1 h外周血IL-6水平>39.02 pg/mL及生后1 h外周血WBC計數>30.345×109/L與發生重度MAS相關(P<0.05)。見表4。

表4 重度MAS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圖1診斷重度MAS的ROC曲線分析
2.5 各組患兒出生復蘇和復蘇后呼吸支持情況比較
295例MSAF新生兒中,無活力患兒占24.1%(71/295),其中82%(58/71)行氣管插管胎糞吸引,33%(19/58)的新生兒吸出多于1 mL黏稠胎糞。其中重度MAS組38%(5/13)吸出多于1 mL黏稠胎糞,輕度/中度MAS組44%(12/27)吸出多于1 mL黏稠胎糞,無MAS組11%(2/18)吸出多于1 mL黏稠胎糞。
兩兩比較顯示:重度MAS組患兒出生時無活力發生率及行胎糞吸引術的比例高于輕度/中度MAS組及無MAS組(P<0.017),輕度/中度MAS組患兒出生時無活力發生率及行胎糞吸引術的比例高于無MAS組(P<0.017)。
19例重度MAS患兒中,有6例經無創呼吸支持失敗24 h內改有創通氣,其中4例是在12 h內無創呼吸支持失敗改有創通氣;有4例在機械通氣過程中使用了高頻振蕩通氣模式。77例輕度/中度MAS患兒中,有6例無創呼吸支持失敗24 h內改有創通氣,其中3例是在12 h內無創呼吸支持失敗改有創通氣。見表5。

表5 各組患兒出生復蘇和呼吸支持方案比較 [n(%)]
3 討論
MAS反映了MSAF新生兒的一系列疾病,從輕微的呼吸急促到嚴重的呼吸窘迫,以及休克、心肌功能障礙和肺動脈高壓等多種并發癥[16]。本研究表明住院Ⅲ°MASF新生兒中有32.5%發生MAS,其中重度MAS占20%,輕度/中度MAS占80%,28%的MAS患兒需要有創機械通氣;大部分重度MAS患兒在出生早期即發生嚴重呼吸窘迫,而輕度/中度MAS患兒很少進展到重度MAS。
早期識別MAS、尤其是重度MAS,至今尚未有統一和準確的指標,Mazouri等[17]的研究表明,臍血乳酸水平升高(>4.1 mmol/L)可有效判斷MAS的嚴重程度。有學者[18-19]認為重度MAS與輕度/中度MAS相比有明顯的病理生理學差異,重度MAS可能并不全是輕度/中度MAS的線性延伸加重,故本研究在探討MSAF新生兒發生重度MAS的高危因素時,對輕度/中度MAS的數據進行統計學分析,結果顯示,5 min Apgar評分和臍動脈血乳酸水平在輕度/中度MAS組和無MAS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但在重度MAS組和輕度/中度MAS組、重度MAS組和無MAS組間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提示5 min的低Apgar評分和臍動脈血高乳酸水平與重度MAS的發生相關,但與輕度/中度MAS的發生無關。我們同時比較了3組患兒生后1 h動脈血氣pH值和乳酸水平,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提示生后1 h動脈血低pH值、高乳酸水平與MAS的發生風險和嚴重程度相關。臍血中的乳酸主要來自于胎兒,受母體和胎盤影響因素小,臍血乳酸水平升高提示胎兒窒息缺氧[20],說明胎兒宮內窘迫等上游因素參與了MAS的發生,尤其是重度MAS。
既往有學者報道了宮內炎癥與MAS的病理生理機制存在相關性[21-22],IL-6作為一種多效性細胞因子,參與炎癥、感染、代謝等過程的調節[23],胎兒臍血IL-6>11 pg/mL作為診斷胎兒炎癥反應綜合征的主要指標被廣泛應用[24]。本研究對比了3組患兒生后1 h外周血IL-6的數據,輕度/中度MAS組和無MAS組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但重度MAS組和輕度/中度MAS組、重度MAS組和無MAS組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本研究中重度MAS新生兒生后1 h外周血IL-6中位水平為117.2(50.8,359.6)pg/mL,遠高于足月健康新生兒出生時的水平[1.69(95%CI:1.28~2.23)pg/mL][25],提示出生早期外周血IL-6水平升高與重度MAS的發生顯著相關。ROC曲線及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提示生后1 h外周血IL-6水平>39.02 pg/mL及生后1 h外周血WBC計數>30.345×109/L為重度MAS發生的預警指標。
MAS曾經被認為是產后事件,在胎兒娩出后呼吸時發生胎糞誤吸,但有研究發現,部分MAS患兒沒有產時誤吸胎糞的證據,甚至出生后48 h內因重度MAS死亡的病例尸檢時沒有發現氣道或肺泡組織存在大量胎糞的組織學證據[3,26]。Viraraghavan等[9]對出生無活力MSAF新生兒760例進行選擇性氣管插管抽吸,發現46%的新生兒從氣管導管吸出的胎糞量微不足道,僅14.4%的新生兒從氣管吸出大量胎糞。自2015年國際復蘇聯絡委員會不再推薦MSAF時常規氣管內吸引胎糞(無論有無活力),國內外許多研究對比了復蘇策略改變前后病人的結局變化,但結果迥異[27-28],目前國內指南仍然建議對出生無活力MSAF新生兒進行氣管插管行胎糞吸引[29]。本研究表明MSAF新生兒出生無活力發生MAS風險增加,但同時也提示出生無活力新生兒行胎糞吸引術不能完全阻止重度和輕度/中度MAS的發生發展,同樣,出生無活力新生兒未行胎糞吸引術也不一定會發生MAS。
本研究不足之處:本研究納入病例全部是出生Ⅲ°MSAF新生兒,沒有分析不同程度MSAF在MAS發生發展中的作用;另外,我們沒有納入研究期間全部產科分娩的MSAF新生兒,僅是納入新生兒科收治的MSAF患者,故本研究中MSAF新生兒發生MAS的比例可能被高估,不能代表MSAF新生兒并發MAS的實際發生率。本院出生的重度MAS病例較少,鑒于外院轉診的MAS患兒在產房復蘇和早期管理方案中的差異,這部分患兒沒有納入分析,下一步需要更大量的病例進行研究。
綜上所述,重度MAS的發生不全是由于嚴重胎糞吸入導致,也不全是輕度/中度MAS的延伸加重,慢性宮內缺氧、炎癥等產前因素可能與重度MAS的發生相關。臍動脈血高乳酸水平和生后1 h外周血IL-6水平升高與重度MAS的發生相關;生后1 h外周血IL-6水平>39.02 pg/mL及生后1 h外周血WBC計數>30.345×109/L可作為重度MAS發病的預警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