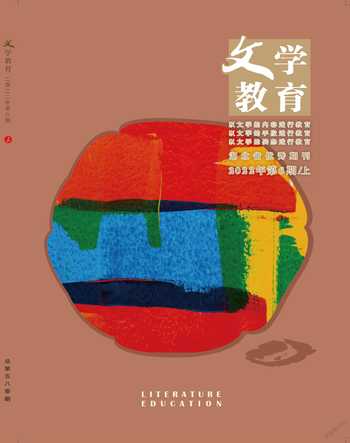鄭振鐸《貓》中第四只黑貓不需要蜷伏
栗雅芝
內容摘要:鄭振鐸的《貓》講述了“我”三次得貓、失貓的故事,由于第四只黑貓的出現,才讓“我”意識到冤枉了第三只貓,由此引發“我”對人性的反思。本文擬圍繞小說文體、關鍵詞句、貓的命名解讀文本,分析教材,準確定位文章文體;結合關鍵語句,以第四只被忽視的黑貓作為切入口,分析黑貓的獨特作用;第四只黑貓的出現,揭示謎底,引發“我”深刻反思自己。探討命名,理性分析人性真假。明白主觀臆斷會給他者帶來痛苦。因此,不要帶有偏見去看待動物和他者。
關鍵詞:鄭振鐸 《貓》 第四只黑貓
鄭振鐸的《貓》集中描寫了“我”誤會了第三只貓,由此引發“我”生發愧疚之情。“我”對三只貓的情感隨著它們的去世而不斷變化,最后引發“我”對人性的反思。借此來表達弱小者“蜷伏”在他人屋檐下的悲憫,引發對人性的看法。貓就是人物形象,透過“貓”來反思人性,批判人性丑陋,引發深深的思考。作者以文本為憑借,思考人性應該向善向美,使得弱小的群體不需要“蜷伏”,活出自己的精彩。大多數人圍繞作者冤枉了第三只貓,引發對良心的叩問來加以解讀。但是,如果沒有出現第四只貓,第三只貓就會一直被冤枉,這篇文章大抵也不會出彩。因為不講第四只貓,就證明沒有讀懂這篇文章,極大地流失了《貓》文傳達的意義思考,尤其是不能將此文上升到更加“有用”的境界[1]。
一.追本溯源,探散文化小說文體
經典的作品的藝術魅力何以如此長存?這就需要去揭秘。歌德的“秘密說”指出,形式對于大多數人都是個秘密。作品有它自己的命運,寫完作者都不知道它的命運如何。因此,解讀《貓》這篇經典文章,就需要去揭秘文本形式的奧秘。文本越是經典,形式秘密隱藏的越深。需在語文教學中不放過一字一句,潛入文本,深入探究。
《貓》的文體歷來備受爭議,散文還是小說,一直都是學界探討的問題。瀏覽文獻發現,人教版將選文中“我”等同于作者,配套參考文獻定位是一篇散文。部編版教材問世,出現了定位小說,源于部編版中將“我”不等同于作者。
據課文最早出處《家庭的故事》,作者在自序中寫到,“它們并不是我的回憶錄,其中未免有幾分是舊事,卻決不是舊事的紀事[2]”。鄭振鐸先生的兒子鄭爾康在《石榴又紅了——回憶我的父親鄭振鐸》中提到,“其中家里的第一只貓被打死,第二只貓被摔死。自從這兩事情發生不久,父親便寫了他的《家庭的故事》[3]”。與文中的描寫有出入,所以《貓》應該就是在“舊事”的基礎上想象和虛構的。
加之這篇文章沒有傳統的小說套路和凸顯的情節,有的只是三只貓經歷敘述。這也與作者本人有關,鄭振鐸不追求傳統的套路,追求文章的“質樸”“真率”,善于寫‘平平淡淡的家庭瑣事與脈脈溫情中輕籠的哀愁[4]”。這就給人一種散文的理解。語文教師要有自己的解讀,最好是從學生的已知中去揭示未知,用自己的生命去作獨特的領悟、探索和發現。其實《貓》是鄭振鐸秉承“為人生”而創作的系列小說之一,文章從一個獨特的視角觀照社會,審視人性[5]。《貓》的文體根據教材以及作者自序,這是一篇散文化的小說文體,不是典型的小說,而是用散文的筆調來寫的小說。
這篇文章的文體是小說,落點就是“貓”作為人物形象的分析。那么,第四只貓是如何起作用的呢?文中只是有三只貓嗎?文體決定思考方向,文本體式是首先要思考的問題,這是進入《貓》文本解讀應該思考的問題。很多老師在教學《貓》,會忽視文本體式,按照小說內容教,又講散文特點。散文教學是聚焦作者的所思所感,高度個人化的言說對象,個性情感的表達。朱自清的《背影》只是朱自清的背影。而小說是小說,文本應落點在教會學生解讀小說的策略,學習一篇小說,就要學會解讀此類小說的策略,舉一反三,以此類推。而不是聚焦作者的情感大說特說,豈不是把這堂課可惜了?作者也不等于文章的“我”。區分開散文與小說的教學策略,教師就有了抓手。要學會抓住“貓”的形象,尤其是聚焦第四只貓,以顏色、命運、“我”情感的變化來展開教學。
“我”的感情隨著第四只貓的出現,達到潮。他開始自責,反思自己行為。作為讀者,比較容易看見文本內容,而文本形式秘密難以看見。就需要挖掘文本,拋開大多數人可以看見的,找到《貓》的秘密。這篇文章隱藏得極深的就是第四黑只貓,為什么教學的時候偏偏忘了它?這就是慣性,就是文體把握不準的結果。解讀文本不可以只突出第三只貓,忘記黑貓。作為一篇散文化的小說,文中對四只貓的描寫都有它特定的作用。第四只黑貓的作用是為了揭示“我”的暴行,相當于案件的突破者。在全文中起到了關鍵人物的作用。對于文本解讀,要本著追本溯源的態度,不可以淺嘗轍止。
二.關鍵詞句,析黑貓的獨特作用
《貓》這篇文章結構十分明顯,四只貓的出場都有它的順序。對于前三只貓的感情變化和態度都有關鍵語句。首先,文章的總起句“我家養了好幾次貓,結局總是失蹤或死亡”。點明文章是要寫養貓的結果,這個結果是很悲慘的!“總是”一詞點明,養貓達不到好結果,沒有一只貓可以安穩地在“我”家待著。第一只可愛的,第二只更有趣的,第三只帶有憂郁性的,三種性格的貓在“我”家都待不了多久。要不就是“失蹤”或“死亡”,貓死了,“我”就會有情感的反應。于是,前兩次“貓亡失”后,出現了“自此,我家好久不養貓”。為什么兩只貓都亡了,才說這句話?這樣合在一起寫,是為了更好的引出第三只貓,“自此,我家永不養貓”,這句話與前面那句做對比,去思考“我”和家人是真的愛貓嗎?既然說很愛貓,為什么會接二連三的出現“天災”“人禍”“我之過”的?這是自然災害和人為因素的結合,在貓出現病態的時候,如果及時治療,出于喜歡肯定會心疼,然而,文章中并沒有提到這些,如為貓找醫生,為貓診斷原因等。
可見“我”和家人并不是真愛貓,從冤枉第三只貓中可以發現。‘我很憤怒,叫道:“一定是貓,一定是貓”’,作為一個愛貓的人士,是不可能這樣主觀臆斷的,如果真的是第三只貓做的,沒準兒還會為其辯解,吃了芙蓉鳥就吃了吧。相反,妻子果斷認為是第三只貓;三妹直接引導“我”找到第三只貓;而“我”直接怒氣沖天,追過去打。如果文章分析到這里就停了,就可以直接過渡到作者良心的譴責嗎?答案是否定的。“以為”“好像”“一定”“我想”等等這些詞語都表明“我”是在主觀臆斷,妄下結論。這完全是沒有根據的推理,完全是偏見的影響。不禁再一次思考,文中的“我”是真的愛貓嗎?
第四只貓出場了,“同時我看見一只黑貓飛快地逃過露臺,嘴里銜著一只黃鳥。我開始覺得我是錯了!”主語是“我”,必然要強調是“我”看見了。第四只貓的筆墨不多,但是它的一閃而過,也恰恰證明了“我”在一閃而過的瞬間,想得到是冤枉第三只貓。如果“我”能夠淡定地分析來龍去脈,而不是先入為主的去審判第三只貓。或許結局就不是這樣了。
《貓》中的關鍵句“自此,我家永不養貓”,一望而知的是“我”意識到自己的主觀臆斷,冤枉了貓,剝奪了貓的清白。這是人人心中有的。那秘密是什么?“個個筆下無”,“無”在何處?“自此,我家永不養貓”寫出了“我”家永遠不養貓的結局,探討一家最愛貓的家庭永遠不養貓,僅僅是因為“我”冤枉貓嗎?第四只貓這個見證者可以看出,如果第四只貓不出現,“我”壓根不會去思考第三只貓是否真的吃了“芙蓉鳥”。“我”會沾沾自喜地以為“我”替芙蓉鳥報了仇,替妻子出了一口氣,幫助三妹清理走了一個憂郁不討人喜歡的動物。實際教學中,學生分析“我”的情感就是比較單薄的。他們心里會認為:“哦,芙蓉鳥不是第三只貓吃的。“我”冤枉了貓,所以自責。”不會去關注那只被遺忘的“黑貓”。雖然黑貓是兇手,但在文本中是關鍵人物形象,分析文本不可忽視。也就是說,人們傾向于分析主要人物形象,而偏見不去理會次要人物。
三.探討命名,思人性的主觀臆斷
要讓小說有震撼力,就是讓人物的命運和讀者的同情發生逆差。讀者越是同情,作家越是要折磨人物,人物的命運越是和讀者的期望有反差,就越有閱讀吸引力,理論上稱為“情感逆行”[6]。《貓》作為經典課文,“情感逆行”表現得更明顯,貓沒有亡失之前,“我”盡情地享受前幾只貓帶來的樂趣,每失去一只貓,又有第二只貓來填充的“我”的生活。可是,第四只黑貓的出現卻不是使“我”的心靈快樂,而是深深地自責與愧疚。第四只黑貓消失,再也沒有第五只貓可以釋放“我”良心上的譴責!“我”是很同情第三只貓的,第三只貓的悲慘命運是“我”一手造成的。“我”先前在廊前慵懶地曬著陽光的快樂,在此刻煙消云散。情緒強烈的轉折,“我”的情感遭受重大的打擊。聚焦關鍵句“我家養了好幾次貓,結局總是失蹤或死亡”。作者為什么選材這個?主要是因為情感巨大的差距,使人內心無法擺脫內疚。讀者在生活中也會有類似的事情,讀者聯系生活也是會引起共鳴。
文本中說到“我”一家是很愛貓的,為什么不給每只貓取一個名字?名字是事物特征,對動物表示喜愛,就會給動物取名字。文中卻只是按照順序來描寫貓,加之在貓亡失后,才逐一給它命名,“小侶”“親愛的同伴”。第三只貓連命名都沒有。而且這還不算嚴格意義的命名。僅僅因為“我”冤枉第三只貓引起了“我”情感的漣漪,造成了內疚、悔恨。倘若沒有這個事情,“我”對第三只貓也不會有多少情感。
最關鍵就是黑貓命名,為什么這只貓冠以顏色?文中第一只貓,寫出它的顏色是:花白的”“泥土的白雪球”,這在視覺上給人一種美妙的享受。也可以看出“我”是很喜歡的。后面的“生命的新鮮與快樂”也證明了這一點。第二只貓是渾身黃色,“我”的飯后娛樂就是看貓;第三只貓雖然寫其是花白,但是不好看!“不好看”就足以埋下伏筆。第四只貓是黑色的。最后這只貓也沒名字,但是終點就在它的名字是“黑—貓”。前面的貓為什么不叫白貓、黃貓?就是“我”對貓確實不是真的喜愛。“我”只是把“貓”當作一個玩耍的動物而已。加之,巧妙的設計“黑”,“黑”沖擊讀者的視覺,自然而然的聯系壞人這個角色。如果安排一只白色好看的貓,那就構不成強烈的顏色沖突,即無法在文中構成矛盾沖突。加之,黑貓更可以證明“我”的主觀臆斷。換句話說,要是真的是一只好看的貓,文中沒有設置“我“親眼所見的話,想必,第三只貓永遠不會得到澄清。也更好的強調了“我”一直都在主觀臆斷,而且存在偏見。
文中的張媽、李媽也是“貓”,她們是下人,是家里沒有話語權的人群。她們的命名只是姓氏,她們有自己的名,卻還是以姓氏+媽。而且張媽是“默默無言,不能有什么話來辯護”,她也被斥責了,她因為沒有照看好芙蓉鳥,和第三只貓一樣只能默默被說。通過第四只貓聯系張媽、李媽,可以想象這文中有第五只“貓”,甚至社會上還有更多的類似的“貓”。就像是文章中的第四只貓,人類中還有很多類似的“貓”,他們無法站出來,只能“蜷伏”!他們不敢也不能。
第四只黑貓是文中重點,盡管前面三只貓筆墨很多,但,這些內容一望而知,解讀小說要看到一望無知的東西。解讀小說要聚焦關鍵部分,像這篇散文化的小說,不要跑到文本外去尋找答案,要集中心思探尋本文的內容,不要過度聚焦談論作者感情。既是小說,作者就不是文中的“我”,事情可以是虛構的,但是小說的感情和散文的感情一樣也必須是真的。聚焦第四只黑貓,去探討“我”冤枉了第三只貓后,對人類人性反思和思考才是真正要解決的問題。
文章帶來的思考,以及教會學生如何解讀小說作品,才是小說教學的根本。文章的意蘊是人類在處理人與社會、動物、人類的關系的時候,要用真心去看待事物,不要心存偏見,主觀臆斷,偏見會給他者帶來不可預估的傷害,也會讓自己的良心受到譴責。那學生遇到下一篇小說時,他會如何去解讀,教師要思考的也是要教的內容。小說教學教什么,一定要區分開散文教學,不要先入為主,一定要先定好主題,讓學生訓著這個主題開展學習,一步一步發現小說意蘊。學生掌握這樣的意蘊,需要教師文本解讀。教師需有一把解讀小說意蘊的鑰匙,如何鍛造這把鑰匙,就需要深厚的火候,扎實的理論基礎知識,豐富的教學經驗等。總之,深入文本,潛入文本。
相對最好的解讀絕不是最難的解讀,相反,它可能最能激發學生的共鳴感、興奮感。從教育的角度尤其是基礎教育的角度,更應該把相對最好的解讀奉獻給青少年,讓他們的學習每一次都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7]。鄭振鐸這篇文章《貓》中相對較好的解讀,是從被忽視的第四只黑貓入手,找出第三只貓亡失更難過的原因,揭開“自此,我家永不養貓”的深層意蘊。文本解讀要在一望而知的基礎上,進入隱秘的意蘊和挖掘更秘密的表現形式,引導學生透過表層揭示那隱藏的本質和奧秘。學生才會在每一次的學習中有所收獲,教師教給學生的應該是閱讀小說的策略,讓學生定位文體,聚焦語言,能夠在文本中發現文本的形式秘密。
參考文獻
[1]陳罡.《貓》的文體知識辨析及教學價值探討[J].中學語文教學,2018(09):22-26.
[2]李曉榮.初中語文文本解讀中的“悲憫”意味——以人教版《貓》一文的解讀為例[J].語文教學與研究,2021(06):26-27.
[3]王春紅.蜷伏里的悲憫——鄭振鐸《貓》的文本解讀[J].語文教學之友,2017,36(05):30-31.
[4]華俊萍.不可缺失的黑貓——鄭振鐸《貓》文本解讀[J].中學語文教學參考,2019(26):61-62+74.
注 釋
[1]徐江,王從華.不能忽略第四只貓而且是“黑貓”——鄭振鐸《貓》文解讀教學之疏[J].中學語文教學,2015(04):48-51
[2]鄭振鐸.家庭的故事[M].上海遠東圖書公司.1928.
[3]鄭爾康.石榴又紅了---回憶我的父親鄭振鐸[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12.
[4]溫儒敏.中學語文教科書(七年級上冊)[M].人民教育出版社(部編本),2016 年7月第1版.
[5]肖培東.我們都可能會是那只貓——《貓》教學思考[J].語文建設,2018(22):34-39.
[6]賴瑞云.文本解讀與文本解讀新論[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5(2018.12重印).211.
[7]賴瑞云.文本解讀與文本解讀新論[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5(2018.12重印).272.
(作者單位:佛山科學技術學院人文與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