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書籍設計中的手工元素
文 藝
(安徽工程大學 藝術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0)
書籍是人類知識傳播和文化傳承的主要載體。我國古代四大發明中有兩個與書籍有關。廣義上的書籍可以從甲骨文算起,從龜甲獸骨到竹簡木犢,從絲帛到紙張,從刀刻到書寫,從雕版到活字,材料、工藝、技術不斷創新,書籍的種類也越來越繁多,而書籍記錄與傳承人類文明的功能卻從未發生變化 ,帶給人們體味書韻墨香的美好追求從未改變。
1 手工元素在書籍裝幀中的應用
蓬勃發展的網絡信息技術,引領人們快速進入數字閱讀時代。電子讀物以其巨大的信息載量和飛快的傳播速率,對傳統書籍造成了巨大沖擊。快節奏的生活讓人們更傾向于接受圖像和影音作品,而非傳統的紙媒讀物;紙媒的式微收窄了書籍裝幀設計的市場,使得具有手工元素的書籍也越來越罕見[1]。
現代書籍設計在運用現代設計方法的同時,將手工的拼貼裁剪、手工刺繡、立體折疊、混合材料等不同技法結合在一起,使其既能傳承手工元素原本的質樸、隨性與靈動,又能滿足書籍設計所需的內涵與理性,突出書籍的特色,讓手工表現元素以承繼與創新的形式使書籍設計煥發新的光彩[2]。
①拼貼裁切。拼貼是書籍裝訂與書籍內容設計當中常用的手工元素,古代的旋風裝、蝴蝶裝等裝幀形式都應用到了拼貼。拼貼的技術含量相對較低,所以可以通過機械進行制作。目前,書籍設計主要將拼貼應用在書籍內頁的設計上,其中藝術類、兒童類等類型的書籍應用得比較多。這種形式可以增強書籍的趣味性。如未來出版社出版的樂樂趣童書《過年啦!》是專為兒童設計的中華傳統節日體驗立體書,書中運用拼貼的方式設計了大量可翻轉、可打開、可拉移的小機關,代入感極強。裁切多以異形裁切和鏤空等形式被應用在書籍的造型上。隨著印刷技術的發展,手工裁切已被機器模切取代。現代書籍常以這種多元化多維度的視覺符號豐富書籍層次,展現特別的視覺趣味,優化書籍的視覺效果。
②手工刺繡。刺繡是中國歷史悠久的傳統手工工藝。將傳統刺繡材料的多樣性特征與現代藝術的裝飾性特征結合起來運用于書籍設計,可以極大強化書籍的立體感。企鵝蘭登出版的企鵝手繡經典系列(Penguin Threads),以特殊的創意和工藝展現文學名著之美。這個系列每本書的封面設計均來自刺繡藝術家的純手工刺繡,整個封面、封底、前后勒口全部覆滿刺繡花紋,書封內側也保留了手工刺繡過程中留下的線頭和針腳,使作品在圖案上既有藝術家的個人風格,又具有質感多變、層次鮮明細膩、立體感強的特點,極具藝術價值。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朱贏椿設計的《不裁》一書中在封面封底及勒口采用隨意的紅色縫紉走線,風格極簡,這種表現形式極具個性,由設計思維不斷轉化、深入,促使手工表現元素與設計者思維之間產生互動融合,展現書籍設計的文化底蘊[3]。
③手繪。手繪是一種歷史悠久的藝術,從古代的彩畫到現代的漫畫、插圖都屬于手繪。書籍裝幀設計當中的字體、插圖都屬于手繪元素。目前手繪主要應用在書籍封面與插圖的設計當中[4]。設計人員可以利用書法、涂鴉、漫畫等元素設計書籍的封面,增強書籍封面的藝術氣息。在信息時代,大量設計者使用手繪板模擬油畫、速寫等不同筆觸,為書籍繪制插圖,可節約繪制時間,且最大程度地保留手繪的筆觸痕跡,優化繪制效果。
④折疊。傳統書籍裝幀形式中的經折裝、蝴蝶裝等都是使用折疊手法的裝訂方式。折疊因其制作方法簡單、效果豐富成為書籍設計中常用的手工元素。設計者通過翻折、旋轉或斷折等方式來進行塑型,利用紙張的方向變化組合成豐富層次,使視覺效果得到升華。如圖1的《紅樓夢》內頁就采用了傳統經折裝的設計形式,并利用向內翻折的手法改變了內頁的單調,層次飽滿,更好地反映出書籍特色。

圖1 《紅樓夢》書籍內頁設計[5]
⑤其他方式。中國古代用以防范機要信函被拆的傳統封緘形式——火漆,逐漸在現代書籍設計中得以應用。為優化書籍的藝術效果,在封面用火源熔化火漆,加蓋專門設計的印章,既美觀又有復古感。早期火漆章的圖形以家族標志或個人標志陰文篆刻為主,用在現代書籍設計中則題材更為廣泛,多結合運用文字及代表書籍內涵的圖形。這種傳統手工元素以其悠久的歷史、斑駁的蠟印痕跡吸引著讀者。
2 手工元素在書籍設計中的特性表現
2.1 藝術性與功能性
手工元素以其樸實自然的特色、多樣的藝術表現形式在現代書籍設計中占有重要地位。設計者通過運用書法文字和傳統手工裝訂形式等元素來表現民族特色,不僅保留了鮮明的藝術風格,而且更能反映書籍的文化內涵,為讀者提供美的感受。同時,在書籍設計中運用手工元素可以強化元素的整合、局部的設計細節等,彰顯書籍的功能性。設計者在設計過程中將藝術與書籍的實用性有機融合,注重書籍內容的可讀性,尊重閱讀規律,達到審美形式與閱讀功能的完美結合[6]。
2.2 主題性與系統性
書籍設計是一個三維的、多層次多角度的系統工程,設計者需要根據書籍的主題以獨特的藝術形式予以表現,體現設計的主體性與系統性。合理運用手工元素可以體現出設計者的立意,如利用手工折紙粘貼增加兒童書籍的趣味性,或通過手繪插圖來表現情節等。圖2是全國裝幀金獎作品、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小紅人的故事》的設計,作者采用剪紙小紅人形象,傳統線裝形式,從右到左的內文版式等,呈現出手工元素的獨特魅力[7]。

圖2 《小紅人的故事》裝幀設計
2.3 民族性與獨特性
現代書籍設計師開始探索本民族傳統文化和現代設計風格的融合,以形成既具有民族特色又適應當代審美需求的書籍設計形式。扎染肌理、剪紙等手工元素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或不可復制性,正是這一獨特性滿足了讀者求異求趣的需求。如圖3,剪紙藝術家趙希崗在獲2015年“中國最美的書”、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的《兔兒爺丟了耳朵》的內頁設計中,創造了最具北京特色的非遺形象“兔兒爺”的新剪紙形象,增添了中國傳統節日氣息。在這一作品中,作者為適應低幼兒讀者需求,打破了傳統剪紙的單一色調,設計整體簡約大氣,是新剪紙元素在書籍設計中的杰出典范[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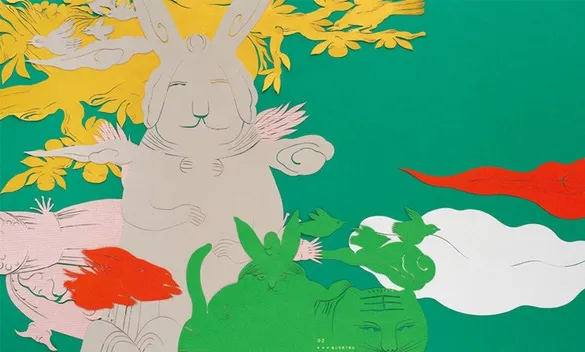
圖3 《兔兒爺丟了耳朵》書籍內頁設計
2.4 商業性與前瞻性
在網絡技術發達的時代,讀者的消費觀念與消費行為正脫離原有二維模式,迅速進入創新變革時期。設計者不斷嘗試以手工媒介為載體,組編信息創新書籍傳播方式。書籍的手工化是一個具有前瞻性的實踐領域,它不再局限于傳統書籍信息的二維化形式,而是更加突出“手工加創新”這種表達方式來使圖書具有強大的感染力,從而影響讀者的選擇。因此,足夠的想象力和創新力對書籍設計的前瞻性尤為重要。
讀者閱讀習慣的改變,書籍材質媒介的不斷更新,必然導致書籍傳播方式的改變。書籍設計以展示文化商品為目的,在設計中要不拘泥于現有的書籍模式,通過使用不同的手工技巧展現書籍的特點等基本特征,為讀者提供直觀的圖書信息和強烈的視覺沖擊,以激起讀者的購買欲望。
3 書籍設計中手工元素的美學價值
3.1 寓意之美
中國古代美學講究“寄情于物、借物抒情”,只有注入真實情感的藝術作品才能更加鮮明突出,情理融合。我國自古以來就有強烈的趨吉避兇觀念,常用諧音字或通假字來傳遞美好寓意,如用“葫蘆”表示“福祿”、用“魚”象征“有余”、用“蝙蝠”象征“福”等;或利用一種事物的特性來贊美另一事物,如烏龜象征著長壽,回紋由于其連續的特征常用來表達富貴不斷的吉祥寓意等。我國傳統書籍以線裝為主,古樸溫雅;在現代書籍設計中,有的設計者繼承了我國傳統書籍繁復而有儀式感的裝訂工序:搓捻、打孔、貼皮、選線、貼簽,或將“四眼一線”的傳統裝訂方式改進為象征吉祥意義的回紋線裝或龜背紋線裝等。這種設計“圖必有意,意必吉祥”,形式更為美觀,意在利用傳統紋樣傳達祝福,滿足人們祈福的心理需求,表達對傳統文化的敬意,并用這種設計方式拓展了設計者在利用傳統紋樣創作時的意象化審美觀念,使書籍更增添了寓意之美。
3.2 品味之美
讀者閱讀品味的提升要求書籍設計者不斷提高審美觀念,使書籍從文字記錄發展為高品質閱讀載體。書籍的品味之美由設計者的地域、民族、審美、情感等元素決定。傳統手工藝元素應用于書籍設計的主旨在于凸顯東方文化氣質:如設計者使用中式傳統服裝手工盤扣工藝于書套的封口處,既起固定連接書套作用,又凸顯了圖書的獨特品味,兼具實用性與裝飾性。
3.3 生態之美
傳統印刷業對紙張的依賴對生態產生了一定影響,由原材料和印刷廢棄物造成的環境污染已引起設計師的重視。為使圖書出版印刷產業獲得尊重環境下的可持續發展,設計者在作品中表現生態之美和環保理念是題中應有之意。呂敬人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食物本草》一書設計中采用藤編工藝制作書盒外部造型,把傳統手工編織工藝融入書籍設計,改變了紙張為書籍唯一載體的傳統。還有設計者采用環保不織布結合刺繡方式設計書籍封面,手感溫潤,質感獨特。采用綠色生態的手工藝形式不僅順應潮流,更可發揮其較為靈活的藝術特點,增加書籍藝術表現的多樣性,在書籍設計中釋放新的生機。
4 結語
電子讀物的猛烈沖擊和讀者審美能力的提升,使手工元素在書籍中具有了無限的可操作性與創造性。然而將趣味隨性的手工表現元素運用于理性的書籍設計中,就必須在分析各種傳統手工元素的形式特點、表現方式基礎上提煉、創新,用個性化的手工思維彌補計算機設計的僵化重復,使書籍設計呈現出溫暖、趣意的獨特風格,滿足讀者視覺和心理的雙重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