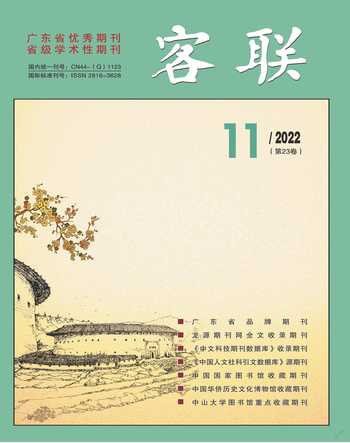封建王朝的基層控制
姚興益
摘 要:中國歷代封建王朝都十分重視社會的穩定,實現對基層的有效控制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前提。明朝是我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朝代,起源于唐五代時期的巡檢司制度在明朝得到發展和推廣,明朝統治者通過巡檢司制度,使中央統治力度向基層深入,加強朝廷對地方的管控。但在不同的空間,明朝的巡檢司制度具體實施情況不同,在不同的時間段,巡檢司制度的效果也不同。不論明朝時的巡檢司制度在空間上和時間上的具體實施情況與實施效果如何,它始終作為一項重要的制度影響著明朝的基層控制,直到明朝滅亡也沒有被廢止,考察明朝時期的巡檢制度,厘清制度運行背后的邏輯,對當今的基層治理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明朝;巡檢司制度;基層控制
一、引言
巡檢司制度在我國歷史上長期存在,在封建王朝時期,在管控基層鄉村,維護社會穩定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關于巡檢司制度的起源問題,目前學界還沒有完全達成一致,早年的《中國歷史大辭典》中對巡檢司制度的歷史沿革有比較完整的說明:巡檢司是地方治安機構,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始于京東五路置,其后各路分置,或者置都巡檢司;西夏時期沿置,但一度遭到廢除,以巡檢為長官;金、元時期在京城以及一些要害之地設置,同樣以巡檢為長官;明洪武二年(1369年)于廣西設置,后于各州縣關隘要沖之處增置,京城不設置,通過設置巡檢、副巡檢等職官來擔任緝捕盜賊和盤詰行人的工作任務,維持地方的治安。到了明朝時期,巡檢司制度得到推廣,更加規范化和制度化。
明朝的巡檢司制度在還未正式建國前就已經開始孕育,朱元璋為便于在統一戰爭中征調賦稅,開始在他占領的部分地區設置巡檢司。明朝正式成立后,就開始正式運用,并逐漸推廣。洪武二年(1369年),由于廣西地接瑤、僮,他首先在廣西的關隘要沖之處設置巡檢司。明朝時期的地方官僚體系,主要由府、州、縣幾個行政層級構成,巡檢司就遍布于這幾級行政機構之中,明朝時期的巡檢司所屬主要有三種情況:一是為府所屬,二是為州縣所屬,三是為土司、衛所所屬。巡檢司作為一個機構,需要一定的人員配置,巡檢和副巡檢都是正印官,從九品,配有一名司吏作為辦事人員,有的巡檢還會配備書辦,在巡檢司中,主要由巡檢、副巡檢及其屬下的弓兵行使職責。從巡檢司的所屬、巡檢的品級以及巡檢司人員的構成情況來看,巡檢的地位較低,甚至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八月,明太祖朱元璋將天下巡檢定為雜職,后來又在洪武十七年(1384年)十月,改巡檢司巡檢品級為從九品。
明朝巡檢司制度的總體情況如上所述,作為府、州縣以及土司或衛所的下屬機構,它廣泛存在于明朝的基層鄉村,在加強基層控制、維護地方社會的穩定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就整個明朝疆域的不同區域進行橫向比較,巡檢司制度的具體實施情況存在一些不同之處,為什么同一套制度,在不同地區實施起來會存在不同,其背后的邏輯值得關注;縱觀整個明朝時期,巡檢司制度的具體實施情況也不相同,可以說一直處于變遷之中,背后的原因同樣引人深思。
二、明朝巡檢司制度的具體實施情況
本文將通過幾個具體的案例來考察明朝巡檢司制度的具體實施情況。這幾個案例包括處西南民族地區的四川省都掌蠻地區的巡檢司,地處沿海地區的廣東省潮州府的巡檢司以及地處經濟繁華之地的蘇州地區的巡檢司。
(一)明代巡檢司制度在四川省都掌蠻地區的實施情況
元朝末年。明玉珍帶領的起義軍占領蜀地,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于重慶稱帝,國號大夏。分置蜀地為八道,在少數民族地區,設宣慰司、安撫司、軍民府等。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遣大將湯和、傅友德指揮南北兩路大軍平定四川,大夏政權宣告滅亡。盡管大夏政權滅亡了,由于四川遍布包括藏族、羌族、彝族、苗族、都掌蠻等少數民族,明王朝要實現對四川的有效管控十分困難。遍設巡檢司是加強對四川地區及其少數民族管控的重要途徑,同時這些巡檢司的地址也在不斷發生變化。
明代四川行省前后共設置了巡檢司82個,其中土巡檢、土副巡檢9個,普通巡檢73個,在四川16個府級行政區內設置巡檢司的數量從多到少依次是:成都府、敘州府、夔州府、重慶府、四川行都司、嘉定州、烏撒軍民府、保寧府、四川都司、瀘州、邛州、眉州、馬湖府、龍安府、雅州、順慶府。其中成都府數量最多,有16個;其次是敘州府,有13個;然后是夔州府、重慶府,分別有9個、7個;而順慶府最少,僅有1個。可見,在巡檢司的設置上,并非每個州縣都有,而是根據當地的實際需要來設立。
明朝時期,四川地區的少數民族曾經多次進行反抗斗爭,受到明王朝的多次鎮壓,在這些沖突中,以都掌蠻的遭遇最為突出。都掌蠻主要分布于徐州府的戎、珙、筠、高、長寧、慶符等地,在與明王朝發生多次軍事沖突后,退到戎縣,占據了九絲城,而以都都寨為左翼,凌霄城為前障,地勢十分險惡,易守難攻,是明王朝的心腹大患。直到萬歷元年,四川巡撫曾省吾成功戰勝都掌蠻,更改九絲城為平蠻城,凌霄城為拱極城,都都寨為定都寨,在此地建造建武千戶所。據《明太宗實錄》記載,永樂十九年冬十二月丙申,設置徐州府筠連縣三岔口、高縣江口、珙縣洞門鋪三巡檢司。而根據《明神宗實錄》記載,萬歷三年正月,四川巡撫曾省吾奏移洞門巡檢司改置建武,鹽水壩巡檢司改置歇馬壩,都寧驛改置上羅堡。顯然,徹底平定都掌蠻后,洞門巡檢司的位置直接從珙縣遷徙到了建武城中,可見,巡檢司的設置并非一成不變的,而會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進行調整。
(二)明代巡檢司制度在廣東省沿海地區的實施情況
明代廣東行省的地理環境和社會環境十分復雜,因此巡檢司需要承擔的職能也很復雜,潮州府是其中的典型。明代的潮州府位于粵、閔、贛三省交界之處,北部皆為山區,盜賊眾多,中南部毗鄰南海,倭寇橫行,域內橫亙多條大江大河,水道交通網絡發達。據《潮州府志》記載,從洪武二年(1369年)到洪武四年(1371年)之間,共設置了11處巡檢司,其中山區5處,沿海6處。山區的設置的巡檢司是為了對抗盜賊,沿海設置的巡檢司則為了抵御倭寇,這個時間段防山和防海并重。
在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巡檢司進行了第一次大的調整,北山司由北山村移到沿海的神泉村,改稱神泉司,扼守神泉港,由于潮陽守御千戶所由潮陽縣城移到了海口村,取代了海口司的位置,故該司搬到了招收都招寧村,改稱招寧司,扼守達濠港;吉安司也由南山遷到練江之畔的貴嶼村,雖然貴嶼村仍屬山區,但由港口沿練江而上可直達該司。由此看來,這個時間段更加強調巡檢司的海防功能。隨著倭寇的日益猖獗,原有的海防體制已不足以應對,到了嘉靖中后期,在總督吳桂芳的統一領導下,南海構建了以六大水寨為主體的海防體系,潮州府的海防由其中的柘林水寨分管,巡檢司的海防功能不再如前期重要。潮州府巡檢司的第二次大的調整就發生在嘉靖年間,山區的巡檢司大幅增加,這次調整則進一步強調了巡檢司的山防功能。
(三)明代巡檢司制度在蘇州地區的實施情況
蘇州地區地處我國東南沿海,物產豐富且水系縱橫,水陸交通皆十分便利,在我國的歷史上,整個蘇州地區長期以來都是經濟比較發達、商旅眾多,而且社會穩定,明朝時期也是如此。蘇州地區的巡檢司在明朝時期的變動較大,但蘇州地區巡檢司的駐地,不論明初設置的地點還是遷移后的地點,都是境內水陸要道或重要市鎮。如木瀆巡檢司所駐木瀆鎮是擺渡太湖必經之地,吳塔巡檢司嘉靖間駐的蠡口鎮被稱為“府北之門”,巴城巡檢司所駐的真義舖是昆山縣“西境之咽喉”,石浦巡檢司駐千墩舖, 則是新陽江諸水匯入吳淞江的要害之處。
盡管蘇州府經濟發達、社會穩定、商旅眾多,但毗鄰太湖,在給當地帶來諸多便利的同時也增加了治理的壓力,而且這仍然是個臨海的地方,同樣面臨海防的壓力。根據是否臨海,蘇州府不同縣域的巡檢司的功能也不同。對于蘇州府內部的吳、長、元地區,巡檢司的主要職責是太湖水面的防護、蘇州城的防護以及滸墅關鈔關的防護;對于蘇州府的沿海的地區,物品可能通過入海口走私出去,倭寇也可能入侵進來,這些地區巡檢司的職責則主要是防止走私和外敵入侵。
根據以上三個案例不難發現,巡檢司的存在,除了基本的緝捕盜賊和盤詰行人之外,不同地區的地理環境與社會經濟環境還賦予了這個機構不同的功能。在西南民族地區,巡檢司在其設置之初主要承擔軍事功能,是具有輔助意義的軍事機構,與里甲制度、堡兵制度相配合,以便完成明王朝對少數民族的鎮壓,當實現了對少數民族的鎮壓后,就轉變為行政機構,對少數民族進行治理和管控。與其他地區不同的是,上述來自西南民族地區的案例,因為也任用土著少數民族中的有勢力的首領擔任正巡檢或副巡檢,往往,也由他們帶領的當地土兵取代了弓兵,與流官擔任正巡檢和弓兵承擔相應任務的巡檢司相對而言,由土官擔任巡檢和弓兵或者土兵承擔相應任務的巡檢司也被稱為“土巡檢司”。西南民族地區土巡檢司的存在,是統治者統治智慧的充分體現,由于文化、地理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中央的政令很難深入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尤其是深入到這些地方的基層鄉村,流官很難對該地區或該少數民族具有充分的了解,在鎮壓這些少數民族后,選擇這些少數民族中有勢力的首領,予以巡檢或副巡檢的官職,讓他們加入對該地區進行基層治理的隊伍,能夠實現“以夷制夷”。
而在廣東地區的巡檢司,同樣也承擔著進行軍事防御的職責,這主要是由當地獨特的地理環境決定的,但這些地方的巡檢司都不是主要的軍事防御力量,在抵御外敵入侵的斗爭中,他們并非主力,而僅僅是輔助機構,但它們又是必不可少的,在明朝時期,衛所是國家軍隊的編配,承擔著維護國家軍事安全的重擔,由國家財政供給,承平之時,在地方也承擔維護地方治安的職責,但國家財政有限,衛所幾無可能廣泛分布于王朝的各個角落,巡檢司則恰恰可補給衛所之不足,設置靈活,數量較少,由所在區域相應丁糧戶內僉派,并不增加國家財政負擔,衛所與巡檢司相互協作,形成層次分明的地方防御體系。當廣東沿海的倭寇猖獗時,通過設置巡檢司能夠分散一些抗倭壓力,而當廣東沿海的軍事防御體系得到完善,不再需要巡檢司就足以抵御倭寇入侵后,通過遷撤銷或遷移巡檢司的駐地,又能夠及時轉變巡檢司的功能,將巡檢司的力量運用到需要的地方,由此可見,巡檢司制度比較靈活。
而在蘇州地區的巡檢司制度則充分體現了巡檢司在經濟發達、人流量大的地方的存在價值,在這樣的地方,流動人口較多,對流動人口的管控是一大難題,在中國的封建王朝時期,里甲制度在國家銜接國家權力方面具有重要意義,承擔著征發徭役,征收賦稅的職責,是國家在固定區域內對固定人口的有效控制,但對于流動人口,里甲的作用就顯得極為薄弱,而巡檢司則正好能夠解決對于在路途中、處于流動人口的監管不到位問題。巡檢司與里甲制度互為補充,形成了對鄉村人口的全面防控。同時,巡檢司在蘇州府還承擔著稽查走私、湖泊治理、督造水利、防范海盜的功能,這也體現了巡檢司任務的繁重。
三、明朝巡檢司制度的實施效果
任何一項制度的確立,其初衷都是好的,巡檢司制度的建立,就是為了加強對基層鄉村的控制,維護地方社會的穩定,鞏固明王朝的統治地位。在緝捕盤詰、防止走私、暢通商路、抵御外敵、征收賦稅、基層管控等方面,巡檢司制度的確發揮著積極作用,從整體的實施效果上來看,的確達到了統治者集團的初衷。但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不同的地區難免會產生不同的成效。而且隨著時間的推進,任何一項制度設計都有可能會逐漸暴露出它的弊端。
這幾個例子能夠說明這項制度的實施效果的差異:一是海瑞在《興國縣八議》中記載,巡檢官在每年下鄉巡查時都會勒索當地,盡管海瑞到任后嚴禁這種行為,但巡檢官會在深山窮谷地區借口盤緝騙人屢禁不止。二是《明宣宗實錄》中所記載的:“專一在鄉,設計害民,占據田產,騙要子女,稍有不從,輒加以拒捕私鹽之名,各執兵杖,圍繞其家擒獲,以多槳快艦裝送司監收,挾制官吏,莫敢誰何,必厭其意乃已,不然,即聲言起解赴京,中途絕其飲食或戕害致死。小民畏之甚于豺虎。”這兩個案例說明了巡檢為了謀取自己的私立,仰仗把守關津要害之便,以執行公務之言,行牟利坑害之實,這樣的案例想必在整個明朝統治的遼闊疆域、在漫長的明朝統治時期,應該不勝枚舉,這樣看來,這項制度,并非在所有地方都達到了良好的實施效果。但在《明宣宗實錄》中,也記載著比較正面的案例,四川順慶府蓬州東接營山、渠縣,南抵廣安州,當地原本設置了巡檢司,后來又廢除,廢除巡檢司后,居民不能抵御盜賊,當地重新設置了巡檢司,終于盜息民安。可見,在一些地方,巡檢制度確實取得過良好的實施效果,得到了百姓的認可。
另外,如前文所述,從巡檢司的所屬、巡檢的品級以及巡檢司人員的構成情況來看,巡檢的地位很低,而巡檢司卻承擔著緝捕盤詰、防止走私、暢通商路、抵御外敵、征收賦稅等方面、基層管控等方面的職責,職能繁雜、任務艱巨。而無論是普通的巡檢還是土巡檢,都面臨嚴格的考核要求,關于巡檢的考核,原本只看任內有無過失,但在洪武二十五年,更改了巡檢的考核標準,確定巡檢的職責是逮捕逃軍、逃走的囚犯和抓捕盜賊等,根據捕獲200名、100名、30名等為層次,參考在工作途中有無過失加以升降獎懲。巡檢想要從從九品的品級往上升,非常困難,這樣嚴格的考核要求,直接打擊了巡檢的積極性,也無法吸引人擔當巡檢的工作,不利于巡檢工作隊伍的發展,也就阻礙了巡檢司制度的發展。
四、明朝巡檢司制度的當代價值
明朝時期的巡檢司制度,能夠始終存在,沒有被廢止,并延續到清朝時期,是因為在那個時代發揮著積極作用,對統治集團而言,具有長期存在的價值;同時,作為我國警察制度的前身,它也具有重要的當代價值。
首先,明朝時的巡檢司制度充分體現了因地制宜的特點,在四川地區尤為顯著。在巡檢司的設置上,16個府州中,成都府數量最多,有16個;其次是敘州府,有13個;然后是夔州府、重慶府,分別有9個、7個;而順慶府最少,僅有1個可見,并非每個州縣都有,而是根據當地的實際需要來設立。 成都府是四川行省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有藏族、彝族、羌族等少數民族聚居區域的責任,管轄著總數眾多的人口,在征收賦稅方面面臨著繁重的任務,出于政治穩定需要在成都府設置的巡檢司數量是最多的;而敘州府地處四川西南部,與云南行省、貴州行省接壤,是云、貴、川三地交界之處,是重要的津要關隘之地,另外此地高山眾多,少數民族廣布,且長期存在反體制的少數民族群落,需要加強管控;而夔州府與重慶府地處川西,域內有重要的水路,是溝通四川行省與中原腹地的重要地區,是川西面向中原的“咽喉之地。”在這些緊要之地設置巡檢司,是因地制宜的表現。
其次,西南民族地區設置的土巡檢司,為處理央地關系提供了思路,在這些地區,在鎮壓少數民族之后,通過任用當地的少數民族土著首領來對該地進行管理,實現“以夷制夷”的效果。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往往就是中央與地方權力之間的博弈,通過將地方的利益轉化為中央的利益,使中央和地方在利益博弈中實現共贏,既實現中央的統治目的,又能緩和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矛盾,這也是值得學習的地方。
再次,在基層治理的過程中,要注重協同治理。如在沿海地區巡檢司與衛所的協同合作,巡檢司作為衛所的補充,彌補了衛所的不足,共同構筑了比較完善的沿海防御體制;而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巡檢司制度同樣與堡兵制度相互配合,加強中央對地處邊遠的少數民族地區的控制;同時,中國古代封建國家實行里甲制度,但里甲制度對于流動人口的控制薄弱,巡檢司制度與里甲制度相輔相成,共同構建了基層鄉村的控制體系,加強了對基層的管控。在當今的治理中,同樣應該注重協同治理,使多種制度設計相互配套,形成合力。
最后,通過明朝巡檢司制度在官員考核上暴露出來的問題,也能帶給我們啟示。任何一套制度設計,都要注意在這項制度中人的作用,要注重人才隊伍的培養,通過各種激勵措施充分發揮官員的積極性,才能使該項制度能夠良好地運行。
五、結論
明朝時期的巡檢司制度,是聯系地方政府與基層鄉村的重要紐帶,對于加強基層鄉村的控制、維護地方社會的穩定具有重要作用。
在不同的地區,巡檢司制度的具體實施情況不同,這主要是由當地的地理、經濟、社會環境決定的,巡檢司的設置充分體現了因地制宜的特點,也體現了巡檢司職能的繁重與工作的艱巨;隨著時間的推進,巡檢司制度的弊端也暴露出來,巡檢地位較低而任務繁重,上升的路徑卻不暢通,不利于培育官員的工作積極性。
明朝的巡檢制度盡管存在一些問題,但總的來看,它在那個時代發揮著積極作用,對統治集團而言,具有長期存在的價值;其反映了因地制宜、“以夷制夷”、治理協同以及注重對官員激勵的重要性。
參考文獻:
[1]鄭天挺主編:《中國歷史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年,第1288頁。
[2]李良品,羅婷:《論明清時期西南民族地區巡檢制度》,《三峽論壇》2015年第4期。
[3]王偉凱:《試論明代的巡檢司》,《史學月刊》2006年第3期。
[4]李良品,羅婷:《論明清時期西南民族地區巡檢制度》,《三峽論壇》2015年第4期。
[5]陳世松主編:《四川通史》(第五冊),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70年,第24頁到25頁。
[6]吳宏郡:《明代四川地區巡檢司分布變遷考》,重慶:西南大學,2011年。
[7]周偉峰,黃忠鑫:《明代潮州府巡檢司的設置與山海防御》,《歷史檔案》2017年第3期。
[8]趙思淵:《明清蘇州地區巡檢司的分布與變遷》,《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