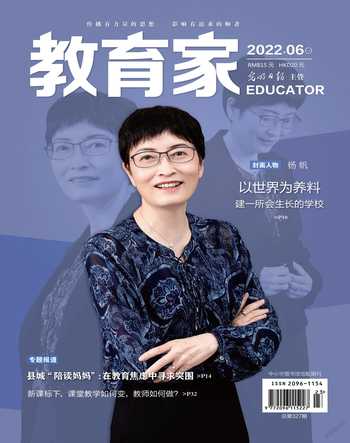教育決策要少拍腦袋多做實驗
葉存洪

教育實驗,按照《教育大辭典》的解釋,是指在一定教育理論或假設指導下,通過實驗探究教育規律的活動。通常根據研究課題的設想和一定的實施方案,在特定條件下有組織地進行。可以有目的、有計劃地觀察與鑒別各種教育措施的實效,找出實據和規律,為教育改革提供可靠依據。主要特征是:以科學的假設為前提,實驗過程被施行嚴格的、積極主動的控制,探求變量間的因果關系,具有可重復性。通過教育實驗,既可以檢驗現有教育理論和觀點的科學性、先進性,也可以為解決教育實踐活動中的現實問題提供理論依據,或為改進教育實踐提供最優化的互動策略。
近現代以來我國教育領域開展了不少典型實驗——
有以學校為單位進行的教育實驗。比如,1929年,上海第一實驗小學在全市19所公私立小學選拔天才兒童,為他們設計了更有針對性的課程,開展天才兒童教育實驗。又如,燕子磯實驗小學開展生活教育實驗:國語課上,教學生寫信、寫田契;自然課上,帶學生到長江邊燕子磯巖石下,了解江水風雨侵蝕的力量;教農事時,帶學生到農場親手種植作物、畜養動物,把生活與教育的關系演繹得淋漓盡致。
也有以區域為單位進行的教育實驗。比如,晏陽初1926年起在河北定縣開展平民教育實驗,在深入調查的基礎上,總結中國農村存在愚、窮、弱、私“四大病”,相應地實施文藝、生計、衛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并從學校、家庭、社會三大方面整體推進,形成了舉世聞名的“定縣模式”。又如,梁漱溟自1931年開始在山東鄒平開展鄉村建設運動,這是一個綜合性改造中國鄉村社會的方案,內容涉及方方面面,概括起來四個字——“政、教、養、衛”。后來實驗區逐步擴大到十幾個縣,在海內外產生了廣泛影響。
反觀今天,很多教育決策不是從實驗中得出,而是——
一憑經驗決策。經驗其實是一把“雙刃劍”,它可能是我們解決新問題的優勢,也有可能成為束縛我們手腳的心理定式或思維定式。過往的優勢此時說不定已經不是優勢,彼處的經驗此地說不定已經成為包袱,如果靜止地看問題,以不變應萬變,無異于刻舟求劍。
二靠權力決策。有的地方權力“一言堂”,誰官大誰說了算:“這事就這么定了,不用再說了!”“驚堂木”一拍,事就定下來了。領導是從優秀員工中產生的,不排除他比一般員工懂得更多,特別是當上領導之后,接觸的領域廣,鍛煉的機會多,視野會更為寬闊,能力發展也更為全面。但即便如此,也很難保證單靠權力決策不出任何問題。
當然,也有調查研究。毛澤東同志是調查研究的行家里手,他認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在極其繁重的革命和建設工作中,他親自做過無數次深入細致的調查。僅大革命時期保留下來的,就有《尋烏調查》《興國調查》等至少七篇調查報告。他的調查費時數月乃至數年,身子沉下去,實情撈上來。再看今天的一些調研,不深入,似蜻蜓點水,如浮光掠影。雖然這樣多少也能夠了解到一些情況,但更多的恐怕只是面上的眾所周知的東西。
今天有很多重大教育課題需要進行嚴謹、科學的實驗——
九年一貫制學校如何“一貫”?20世紀80年代,強調教育界要“只爭朝夕育人才”“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多出人才”,于是,1984至1989年,各地陸續開辦小學和初中聯體辦學的九年一貫制“實驗學校”。2021年6月,教育部、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印發《關于深入推進義務教育薄弱環節改善與能力提升工作的意見》,提出“鼓勵各地建設九年一貫制學校”。現在九年一貫制學校越來越多,但事實上,很多學校有“九年”無“一貫”,“小學”“初中”兩個學段學區劃分往往不一樣,部分小學畢業生會去別的學校上初中,而初中新生也有一部分不是本校小學部升上來的,所以無法開展管理、課程、德育等一體化實驗,甚至連教育行政部門對學校的考核評價都是分“小學”“初中”兩撥進行的。
教育集團如何運作?而今集團辦學成為一種趨勢,一些區(縣)規定,一兩年之內全區(縣)所有學校實現集團化辦學,以促進教育資源優質均衡。那么,集團化是不是一服“一‘集團’就‘優質’”的靈丹妙藥?各個校區如何實現既有統一要求又有靈活自主?集團管理層的“縣官”與所在區(縣)教育行政部門的“現管”之間如何有效協調?這些都是亟待解決的嶄新課題。
普職如何融通?當下,“普職分流”引起社會各有關方面的廣泛關注,家長的焦慮也由原來的高考下移到了中考。分流的比例應該根據地方的產業結構、人才資源需求科學研判,不宜“一刀切”。普、職可否不那么涇渭分明,開展綜合高中建設的嘗試,探索育人的新模式、新路徑?
超常兒童如何培養?人的智商有高有低、發展有快有慢,這是一個客觀事實。是不是把中學“少年班”取消,讓智商高低有別的孩子坐在一起受教育就叫作教育公平、教育均衡?實踐和研究都表明,只要教育方式方法得當,智商高的孩子完全可以提前1—2年學完中小學的全部內容,并提前參加高考。美國從20世紀50年代就開始鼓勵天才教育,通過《國防教育法》《天才兒童教育法》《杰維斯資賦優異學生教育法案》《授權教師給予天才和高能力學生幫助法》等,加強天才兒童的教育和研究。
學制多長合適?近年不時有人建議適當縮短學制,或調整“六三”為“五四”。2016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莫言在分組討論時發言建議,將中小學學制從12年改成10年,并取消小升初和中考。同年7月,21世紀教育研究院在北京召開了一場以“基礎教育學制改革”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與會教育專家對莫言的建議表示反對,認為其觀點缺乏理論支撐與科學依據。你可以不同意別人的觀點,但不要這么簡單、武斷地否定,可以開展實驗。
……
當然,不是所有的教育問題都需要實驗,也不是所有的教育問題都可以實驗,但上述問題或許大多可以實驗為基礎,先行先試,待取得經驗后,再逐步推廣。領導要少簽、慎簽一些“全省(市、縣)推廣”之類的批示。各地土壤、水分、光照等都不一樣,“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這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道理。歷史經驗表明,凡是以“齊步走”“一刀切”的方式推進的教育改革,幾乎沒有成功的。等到不成功了,又“很大方”地寬慰自己“就當交學費了”,接著開始新一輪的“全省(市、縣)推廣”,希望以此糾正、彌補上一輪改革的問題和缺陷。我們還沒有“富”到不需要考慮“錢”的時候,沒有那么多錢動不動“交學費”,最為關鍵的是,培養人的事經不起這般折騰。英國哲學家、教育家洛克說得好:“教育上的錯誤比別的錯誤更不可輕犯。教育上的錯誤正和錯配了藥一樣,第一次弄錯了,決不能借第二次、第三次去補救,它們的影響是終身洗刷不掉的。”
所以,教育改革,少拍腦袋、多做實驗為好。
責任編輯:劉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