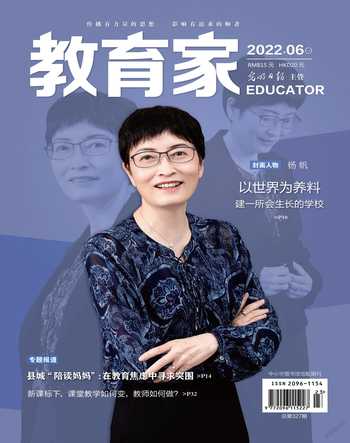“要是把孩子耽誤了,咱一輩子后悔”
周麗
手機屏幕里,42歲的向陽形貌樸實,一張黑瘦的臉,顴骨略突起,咧嘴笑時可以看到上牙缺失了一顆。講述中,她每一段話語后都跟著幾秒鐘深思熟慮似的停頓。帶著京腔的口音,刻錄著她多年的北漂時光。隨著對話的深入,從掀開的生活一角,記者窺視到平凡生命里一抹堅韌、溫暖的底色。
回來上學是兒子的決定
今年是向陽回到自己的家鄉——江西宜春靖安縣的第三年。在此之前,她已在北京漂了16年。這段歲月里,她經歷了懷孕、生子、喪夫,以及漫長的拉扯孩子長大的單親媽媽生活。如果不是因為兒子子航的求學問題,也許她會一直漂下去。盡管這座城市,對異鄉人既包容,又疏離。
2018年,子航面臨小升初。和很多流動家庭一樣,向陽和兒子開始提前考慮中考的問題。按照政策,要考普通高中,他們只能回戶籍地。向陽本打算讓兒子上初三時再轉學。“他不干,說等到那時候肯定不習慣,考不上高中。”子航決定初一就回老家,并且是自己一個人回去。這一決定出于多方面的考量:媽媽可以繼續留京掙錢養家,而他和北京之間的牽絆也不會就此中斷。
向陽雖不放心,但見兒子態度堅決,且打小就被培養得很獨立,也就同意了。就這樣,不到13歲的子航獨自轉回靖安的一所鎮初中。
同一年,向陽弟弟的孩子幼升小,她的母親和弟媳帶著孩子從北京回到老家上學。一開始,向陽請母親去照看子航,但沒幾天,體諒外婆更習慣住在農村老家,子航便讓她回去了,自己走讀。
自出生起,子航便在北京長大,其間返鄉的次數屈指可數。對于子航而言,家鄉的一切都是那么陌生。新的學習階段,陌生的生活環境,再加上“舉目無親、無依無靠”,很快,向陽擔心的情況就出現了。
“我一禮拜至少跟老師溝通兩三次。因為我不在身邊,對這孩子就特別上心,跟老師溝通特別勤。”從和老師的交流中,向陽獲知子航經常不寫作業,無故不請假不上學,學習退步了很多——在北京那會兒,子航的成績在三年級之前可以拿滿分,四年級之后稍微往下掉了一點兒,但仍屬于“上等”。得知子航的表現,向陽無比揪心。
被問及為何不寫作業、不上學,子航開始只說“不適應”。在向陽反復的勸解下,子航才吐露心聲:“我回來就不想寫,因為家里面一個人沒有……”
眼看這樣下去不行,向陽知道自己非回去不可。這種抉擇里也包含著她對自己沒能讀高中的遺憾。上初中時,因為家境貧寒,向陽很早就被母親宣告,“考上了也不讓你上學”。為此,向陽一度對母親心存芥蒂。她不希望兒子如她一樣,在成長的關鍵期,缺失了來自母親的支持。向陽深知:“掙的錢是有數的,但要是把孩子耽誤了,咱一輩子后悔。”
子航上初二時,向陽回到了兒子身邊。
隨向陽一起回老家的,還有她的外甥小宇。小宇是子航姑姑的兒子,和子航同齡,也隨父母在北京出生、長大。在此之前,小宇母親打算等他上初三再送他回老家上寄宿學校。一聽說向陽回去,立馬就把孩子交給了她。由此,向陽成了兩個孩子的“陪讀媽媽”。
“雞飛狗跳”的陪讀日子
回到靖安后,向陽沒有像在北京那樣,做小買賣、干家政,而是進入一家照明廠,成了一名燈具組裝流水線上的工人。向陽解釋道,上班有固定的時間,不像自己單干需要操心,沒有精力管孩子。
陪讀兩年后,子航和小宇考上了靖安縣最好的高中。向陽在縣城租了一套房子,距離學校只有一公里,到她上班的工廠騎車也只要五分鐘。
如今,向陽每天過著兩點一線的生活,7:30上班,17:30下班,中午有一個小時休息時間。因為孩子們早上“隨便吃點”就上學了,晚飯又因要上晚自習而在學校吃,為了給他們加強營養,向陽每天中午都會趕回家做飯。
在這一餐上,向陽沒少花心思。頭天晚上她就得想好第二天給孩子們做什么。中午時間短,她通常早上5點多就起來準備午飯,把費時的菜、湯之類的先燉好。每周的食譜,兩頓排骨、兩頓牛肉和兩頓魚是標配。“我也不能給他們什么,只能給他們一個好身體,讓他們長大了自己奔。”
除了照顧子航和小宇的飲食起居,向陽還要處理兩個孩子間的矛盾,盡到“代理媽媽”的職責。
在北京時,因為生活在不同區,距離較遠,向陽和大姑姐兩家人極少見面,子航和小宇也因此并不熟絡。“他們倆一個屬雞,一個屬狗,屬相不對付,合不到一塊。”在向陽看來,兒子和外甥是兩種性格。一個是有事說事的直腸子,另一個是沉默寡言的悶葫蘆;一個喜歡跑步、打球,另一個愛宅家玩電子游戲……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子航和小宇之間摩擦不斷,向陽時常要充當兩人之間的“潤滑劑”。
向陽坦言,對待兒子和外甥,她是有所“區別”的。“兒子有什么事做得‘過分’了,我肯定會跟他急,嚷嚷他。對外甥,我就會婉轉地跟他談話,不會向他發脾氣,但是別的我都一樣,我是真管他。”
剛回來的一段時間,小宇常玩游戲到很晚,向陽提醒他兩回仍不聽,第三次時,向陽直接把他的iPad沒收了。幾個回合“較量”下來,即使小宇“尋死覓活”,向陽也沒有妥協。“他跟了我有幾個月,我了解他,他不是那種犯渾的孩子。”經過苦口婆心的開導,小宇最終答應只在周末玩一會兒。
與父母在一起時,小宇作為家中唯一且最小的男孩,備受寵溺,生活起居基本上被母親承包,甚至于“連自己的洗臉毛巾都不認得”。向陽以從小對兒子的標準要求小宇,教他洗衣、刷碗、疊被……鍛煉他的生活自理能力。現在,小宇“什么都會了”,學習上也沒有耽誤,有時成績比子航還要好。中考后,小宇父母本想讓他回自己的原籍——南昌市的一所縣中就讀,但他還是選擇了留下。
至于子航,向陽對兒子的身心健康問題比較放心,主要擔心的是他的學習。“他偏科特別嚴重,數理化應該說屬于優秀,但語言方面的學科就比較薄弱。”
在子航的學習問題上,向陽除了言語敲打,很多時候只能干著急,同時她也不想給孩子過大的壓力,因為她知道,子航看上去不慌不忙,其實心里憋著一股勁——下晚自習后,子航總會跑步半小時,大汗淋漓一場。這是他緩解壓力的方式。
陪讀,是精神上的陪伴
問及媽媽在身邊陪讀的感受,子航答:“可能是精神上的一種支柱,每次回家看到媽媽,就感覺心里很踏實。”
“陪伴是一種力量,可以抵擋世間所有的堅硬,溫暖生命所有的歲月。” 于向陽母子,更是如此。
子航兩三歲時,向陽的丈夫就因病去世。多年來,忙于生計的向陽一直未再婚,母子倆相依為命。
在北京的頭幾年,向陽一邊開小賣部一邊經營棉被加工。后來,店鋪面臨拆遷,租不到合適的場地,向陽偶然在一個鄰居的介紹下,做起了家政。
為了照顧兒子,向陽沒有做住家家政,而是干鐘點活兒。因為干活實在、細致、負責任,再加上性格樂觀、爽朗,向陽深得雇主的認可和信賴。這份工作,向陽其實很舍不得丟。“我最懷念的就是干家政的那些年。”向陽說,“因為我接觸的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我可以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知識,比如怎么教育孩子,怎么跟孩子溝通……我特別感謝他們。”
如今,每天在流水線上重復著單調枯燥的動作,聽著周圍的人聊家長里短、是是非非,向陽“隨遇而安”,但沒有“隨波逐流”。難得的閑暇時間,她用看書、運動來填充。“每年我都會給孩子買書,我自己也看,像孩子上小學時看的《戰馬》《記憶傳授人》,還有《追風箏的人》《四世同堂》《駱駝祥子》《海底兩萬里》《平凡的世界》……反正逮著什么就看什么。”
孩子高考以前,向陽陪讀的日子將繼續下去。至于更遠的打算,向陽說:“看兒子考哪兒,如果他考到北京,我就繼續陪他。因為原來的雇主們盼著我回去,我也特別想念北京……”
而這,也是子航的愿望。子航有兩個要好的小學同學,同樣在小升初時各自回到山東、河南老家。他們三人約定,以后一起考回北京。在這個大方向之下,子航還給自己定了一個具體的“小目標”——在北京時,子航曾參加一個名為“小伴讀”的公益輔導項目。在這里,他得到了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任教的一位志愿者的輔導和關愛。受此影響,北航成了他的向往之地。
目前,子航的成績處于年級中上游,這讓他有些許泄氣。前幾天,子航對向陽說:“媽,我以前好像說大話了。”向陽鼓勵兒子:“這‘大話’既然放出去了,就得加倍努力,不到最后誰也不知道啥結果,咱們絕對不能放棄。”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