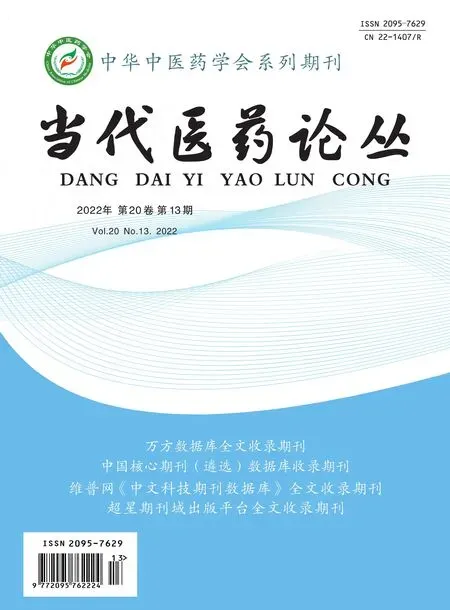3D打印技術在骨盆骨折合并髖臼骨折患者術前規劃中的應用價值
楊 雷,鄧 延,任 洋,紀丁琦,王曉東
(洋縣人民醫院骨二科,陜西 漢中 723300)
骨盆骨折合并髖臼骨折屬于暴力損傷所致骨折的一種。據統計,骨盆骨折合并髖臼骨折患者約占全身骨折患者總數的3%。由于人體骨盆和髖臼的解剖結構復雜,因此骨盆骨折合并髖臼骨折的治療較為棘手,是骨科醫生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現階段,臨床醫生在術前評估患者的骨折類型時多以螺旋CT 平掃、X 線片等影像資料及自身的手術經驗為依據,因此常存在主觀性和差異性,術前所制定的手術復位固定策略缺乏可靠性和精準性[1]。近年來,3D 打印技術在臨床骨科得到了廣泛應用,大大提高了手術的精準性。基于螺旋CT 三維圖像的3D 技術,可按照1:1 的比例將骨盆及髖臼骨折的三維模型打印出來,顯示骨折部位的整體面貌,通過多視角全面了解骨盆及髖臼骨折的情況,進而可為手術方案的制定提供確切依據[2]。本文主要是探討3D 打印技術在骨盆骨折合并髖臼骨折患者術前規劃中的應用價值。
1 資料與方法
1.1 基線資料
本文納入的研究對象為洋縣人民醫院收治的60 例骨盆骨折合并髖臼骨折患者,其入組時間為2019 年7 月至2021 年8 月。其納入標準是:病情符合骨盆骨折合并髖臼骨折的診斷標準,且經影像學檢查得到確診;具有進行手術治療的指征;各項臨床診療資料完整、真實、有效;自愿參與本研究。其排除標準是;擬行保守治療;有骨盆或髖臼手術史;術后隨訪脫落或中途退出本研究。依據術前是否使用3D 打印技術將其分為常模組(n=28)和3D 組(n=32)。在3D 組患者中,男性、女性患者分別有17 例、15 例;其年齡為23 ~67歲,平均年齡為(45.74±2.13)歲。在常模組患者中,男性、女性患者分別有15 例、13 例;其年齡為24 ~68 歲,平均年齡為(46.14±2.49)歲。兩組患者的基線資料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0.05)。
1.2 方法
1.2.1 術前處理及規劃 在兩組患者入院后,首先對危及其生命的合并傷進行處理,用骨盆加壓帶固定制動其骨盆和髖臼部位,或采取骨盆外固定支架對其骨盆和髖臼進行固定。若患者早期有血流動力學不穩定的現象出現,應對其進行抗休克治療。骨折內固定手術多于實驗室檢查結果出來及患者血流動力學穩定后實施。常模組患者在術前規劃中未使用3D 打印技術,主要依據CT、X線片等影像學資料制定手術計劃,并基于此執行傳統的手術方案。3D 組患者在術前規劃中使用3D 打印技術,按照1:1 的比例將骨盆及髖臼骨折的三維模型打印出來,并多次、反復地進行手術預演,然后基于此執行精準手術方案,具體為:對患者進行螺旋CT 掃描(層厚為1 mm)及骨盆X 射線檢查,將掃描、檢查獲取的骨折圖像以DICOM 格式保存。將圖像資料導入相應的軟件中,建立數據包。在雙噴頭全封閉3D 打印機中導入數據,以聚乙烯合成材料按照1:1 的比例打印出骨盆及髖臼骨折模型。在模型中進一步明確骨折塊的數量、骨折粉碎的情況、移位方向及骨折類型,并確定具體的內固定方式及手術入路方式。在3D打印模型上反復預演內固定鋼板的塑形、骨折的復位固定、螺釘進針的長度、方向及數量等手術操作。術前對已塑形的內固定物進行常規消毒,備用。
1.2.2 手術方法 兩組患者均由同一組臨床經驗豐富的外科醫生進行手術。術中對患者進行氣管插管全身麻醉。手術入路方式有后方Kocher-Langenbeck 入路、腹直肌旁入路、Stoppa 入路及前方髂腹股溝入路等。前方髂腹股溝入路適用于大部分的骨盆前方骨折患者,前部可將恥骨支骨折處和恥骨聯合顯露出,中間可將髖臼前柱、前壁顯露出,后部可將骶髂關節部位骨折顯露出。常模組患者主要依據術者閱片及臨床經驗設計手術方案。術中輔助患者取合適的體位,一般為髖臼骨折側在上的漂浮體位,以便于術中更換手術入路方式。3D 組患者依據術前模擬、演練的方法,經合適入路將骨折部位暴露出,依據術前的設計方案對骨折端進行復位,置入內固定系統,并于最佳位置打入內固定螺釘。
1.2.3 術后處理 在圍手術期為患者應用抗生素,以防其發生感染。于術后第2 天用低分子肝素鈣對患者進行抗凝治療,以防其發生下肢深靜脈血栓。從術后第1 d 開始,指導患者進行踝關節的跖屈、背伸活動和下肢肌肉的等長收縮訓練。于術后28 d 協助患者進行下床訓練,于術后8 周讓患者拄雙拐逐步站立或使用助行器行走,于術后10 ~12 周指導患者進行負重行走訓練。
1.3 觀察指標與療效判定標準
比較兩組患者圍手術期的各項指標[3],包括手術的時間、術中透視的次數、術中的出血量和圍手術期的輸血量。比較兩組患者的臨床療效。依據Majee 評分(包括7 個維度,各維度的分值均為1 ~6 分,總分為42 分)將患者的臨床療效分為優、良、可、差4 個等級。優:術后患者的Majee 評分較治療前提高≥90%。良:術后患者的Majee 評分較治療前提高80% ~89%。可:術后患者的Majee 評分較治療前提高70% ~79%。差:術后患者的Majee 評分較治療前提高<70%。優良率=(優例數+ 良例數)/ 總例數×100%。比較兩組患者術后并發癥(如下肢深靜脈血栓、切口淺表感染、切口脂肪液化等)的發生率。
1.4 統計學方法
用SPSS 19.0 軟件處理本研究中的數據,計量資料用±s表示,用t 檢驗,計數資料用% 表示,用χ2檢驗,P <0.05 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圍手術期各項指標的比較
3D 組患者手術的時間短于常模組患者,其術中透視的次數、術中的出血量和圍手術期的輸血量均少于常模組患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0.05)。詳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圍手術期各項指標的比較(± s)

表1 兩組患者圍手術期各項指標的比較(± s)
組別 術中的出血量(mL) 手術的時間(h) 術中透視的次數(次) 圍手術期的輸血量(U)3D 組(n=32) 7.12±1.35 3.12±0.35 9.24±1.38 7.21±1.04常模組(n=28) 10.38±1.74 4.46±0.43 13.20±2.31 10.20±1.56 t 值 8.160 13.302 8.178 8.833 P 值 <0.001 <0.001 <0.001 <0.001
2.2 兩組患者治療優良率的比較
3D 組患者治療的優良率為96.87%,常模組患者治療的優良率為75.00%。3D 組患者治療的優良率高于常模組患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0.05)。詳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治療優良率的比較
2.3 兩組患者術后并發癥發生率的比較
3D 組患者術后并發癥的發生率為6.25%,常模組患者術后并發癥的發生率為14.29%。3D 組患者術后并發癥的發生率低于常模組患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0.05)。詳見表3。

表3 兩組患者術后并發癥發生率的比較
3 討論
創傷骨科中骨盆骨折合并髖臼骨折屬于嚴重創傷。雖然骨盆骨折與髖臼骨折可在遭受高能量暴力時同時發生,但兩者的損傷情況卻有不同的特征,治療重點也有所區別。骨盆骨折早期的治療重點是控制損傷、挽救生命,后期治療應以維持骨盆環的穩定為主[4]。髖臼骨折是一種關節內骨折,其治療重點是精準復位骨折端并進行堅強內固定。由于骨盆與髖臼的解剖結構復雜,骨骼形態不規則,周圍密布重要的組織,顯露困難,且發生骨折后呈明顯的個體差異,因此骨盆骨折合并髖臼骨折的手術難度較大[5]。近年來隨著我國醫學技術的不斷進展,臨床上能通過對骨折患者的薄層CT 數據進行分析,實現對骨折部位的三維式復位編輯、重建及手術模擬操作,同時也可精準地打印出骨折位置的3D 模型。該技術的應用能夠幫助臨床醫生在手術前更為全面、精準地掌握患者骨折部位的立體形態、空間結構關系及關節面受損的情況等,有利于手術方案的制定,同時能通過3D 打印模型反復預演手術步驟,進而可在手術的過程中精準地完成骨折塊的復位、固定等操作。3D 打印技術在復雜形態骨折的診斷、手術治療和分型中均可發揮重要的指導作用。在骨盆骨折合并髖臼骨折患者的術前規劃中應用3D 打印技術具有以下優勢:1)可全面了解骨盆骨折及髖臼骨折的類型,評估骨折的情況。以往臨床上在手術前通常以CT、X 線片等影像學資料評估骨盆及髖臼骨折,即使是通過三維重建的影像資料,仍然是以二維的平面資料描述骨折的形態學,很難從整體上細致、全面地展示骨盆骨折的具體情況[6]。而3D 打印技術的應用可將骨折的形態學變化直觀地展示出來,使術者在手術前能夠準確地評判骨折的類型,基于此制定的手術方案更有針對性[7]。2)骨盆和髖臼均屬于骨性結構,按照1:1的比例將骨盆及髖臼骨折的三維模型打印出來,可于術前呈現骨盆與髖臼骨折的全貌,利于從多角度進行觀察,并能進行手術預演。3)可降低手術操作的難度,提高手術操作的精準性,減輕患者的手術創傷,有利于其術后恢復[8]。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3D 組患者手術的時間短于常模組患者,其術中透視的次數、術中的出血量和圍手術期的輸血量均少于常模組患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0.05)。3D 組患者治療的優良率高于常模組患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0.05)。3D 組患者術后并發癥的發生率低于常模組患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0.05)。可見,在骨盆骨折合并髖臼骨折患者的術前規劃中應用3D 打印技術能顯著縮短患者手術的時間,減少其術中透視的次數、出血量和圍手術期的輸血量,降低其術后并發癥的發生率,促進其骨盆功能的恢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