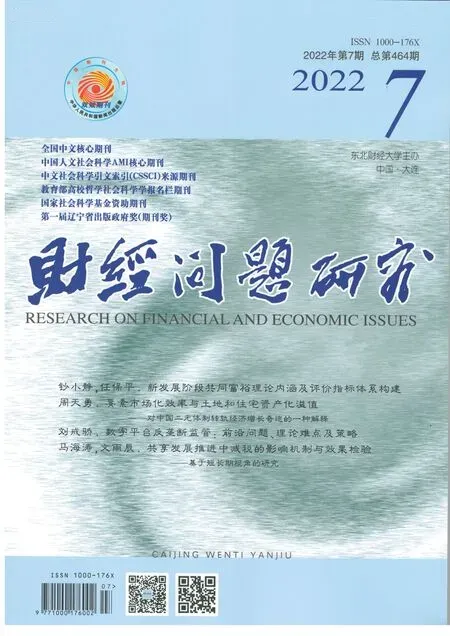消費(fèi)者目標(biāo)沖突對沖動(dòng)性購買的影響機(jī)理研究
劉冰 李懷斌




摘 要:沖動(dòng)性購買幾乎涉及所有消費(fèi)者,是營銷學(xué)和心理學(xué)共同關(guān)注的主題,但是一直以來消費(fèi)者目標(biāo)沖突對沖動(dòng)性購買的影響受到了有限的關(guān)注,本文以689名消費(fèi)者為樣本,采用逐步回歸法和層次回歸分析方法,實(shí)證檢驗(yàn)了消費(fèi)者目標(biāo)沖突與沖動(dòng)性購買之間的關(guān)系,并驗(yàn)證了潛在機(jī)制和邊界條件。研究結(jié)果表明,消費(fèi)者目標(biāo)沖突抑制了沖動(dòng)性購買,目標(biāo)沖突對沖動(dòng)性購買的抑制作用通過降低閉合需求和提高識解水平實(shí)現(xiàn),目標(biāo)沖突下的資源有限性感知促使消費(fèi)者形成更低的閉合需求和更高的識解水平,消費(fèi)者目標(biāo)沖突與沖動(dòng)性購買之間的關(guān)系受到調(diào)節(jié)聚焦的影響,與防御聚焦相比,促進(jìn)聚焦進(jìn)一步抑制了目標(biāo)沖突消費(fèi)者的沖動(dòng)性購買。本文聯(lián)結(jié)了目標(biāo)沖突與沖動(dòng)性購買的研究網(wǎng)絡(luò),提出了消費(fèi)者目標(biāo)沖突可能是抑制沖動(dòng)性購買的重要原因,或成為首批將目標(biāo)沖突納入沖動(dòng)性購買的研究之一。本文進(jìn)一步增強(qiáng)了對消費(fèi)者如何分配自我資源的理解,企業(yè)管理者和營銷人員可以通過降低消費(fèi)者目標(biāo)沖突、提高閉合需求和降低識解水平來提高消費(fèi)者沖動(dòng)性購買的營銷績效。
關(guān)鍵詞:目標(biāo)沖突;沖動(dòng)性購買;閉合需求;識解水平;調(diào)節(jié)聚焦
中圖分類號:F724.6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22)07-0111-09
一、問題的提出
消費(fèi)者相互對立的兩種或者多種可能性之間的認(rèn)知失調(diào)稱為消費(fèi)者目標(biāo)沖突,消費(fèi)者目標(biāo)沖突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當(dāng)消費(fèi)者追求一個(gè)目標(biāo)而損害對其他目標(biāo)的追求時(shí),消費(fèi)者目標(biāo)沖突就會(huì)發(fā)生[1]。受目標(biāo)沖突影響的消費(fèi)者遇到心動(dòng)的商品,會(huì)直接購買還是控制不買?目標(biāo)沖突之下,消費(fèi)者更具理性還是更加沖動(dòng)?消費(fèi)者目標(biāo)沖突促進(jìn)了沖動(dòng)性購買還是抑制了沖動(dòng)性購買?已有研究表明,目標(biāo)沖突令人厭惡,與沮喪、神經(jīng)過敏、疾病等相聯(lián),降低任務(wù)表現(xiàn)并且損害個(gè)體決策效果,然而,Etkin和Memmi[2]的研究表明,消費(fèi)者目標(biāo)沖突不僅不會(huì)損害個(gè)體知覺,反而會(huì)對決策和行為產(chǎn)生積極影響。目前,較少有文獻(xiàn)將目標(biāo)沖突與沖動(dòng)性購買建立聯(lián)系闡明二者之間的潛在機(jī)制和邊界條件,從目標(biāo)沖突角度為企業(yè)管理者及營銷人員提供沖動(dòng)性購買營銷策略的理論尚存在一定缺口。
本文從消費(fèi)者目標(biāo)沖突與沖動(dòng)性購買的效應(yīng)關(guān)系出發(fā),Dholakia[3]認(rèn)為,如果個(gè)體認(rèn)識到制約因素,他們將經(jīng)歷某種程度的心理不適,這促使他們轉(zhuǎn)向?qū)_動(dòng)性購買后果的評估,在負(fù)面評價(jià)情況下,消費(fèi)者采用抵制沖動(dòng)性購買的策略。當(dāng)假設(shè)購買情境中沒有出現(xiàn)限制因素時(shí),個(gè)體沖動(dòng)對沖動(dòng)性購買的預(yù)測作用強(qiáng)于對購買的評估評級,當(dāng)約束因素存在時(shí),對購買的評估評級比個(gè)體沖動(dòng)更能預(yù)測沖動(dòng)性購買,因?yàn)橄M(fèi)者會(huì)形成更具評價(jià)性的深思熟慮。消費(fèi)者目標(biāo)沖突抑制了無關(guān)信息的激活,加深了信息加工,鼓勵(lì)了對立辯證思考,增加了對顯著理由的依賴,影響了后續(xù)無關(guān)決策的選擇延遲,改變了消費(fèi)者原有的認(rèn)知定勢,使資源看起來更少,故可形成更加合理、客觀的評價(jià)和決策[2]。筆者認(rèn)為,消費(fèi)者目標(biāo)沖突會(huì)抑制沖動(dòng)性購買。目標(biāo)沖突聚焦零和選擇,降低注意廣角[4],鼓勵(lì)辯證思維,引發(fā)更加詳細(xì)的信息搜索,接受先前存在的假設(shè)偏見并確認(rèn)偏差,使資源看起來更加有限,資源稀缺導(dǎo)致一種普遍的定向認(rèn)知,定向側(cè)重于約束,這種約束會(huì)持續(xù)影響后續(xù)無關(guān)任務(wù)的績效,之前情境激活的思維模式持續(xù)存在,并塑造消費(fèi)者隨后處理信息的方式,對刺激目標(biāo)總體性評價(jià)形成更加理性的行為意愿[5]。本文旨在探索消費(fèi)者目標(biāo)沖突與沖動(dòng)性購買的相互關(guān)系,以閉合需求和識解水平的影響為切入點(diǎn),以調(diào)節(jié)聚焦作為邊界條件,研究目標(biāo)沖突對沖動(dòng)性購買的影響機(jī)制,為企業(yè)管理者和營銷人員提高沖動(dòng)性購買營銷績效提供決策支持和營銷策略建議。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shè)
(一)目標(biāo)沖突與沖動(dòng)性購買
早期的目標(biāo)沖突理論捕捉到個(gè)體可能被推向或者拉向相互競爭欲望的各種方式[6], 目標(biāo)沖突可能是直接目標(biāo)干擾的結(jié)果或者是資源的限制[7]。,如缺乏可用的時(shí)間可能會(huì)造成事業(yè)與家庭目標(biāo)之間的沖突。目標(biāo)沖突引入營銷學(xué)領(lǐng)域主要定義為消費(fèi)者在一個(gè)目標(biāo)和一種資源間的權(quán)衡,或者兩個(gè)或多個(gè)目標(biāo)與資源之間的權(quán)衡[8]。Etkin等[9]發(fā)現(xiàn),目標(biāo)沖突使資源看起來更加稀缺,消費(fèi)者常處于資源性目標(biāo)沖突之中。,如沒有足夠的錢既買房又裝修,如一天只有24小時(shí)完成所有自己想做的事情,消費(fèi)者經(jīng)常在跨活動(dòng)分配資源上權(quán)衡沖突[7],內(nèi)在沖突特征是實(shí)現(xiàn)不同目標(biāo)所需的最終狀態(tài)或策略之間的根本性矛盾,研究普遍表明標(biāo)準(zhǔn)化目標(biāo)沖突與特質(zhì)性目標(biāo)沖突研究結(jié)果一致。Kleiman和Enisman[10]發(fā)現(xiàn),目標(biāo)沖突在認(rèn)知和動(dòng)機(jī)方面的好處和優(yōu)勢是思考目標(biāo)沖突會(huì)引發(fā)更加詳細(xì)的信息搜索,減少錯(cuò)誤,接受假設(shè)偏見。Etkin和Memmi[2]發(fā)現(xiàn),目標(biāo)沖突促進(jìn)了消費(fèi)者對如何分配資源的理解,感知到更高的目標(biāo)沖突增加消費(fèi)者對顯著理由的認(rèn)知依賴,激活的心理影響的后續(xù)決策,覺察到更高的目標(biāo)沖突促使消費(fèi)者將資源向更加容易證明合理的方向分配,鼓勵(lì)消費(fèi)者作出更加理性的判斷和決策。前沿目標(biāo)沖突研究展示了一種新穎的偶然效應(yīng),在某一背景下對高目標(biāo)沖突的感知可以獨(dú)立于原始沖突目標(biāo)的判斷和決策,感知到更高的目標(biāo)沖突會(huì)產(chǎn)生同樣的下游影響,目標(biāo)沖突鼓勵(lì)消費(fèi)者在更容易證明正當(dāng)?shù)臎Q策上分配更多資源,筆者推斷目標(biāo)沖突是抑制消費(fèi)者沖動(dòng)性購買的重要原因。
沖動(dòng)性購買是常見的購買現(xiàn)象,幾乎每個(gè)消費(fèi)者都經(jīng)歷過沖動(dòng)性購買,對于部分商品而言,沖動(dòng)性購買可占到商品整體銷量的80%以上[11]。沖動(dòng)性購買早期概念化為計(jì)劃外購買,廣泛定義為情感沖突和結(jié)果忽略的溢出購買效應(yīng)[12],是一系列缺乏考慮的、追求短期獎(jiǎng)賞的、與情境不相符合的、無法實(shí)現(xiàn)延遲滿足的非理性購買決策[13]。沖動(dòng)性購買對消費(fèi)者來說是個(gè)人意義的感覺,常引發(fā)消極的后果,被描述為“沒有仔細(xì)或者徹底地考慮購買是否與一個(gè)人的長期目標(biāo)、理想、決心和計(jì)劃一致”[14],是欠缺合理認(rèn)知評價(jià)的購買沖動(dòng)。沖動(dòng)性購買受到內(nèi)生性和外源性因素的影響,消費(fèi)者內(nèi)生性因素成為沖動(dòng)性購買的關(guān)鍵潛在誘因[15]。沖動(dòng)性購買早期概念化為計(jì)劃外購買,廣泛定義為情感沖突和結(jié)果忽略的溢出購買效應(yīng)[12],是一系列缺乏考慮的、追求短期獎(jiǎng)賞的、與情境不相符合的、無法實(shí)現(xiàn)延遲滿足的非理性購買決策[13]。Dougherty等[14]提出,抑制沖動(dòng)性購買包括中止現(xiàn)有優(yōu)勢行為、忍耐延遲滿足和合理估測時(shí)間因素。沖動(dòng)性購買往往與輕易作出決策有關(guān),Dholakia [3]認(rèn)為,雖然消費(fèi)沖動(dòng)性是自動(dòng)產(chǎn)生的,但個(gè)體對這種沖動(dòng)性的反應(yīng)并不是自動(dòng)的,換句話說,沖動(dòng)性是自發(fā)的,但是購買不是,它可以被抑制。Dholakia [3]為消費(fèi)者沖動(dòng)形成提供了目前最完整的沖動(dòng)性購買模型(CIFE),該模型包括感知消費(fèi)沖動(dòng)的前置因素、對約束因素的認(rèn)知以及導(dǎo)致購買或者使用自我阻抗抑制沖動(dòng)性的認(rèn)知評估。購買沖動(dòng)與一般沖動(dòng)、尋求刺激傾向以及某些人格維度,如結(jié)構(gòu)需要和需求評估等呈正相關(guān),個(gè)體購買沖動(dòng)是沖動(dòng)性購買的最強(qiáng)預(yù)測因素之一,沖動(dòng)性購買程度高的人不僅更有可能完成沖動(dòng)性購買,也更可能在最初就體驗(yàn)到購買沖動(dòng),其他可以預(yù)測沖動(dòng)性購買的行為傾向包括快速作出決定的傾向以及自動(dòng)自發(fā)行為的傾向。解釋沖動(dòng)性購買行為的努力主要集中在有問題的沖動(dòng)性購買上,這種關(guān)注源于心理學(xué)和行為經(jīng)濟(jì)學(xué)傳統(tǒng),直接、沖動(dòng)的選擇被描述為具有誤導(dǎo)性的吸引力,即“似是而非”,而且只是“暫時(shí)更可取”[15],是個(gè)體快速、短視的心理系統(tǒng)產(chǎn)物。Hoch和Loewenstein[16]的時(shí)間不一致偏好定義與沖動(dòng)性購買定義有相似之處,主要指個(gè)體如果從客觀、冷靜的角度考慮,就不會(huì)作出購買選擇。金融領(lǐng)域研究表明,發(fā)生沖動(dòng)性購買是由于消費(fèi)目標(biāo)不明確,未能監(jiān)控消費(fèi)行為,或者缺乏改變消費(fèi)行為所需的意志力,如有既定支出規(guī)則(標(biāo)準(zhǔn))的家庭比沒有儲蓄規(guī)則(標(biāo)準(zhǔn))的家庭消費(fèi)更少。兩個(gè)自我經(jīng)濟(jì)人/規(guī)劃者—實(shí)干者模型[17]解釋了個(gè)體在同一時(shí)間點(diǎn)想要實(shí)現(xiàn)兩個(gè)相互沖突的目標(biāo)這一看似矛盾的狀態(tài),兩個(gè)自我經(jīng)濟(jì)人由一個(gè)基于短視考慮的實(shí)干者和一個(gè)基于長遠(yuǎn)考慮的規(guī)劃者組成,規(guī)劃者生活在實(shí)干者的行為后果中,但規(guī)劃者動(dòng)機(jī)會(huì)影響實(shí)干者行為,規(guī)劃系統(tǒng)負(fù)責(zé)建立旨在抑制實(shí)干系統(tǒng)的更沖動(dòng)和更短視傾向的長期目標(biāo)、規(guī)則或者承諾。雙重系統(tǒng)模型[20]植根于消費(fèi)者反思性或者沖動(dòng)性系統(tǒng),反思性系統(tǒng)包括較慢的、基于規(guī)則的推理,并負(fù)責(zé)進(jìn)行更周到地評估,沖動(dòng)性系統(tǒng)通過沿著關(guān)聯(lián)鏈接快速而平行地激活傳播,更自動(dòng)地處理信息,沖動(dòng)性系統(tǒng)更有可能被與物理感覺相關(guān)的刺激激活,激活的強(qiáng)度取決于刺激(暫時(shí)或空間上)與感知的距離有多近,反思性系統(tǒng)負(fù)責(zé)對被激活的鏈接作出評估判斷,這兩個(gè)系統(tǒng)在影響行為方式上有所不同,反思性系統(tǒng)根據(jù)對行為如何以及是否會(huì)影響未來狀態(tài)的詳細(xì)評估提示行為,沖動(dòng)性系統(tǒng)通過更自動(dòng)地激活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行為關(guān)聯(lián)來提示行為,反思性系統(tǒng)和沖動(dòng)性系統(tǒng)不是在彼此完全孤立的情況下運(yùn)行的,反思性系統(tǒng)接收來自沖動(dòng)性系統(tǒng)的輸入(激活的行為圖式),并且可以采用自我調(diào)節(jié)策略來克服目標(biāo)不一致行為的激活。沖動(dòng)性購買的主體是消費(fèi)者,而非商品本身,對消費(fèi)者沖動(dòng)性特質(zhì)的探索和在沖動(dòng)性購買過程中消費(fèi)者內(nèi)心活動(dòng)是核心研究,消費(fèi)者如何權(quán)衡利弊得失是決定是否進(jìn)行沖動(dòng)性購買的最為關(guān)鍵的一環(huán)。
目標(biāo)沖突激活了心理過程,在對稀缺性的研究中證明了類似的結(jié)轉(zhuǎn)效應(yīng)[2],資源稀缺導(dǎo)致普遍的定向約束認(rèn)知,持續(xù)影響后續(xù)無關(guān)任務(wù)績效,塑造消費(fèi)者處理信息的方式。消費(fèi)者經(jīng)常處于資源沖突之中,傾向于優(yōu)先考慮更容易被證明是正當(dāng)?shù)臎Q策活動(dòng),意識到更高的目標(biāo)沖突會(huì)增加更容易證明合理活動(dòng)上的資源。筆者認(rèn)為,消費(fèi)者目標(biāo)沖突抑制沖動(dòng)性購買,大量研究表明,消費(fèi)者目標(biāo)沖突增加了為焦點(diǎn)選擇辯護(hù)的必要性,目標(biāo)沖突促使消費(fèi)者尋求和構(gòu)建選擇的理由,傾向于提供更充分理由的選擇,更依賴顯著理由的選擇,傾向于更容易證明正當(dāng)?shù)倪x項(xiàng),選擇往往需要在個(gè)體目標(biāo)之間權(quán)衡,消費(fèi)者目標(biāo)沖突增加了證明重點(diǎn)決策合理的必要性。基于相互競爭目標(biāo)的選擇沖突尤其可能增加對顯著理由的依賴,這種沖突不容易通過其他補(bǔ)償性推理過程來解決, Urminsky和Kivetz[18]發(fā)現(xiàn),為一個(gè)相互競爭的目標(biāo)提供顯著的理由會(huì)增加對與該目標(biāo)相關(guān)選項(xiàng)的選擇,并且感知到更高的目標(biāo)沖突會(huì)增加這種效果。個(gè)體背景目標(biāo)和焦點(diǎn)選擇集目標(biāo)之間的沖突增加了消費(fèi)者對更合理選項(xiàng)的偏好[21],并且隨著對目標(biāo)沖突的更多感知而增強(qiáng)。沖動(dòng)性購買本質(zhì)上更難證明是合理的,感知到更高的目標(biāo)沖突會(huì)促使消費(fèi)者不愿意在更難證明是合理的購買行為上花費(fèi)資源,而考慮那段時(shí)期更為明確的機(jī)會(huì)成本。與計(jì)劃性購買相比,沖動(dòng)性購買更難被證明是正當(dāng)?shù)模?jì)劃性購買的收益往往是有用的和具體的,易于量化和評估,因而把資源用于計(jì)劃性購買往往更容易證明是合理的,相比之下,沖動(dòng)性購買的利益,往往是無形和模糊的,很難量化和評估,因此,沖動(dòng)性購買往往更難證明是合理的,享樂主義與放縱性購買進(jìn)一步加劇了證明沖動(dòng)性購買正當(dāng)?shù)碾y度。基于此,筆者提出如下假設(shè):
H1:消費(fèi)者目標(biāo)沖突對沖動(dòng)性購買具有負(fù)向影響。
(二)閉合需求對目標(biāo)沖突與沖動(dòng)性購買的中介效應(yīng)
閉合需求由Webster和Kruglanski[19]提出,被認(rèn)為是決策背后重要的動(dòng)機(jī)因素。閉合需求指對給定的問題獲得一個(gè)確定答案的渴望,個(gè)體的閉合需求被看做一個(gè)連續(xù)體,隨著閉合需求由低到高,個(gè)體對于不確定性的忍耐程度越來越低,高閉合需求者往往采用消耗最少認(rèn)知努力的策略直接獲得問題的答案,不一定全局最優(yōu),而低閉合需求者則對于不同信息的來源有更高的接受能力,能夠?qū)栴}進(jìn)行復(fù)雜而精細(xì)的思考與加工,并且在獲得足夠的信息之前不會(huì)輕易斷言作出決策。認(rèn)知閉合平衡論[20]認(rèn)為,所有個(gè)體都處于認(rèn)知閉合的平衡中,并且不斷自我協(xié)調(diào)這種需求關(guān)系,處于平衡一端的個(gè)體對認(rèn)知閉合需求十分強(qiáng)烈,因?yàn)檎J(rèn)知閉合能為預(yù)測性提供基礎(chǔ);但處于平衡另一端的個(gè)體認(rèn)知?jiǎng)t對避免封閉性的需求很強(qiáng)烈,尤其是當(dāng)認(rèn)知閉合后的高代價(jià)變得更可察覺,或者說當(dāng)認(rèn)知不閉合帶來的效益顯而易見時(shí)尤為突出。閉合需求描述為凍結(jié)與奪取兩階段論,高認(rèn)知閉合個(gè)體在凍結(jié)階段有認(rèn)知迅速閉合的表現(xiàn),因此,他們賦予新信息的權(quán)重較小,甚至?xí)桃夂雎孕滦畔ⅲM(jìn)而盡快進(jìn)入閉合狀態(tài);低認(rèn)知閉合個(gè)體對信息的接收和處理相對更加詳盡,處于奪取階段不會(huì)讓其感到不適,新信息相應(yīng)被賦予更多權(quán)重,他們在信息處理過程中比較理性和系統(tǒng)。個(gè)體認(rèn)知能力的差異是閉合需求差異的重要原因,閉合需求從本質(zhì)上講是一種動(dòng)機(jī),動(dòng)機(jī)的細(xì)微差異可以影響個(gè)體的信息加工過程,Kruglanski等[20]認(rèn)為,高認(rèn)知閉合個(gè)體決策占用時(shí)間短,傾向于簡化信息的加工過程,而低認(rèn)知閉合個(gè)體傾向于對事物進(jìn)行完整詳細(xì)的分析加工,采用系統(tǒng)方式處理信息,決策占用時(shí)間較長。
筆者認(rèn)為,消費(fèi)者高目標(biāo)沖突降低了閉合需求,閉合需求表現(xiàn)為迅速解決一個(gè)模棱兩可問題以及對不確定性的厭惡,潛在變量通過五個(gè)維度表現(xiàn):封閉的頭腦、對模棱兩可的不適、對結(jié)構(gòu)的需要、更大的決斷性和對可預(yù)測性的渴望[20],這五個(gè)維度被視為代表需要關(guān)閉的不同潛在來源的有效方式,五個(gè)維度合計(jì)得分高的個(gè)體有更高的閉合需求。高目標(biāo)沖突可能會(huì)抑制閉合需求的五個(gè)方面。:第一,高目標(biāo)沖突消費(fèi)者思想不封閉,他們可以同時(shí)容納兩個(gè)或者多個(gè)目標(biāo)及多種想法,兼顧異質(zhì)性,面對不同的問題持開放性態(tài)度,而事實(shí)上,分享不同的觀點(diǎn)和接受多樣性激發(fā)消費(fèi)者更多的辯證思考。第二,高目標(biāo)沖突消費(fèi)者適應(yīng)多個(gè)目標(biāo)模棱兩可共存的思維情境,在關(guān)系之間沒有明確的界限,目標(biāo)沖突的動(dòng)態(tài)權(quán)衡決定了思維結(jié)構(gòu)的可塑性,高目標(biāo)沖突與角色模糊呈正相關(guān)。第三,高目標(biāo)沖突消費(fèi)者對結(jié)構(gòu)需求更低,秩序和結(jié)構(gòu)需求的降低提高了決策任務(wù)中考慮替代方案的數(shù)量,進(jìn)而延遲了關(guān)閉。第四,目標(biāo)沖突降低了快速達(dá)成決策的趨勢,增加了思考時(shí)間,高目標(biāo)沖突消費(fèi)者傾向于謹(jǐn)慎決策,陷入模棱兩可、進(jìn)退兩難的困境迫使消費(fèi)決策更傾向長遠(yuǎn)利益,因周密思考延緩作出決定的時(shí)間,不會(huì)輕易達(dá)成結(jié)論性解決方案,更有動(dòng)力得出經(jīng)過深思熟慮的結(jié)論,閉合需求更低。第五,高目標(biāo)沖突消費(fèi)者不完全認(rèn)可預(yù)測性,目標(biāo)沖突可能導(dǎo)致左右為難,因而較少有明確規(guī)則,更多被目標(biāo)之間的沖突所困,因而結(jié)論是目標(biāo)沖突后的水到渠成,所以對在沖突過程中沒有得出決定性的解決方案不會(huì)有更大壓力,閉合需求更低。對于高目標(biāo)沖突消費(fèi)者而言,結(jié)論是反復(fù)辯證思考過程的產(chǎn)物,過程的反復(fù)權(quán)衡決定了結(jié)果的相對慎重與理性。閉合需求有多個(gè)來源,單獨(dú)維度不具備總體預(yù)測能力,因?yàn)樯蠈咏Y(jié)構(gòu)比它的離散成分更重要,代表了比單個(gè)方面更適合的抽象水平[21]。高目標(biāo)沖突消費(fèi)者的閉合需求降低了在給定期權(quán)上抓住并凍結(jié)的傾向,提高了尋找正當(dāng)合理決策的動(dòng)機(jī),從而抑制了沖動(dòng)性購買。對沖動(dòng)性購買的抑制作用是高目標(biāo)沖突消費(fèi)者延遲閉合需求的結(jié)果,延遲結(jié)案的高目標(biāo)沖突消費(fèi)者傾向于更多信息搜索,反復(fù)權(quán)衡后得出結(jié)論,進(jìn)而將認(rèn)知資源分配給更具合理意義的活動(dòng),而低結(jié)案消費(fèi)者傾向于采用補(bǔ)償性規(guī)則,即基于備選方案而非屬性進(jìn)行搜索,使得他們能夠作出更加謹(jǐn)慎的決策。閉合需求的降低增加了考慮的信息量,降低了決策速度,延緩了抓住和凍結(jié)的需要,增加了對復(fù)雜證據(jù)的使用,全面權(quán)衡后得到更加合理的結(jié)論。消費(fèi)者高目標(biāo)沖突抑制了閉合需要,降低了完成任務(wù)的緊迫感,更傾向于時(shí)間上的遠(yuǎn)端選項(xiàng)而不是時(shí)間上的近端選項(xiàng),當(dāng)將這一謹(jǐn)慎的決策傾向應(yīng)用于沖動(dòng)性購買時(shí),低閉合需求消費(fèi)者搜索更加合理的決策依據(jù)抑制沖動(dòng)性購買。基于此,筆者以閉合需求為中介變量,圍繞目標(biāo)沖突、沖動(dòng)性購買兩者的關(guān)系,筆者提出如下假設(shè):
H2a:目標(biāo)沖突對閉合需求具有負(fù)向影響。
H2b:閉合需求對沖動(dòng)性購買具有正向影響。
H2:閉合需求在目標(biāo)沖突與沖動(dòng)性購買之間起到中介效應(yīng)。
(三)識解水平對目標(biāo)沖突與沖動(dòng)性購買的中介效應(yīng)
Trope和Liberman[22]在心理距離基礎(chǔ)上提出識解水平理論,用于研究理解和評估個(gè)體編碼和信息提取。消費(fèi)者預(yù)測評估和行為意圖受到識解水平的影響,識解水平表征方式影響消費(fèi)者決策。高識解水平指整體的、核心的、抽象的、去情境化的、與主要目標(biāo)相關(guān)聯(lián)的心理表征,低識解水平指表面的、次要的、具體的、依賴于情境的、與目標(biāo)不相關(guān)聯(lián)的心理表征。當(dāng)消費(fèi)者心理過程被更高水平、更抽象的解讀所激活時(shí),其對未來結(jié)果理性決策更有信心[23]。當(dāng)評估既包含中心方面又包含外圍方面時(shí),高識解水平可以促進(jìn)消費(fèi)者對問題的中心、主要方面的思考,識解水平理論為消費(fèi)者決策提供了具有較強(qiáng)系統(tǒng)性和綜合性的理論框架。近年來,已有大量研究將識解水平理論應(yīng)用于消費(fèi)者決策偏好、價(jià)值判斷和自我控制等方面。高識解水平是事件或物體更本質(zhì)、更抽象的特征,屬于事件的上位概念,與識解水平理解最密切相關(guān)的是心理距離,基于心理距離與識解水平的相互影響,識解水平理論提出主觀心理距離根據(jù)空間、時(shí)間、社會(huì)和假設(shè)距離維度上的自我中心參照點(diǎn)形成[24],識解水平理論將心理距離與抽象聯(lián)系起來,暗示個(gè)體基于心理距離理解物體、事件、概念或人,心理距離越遠(yuǎn),識解水平越高,情感驅(qū)動(dòng)效價(jià)比認(rèn)知驅(qū)動(dòng)效價(jià)遞減更明顯,情感因素通常在具體層面表征,而認(rèn)知因素大多在抽象層面表征,伴隨心理距離的增加,在結(jié)果判斷上,認(rèn)知權(quán)重增加,情感權(quán)重減少,認(rèn)知性效用在遠(yuǎn)期事件中表現(xiàn)更大的權(quán)重。
筆者認(rèn)為,消費(fèi)者高目標(biāo)沖突啟動(dòng)了高識解水平,高目標(biāo)沖突啟動(dòng)了更高級別的、去語境的心理表征,反映出對行為和事件的更一般的理解,更具典型性和概括性。高識解水平強(qiáng)調(diào)結(jié)果的可欲性,低識解水平關(guān)注結(jié)果的可及性。Vallacher和Daniel[25]通過行為識別理論提出,個(gè)體行為可以通過高級的和次級的目標(biāo)表征,前者相當(dāng)于行為的“為什么”層面,更加抽象,更能表現(xiàn)行為本身的意義,證明了可欲性構(gòu)成了高識解水平,高目標(biāo)沖突消費(fèi)者對資源稀缺與限制產(chǎn)生了緊迫感[7],對資源分配方式深度權(quán)衡,高目標(biāo)沖突加深了對資源稀缺性的心理加工,更關(guān)注長期目標(biāo)可及性及行為達(dá)成目標(biāo)后的價(jià)值,資源稀缺導(dǎo)致消費(fèi)者焦慮未來,有利于消費(fèi)者從全局角度看待長遠(yuǎn)利益,高目標(biāo)沖突消費(fèi)者傾向于作出與高識解水平相關(guān)的遠(yuǎn)期偏好。在高目標(biāo)沖突下,心理識解過程與本身分離,促進(jìn)消費(fèi)者心理距離沿著時(shí)間距離、空間距離、社會(huì)距離或概率等維度離開自我參考點(diǎn)增加心理距離。高目標(biāo)沖突消費(fèi)者傾向于關(guān)注與事物核心意義相關(guān)特征,通過形成遠(yuǎn)端抽象心理識解超越此時(shí)此地,從細(xì)節(jié)的、附帶的特征聚焦到中心的、基本的特征,在高識解水平模式下,消費(fèi)者繼續(xù)抽象思維,提取關(guān)鍵特征,全盤思考,保持對終極目標(biāo)的一致性,強(qiáng)化事情本身核心意義,同時(shí)忽略與實(shí)現(xiàn)主要理性目標(biāo)無關(guān)、細(xì)節(jié)化的特征。高目標(biāo)沖突消費(fèi)者注意力集中在一個(gè)從狹窄到寬闊的連續(xù)體上,目標(biāo)沖突聚焦沖突,抽象減少了信息,降低了注意廣度[4],激發(fā)了消費(fèi)者更高識解水平,形成遠(yuǎn)端心理距離,促進(jìn)了消費(fèi)者對沖動(dòng)性購買的意義與價(jià)值更深度的思索。Liberman等[26]檢驗(yàn)了特定心理距離維度對消費(fèi)者決策、選擇和推理形成的影響,心理距離維度共享積極關(guān)聯(lián),共同的潛在因素沿著心理距離其他維度探索自我表征,通過遠(yuǎn)端視角改變個(gè)體對特定情況的重視程度,隨著心理距離或者識解水平的增加,消費(fèi)者更不易發(fā)生沖動(dòng)性購買,因?yàn)檫h(yuǎn)端視角啟動(dòng)了理性思維,長期利益與短期利益權(quán)衡的結(jié)果可以抑制短期誘惑帶來的非理性沖動(dòng)。在高目標(biāo)沖突之下,消費(fèi)者遠(yuǎn)端心理距離視角構(gòu)思充分,思考嚴(yán)密,不草率行事,可實(shí)現(xiàn)減少采取與所處境況不符或者過度激進(jìn)的行為,抑制冒險(xiǎn)性的、缺乏考慮的、可能產(chǎn)生不良后果的沖動(dòng)性購買。沖動(dòng)性購買受到基于高識解水平的抑制調(diào)控,中止無用的或與終極目標(biāo)不相關(guān)的活動(dòng),抑制優(yōu)勢反應(yīng)及與內(nèi)部或者外部刺激干擾及時(shí)間不一致的偏好,在高識解水平下,消費(fèi)者從客觀角度冷靜思考,更不易發(fā)生沖動(dòng)性購買,更傾向于忍耐延遲滿足,抑制輕易作出的高風(fēng)險(xiǎn)決策,詳細(xì)而徹底地考慮購買是否與個(gè)體長期目標(biāo)、計(jì)劃追求、規(guī)則承諾相一致,理性面對暫時(shí)更可取的快速、短視的心理系統(tǒng)產(chǎn)物。筆者推斷,高目標(biāo)沖突啟動(dòng)高識解水平,有利于消費(fèi)者從總體、全局角度看待長期利益與短期利益的矛盾,克服短期誘惑帶來的沖動(dòng),接納長期任務(wù)帶來的戰(zhàn)略效益。筆者以識解水平為中介變量,圍繞目標(biāo)沖突、沖動(dòng)性購買兩者的關(guān)系,基于此,筆者提出以下假設(shè):
H3a:目標(biāo)沖突對識解水平具有正向影響。
H3b:識解水平對沖動(dòng)性購買具有負(fù)向影響。
H3:識解水平在目標(biāo)沖突與沖動(dòng)性購買之間起到中介效應(yīng)。
(四)調(diào)節(jié)聚焦
本文通過消費(fèi)者調(diào)節(jié)聚焦推動(dòng)現(xiàn)象的邊界。調(diào)節(jié)聚焦理論[27]解釋了如何通過自我調(diào)節(jié)行為實(shí)現(xiàn)目標(biāo),當(dāng)人們追求目標(biāo)與他們的調(diào)節(jié)取向一致時(shí),人們更有可能實(shí)現(xiàn)目標(biāo)。Higgins[28]指出,人們經(jīng)歷了一種調(diào)節(jié)適應(yīng),因?yàn)樗麄兊哪繕?biāo)追求意味著符合他們的調(diào)節(jié)導(dǎo)向,這種調(diào)節(jié)適應(yīng)增加了目前行為的價(jià)值,消費(fèi)者選擇受到調(diào)節(jié)聚焦的影響,調(diào)節(jié)聚焦是個(gè)體在追求目標(biāo)過程中采取的特定戰(zhàn)略和動(dòng)機(jī)取向,調(diào)節(jié)聚焦分為促進(jìn)聚焦和防御聚焦,促進(jìn)聚焦強(qiáng)調(diào)方法導(dǎo)向策略,防御聚焦強(qiáng)調(diào)逃避導(dǎo)向策略。促進(jìn)聚焦消費(fèi)者比防御聚焦消費(fèi)者使用更少的類別對對象進(jìn)行分類,促進(jìn)聚焦系統(tǒng)[27]起源于對生長和養(yǎng)育需求的調(diào)節(jié),在追求理想時(shí)尤其活躍,以促進(jìn)聚焦為重點(diǎn)的自我調(diào)節(jié)基于接近與期望的最終狀態(tài)匹配,培養(yǎng)更加強(qiáng)烈的追求理性的渴望,促進(jìn)聚焦可以產(chǎn)生更大的動(dòng)力推動(dòng)邊界,事實(shí)證明,促進(jìn)聚焦越迫切,越會(huì)對判斷和決策產(chǎn)生下游后果,與防御聚焦相比,促進(jìn)聚焦消費(fèi)者往往更愿意接受新的選擇和新的行動(dòng)方案[29],思想更加靈活,對問題持開放性態(tài)度,為了追求理想狀態(tài),可以適應(yīng)模棱兩可的不確定性及不可預(yù)測性,有更強(qiáng)的包容力和忍耐力,傾向付出更多的認(rèn)知努力獲得全局最優(yōu),對多元信息有更高的接納度。,促進(jìn)聚焦降低了消費(fèi)者結(jié)構(gòu)需要,接受替代方案,在充分獲得信息之前,三思后行,延緩作出決定的時(shí)間。因?yàn)樽非罄硇岳硐霠顟B(tài),促進(jìn)聚焦消費(fèi)者尤其擔(dān)心斷然作出決定可能承受的高代價(jià),更加謹(jǐn)慎地決策。本文預(yù)測,促進(jìn)聚焦進(jìn)一步降低了消費(fèi)者閉合需求,他們的基線閉合需求較低,并且有更強(qiáng)抑制閉合需求的潛力,即促進(jìn)聚焦會(huì)進(jìn)一步降低高目標(biāo)沖突消費(fèi)者的閉合需求。從調(diào)節(jié)聚焦出發(fā),圍繞目標(biāo)沖突與沖動(dòng)性購買兩者的關(guān)系,基于此,筆者提出如下假設(shè):
H4:與防御聚焦相比,促進(jìn)聚焦促進(jìn)了消費(fèi)者目標(biāo)沖突對沖動(dòng)性購買的抑制作用。具體來說,促進(jìn)聚焦降低了高目標(biāo)沖突消費(fèi)者的閉合需求,進(jìn)一步抑制了高目標(biāo)沖突消費(fèi)者的沖動(dòng)性購買。
Semin等[30]認(rèn)為,消費(fèi)者使用更加抽象的語言描述促進(jìn)聚焦,使用更加具體的語言描述防御聚焦, 消費(fèi)者促進(jìn)聚焦不僅在精神上代表不同抽象層次的信息,而且在作出決定時(shí)也在不同抽象層次上搜索信息,促進(jìn)聚焦消費(fèi)者傾向于在更抽象的層面上表征信息,在更高級別信息層次上花費(fèi)更多的時(shí)間和精力,而防御聚焦消費(fèi)者傾向于在更具體的層面上表征信息。筆者預(yù)測,由促進(jìn)聚焦引起的抽象表征提升了消費(fèi)者識解水平,他們的基線識解水平較高,并且有更高增長潛力,促進(jìn)聚焦會(huì)增加高目標(biāo)沖突消費(fèi)者的識解水平,從而進(jìn)一步抑制沖動(dòng)性購買。基于此,筆者提出如下假設(shè):
H5:與防御聚焦相比,促進(jìn)聚焦促進(jìn)了消費(fèi)者目標(biāo)沖突對沖動(dòng)性購買的抑制作用。具體來說,促進(jìn)聚焦提高了高目標(biāo)沖突消費(fèi)者的識解水平,抑制了高目標(biāo)沖突消費(fèi)者的沖動(dòng)性購買。
基于以上假設(shè)所表達(dá)的變量間關(guān)系,本文歸納出如圖1所示的研究模型。
三、研究設(shè)計(jì)
(一)樣本選取和數(shù)據(jù)來源
為了檢驗(yàn)上述理論假設(shè),本文采用虛擬情境實(shí)驗(yàn)法通過線上和線下兩種途徑獲取數(shù)據(jù),題項(xiàng)設(shè)計(jì)上引入成熟測量量表,覆蓋目標(biāo)沖突、閉合需求、識解水平、調(diào)節(jié)聚焦和沖動(dòng)性購買。針對變量屬性和研究需要,數(shù)據(jù)采集分為三部分,包括人口統(tǒng)計(jì)特征、消費(fèi)者目標(biāo)沖突操縱與測量及閉合需求、識解水平、調(diào)節(jié)聚焦和沖動(dòng)性購買的測量。被試總計(jì)750人,經(jīng)對所獲數(shù)據(jù)清洗,合規(guī)被試689人,從樣本基本描述看,收集樣本比例合理,具有代表性,符合研究要求。
(二)變量測量
本研究中被試的目標(biāo)沖突通過虛擬情境實(shí)驗(yàn)測量。首先,目標(biāo)沖突。測量方法來源于Etkin和Memmi[2]的研究。被試會(huì)在一個(gè)界面讀到:人們通常有多個(gè)想要追求的目標(biāo),請列出你目前目標(biāo)中的兩個(gè)目標(biāo);在另一個(gè)全新界面,操縱消費(fèi)者兩個(gè)目標(biāo)之間感知到的沖突,確保不同條件下列出的目標(biāo)類型不會(huì)有系統(tǒng)性差異。在高目標(biāo)沖突情況下,被試選擇“感知到這些目標(biāo)之間的沖突”;在低目標(biāo)沖突情況下,被試選擇“感知不到這些目標(biāo)之間的沖突”,被試按照Likert 1—5對感知目標(biāo)沖突的強(qiáng)弱程度進(jìn)行打分(1表示強(qiáng)烈不同意、2表示不同意、3表示不確定、4表示同意、5表示強(qiáng)烈同意)。其次,閉合需求。量表來源于Webster和Kruglanski[19]的閉合需求量表,該量表從5個(gè)方面測量消費(fèi)者認(rèn)知閉合水平(對于秩序的偏好、對于預(yù)測性的偏好、個(gè)體決斷性、對模糊的厭惡性及心理封閉),大量研究結(jié)論證明該量表的縮減版測量方法常用且同樣可行,根據(jù)閉合需求的五個(gè)研究維度,每個(gè)維度設(shè)置3個(gè)題項(xiàng),選取了15個(gè)最具代表性的測量題項(xiàng)。再次,識解水平。量表源于Vallacher和Daniel[25]的行動(dòng)識別量表BIF,共包含25種目標(biāo)行為,每種行為后面都有對此行為的兩類表征陳述,如“粉刷房間”“用刷子刷”(低識解水平表征)與具體方法有關(guān),“使房間變得美觀”(高識解水平表征)與目標(biāo)動(dòng)因有關(guān),被試需要選出此時(shí)感覺更加適合描述目標(biāo)行為的選項(xiàng),并將所選行為原因題項(xiàng)反轉(zhuǎn)加和,分?jǐn)?shù)越高,表明識解水平越高,反之越低。最后,調(diào)節(jié)聚焦。基于Jain等[31]的研究,結(jié)合本文實(shí)際,經(jīng)對量表題項(xiàng)調(diào)整完善,分?jǐn)?shù)加和越高,表明促進(jìn)聚焦水平越高,反之防御聚焦水平越高。
四、實(shí)證分析
(一)信度和效度檢驗(yàn)
本文運(yùn)用SPSS軟件,結(jié)合Cronbachs α系數(shù)值對變量信度加以檢驗(yàn),檢驗(yàn)結(jié)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各測量量表Cronbachs α系數(shù)值均大于0.700,各變量組合信度(CR)在0.914—0.996之間,大于0.800的高信度標(biāo)準(zhǔn),表明量表信度良好。效度方面,各變量KMO值均大于0.700,因子載荷在0.600以上,滿足標(biāo)準(zhǔn)化因子載荷大于0.500,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
(二)相關(guān)性分析
由相關(guān)性分析結(jié)果相關(guān)性分析未在文中列出,留存?zhèn)渌鳌?芍繕?biāo)沖突與沖動(dòng)性購買、閉合需求的相關(guān)系數(shù)分別為-0.711和-0.860,可得目標(biāo)沖突與沖動(dòng)性購買、閉合需求存在負(fù)相關(guān)關(guān)系;目標(biāo)沖突與識解水平、調(diào)節(jié)聚焦相關(guān)系數(shù)分別為0.894和0.903,可得目標(biāo)沖突與識解水平、調(diào)節(jié)聚焦存在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閉合需求、識解水平與沖動(dòng)性購買相關(guān)系數(shù)分別為0.773和-0.767,可得閉合需求、識解水平與沖動(dòng)性購買分別存在正向、負(fù)向相關(guān)關(guān)系。
(三)假設(shè)檢驗(yàn)
1.主效應(yīng)分析
本文通過逐步回歸分析檢驗(yàn)主效應(yīng),結(jié)果如表2所示。由表2列(1)可知,目標(biāo)沖突顯著負(fù)向影響沖動(dòng)性購買(限于篇幅,主效應(yīng)與其后中介效應(yīng)分析合并列表),H1得到驗(yàn)證。此外,進(jìn)一步以目標(biāo)沖突(高目標(biāo)沖突VS低目標(biāo)沖突)為自變量,沖動(dòng)性購買為因變量進(jìn)行獨(dú)立樣本t檢驗(yàn),檢驗(yàn)結(jié)果顯示,相較于一般目標(biāo)沖突被試的沖動(dòng)性購買,低目標(biāo)沖突被試的沖動(dòng)性購買均值更高、標(biāo)準(zhǔn)差更大(M=17.083,SD=2.376),高目標(biāo)沖突被試的沖動(dòng)性購買均值更低、標(biāo)準(zhǔn)差更大(M=10.806,SD=3.438),兩組P值均為0.000,高低目標(biāo)沖突兩組被試的沖動(dòng)性購買存在顯著差異。
2.中介效應(yīng)分析
本文借鑒溫忠麟和葉寶娟[32]的逐步回歸分析方法對中介效應(yīng)進(jìn)行檢驗(yàn),結(jié)果如表2所示。由列(1)、列(6)和列(2)可得,目標(biāo)沖突顯著負(fù)向影響沖動(dòng)性購買,目標(biāo)沖突顯著負(fù)向影響閉合需求,閉合需求顯著正向影響沖動(dòng)性購買;由列(3)可得,閉合需求作為中介變量加入后,目標(biāo)沖突對沖動(dòng)性購買的顯著性消失,表明閉合需求完全中介了目標(biāo)沖突對沖動(dòng)性購買的影響, H2、H2a和H2b得到驗(yàn)證。由列(7)和列(4)可得,目標(biāo)沖突顯著正向影響識解水平,識解水平顯著負(fù)向影響沖動(dòng)性購買;由列(5)可得,加入識解水平作為中介變量后,目標(biāo)沖突對沖動(dòng)性購買的顯著性消失,表明識解水平完全中介了目標(biāo)沖突對沖動(dòng)性購買的影響,H3、H3a和H3b得到驗(yàn)證。
本文采用SPSS PROCESS的BOOTSTRAP區(qū)間檢驗(yàn),進(jìn)一步驗(yàn)證閉合需求和識解水平的中介效應(yīng),樣本量為5 000。將閉合需求作為中介變量,得到目標(biāo)沖突對沖動(dòng)性購買的間接效應(yīng)置信區(qū)間不包含0(LLCL=-7.323,ULCL=-2.549),直接效應(yīng)置信區(qū)間包含0(LLCL=-4.444,ULCL=1.314),再次驗(yàn)證了閉合需求的中介效應(yīng);將識解水平做為中介變量,得到目標(biāo)沖突對沖動(dòng)性購買的間接效應(yīng)置信區(qū)間不包含0(LLCL=-8.170,ULCL=-2.585),直接效應(yīng)置信區(qū)間包含0(LLCL=-4.436,ULCL=2.236),再次驗(yàn)證了識解水平的中介效應(yīng)。
3.調(diào)節(jié)效應(yīng)分析
本文運(yùn)用層次回歸分析方法檢驗(yàn)調(diào)節(jié)效應(yīng),結(jié)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列(1)和列(2)顯示,調(diào)節(jié)聚焦對閉合需求具有顯著的負(fù)向影響,目標(biāo)沖突與調(diào)節(jié)聚焦的交互項(xiàng)對閉合需求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調(diào)節(jié)聚焦對目標(biāo)沖突與閉合需求的關(guān)系存在顯著的正向調(diào)節(jié)效應(yīng)。列(3)和列(4)顯示,調(diào)節(jié)聚焦對識解水平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目標(biāo)沖突與調(diào)節(jié)聚焦的交互項(xiàng)對識解水平存在顯著正向影響,調(diào)節(jié)聚焦對目標(biāo)沖突與識解水平間的關(guān)系存在顯著的正向調(diào)節(jié)效應(yīng)。依據(jù)調(diào)節(jié)效應(yīng)結(jié)果做進(jìn)一步分析,與防御聚焦(低于一個(gè)標(biāo)準(zhǔn)差)相比,促進(jìn)聚焦(高于一個(gè)標(biāo)準(zhǔn)差)在目標(biāo)沖突與閉合需求、識解水平關(guān)系間的調(diào)節(jié)效應(yīng)更明顯,與防御聚焦相比,促進(jìn)聚焦進(jìn)一步抑制閉合需求、提升識解水平,從而抑制了沖動(dòng)性購買。由此,H4、H5得到驗(yàn)證。
綜上,閉合需求和識解水平在目標(biāo)沖突與沖動(dòng)性購買之間起到中介效應(yīng),其中,閉合需求對沖動(dòng)性購買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識解水平對沖動(dòng)性購買具有顯著負(fù)向影響;調(diào)節(jié)聚焦顯著增強(qiáng)了目標(biāo)沖突對閉合需求的負(fù)向影響以及目標(biāo)沖突對識解水平的正向影響,在目標(biāo)沖突與閉合需求間及目標(biāo)沖突與識解水平間存在顯著的正向調(diào)節(jié)效應(yīng),與防御聚焦相比,促進(jìn)聚焦進(jìn)一步增強(qiáng)了目標(biāo)沖突對閉合需求的負(fù)向影響及對識解水平的正向影響,進(jìn)一步抑制了沖動(dòng)性購買。
五、結(jié)論、研究局限及未來展望
本文考察了消費(fèi)者目標(biāo)沖突對沖動(dòng)性購買的影響,對提出的假設(shè)運(yùn)用大樣本分析進(jìn)行了檢驗(yàn),得到以下結(jié)論:
第一,消費(fèi)者目標(biāo)沖突對沖動(dòng)性購買具有顯著的負(fù)向影響。企業(yè)管理者和營銷人員可以通過降低消費(fèi)者目標(biāo)沖突來提高沖動(dòng)性購買的營銷績效。
第二,消費(fèi)者目標(biāo)沖突對閉合需求具有顯著的負(fù)向影響,消費(fèi)者閉合需求對沖動(dòng)性購買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閉合需求在消費(fèi)者目標(biāo)沖突與沖動(dòng)性購買之間發(fā)揮中介效應(yīng),可以通過提高消費(fèi)者閉合需求來提高沖動(dòng)性購買的營銷績效。
第三,消費(fèi)者目標(biāo)沖突對識解水平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消費(fèi)者識解水平對沖動(dòng)性購買具有顯著的負(fù)向影響,識解水平在消費(fèi)者目標(biāo)沖突與沖動(dòng)性購買之間發(fā)揮中介效應(yīng),可以通過降低消費(fèi)者識解水平來提高沖動(dòng)性購買的營銷績效。
第四,與防御聚焦相比,促進(jìn)聚焦增加了目標(biāo)沖突對沖動(dòng)性購買的負(fù)向影響。降低促進(jìn)聚焦水平,有利于提高消費(fèi)者閉合需求,降低消費(fèi)者識解水平;對防御聚焦消費(fèi)者做精準(zhǔn)營銷,有利于降低消費(fèi)者識解水平,從而提高沖動(dòng)性購買的營銷績效。
(二)研究意義
本文的理論意義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gè)方面:一是構(gòu)建了消費(fèi)者目標(biāo)沖突和沖動(dòng)性購買之間關(guān)系的框架。消費(fèi)者目標(biāo)沖突、沖動(dòng)性購買在各自研究領(lǐng)域蓬勃發(fā)展,兩者的研究基本上是相互獨(dú)立的,少有交叉,本文整合了目標(biāo)沖突和沖動(dòng)性購買的關(guān)系模型,提出了目標(biāo)沖突可能是抑制沖動(dòng)性購買的潛在原因。二是發(fā)現(xiàn)了目標(biāo)沖突對沖動(dòng)性購買的抑制效應(yīng)在于目標(biāo)沖突可以激活消費(fèi)者心理,閉合需求、識解水平中介了目標(biāo)沖突與沖動(dòng)性購買之間的關(guān)系。三是擴(kuò)展了消費(fèi)者目標(biāo)沖突與沖動(dòng)性購買的邊界研究,消費(fèi)者目標(biāo)沖突在不同調(diào)節(jié)聚焦水平下表現(xiàn)出不同的特征,說明了不同類型的消費(fèi)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操縱。本文的實(shí)踐意義:一是明確了消費(fèi)者目標(biāo)沖突的客觀存在性,促進(jìn)了對消費(fèi)者如何分配自有資源的理解。二是企業(yè)管理者和營銷人員可積極把握消費(fèi)者目標(biāo)沖突的影響因素,在制定消費(fèi)者沖動(dòng)性購買營銷策略時(shí),建構(gòu)內(nèi)外部情境,降低消費(fèi)者目標(biāo)沖突或規(guī)避引發(fā)目標(biāo)沖突的誘因。消費(fèi)者目標(biāo)沖突抑制沖動(dòng)性購買的發(fā)現(xiàn)可以幫助企業(yè)管理者及營銷人員進(jìn)行消費(fèi)者細(xì)分,有針對性地制定營銷計(jì)劃,,提高營銷績效,如企業(yè)管理者和營銷人員可以通過軟硬廣告、設(shè)計(jì)購物情境或者巧妙構(gòu)思口號等營銷刺激,降低消費(fèi)者目標(biāo)沖突,可以通過喚起消費(fèi)者更高的閉合需求、降低識解水平促進(jìn)沖動(dòng)性購買。三是促進(jìn)企業(yè)管理者和營銷人員通過操縱消費(fèi)者調(diào)節(jié)聚焦水平,進(jìn)一步強(qiáng)化目標(biāo)沖突、閉合需求、識解水平與沖動(dòng)性購買的模型作用關(guān)系,可以通過降低促進(jìn)聚焦提升沖動(dòng)性購買的營銷績效。
(三)研究局限及未來展望
本文對消費(fèi)者目標(biāo)沖突與沖動(dòng)性購買的研究尚存在一定局限性。第一,研究方法相對單一。筆者采用虛擬情境實(shí)驗(yàn)法雖具有較高的內(nèi)部效度,但研究結(jié)論是否具有較高的外部效度,仍需外部數(shù)據(jù)支持,可以采用大數(shù)據(jù)、建模等方法得到更加可靠的數(shù)據(jù)。第二,數(shù)據(jù)來源比較單一。本文數(shù)據(jù)全部采用虛擬情境實(shí)驗(yàn)法收集的一手?jǐn)?shù)據(jù),保證了研究模型的有效性,但缺乏外部二手?jǐn)?shù)據(jù)的驗(yàn)證,由于二手?jǐn)?shù)據(jù)獲取難度較大,因而暫時(shí)放棄了采用二手?jǐn)?shù)據(jù)的驗(yàn)證方式。第三,本文僅對現(xiàn)實(shí)影響因素進(jìn)行了初步探究,并未對目標(biāo)沖突影響沖動(dòng)性購買的內(nèi)在解釋機(jī)制進(jìn)行深入研究,除文中提到的變量外,仍可能存在其他機(jī)制對這一現(xiàn)象進(jìn)行解釋,未來研究可以對其他機(jī)制進(jìn)行探討。目標(biāo)沖突對消費(fèi)者購買決策影響研究有較大空間,如根據(jù)本文發(fā)現(xiàn),目標(biāo)沖突抑制閉合需求,而低閉合需求消費(fèi)者具有更高的價(jià)格敏感性,高目標(biāo)沖突可能會(huì)預(yù)測消費(fèi)者更高的價(jià)格敏感性,等等,最新關(guān)于目標(biāo)沖突增加焦點(diǎn)選擇合理性需求,激活心理及其附帶效應(yīng)影響的偶然效應(yīng),可能更為廣泛地影響消費(fèi)者購買決策,目標(biāo)沖突對消費(fèi)者購買決策及行為的影響研究作為一片學(xué)術(shù)藍(lán)海,有待系統(tǒng)深入地開展。
參考文獻(xiàn):
[1]
GRAY J S, OZER D J, ROSENTHA R. Goal conflict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 meta analysis[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2017, 66(5):27-37.
[2] ETKIN J, MEMMI S A. Goal conflict encourages work and discourages leisure[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21, 47(5):716-736.
[3] DHOLAKIA U M. Temptation and resistance:an integrated model of consumption impulse formation and enactment[J]. Psychology and marketing, 2000, 17(11):955-982.
[4] STREICHER M C, ESTES Z, BüTTNER O B. Exploratory shopping:attention affects in-store exploration and unplanned purchasing[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21, 48(1):51-76.
[5] METHTA R, ZHU M. Creating when you have less:the impact of resource scarcity on product use creativity[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16, 42(5):767-820.
[6] EMMONS R A, KING L A. Conflict among personal strivings:immediate and long-term implications for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well-being[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8, 54(6):1040-1048.
[7] ETKIN J. Time in relation to Goals:science direct[J].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2019, 26(2):32-36.
[8] LARAN J, JANISZEWSKI C. Behavioral consistency and inconsistency in the resolution of Goal conflict[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09, 35(6):967-984.
[9] ETKIN J, EVANGELIDIS I, AAKER J. Pressed for time? Goal conflict shapes how time is perceived, spent, and valued[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15, 52(3):394-406.
[10] KLEIMAN T, ENISMAN M. The conflict mindset:how internal conflicts affect self-regulation[J].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2018, 12(5):1-10.
[11] 李志飛.異地性對沖動(dòng)性購買行為影響的實(shí)證研究[J].南開管理評論,2007(10):11-18.
[12] ROOK D W. The buying impulse[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987,14(2):189-199.
[13] 韓德昌,王艷芝.心理模擬:一種有效預(yù)防沖動(dòng)購買行為的方法[J].南開管理評論,2012(01):142-150.
[14] BAUMEISTER R F. Yielding to temptation: self-control failure, impulsive purchasing, and consumer behavior[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02, 28(4): 670-676.
[15] 吳俊寶,江霞,楊強(qiáng).不同趨近動(dòng)機(jī)積極情緒對沖動(dòng)性購買的影響——自我控制資源有限性視角[J/OL].(2021-10-20)[2021-10-26].南開管理評論.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2.1288.F.20211019.1734.008.html
[14] DOUGHERTY D M, MATHIAS C M, MARSH D M,et al. Laboratory behavioral measures of impulsivity[J].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2005,37(1):82-90.
[15] AINSLIE G. Specious reward:a behavioral theory of impulsiveness and impulse control[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75, 82(4):463-496.
[16] HOCH S J, LOEWENSTEIN G F. Time-inconsistent preferences and consumer self-control[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991,17(4):492-507.
[17] THALER R H,SHEFRIN H M.An economic theory of self-control[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1,89(2):392-406.
[20] STRACK F, WERTH L, DEUTSCH R. Reflective and impulsive determinants of consumer behavior[J].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2006, 16(3):205-216.
[21] FRIEDMAN E S, SAVARY J,DHAR R. Apples, oranges and erasers: the effect of considering similar versus dissimilar alternatives on purchase decisions[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18, 45(4):725-742.
[24] ETKIN J. The hidden cost of personal quantification[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16, 42(6):967-984.
[25] SELA A, BERGER J, LIU W. Variety, vice, and virtue: how assortment size influences option Choice[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19, 35(6):941-951.
[21] GOLDSMITH K, FRIEDMAN E S, DHAR R. You don’t blow your diet on twinkies: choice processes when choice options conflict with incidental goals[J].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nsumer research, 2019, 4(1):21-35.
[18] URMINSKY O, KIVETZ R. Scope insensitivity and the‘mere token’effect[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2011, 48(2):282-295.
[19] WEBSTER D M, KRUGLANSKI A W.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4, 67(6):1049-1062.
[20] KRUGLANSKI A W, DEGRADA E,MANNETTI L,et al. Psychological theory testing versus psychometric nay saying: comment on Neuberg et al.’s critique of the need for closure scale[J]. Personality processes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997,73(5):1005-1016.
[21] KELLEY H H. Salience of membership and resistance to change of group-anchored attitudes[J]. Human relations,1955,8(3):275-289.
[22] TROPE Y, LIBERMAN N. Temporal construal[J]. Psychological review,2003,110(31):403-419.
[23] NUSSBAUM S, LIBERMAN N,TROPE Y. Creeping dispositionism: the temporal dynamics of behavior prediction[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3,84(3):485-497.
[24] TROPE Y, LIBERMAN N. Construal-level theory of psychological distance[J]. Psychological review,2010,117(2):440-463.
[25] VALLACHER R R, DANIEL M. Levels of personal agency:individual variation in action identification[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9,57(4):660-671.
[26] LIBERMAN N, TROPE Y,MCCREA S M,et al. The effect of level of construal on the temporal distance of activity enactment[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2007,43(1):143-149.
[27] HIGGINS E T. Beyond pleasure and pain[J]. American psychologist,1997,52(12):1280-1300.
[28] HIGGINS E T. Making a good decision: value from fit[J]. American psychologist,2000,55(11):1217-1230.
[29] LIBERMAN N, MOLDEN D C,IDSON L C,et al. Promotion and prevention focus on alternative hypotheses:implications for attributional function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1,80(1):5-18.
[33] SMIN G R, HIGGINS T,DE MONTES L G,et al. Linguistic signatures of regulatory focus:how abstraction fits promotion more than prevention[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5, 89 (1): 36-45.
[34] LEE H,LALWANI A K, WANG J J. Price no object! the impact of power distance beliefconsumers’price sensitivity[J].Journal of marketing, 2020, 84(6):113-129.
[30] SEMIN G R, HIGGINS T,DE MONTES L G,et al.Linguistic signatures of regulatory focus:how abstraction fits promotion more than prevention[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5,89(1):36-45.
[31] JAIN R S, AGRAWAL N, MAHESWARAN D.When more may be less:the effects of regulatory focus on responses to different comparative frames[J].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2006,33(6):492-507.
[32] 溫忠麟,葉寶娟.中介效應(yīng)分析:方法和模型發(fā)展[J].心理科學(xué)進(jìn)展,2014,22(05):731-745.
(責(zé)任編輯:劉 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