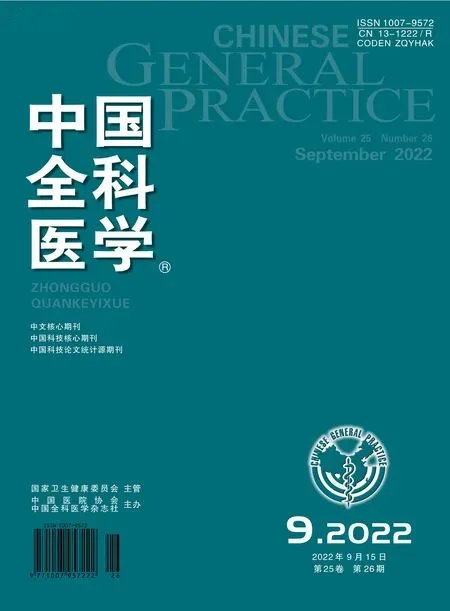泄濁消癥法治療晚期糖尿病腎臟病的臨床研究
楊涵雯,王耀獻,吳巧茹,張佳樂,閆潤澤,王曉娜,王珍,孫衛衛*
據國際糖尿病聯合會(IDF)統計,2017年全球約有4.51億糖尿病患者,預計到2045年將增加至6.93億,其中有30%~40%的患者進展為糖尿病腎臟病(DKD)[1]。DKD一旦發生,就會出現持續性蛋白尿,腎臟病變常不可逆轉,最終在較短時間內進入終末期腎病(ESRD)。我國的DKD患病形勢同樣嚴峻,2型糖尿病患者中DKD患病率為21.8%,在西部地區高達41.3%[2]。北京大學第一醫院2016年的統計結果顯示,住院患者中糖尿病引起的慢性腎臟病已經超過腎小球腎炎相關慢性腎臟病,成為慢性腎臟病的首要病因,并且估計目前的患病人數已達2 400萬以上[3]。
DKD是現代醫學治療的重點和難點,雖然近年來不斷有新型藥物包括鈉-葡萄糖協同轉運蛋白2(SGLT2)抑制劑、胰高血糖素樣肽-1(GLP-1)受體激動劑應用于臨床,但在中、重度腎病人群中的應用仍十分受限,DKD仍然是導致ESRD的主要原因,亦已成為心腦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險因素,是嚴重威脅人類生命健康的重大慢性非傳染性疾病之一[4]。DKD晚期患者的腎功能明顯受損,治療手段局限,效果欠佳,所以尋找DKD晚期有效治療方法是亟待解決的科學問題。
中醫藥在糖尿病及其并發癥的治療中歷史悠久、理論豐富,經過古今醫家的不斷探索,中醫藥治療在DKD的治療中療效確切且具有優勢。王耀獻教授在“伏熱”理論和“腎絡癥瘕”理論的指導下,針對DKD晚期熱邪的病機特點和腎絡癥瘕的狀態,以泄濁消癥為基本治療原則進行辨證施治,取得良好療效。因此,本研究開展隊列研究,觀察消癥散結法治療晚期DKD的療效及安全性。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采用基于真實世界的前瞻性隊列研究設計,選取2016—2020年于北京中醫藥大學東直門醫院、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中醫醫院、中國中醫科學院望京醫院、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北京市中西醫結合醫院、北京市房山區中醫醫院就診并符合本研究納入標準的DKD患者,以泄濁消癥法作為暴露因素,分為治療組和對照組。
1.2 DKD診斷依據及分期標準 DKD診斷依據及分期標準參考文獻[5]和2012年全球腎臟病預后組織(KDIGO)發布的慢性腎臟病評估與管理臨床實踐指南[6]以及《糖尿病腎病防治專家共識(2014年版)》[7]擬定。
DKD診斷標準:對于有明確糖尿病病史的患者出現以下任意一條即可診斷:(1)白蛋白尿:尿白蛋白與肌酐比值(UACR)≥30 mg/g或尿白蛋白排泄率(UAER)≥30 mg/24 h,3~6個月內復查,3次結果中2次或以上異常;(2)估算腎小球濾過率(eGFR)≤60 ml·min-1·(1.73 m2)-1持續3個月以上;(3)經腎活檢證實為DKD。
出現以下任意一條,則為非DKD,(1)病程較短(1型糖尿病<10年)或未合并糖尿病視網膜病變;(2)eGFR較低或下降過快(特別是無持續蛋白尿而出現腎功能不全);(3)尿蛋白迅速增加或出現腎病綜合征而無糖尿病視網膜病變者;(4)頑固性高血壓;(5)出現活動性尿沉渣或有顯著腎小管功能減退,或合并明顯的異常管型尿等;(6)伴有其他系統性疾病的癥狀或體征(如自身免疫性疾病及結締組織病、血液病、腫瘤、藥物繼發腎損害)。
DKD晚 期 分 期 標 準:eGFR為 30~60 ml·min-1·(1.73 m2)-1;或病理表現為晚期腎小球硬化。eGFR采用慢性腎臟病流行病學協作組(CKD-EPI)方程計算[8]。
1.3 中醫癥狀積分評價標準 參考《消渴病(糖尿病)中醫分期辨證與療效評定標準》中的消渴病辨證診斷參考標準[9]以及本研究前期德爾菲法專家咨詢的調查結果制定熱證證候判定標準及療效評定標準[10],對中醫癥狀進行量化打分,劃分為無、輕度、中度、重度4個級別,分別記為0、2、4、6分。熱證舌苔與脈象分無、有2個級別,分別賦以0、2分。
1.4 納入標準 (1)臨床診斷為DKD并符合本課題制定的DKD晚期分期標準;(2)性別不限,年齡18~75歲;(3)未接受透析治療;(4)經基礎降壓治療后血壓≤140/90 mm Hg(1 mm Hg=0.133 kPa)者(>60歲的老年人收縮壓≤150 mm Hg),經基礎降糖治療后血糖控制達標者〔糖化血紅蛋白(HbA1c)≤8.0%〕;(5)受試者同意并已簽署知情同意書。
1.5 排除標準 (1)4周內合并嚴重感染、中重度貧血、電解質紊亂、糖尿病急性并發癥等;(2)入組前3個月發生過嚴重心、腦、肝和造血系統等嚴重疾病以及使用過糖皮質激素或免疫抑制劑;(3)少尿或無尿、嚴重的水腫、大量胸腔積液及腹腔積液;(4)腎移植術后;(5)有精神類疾病史;(6)妊娠或準備妊娠、哺乳期婦女;(7)已知對所用藥物過敏;(8)正在參與其他干預性臨床試驗。
1.6 研究終止標準 (1)治療期間出現新發的上述排除標準中提及的情況;(2)治療期間發生嚴重并發癥;(3)出現嚴重不良事件;(4)嚴重違反試驗方案用藥;(5)血肌酐(Scr)水平翻倍升高或進入ESRD;(6)失訪或自行退出試驗;(7)出現其他情況。
1.7 治療方案
1.7.1 對照組 對照組按照《糖尿病腎病防治專家共識(2014年版)》[7]規定實施合理、有效的常規基礎治療,包括降壓、降糖、降脂以及其他伴隨疾病的治療。
1.7.2 試驗組 試驗組的常規基礎治療同對照組,在此基礎上進行分期辨證治療,由副主任醫師級別及以上醫生在主方的基礎上依據患者情況隨癥加減。DKD晚期泄濁消癥法主方:生黃芪、杜仲、土鱉蟲、海藻、熟大黃、土茯苓。
1.8 隨訪與評價指標
1.8.1 療效評價指標 隨訪周期為24周,分別于0、4、12、24周時開展隨訪并檢測Scr、尿素氮(BUN)、24 h尿蛋白定量(24 hUTP)、總膽固醇(TC),計算eGFR,記錄中醫癥狀積分;于0、12、24周時檢測HbA1c,進行療效評價。
實驗室檢查指標在受試者就診醫院進行檢測,中醫癥狀積分由研究者與受試者采用面對面問卷調查獲得。
1.8.2 安全性評價指標 分別于0、4、12、24周時監測丙氨酸氨基轉移酶(ALT)、天門冬氨酸氨基轉移酶(AST)、白細胞計數(WBC)、血小板計數(PLT)、血紅蛋白(Hb)、心電圖,并記錄不良事件發生率。
不良事件包括死亡、病情加重住院、進入ESRD、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心力衰竭、肺部感染、肝功能損傷、白細胞減低、血小板減低、心電圖異常。
1.9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4.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多時間點重復測量數據的比較采用重復測量方差分析;計數資料以相對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本研究共59例患者完成試驗,其中試驗組36例、對照組23例。
2.1 實驗室檢查指標比較 組間與時間對兩組受試者Scr、BUN、24 hUTP、TC、eGFR、HbA1c水平變化不存在交互作用。其中,僅時間對Scr、BUN、eGFR水平主效應顯著(P<0.05)。組內比較顯示,相較于0周,對照組在24周時Scr水平升高,在12、24周時BUN水平升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相較于0周,試驗組在4周時eGFR水平升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組間比較顯示,在24周時,試驗組eGFR水平高于對照組,Scr和BUN水平明顯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對照組和試驗組不同時間點實驗室檢查指標比較(±s)Table 1 Comparison of laboratory inspection indexex in test and control groups at different time

表1 對照組和試驗組不同時間點實驗室檢查指標比較(±s)Table 1 Comparison of laboratory inspection indexex in test and control groups at different time
注:Scr=血肌酐,BUN=尿素氮,24 hUTP=24 h尿蛋白總量,TC=總膽固醇,eGFR=估算腎小球濾過率,HbA1c=糖化血紅蛋白;a表示與0周相比P<0.05,b表示與對照組相比P<0.05;—表示無此項數據
組別 例數 Scr(μmol/L)BUN(mmol/L)0周 4周 12周 24周 0周 4周 12周 24周對照組 23 155.23±42.46 151.25±40.03 168.46±60.72 179.34±65.04a 11.29±4.45 12.11±4.34 13.03±5.87a 13.39±5.96a試驗組 36 143.33±34.49 139.21±41.74 144.35±43.80 147.02±47.04b 10.33±3.23 10.66±3.51 11.09±3.70 11.08±3.19b F 值 F組間=3.22,F時間=4.45,F交互=1.34 F組間=3.07,F時間=5.23,F交互=1.04 P 值 P組間=0.08,P時間=0.01,P交互=0.27 P組間=0.08,P時間<0.01,P交互=0.37組別 24 hUTP(mg/24 h)TC(mmol/L)0周 4周 12周 24周 0周 4周 12周 24周對照組 3 789±3 090 3 887±2 747 4 175±2 767 4 366±3 808 5.28±2.65 5.08±1.55 5.48±2.29 5.14±1.51試驗組 3 701±3 002 4 155±3 151 3 940±3 571 3 346±3 346 5.13±1.70 5.14±1.36 5.02±1.72 5.12±1.42 F 值 F組間=0.13,F時間=0.42,F交互=1.48 F組間=0.15,F時間=0.15,F交互=0.55 P 值 P組間=0.72,P時間=0.72,P交互=0.23 P組間=0.70,P時間=0.93,P交互=0.65組別 eGFR〔ml·min-1·(1.73 m2)-1〕 HbA1c(%)0周 4周 12周 24周 0周 4周 12周 24周對照組 42.82±11.30 44.30±12.59 41.74±17.16 38.13±13.92 6.83±1.06 — 7.01±1.38 6.85±1.09試驗組 45.74±9.92 48.91±12.82a 47.40±14.63 47.31±17.41b 7.04±1.02 — 6.93±1.11 6.90±1.20 F值 F組間=3.09,F時間=2.90,F交互=1.06 F組間=0.07,F時間=0.17,F交互=0.56 P值 P組間=0.08,P時間=0.04,P交互=0.37 P組間=0.79,P時間=0.84,P交互=0.57
2.2 中醫癥狀積分比較 組間與時間對兩組受試者中醫癥狀積分變化存在交互作用(P<0.05)。組間與時間對兩組受試者中醫癥狀積分變化主效應不顯著(P>0.05)。組內比較顯示,相較于0周,對照組在24周時中醫癥狀積分升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組間比較顯示,在24周時,試驗組中醫癥狀積分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對照組和試驗組不同時間點中醫癥狀積分比較(±s)Table 2 Comparison of TCM syndrome score in test and control groups at different time

表2 對照組和試驗組不同時間點中醫癥狀積分比較(±s)Table 2 Comparison of TCM syndrome score in test and control groups at different time
注:a表示與0周比較P<0.05,b表示與對照組比較P<0.05
組別 例數 0周 4周 12周 24周對照組 23 9.4±6.4 8.9±5.4 9.4±6.7 15.1±14.2a試驗組 36 10.5±6.5 9.3±4.9 8.6±5.7 7.6±5.2b F值 F組間=1.57,F時間=1.77,F交互=3.48 P值 P組間=0.22,P時間=0.16,P交互=0.02
2.3 安全性評價 對照組不良事件發生率為21.74%(5/23),試驗組不良事件發生率為8.33%(3/36),兩組間不良事件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2.15,P=0.14),見表3。隨訪期間,兩組均無患者新出現肝功能、血常規、心電圖異常。

表3 對照組和試驗組不良事件發生情況Table 3 Treatment-emergent adverse events in test and control groups
3 討論
3.1 研究結果分析 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人們飲食、生活習慣的轉變,DKD的發病率逐年升高,在我國,糖尿病已成為慢性腎臟病的首要病因[3],在全世界范圍內,DKD已成為導致ESRD的主要原因[4]。然而DKD起病隱匿,進入臨床蛋白尿期后進展迅速,當腎功能明顯受損后,常規治療難以延緩疾病進展。因此,探究能夠延緩晚期DKD疾病進展的切實有效的治療方法是亟待解決的臨床問題。
王耀獻教授根據多年臨床實踐,結合DKD晚期腎絡微型癥瘕形成,濁毒內生的病機特點,提出“泄濁消癥法”。在此理論基礎上,本研究采用分期辨證治療,隨癥加減,充分體現“病-證-癥”結合,宏、微觀辨治結合的治療方法,取得了良好療效。
本研究發現,試驗組eGFR在治療4周時相較0周時明顯升高,其他時點之間比較未見統計學差異。與試驗組相比,對照組eGFR在治療24周時與4周時相比降低,其他時點之間比較未見統計學差異。治療24周時,對照組eGFR較0周時降低,試驗組eGFR較0周時升高,但均無統計學差異。結合組間比較,治療24周時試驗組eGFR高于對照組。提示試驗組在延緩DKD患者eGFR降低方面更有優勢。
此外,組內比較還發現,與0周相比,對照組Scr在治療24周時明顯升高,與治療4周時相比,治療12周時與24周時Scr明顯升高。結合組間比較,治療24周時試驗組Scr水平明顯低于對照組。提示試驗組在降低DKD患者Scr水平方面更有優勢。
另外,組內比較中,與0周相比,對照組BUN水平在治療12周時開始明顯升高,且在24周時也明顯升高。試驗組各時點BUN水平比較未見統計學差異。組間比較可見,兩組在0周時BUN水平無統計學差異,24周時,試驗組BUN水平明顯低于對照組。
綜上可知,在晚期DKD治療中,泄濁消癥法聯合西醫常規治療相較于單純西醫常規治療在延緩eGFR降低、減緩Scr和BUN升高、保護腎臟功能方面具有優勢。
組內比較中,與0周時相比,治療24周時對照組24 hUTP升高,試驗組24 hUTP降低,雖未發現統計學差異,但本研究結果依舊提示泄濁消癥法在晚期DKD治療中有潛在的降低尿蛋白水平的作用。
與0周時相比,對照組中醫癥狀積分在2治療4周時明顯升高。結合組間比較,治療24周時試驗組中醫癥狀積分明顯低于對照組。由此推測,試驗組在降低DKD患者中醫癥狀積分方面更有優勢。隨訪全程,試驗組與對照組間不良事件發生率無統計學差異。
綜上可知,泄濁消癥法治療晚期DKD可從保護腎功能,降低熱證積分方面提高臨床療效,同時未見明顯不良反應。
3.2 泄濁消癥法中醫理論基礎 “泄濁消癥法”基于王耀獻教授針對DKD提出的“內熱致癥”理論。“內熱致癥”理論完整闡述了DKD的病機演變模式并以此確立了核心治法與主方。王耀獻教授認為熱邪是導致DKD的始動因素,為初始病機,“二陽熱結”是消渴病熱邪的源頭;在共通病機方面,DKD的病理損傷表現為腎小球硬化及腎間質纖維化,與此相應,國醫大師呂仁和教授提出的“腎絡微型癥瘕”理論可以很好地解釋本病病變過程中的共通病機[11]。
泄濁消癥法主方中用生黃芪,杜仲益氣扶正強身,土鱉蟲咸寒,破血消癥,且屬蟲類藥,尤善入絡,搜剔絡邪。《神農本草經》中言其:“主治……血積癥瘕,破堅下血閉”。海藻咸寒,散結消癥,《神農本草經》中言其:“主……破散結氣,癰腫癥瘕堅氣”。熟大黃苦寒,瀉熱行瘀,《神農本草經》中言其:“主下瘀血……破癥瘕積聚”。土茯苓甘平,解毒利水瀉濕,黃元御《玉楸藥解》中言其:“味甘,氣平,入足少陰腎經。利水瀉濕”。全方針對DKD晚期核心病機特點,緊扣清泄濁毒,通絡消癥的治療思想,泄作為癥瘕來源之濁毒,同時消作為濁毒結果之癥瘕,輔以益氣扶正。因而在臨床治療中取得了良好療效。
3.3 泄濁消癥法療效作用機制 現代醫學的病理、藥理研究也提示了泄濁消癥法潛在的療效作用機制。DKD過程中,高血糖、脂代謝紊亂、胰島素抵抗等多種機制,均可促進炎癥激活[12]。促炎因子如白介素(IL)-1和IL-6在DKD中表達水平上調[13-14]。炎性細胞和炎性因子會對血管產生傷害,通過改變血管通透性,影響血管舒張功能,促進內皮細胞、系膜細胞、血管平滑肌細胞增殖,誘導細胞凋亡、壞死等多種機制,最終導致DKD的發生和發展[15]。
中醫藥現代研究也發現,濁毒與炎癥關系密切。尿毒清顆粒以大黃為主要成分,具有清瀉濁毒的作用,既往相關研究中發現其能夠降低DKD患者血清超敏C反應蛋白(hs-CRP)、IL-18、腫瘤壞死因子(TNF)-α表達水平[16],在對慢性腎衰竭患者的治療中,也能降低血清C反應蛋白(CRP)、IL-6、TNF-α水平[17]。由此可見,炎癥可能是濁毒的物質基礎之一。腎絡微型癥瘕則為中醫藥抗腎纖維化提供了理論指導,本團隊前期研究中發現散結消癥類方藥可以下調腎臟系膜細胞纖維粘連蛋白(FN)的表達水平,從而抑制纖維化進程[18],這一發現也從側面將腎絡微型癥瘕與腎纖維化進程聯系起來。
泄濁消癥法泄濁毒是方法,消癥瘕是目的。現代中藥作用機制研究發現,大黃活性成分大黃素能顯著降低糖尿病腎病小鼠p65、IL-6、IL-18蛋白及基因轉錄水平,抑制Toll樣受體(TLR4)/p65信號通路激活,從而發揮抗炎作用[19]。土茯苓提取物能夠抑制巨噬細胞TNF-α的蛋白和基因表達水平,提示了其抗炎作用[20]。此外,在糖尿病動物和細胞模型中,黃芪活性成分黃芪皂苷Ⅳ被證實可下調TGF-β1、Smad3、α平滑肌肌動蛋白(α-SMA)、Ⅰ型膠原的蛋白和基因表達水平,同時上調Smad7的蛋白和基因表達水平,發揮抗纖維化的作用[21]。在單側輸尿管梗阻模型大鼠中,杜仲也能下調轉化生長因子(TGF)-β1、Smad2表達水平,同時上調Smad7表達水平,進而改善腎臟纖維化[22]。另有研究發現,海藻活性成分褐藻多糖硫酸酯可下調腎小球系膜細胞FN和TGF-β1表達水平,提示了其在抗腎纖維化方面的作用[23]。此外,既往研究還發現了土鱉蟲活性組分能夠抵御過氧化氫造成的血管內皮細胞損傷,提示了其對血管內皮細胞的保護作用[24]。由此推測,抗炎和抗纖維化可能是泄濁消癥法治療晚期DKD的潛在作用機制,但其具體作用機制有待進一步的基礎實驗研究揭示。
3.4 同類研究結果分析 既往有研究通過對濁毒和癥瘕等實邪病機的干預,在DKD的臨床治療中也取得了良好療效。如劉曉霞等[25]以三黃固本消癥湯聯合常規西藥治療DKDⅣ期患者發現,相較于單純常規西藥治療,加用中藥在降低中醫癥狀積分,降低BUN、Scr,提高內生肌酐清除率(Ccr)等方面均有明顯優勢。方中以酒大黃清泄濁毒,水蛭活血通絡消癥,輔以黃芪、熟地等藥扶助正氣。與本研究采用的泄濁消癥法有異曲同工之處。此外,何振生等[26]在西醫常規治療基礎上,以益氣滋陰活血泄濁法治療DKD腎衰竭期患者,發現其在降低Scr、BUN及中醫癥狀積分方面均優于西醫常規治療。盧冰[27]以補腎泄濁通絡湯聯合西醫常規用藥治療DKD晚期患者,發現其在降低Scr、BUN,保護腎功能,減輕纖維化方面均優于西醫常規治療組。雖然對于中醫治法的文字描述略有不同,但以上研究中,中藥干預所針對的主要病機均聚焦于濁毒和作為癥瘕主要來源的瘀血等病理因素,同時結合DKD晚期患者邪盛正虛的病理特點,輔以顧護正氣之法。由于把握了DKD在晚期階段的關鍵病機,故而均取得了良好療效。
本研究進一步詮釋了“內熱致癥”理論以及在其指導下的針對晚期DKD核心病機的泄濁消癥法,優化了中醫分期辨證干預DKD的治療方案,對提高中醫規范化治療DKD的臨床療效,延緩DKD進展,提高患者生活質量,減輕社會經濟負擔具有一定價值。但本研究也存在局限性:(1)樣本量較小,導致在結果分析中雖然可以發現組間數值有差異,但未顯示出統計學差異;(2)DKD疾病周期較長,24周的研究周期相對較短,可能無法完整體現中藥干預對DKD患者的療效。以上局限性有待今后大樣本、長期隨訪研究進一步完善。
本文作者貢獻:楊涵雯負責病例收集,數據統計,文章撰寫,研究管理與實施;王耀獻指導研究設計,指導文章撰寫;吳巧茹負責病例收集,數據整理,文章協作;張佳樂、閆潤澤、王曉娜負責病例收集,數據整理;王珍負責病例收集,指導研究設計及文章撰寫;孫衛衛負責指導研究設計,指導文章撰寫,研究管理與實施,病例收集,指導數據統計分析,對文章負責。
本文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