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碩小說的消費主義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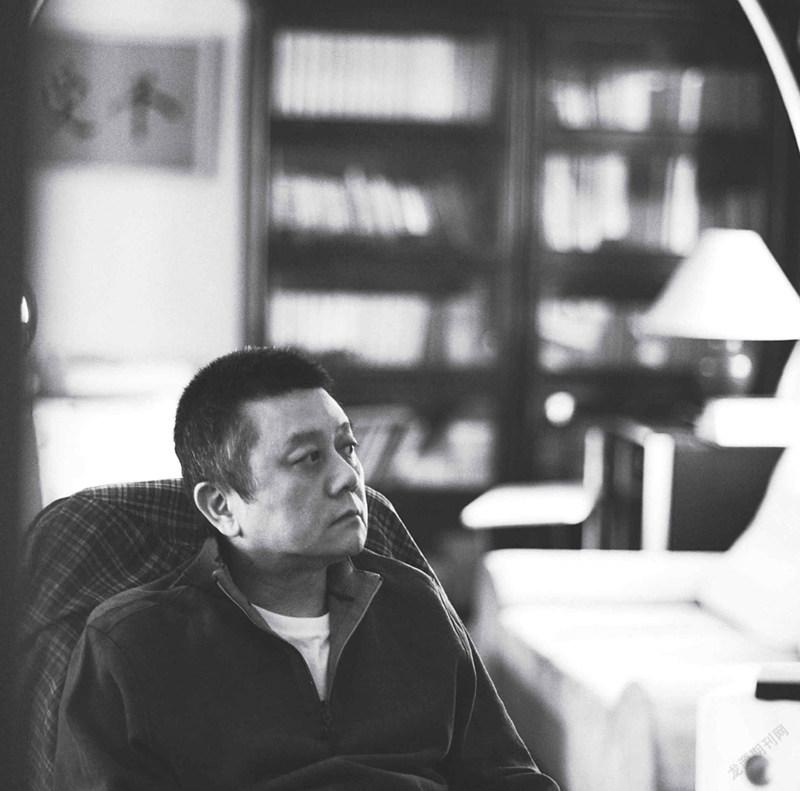

摘要:在“消費時代”這個特殊的文化語境中,文化精神張揚的是反文化、反藝術、反美學的立場,試圖打破傳統的形而上學中心論,倡導非原則性、非理性、不確定性等。王朔小說的解構神圣、解構崇高,顛覆傳統、反抗理性等精神取向與消費主義時代的這種文化精神高度契合。
關鍵詞:王朔;消費主義;世俗化;碎片化;邊緣化
社會進入了鮑德里亞所謂的“消費社會”,在消費社會里,“消費”處于“經濟—社會”生活的主體地位或統治地位。在鮑德里亞看來,消費社會消費的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物品的使用和享受,而是一種關系。消費的對象變成了一種關系,而且這種關系通過一種符號及其意義系統反映出來,從而使消費成為社會關系的一個重構的過程。按照鮑德里亞對消費概念的重新定義,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的重新書寫都是一種消費。王朔是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頗具爭議的作家之一,王朔現象是時代的產物。王朔小說是對傳統關系的一種全新的解讀,體現出對神圣的解構,對崇高的消解。
一、世俗化
在消費時代的全球化語境下,哲學從神性的殿堂走向日常的生活,正如列斐伏爾所說,只有“無現實的真理”和“無真理的現實”相結合,才能消除各自的局限,如果哲學遠離了日常生活,就會陷入自我矛盾和自我破壞。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后,哲學出現的轉向導致了文化的“視覺轉向”,而人們的審美觀念也從自律轉向感知領域,美開始轉向以感覺為核心的生產,更多的是追求一種視覺快感。這顯然不同于自康德以來將美作為一個獨特、純粹的沒有任何商品形式的領域,而與實踐的和認識的領域區分開來。在消費主義時代,美學領域已經滲透了商品邏輯,充斥著無數的虛假廣告、無意識、視覺文化等。傳統意義上的哲學、美學概念的泛化、邊界的擴大使得原本界定的特殊性的邊界日益模糊。消費時代審美觀念的改變和審美實踐就成了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日常生活是個體生活質量的客觀表現,從這點上來說,日常生活的審美化就更加注重于普通人情感的表達、價值觀的取向以及生活態度等反映日常生活的個體生活質量的方面。王朔小說的世俗化是在美學觀上對神圣的解構。在王朔的小說中,沒有宏大的政治生活,也拒絕宏大敘事,有的只是小流氓、小地痞、惡棍等社會邊緣人物的市井生活圖景。他的小說解構了杰姆遜所界定的消費主義時代的美學特征:平面感、斷裂感。小說不再具有現代主義作品中所體現出來的深度意義和宏大書寫,而是以凡俗人生的日常生活為審美對象,以日常生活流程的精細鋪排為情節結構方式;以細碎化、平面感的美學形式,以日常口語化的近乎“嘮叨”式的語言風格消解神圣意義、重大題材、深度模式。王朔小說的反崇高表現在對知識分子的鄙夷與嘲諷上。在頑主們的身上表現為可以忍受種種不便,安適自得,他們鄙夷高尚,因為在他們看來,所謂高尚不過是一層虛偽的外表。在《一點正經沒有》中,開篇寫到:“臉厚不厚?心黑不黑?厚而無形,黑而無色。那就當作家,他的條件簡直就是個天生的作家坯子。那你還猶豫什么?不猶豫了,下決心了,干!蒙誰不是蒙?”[1]
在《頑主》中,王朔寫到:“人家說自殺的辦法有一百種,其中之一就是和作家結婚。”王朔打出“作家就是流氓”的口號。對于像作家一樣的知識分子王朔說:“因為我沒念過什么大書……受夠了知識分子的氣,這口氣難以下咽……只有他們倒了,才有我們的翻身之日……”[2]表現了對知識分子的仇視。所以在《一點正經沒有》《頑主》等作品中充滿了作者對作家的、對知識分子角色的貶損。“你沒聽說過嗎,現在全市的閑散人員都轉業進了文藝界,有嗓子的當歌星,腿腳利索的當舞星,會編瞎話的當作家,國家也是沒辦法,臨街房都開鋪子了,實在沒法安置了,給政策吧。”“誰讓咱們小時候沒好好念書呢,現在當作家也是活該。”[3]文學可以陶冶人的心靈、增加人的知識,作家和許多其他的知識分子一樣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然而在王朔這里將作家從崇高的殿堂上拉下,使知識的價值和神圣被消解。
二、碎片化
王朔以一種玩世不恭的態度反抗理性,解構現實人生、抹殺幸福愛情。他通過日常審美敘事的近似“重復”“仿制”的“模擬美學”方式,將消費時代的文藝審美對象由以往遠離消費個體生命的宏大敘事對象,還原到與每個個體消費者氣息相關的日常生活范疇。在現代主義作品中,作家呈現給讀者的往往是完整的語言、完整的故事情節,表達出一個完整的思想,但是到了王朔這里,一切都是碎片化的,故事、概念、關系都可以重組,人物只不過是一個符號的象征,語言在進行著游戲,文本在進行著符合時尚的話語拼貼。《過把癮就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浮出海面》《動物兇猛》等小說中的主人公方言、高洋、何雷等的橫空出世,突然之間又融入城市,呈現的是“痞子”們的碎片化的人生。而其中最能夠代表這種碎片化的作品是《玩的就是心跳》。主人公方言游走在現實和歷史中,強烈的歷史感的斷裂造成了他現實感的虛無。小說一開始就設置一個懸疑,警察懷疑方言與一樁命案有關,然后故事就在懸疑的氣氛中進行。警察要方言證實過去的七天他在哪里,而方言卻在警察的詢問中一次次地追問自己那七天到底在哪里。為了得到答案,他去詢問他的朋友張莉。張莉告訴他:“這幾天你跟一個叫劉炎的女孩在談戀愛。”他似乎覺得這是在講別人的故事,“劉炎跟我有關嗎?劉炎是什么人?我談了戀愛嗎?我又為什么分手?”可是在人們看來方言就是殺人兇手,他根本不能證實自己的清白,也在一次次的自我追問中不斷地否定自己、懷疑自己。最后,連他自己也懷疑自己是兇手。他的語言中只留存著一些記憶的殘片,“我幾乎忘了”“我記不清”“我恍惚記得”等等。歷史在他的記憶中并不完整,在記憶的斷裂地帶模糊了是與非、真與假、道德與非道德、原則與非原則。消費主義時代對歷史感的割斷正如拉康所說的是一種符號鏈的斷裂,對歷史的記憶反映出一種非連續性的時間觀。歷史與現實的割裂造成人們對歷史的理解只剩下片段的幻象,于是人只能游離在歷史和現實的碎片中,就如同方言一樣,無法理性地定位自我意識。歷史和現實的糾纏就如同一個患有精神分裂的人,時而清醒、時而瘋癲。理性、本原、形而上的東西都被解構了。在鮑德里亞的學說中,他十分重視媒介和信息技術在消費社會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他還同意麥克盧漢的那句話:媒介即信息。當今社會消費的不是作品展示出來的內容而是信息。按照鮑德里亞的意思,當今大眾文化中閱讀的真實和歷史的真實是沒有什么關系的,媒介通過剪輯和包裝,根據自己的原則進行編碼,制造出了一個個的“偽事件”“偽歷史”“偽文化”。“它使物品成為一種偽事件,后者將通過消費者對其話語的認同而變成日常生活的真實事件。”[4]43消費者認同的是被媒介重新編碼過的社會,“那種建立在真偽基礎之上的意義和詮釋的傳統邏輯遭到了徹底顛覆。”[4]媒介文化同資本的合謀對本原、形而上和理性進行了解構。
三、邊緣化
邊緣是和中心相對的詞語,邊緣化是指非主流、非中心,或是被主流、中心所排斥、不包容,向著人或事物發展主流的反方向移動、變化。“邊緣化人物”是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的文學現象。
王朔的邊緣化主要是通過他筆下的文化邊緣人來反映的。王朔作品中的人物極具痞子特征,都是一些地痞、流氓。他們大多經歷了“文革”時期,有著叛逆的心,傳統對于他們來說是八竿子打不著的事,他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玩的就是心跳”。他們具有反傳統的價值觀、道德觀。
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和傳統,儒教、道教、佛教是傳統的精神文化資源。自古以來,我們都重道義,輕功利,有著昂揚的精神和崇高的理想,而在王朔筆下的人物絕大多數是找不到生活的重心,沒有遠大的理想抱負。他們有著強烈的優越意識和等級觀念,但是卻不是時代的寵兒。于是,只能在對過去的無限緬懷中繼續沉淪于現實。過去和現實境況形成強烈的心理落差,造成了他們面對現實的無力感和虛無感,在精神的極度壓抑下他們選擇釋放的方式要么就是繼續回味歷史,要么就是嘲諷和放縱現實。王朔的早期作品中的人物對他們的過去津津樂道,而在面對現實的時候卻是截然不同的態度。在《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張明說道:“所以我一發現要當一輩子的小職員,我就不去上班了。”“所以我抓得挺緊,拼命吃拼命玩拼命樂。”[5]19他們無所顧忌,揮霍青春,“活著嘛,干嗎不活得自在點。開開心,受受罪,哭一哭,笑一笑,隨心所欲一點。總比埋在書中世界慨然浩嘆,羨慕他人命運好。主人公嘛。”那些“無業游民”腦子里面成天都是想的怎樣“玩世”,對生活沒有更高的追求,對自己的人生沒有積極的價值取向。
王朔小說中的人物大多是以自己為中心,奉行的是“他人即地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極度冷漠的,不愛任何人只愛自己。極端的自私自利導致他們為了滿足欲望,不惜觸犯道德的底線,在《玩的就是心跳》中,李江云對方言說:“你已經活得很有點豪杰的味道了,不是殺過人就是奸過人,占上哪條都夠人尊敬的,都算沒白活。”如果用傳統的道德觀念去衡量這句話,絕對是犯了大忌。“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行善除惡向來都是中國傳統思想中倡導的道德觀念。張明、丁建、于觀等,在他們的身上體現的是一種金錢高于一切的價值觀。他們是一群社會“閑雜人員”,和社會對著干,消解一切既定的價值規則、道德觀,用王朔的話來說“玩的就是心跳”。愛情一直被人們視為神圣的、無私的和崇高的精神體驗,但是在王朔這里,愛情已經不再具有傳統意義上的圣潔、崇高。在《頑主》中,人們毫無顧忌地去赴別人女朋友的約會,而且在他們看來這是正常的。愛情的專一性在他們的行為中被消解了。馬青說他的毛病在于“其實我心里對你很好,嘴上不說”。但是,他的妻子卻希望“你心里對我不好,嘴上說”。愛情成為一個假面舞會,面對自己的親人都要口是心非。傳統意義上的愛情的神圣性被解構了。在《空中小姐》中,阿眉的理想戀人和現實戀人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使她原來建立在對軍人的好感基礎上的神圣愛情幻想破滅了。傳統意義上的幸福的愛情對于他們來說都只是一個神話、一個傳說、一件奢侈品。
四、結語
王朔及其小說是二十世紀后二十年出現的一個文學現象。任何一個文學現象的產生,必定有社會歷史文化淵源。王朔小說是應運而生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導致社會轉型,當市場經濟的大潮以洶涌澎湃之勢席卷而來時,當代社會的精英文學正在走向邊緣化,而消費主義文學走向興盛,純文學轉向泛化。文學和哲學、美學一樣從神圣的殿堂走向了日常生活。市民文化的日益擴大使得需要出現表達他們心聲的文學,王朔的“痞子文學”便趕趟似的產生了。王朔小說反叛、嘲笑、褻瀆等被精英文化所視為的神圣和崇高的東西,解構了一切傳統的價值觀、道德觀。王朔小說中所體現出的人欲膨脹、物欲橫流的故事是與消費主義社會的資本本位、品牌本位和當下性有密切聯系的。王朔小說中人物的身世和經歷以及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故事會引起和他一樣從“大院”走出來的“孩子”的共鳴。“大院”里面的“孩子”有著烏托邦幻滅后的失落感和游走于現實生活中的無歸屬感,他們的靈魂沒有找到停靠的港灣,在努力想要找尋過去美好生活而不能的情況下于現實生活中也備受挫折和失意。他們在反抗傳統、褻瀆神圣的顛覆中自娛自樂,這也正好契合了消費文化中的世俗性,以至于這種文學現象在轉型時期的多元文化相互激蕩中能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全球審美文化從精英走向大眾,從高雅走向通俗,從宏大的啟蒙敘事走向了個人化的小敘事。”[6]王朔作品將世間的一切二元對立關系拉到同一層面,使高雅文學和通俗文學的界限變得模糊,走向了像杰姆遜所說的后現代主義的文化擴張。他鮮明的個性和獨特的文學語言使得王朔現象成為二十世紀后文壇上一個永遠值得言說的對象。
作者簡介:周雪(1985—),女,漢族,四川成都人,講師,文學碩士,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高職教育、漢語言文學。
參考文獻:
〔1〕王朔.一點正經沒有[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4.
〔2〕賀仲明."文化邊緣人"的怨懟與尷尬──論王朔的反傳統思想[J].中州學刊,1998(6):91-99.
〔3〕葛紅兵,朱立冬.中國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叢書——王朔研究資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4〕蔣道超.消費社會[J].外國文學,2005(4):39-45.
〔5〕王朔.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4.
〔6〕王金城.論王朔小說的后現代文化特征[J].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4):97-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