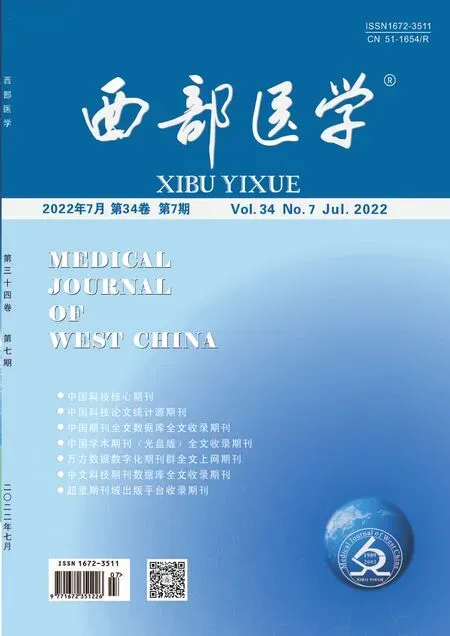血清D-二聚體、纖維蛋白原檢測聯合血栓彈力圖對急性心肌梗死預后的評估價值*
鄧容 李廣權 茍甜甜 張林 陳歡
(三六三醫院檢驗科,四川 成都 610000)
急性心肌梗死(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AMI)是一種因冠狀動脈阻塞、供血不足導致的心肌缺血性壞死,是臨床病死率最高的冠心病[1]。急診冠狀動脈介入(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是臨床治療AMI的有效方法,但由于AMI起病急驟、病情危重,患者術后可能發生心血管不良事件(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MACE),影響患者預后。研究發現,D-二聚體(Dimer,D-D)、纖維蛋白原(Fibrinogen,Fib)與AMI患者PCI術后的心功能及冠狀動脈相關并發癥的發生關系密切[2];血栓彈力圖(Thromboelastography,TEG)是近年來臨床廣泛使用的凝血檢測系統,可反映機體內血液凝固的動態變化過程,其指標變化與AMI患者缺血區域血供、梗死面積有密切關系[3]。因此,檢測患者血清D-D、Fib和TEG指標水平可能對評估AMI患者PCI術后MACE的發生具有重要價值。本研究比較了不同預后患者的血清D-D、Fib和TEG指標水平,旨在為AMI患者術后MACE的防治提供參考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8年8月~2021年2月在本院就診的AMI患者126例為研究對象,根據隨訪期間是否發生MACE將患者分為預后不良組(隨訪期間發生MACE,n=41)和預后良好組(隨訪期間未發生MACE,n=85)。納入標準:①臨床檢測符合AMI的診斷標準[4],且均經冠狀動脈造影確診。②均為首次發病,并接受急診PCI治療,且手術成功患者。③臨床資料完善。④患者知情同意,均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①合并其他心臟疾病者。②合并肝腎等臟器功能障礙者。③合并惡性腫瘤、血液疾病、感染性疾病和自身免疫疾病者。④發病前存在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服用史者。MACE事件主要包括:惡性心律失常11例,非致死性再發心肌梗死12例,心力衰竭10例,心源性休克8例,所有患者經緊急治療后病情轉歸。本研究經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符合《赫爾辛基宣言》。
1.2 方法
1.2.1 臨床資料收集 收集患者的性別、年齡、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基礎疾病(糖尿病、高血壓)、吸煙史、飲酒史、Killip分級、梗死部位、心梗面積、發病至PCI時間、收縮壓(Systolic blood pressure,SBP)、舒張壓(Diastolic blood pressure,DBP)、心率(Heart rate,HR)、血紅蛋白(Hemoglobin,Hb)、總膽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和血小板計數(Platelet count,PLT)等一般臨床資料。
1.2.2 血清D-D、Fib水平檢測 所有患者均于PCI術后次日采集靜脈血5 mL,3000 r/min離心10 min后分離血清,低溫保存待測。使用全自動血凝儀(CA7000型,日本希森美康公司)采用免疫比濁法檢測血清D-D水平,采用凝固法檢測Fib水平;所有試劑盒均由日本希森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嚴格按照相關操作流程進行檢測。
1.2.3 TEG檢測 取患者抗凝血液樣1 mL,采用TEG儀(DRNX-Ⅲ,重慶鼎潤醫療器械有限責任公司)進行檢測,檢測指標包括:凝血反應時間(Coagulation reaction time,R)、凝血形成速率(Coagulation formation rate,Angle角)、血栓最大振幅值(Maximum amplitude of thrombus,MA)和凝血綜合指數(Coagulation index,CI)等。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 預后不良組患者的Killip分級>Ⅱ級占比高于預后良好組,發病至PCI時間長于預后良好組,SBP、DBP水平明顯小于預后良好組,HR明顯高于預后良好組(P<0.05);兩組患者的性別、年齡、BMI、基礎疾病、吸煙史、飲酒史、梗死部位、心梗面積、Hb、TC和PLT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
2.2 兩組患者血清D-D、Fib水平和TEG指標比較 預后不良組患者的血清D-D、Fib水平高于預后良好組,兩組患者的TEG指標R、Angle角、MA值和CI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血清D-D、Fib水平和TEG指標比較
2.3 影響患者預后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血清D-D、Fib、R、Angle角、MA值和CI是影響患者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見表3。

表3 影響患者預后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2.4 D-D、Fib和TEG指標的相關性 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D-D與R呈負相關,與Angle角、MA值和CI均呈正相關(P<0.05);Fib與MA值、CI呈正相關(P<0.05),與R、Angle角無明顯相關性(P>0.05),見表4。

表4 D-D、Fib和TEG指標的相關性分析
2.5 D-D、Fib和TEG指標對AMI患者預后的評估價值 D-D、Fib、R、Angle角、MA值和CI評估AMI患者預后的AUC值分別為0.838、0.824、0.791、0.780、0.808、0.677,對AMI患者預后的評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01),聯合檢測的AUC值最大為0.863。見表5、圖1。

表5 D-D、Fib、凝血指標評價DIC風險的價值分析

圖1 D-D、Fib和TEG指標對AMI患者預后評估的ROC曲線
3 討論
PCI術是治療AMI的重要手段,應用PCI術對AMI患者行血運重建治療,可迅速恢復梗死血管血流、明顯改善患者心肌缺血癥狀。盡管PCI術雖能延緩動脈粥樣硬化的進展,但仍有部分患者發生MACE[5-6]。因此,早期對AMI患者術后MACE的發生進行預測,是改善患者預后的關鍵。本研究比較了不同預后患者的一般臨床資料,發現預后不良組患者的Killip分級>Ⅱ級占比高于預后良好組,發病至PCI時間長于預后良好組,SBP、DBP水平明顯小于預后良好組,HR明顯高于預后良好組,與郝迎軍等[7]研究結果類似,提示AMI患者術后MACE的發生可能與心功能、病程及血壓異常有關。研究發現,心臟自主神經調節能力的下降會增加患者心肌缺血、心源性死亡的風險,患者由于冠狀動脈閉塞,會導致自主神經尤其是迷走神經受損,使迷走神經的調節能力降低,引發竇性心律失常,使患者心率發生變化[8-9]。進一步行Logistic回歸分析發現,Killip分級、發病至PCI時間、SBP、DBP和HR與患者預后無明顯相關性,與Lee等[10]的研究存在差異,考慮與納入樣本量較少、AMI分型不同有關。
D-D是一種纖維蛋白降解產物,當機體凝血系統與纖溶系統被激活時,會使交聯纖維蛋白降解,D-D水平明顯升高[11-13];Fib是一種急性時相蛋白,參與了凝血與止血過程的最后環節,其水平變化可反映機體的血凝狀態[14-15]。一項有關急性ST段抬高性心肌梗死(Acute ST 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STEMI)患者血清D-D、Fib水平變化的研究[16]發現,與健康體檢者相比,STEMI患者的血清D-D、Fib水平更高,且合并肺部感染后,二者水平進一步升高。本研究發現,預后不良組患者的血清D-D、Fib水平高于預后良好組,提示血清D-D、Fib水平升高可能與患者術后出現MACE相關。分析其原因可能是:①AMI患者由于冠狀動脈病變,機體血液高凝和纖溶系統處于亢進狀態,使得D-D水平逐漸升高;而D-D水平的升高會進一步誘導炎癥因子的釋放,加重病情[17]。②Fib一方面可通過促進心血管收縮、促使平滑肌和內皮細胞的增殖等增加血管內壁阻力和血液粘滯性;另一方面可通過介導血小板的聚集,使血液處于高凝狀態,血流速度下降,從而增加MACE的發生風險[18-19]。
本研究發現,兩組患者的TEG指標R、Angle角、MA值和CI存在明顯差異;且D-D與R呈負相關,與Angle角、MA值和CI均呈正相關,Fib與MA值、CI呈正相關,進一步表明術后出現MACE的患者,其凝血功能存在異常,TEG指標可準確反映AMI患者術后的凝血功能。冠狀動脈急性阻塞是AMI發病的生理基礎,患者由于冠狀動脈內急性血栓形成,機體凝血與纖溶系統被過度激活,大量凝血物質被釋放到血液中,導致患者凝血功能出現異常[20]。與傳統的凝血功能檢測指標相比,TEG可全面反映機體的凝血功能變化,包括:血栓形成與纖溶過程、凝血因子的水平及其活性、血小板與Fib的表達水平等,對微小血栓形成的檢測敏感度更高[21]。有研究[22-23]發現,TEG檢測有助于提高醫生對患者凝血時間、凝血穩定性及缺血區域再灌注的了解,幫助識別MACE高危人群。ROC曲線結果顯示,D-D、Fib、R、Angle角、MA值和CI評估AMI患者預后的AUC值分別為0.838、0.824、0.791、0.780、0.808、0.677,聯合檢測的AUC值最大為0.863,提示D-D、Fib和TEG指標對AMI患者術后發生MACE的早期預警有一定臨床意義。因此,臨床上對于心臟PCI治療的AMI患者,可通過血清D-D、Fib水平和TEG檢測,對患者術后發生MACE的的風險進行評估。
4 結論
血清D-D、Fib和TEG指標的變化與AMI患者PCI術后MACE發生存在相關性,對AMI患者預后不良的評估具有一定臨床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