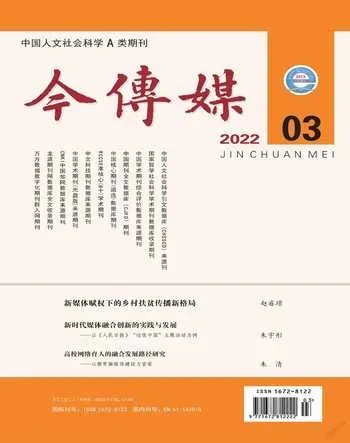空間與內容:新媒介環境下博物館的傳播策略
曹 冉
(蘇州市職業大學吳文化傳承與創新研究中心,江蘇 蘇州 215108)
博物館作為社會公共服務機構,近年來活躍在旅游、文創、社會文化教育等活動中,已從發現、儲存、研究、展示歷史文化資源的機構轉變為地方文化的表達者、傳播者。現代的“傳播”概念指以通信工具、傳播媒介為手段進行信息傳遞,博物館除了傳播主體這一屬性外,本身也是一個綜合性的媒介,是附著信息的渠道和平臺。本文從傳播空間和媒介內容的視角出發,考察分析新媒介環境下,博物館在文化傳播策略上的探索,從而為更好地發揮博物館的社會文化功能提供思考。
一、博物館:媒介性和文本性
(一)博物館即媒介
在經典傳播學視角里,媒介一般指向中介工具、渠道,它能承載信息、讓人和人之間的聯系溝通成為可能。拉斯韋爾提出的傳播過程模式,即“誰(Who)、說什么 (What)、通過什么渠道 (In Which Channel)、對誰 (To Whom)說、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也表明,傳播主體發出的訊息必須經過一定的中介渠道。在進行文化傳播活動時,博物館既是傳播者,也是傳播媒介。博物館的媒介屬性首先體現在博物館具有媒介的物質性,它擁有可被感知的物質空間、機構人員、藏品實物、媒介技術;其次,博物館還具有媒介的形式性,在信息存儲、內容生產、意義傳達上,博物館利用特定的符號表達形式,將信息轉譯成具體的文本才得以實現和受眾的交流;最后,博物館還具有媒介的制度性,它有自己的內部組織架構,在和外部社會環境交流互動時遵守并生產部分社會規則。在新媒介技術的加持下,博物館不斷豐富自己的媒介屬性,拓展了傳播的媒介空間。
(二)博物館傳播的文本性
博物館作為媒介傳播功能的實現,離不開它所傳播的媒介內容以及對內容的編碼轉譯。博物館的館藏文物、研究成果等涉及特定地理空間和時間,囊括自然現象和人類社會生產生活遺跡,這些文化信息是博物館的文化資本,組成了博物館作為媒介的核心傳播內容,并為內容衍生打下基礎。然而這些文化內容只有轉換成外顯的文本形式,才能被受眾接受并理解。以蘇州吳文化博物館為例,它的定位是打造“領先的吳文化展示、研究和學習平臺”,圍繞館藏的江南文化文物,博物館錄制語音講解、印制導覽冊子、拍攝講解視頻、組織舞臺劇,通過語言、文字、影像等受眾容易接受的文本載體對吳文化進行傳播。博物館傳播的文本性,要求博物館必須探索和更新傳播內容,并創新內容的表達形式。
二、博物館傳播空間的拓展
空間是媒介的重要維度之一,因為信息的流動總是發生在特定的虛擬或實體空間。新媒介環境下,博物館利用前沿媒介技術將傳播空間延伸至線上創造虛擬空間的同時,也對線下物理空間進行改造,創造了混合虛擬與現實的新空間,甚至走出博物館在城市開辟新的實體空間。新的媒介空間改變了人們接觸文化的路徑,讓博物館文化成為日常生活審美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拓展線上虛擬空間
新媒體時代,云博物館、數字博物館紛紛出現。不少博物館將館藏精品文物和展覽進行數字化處理,搬運到網站或微信小程序等互聯網自媒體平臺,受眾不僅可以看到正在進行的展出,還可以瀏覽已經結束的陳列展覽活動。2020年,在新冠疫情的促使下,“馬蜂窩旅游”與“快手短視頻”聯合推出“云游全球博物館”系列,以直播形式帶領觀眾游覽全球著名的博物館和美術館;國家文物局還指導“抖音”聯合國家博物館、南京博物院等八家博物館推出“在家云游博物館”直播活動。虛擬媒介空間給博物館帶來了三個突破:首先,觀眾不用去實體博物館也可以接收文化信息,打破了物理空間的限制;其次,突破時間限制,展覽得到了最大程度地使用和保存,賦予了博物館的傳播活動更“長尾”的傳播效果;最后,利用線上空間的強大互動性,觀眾也積極參與到博物館的傳播活動之中,讓傳播主體更加多元化。
(二)實體空間和虛擬空間的結合
實體空間是博物館媒介屬性的重要組成部分,博物館傳統的傳播形式就是讓觀眾置身實體的博物館展廳,按照規劃好的路線移動身體,博物館的陳列語言也主要是實物與文字的組合和互文。現在,通過掃描二維碼,觀眾可以在手機端看到立體的文物展示,可以隨時接收解說詞。借助5G、VR/AR等技術,很多博物館在實體空間上添加虛擬空間,提供給觀眾沉浸式的體驗。河南博物院曾利用沉浸式影院技術,將《千里江山圖》制作成沉浸式動態視頻;故宮博物院利用VR技術重現考古場景;故宮端門數字博物館將全息投影與古建筑相結合,讓游客宛如在宮內游走。現實與虛擬的結合,讓博物館變成了體驗空間、互動空間,信息的流動不再是單一的、靜止的,觀眾游覽的趣味性和體驗感更強。
(三)對實體空間的新探索
除了拓展虛擬傳播空間,博物館在實體空間的利用上也出現了新形式。如舉辦讀書會、親子活動、舞臺劇,設立文創商店、餐飲店等,博物館從展覽空間變成教育、休閑、娛樂、消費的綜合媒介空間。還有一些博物館“走”出場館,進入城市的其他地理空間,將文化符號深入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上海博物館的第一家“博觀悅取”咖啡文創體驗店就開在了黃浦區新天地太倉路123號;河南博物院利用全息投影,把具有特色的文物“搬”到了地鐵站,乘客得以近距離感受歷史文化。博物館“走出去”成為城市的新景觀,這些嵌入日常生活的實體空間,給人們提供了日常交往的公共平臺,有助于建構地方居民的共同記憶與區域認同,對城市生活的運行和城市形象的提升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
三、“博物館+”與年輕化
媒介空間的延伸和創新,以及人民群眾對文化生活的新需求,促使博物館在傳播內容上要創新表達方式。在這方面,博物館主要采用了跨界策略和年輕化策略。
(一)“博物館+”思維下的跨界策略
“博物館+”式的跨界,是指博物館通過整合文化資源打造IP,形成品牌號召力,再攜手其他IP進行內容的二次開發。跨界不僅產生了品牌助力效應,還讓博物館走進衣、食、住、行、玩各個領域。蘇州博物館的“江南四大才子”這一IP,與天貓上的8款茶品牌推出春茶聯名合作款;吳文化博物館“吳門吾景——明清吳中山水勝景”特展與當下國內最熱門的手游之一 《江南百景圖》合作,參觀者可以在博物館內找到沈周、文徵明等人的游戲角色形象、申領游戲任務卡,現場做任務贏取主題紀念品,此次跨界吸引了很多游戲粉絲從全國各地趕過來打卡。“博物館+”模式還涉及酒店、婚禮、時裝秀等市場,博物館IP內容賦予跨界合作方更高的文化意蘊,合作方則提供了更廣闊的市場,使得博物館在創收的同時還擴大了傳播影響力。
(二)內容的年輕化策略
阿里數據 《2018年天貓博物館文創數據報告》顯示,博物館文創線上用戶中,“90后”用戶數量過半,“95后”消費最多,從總體來看,“75”后到“95后”占據全部線上用戶數量的90%。當年輕一代成為文化消費的主力,博物館敏銳捕捉到了市場需求的變化,在博物館文創的開發中積極貼近年輕群體的趣味喜好、時尚前沿、亞文化潮流,將傳統文化符號進行年輕化轉譯。2020年,河南博物院的“考古盲盒”火爆網絡,“盲盒”這一概念來自日本游戲動漫文化,是指消費者不能提前得知具體產品的玩具盒子,只有購買打開后才能知曉真相,這種未知性帶來的刺激使盲盒在年輕人群體中非常流行。河南博物院的“盲盒”把“微型版”的仿造文物藏進土中,消費者購買后可以用小鏟子一點一點刨去泥土,讓“文物”現出真面目,體驗考古挖掘的過程。吳文化博物館的“看,國寶——吳地文物再想象”邀請青年街頭藝術家、自由插畫師、數字藝術家對館藏的9件文物進行了再創作,衍生出動漫插畫、數字藝術裝置和多媒體影像,置放于館內新開放的場域。年輕化策略讓博物館一改往日的陳舊印象,拉近了與年輕受眾的心理距離,轉身成為制造潮流的網紅。
四、博物館傳播的反思
擁抱數字技術和年輕受眾,從視覺體驗、消費、娛樂的途徑走進大眾視野,為公眾提供更多樣化的服務,使得博物館擴大了傳播的輻射范圍,去博物館成為一種流行的文化休閑方式。但博物館要承擔起文化傳播和社會教育的功能,顯然不能滿足于現狀,依然需要思考如何將文物深層次的文化內涵傳播給受眾,避免走馬觀花、打卡式的游覽。館藏文物是博物館傳播內容的核心和根本,但是文物除了形狀、色彩、功能等顯性信息,還有很多更富有文化價值的隱性信息。比如,物品誕生時的社會和文化情境、文物和我們現實生活的聯系,這些隱性信息對受眾來說有一定的挖掘和解讀門檻。如果博物館對文物信息的闡釋停留在文物本身,那么無論是線上還是線下,再多的技術力量也無法讓文化傳播的效果得到質的提升。另外,由于城市在人力和物力上的集中優勢,讓博物館的文化傳播大多停留在城市空間,未來應該結合實際考慮進入鄉村傳播,為鄉村發展注入文化力量。因此,博物館在探索傳播策略的同時,應堅守本源,做好最基本的內容闡釋工作,關照文化資本弱勢群體,讓博物館真正成為傳播民族文化、地方文化的中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