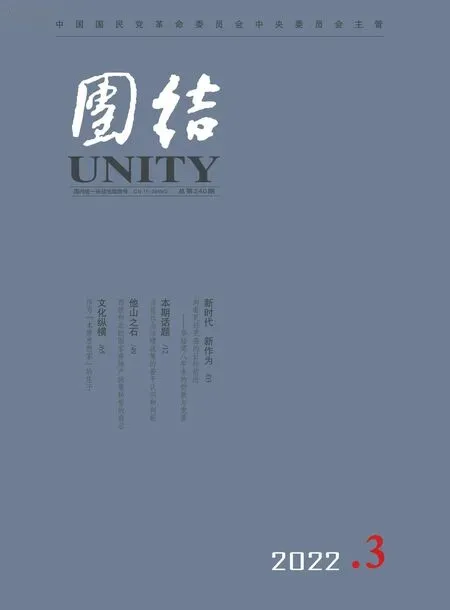民國(guó)時(shí)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yǔ)言研究所的探尋
——評(píng)馬亮寬等《歷史語(yǔ)言研究所與中國(guó)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體制的建構(gòu)》
◎徐慶康
1928 年民國(guó)政府成立了全國(guó)性的最高學(xué)術(shù)研究機(jī)構(gòu)——中央研究院,歷史語(yǔ)言研究所 (簡(jiǎn)稱史語(yǔ)所) 是中央研究院中以研究歷史、 語(yǔ)言、 考古諸學(xué)科為主的學(xué)術(shù)研究機(jī)構(gòu)。 史語(yǔ)所在創(chuàng)所所長(zhǎng)傅斯年的領(lǐng)導(dǎo)下, 進(jìn)行了大規(guī)模地安陽(yáng)殷墟發(fā)掘、 明清檔案整理、 方言調(diào)查等研究活動(dòng), 緊密團(tuán)結(jié)陳寅恪、 趙元任、 顧頡剛、 陳垣、 李方桂、 李濟(jì)等一大批知名學(xué)者, 培養(yǎng)了夏鼐、 勞干、 丁聲樹(shù)等一批學(xué)有專長(zhǎng)的青年學(xué)術(shù)力量, 同時(shí)出版了 《歷史語(yǔ)言研究所集刊》 和 《歷史語(yǔ)言研究所專刊》, 贏得了較高的學(xué)術(shù)聲譽(yù)和國(guó)際影響。
“還記得橡樹(shù)灣動(dòng)物園的管理員爺爺嗎?”園長(zhǎng)爺爺說(shuō),“他是我學(xué)生時(shí)代的朋友。去年他打電話給我,說(shuō)有一個(gè)小男孩也許會(huì)聯(lián)系我,詢問(wèn)一頭小象的事。他說(shuō),‘他是一個(gè)很孤獨(dú)的小男孩,小象安琪兒是他唯一的朋友。我不想告訴他,那頭小象在周末患急癥離世了,這會(huì)讓他非常傷心。所以——’”
近年來(lái), 隨著中國(guó)史學(xué)的不斷發(fā)展及與國(guó)際學(xué)術(shù)的日益接軌, 歷史學(xué)研究的視域不斷地被拓展, 在越來(lái)越公正、 公允評(píng)判歷史事件、 歷史人物的同時(shí), 也有對(duì)以往歷史的反思, 重塑對(duì)歷史的新認(rèn)知。 在民國(guó)史學(xué)中占重要地位的是以傅斯年、 陳寅恪、 顧頡剛、 陳垣等為代表的 “史料學(xué)派”。改革開(kāi)放以來(lái), 國(guó)內(nèi)對(duì) “史料學(xué)派” 成就的發(fā)掘和肯定使得該學(xué)派的許多著作得以出版, 許多人物得以重新登上史學(xué)的祭壇, 而與之緊密聯(lián)系的史語(yǔ)所更是成為關(guān)注的熱點(diǎn), 被不斷地以著作和文章宣揚(yáng)。 還原民國(guó)史學(xué),史語(yǔ)所是繞不過(guò)去的重鎮(zhèn)。 然而, 迄今為止, 盡管史語(yǔ)所在各種論著中被屢屢提及, 但還沒(méi)有以它作為專門研究對(duì)象的論著出版, 這不能不說(shuō)是一個(gè)缺憾。 馬亮寬、 馬曉雪、 劉春強(qiáng)的 《歷史語(yǔ)言研究所與中國(guó)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體制的建構(gòu)》 一書則較好地彌補(bǔ)這一空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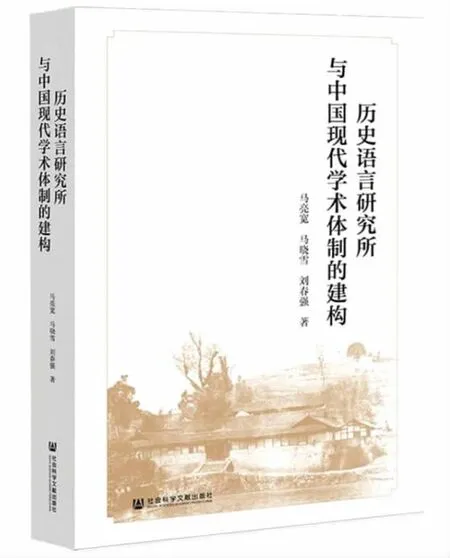
自20 世紀(jì)80 年代以來(lái), 聊城大學(xué)及馬亮寬教授開(kāi)始對(duì)傅斯年及史語(yǔ)所進(jìn)行專題研究。2010 年, 聊城大學(xué)與臺(tái)灣大學(xué)聯(lián)合召開(kāi)紀(jì)念傅斯年逝世50 周年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 會(huì)議期間, 馬亮寬教授赴臺(tái)北中研院進(jìn)行訪問(wèn), 查閱史語(yǔ)所檔案目錄, 決定對(duì)歷史語(yǔ)言研究所進(jìn)行專題研究,2011 年申報(bào)了國(guó)家社科基金課題并獲批準(zhǔn)。 期間馬亮寬多次赴臺(tái)進(jìn)行學(xué)術(shù)交流與訪問(wèn), 尤其是2018 年12 月, 應(yīng)邀訪學(xué)半年, 系統(tǒng)查閱了有關(guān)史語(yǔ)所的檔案書籍資料。 作為國(guó)家社科基金課題, 研究成果于2018 年以 “優(yōu)秀” 等級(jí)結(jié)項(xiàng), 又經(jīng)過(guò)3 年的補(bǔ)充修改, 至2021 年底結(jié)書出版, 真正是“十年辛苦不尋常”。
(1)將從知網(wǎng)中導(dǎo)出的81篇文獻(xiàn)利用CiteSpace中的data Import/Export功能轉(zhuǎn)換為可用于CiteSpace分析的數(shù)據(jù)格式,存儲(chǔ)在“Data”文件夾中。
《歷史語(yǔ)言研究所與中國(guó)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體制的建構(gòu)》 依托 “史語(yǔ)所檔案” “傅斯年檔案” 等未刊、 已刊資料, 以史語(yǔ)所學(xué)術(shù)制度建設(shè)為切入點(diǎn)進(jìn)行了深入探討, 有三個(gè)特點(diǎn): 其一, 全方位、 多層次地展示了史語(yǔ)所作為史學(xué)重鎮(zhèn)的獨(dú)特風(fēng)貌。 本書以精心構(gòu)思的布局, 8 章26 節(jié)近50 萬(wàn)字的篇幅, 將史語(yǔ)所的籌建歷程、 規(guī)制建設(shè)、 組織機(jī)構(gòu)、 聚才、 育才、 用才、 中西學(xué)術(shù)交流、 學(xué)術(shù)創(chuàng)新與學(xué)術(shù)成就、 資料收集與成果發(fā)表等諸多問(wèn)題, 進(jìn)行了清晰的梳理與論述, 全方位、 多層次地展示了史語(yǔ)所作為史學(xué)重鎮(zhèn)的獨(dú)特風(fēng)貌、 邃博內(nèi)涵和巨大成就, 詮釋了它在民國(guó)學(xué)術(shù)史, 特別是史學(xué)史上不可磨滅的地位淵源有自。 其二, 深入探討了史語(yǔ)所在近代中國(guó)學(xué)術(shù)范式轉(zhuǎn)型更新中的重大貢獻(xiàn)。 史語(yǔ)所在大陸存在21 年, 幾乎全是處于戰(zhàn)亂動(dòng)蕩歲月之中。 特別是抗戰(zhàn)時(shí)期, 遷徙頻繁, 敵機(jī)追炸, 資料散亂, 物資匱乏, 研究人員貧病交加。 在這種看似生存難乎為繼的情況下, 它依然維持了正常運(yùn)轉(zhuǎn)并且發(fā)展壯大, 推出了許多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學(xué)術(shù)成果, 在近代中國(guó)學(xué)術(shù)范式轉(zhuǎn)型更新中作出了重大貢獻(xiàn)。 支撐他們頑強(qiáng)拼搏的是對(duì)于祖國(guó)的忠誠(chéng)和延續(xù)祖國(guó)思想文化血脈的矢志堅(jiān)貞。 其三, 本書最值得珍視的, 不僅是還原一個(gè)真實(shí)的史語(yǔ)所, 而且更是它在客觀平實(shí)地述論中力圖揭示具有普遍價(jià)值意義的學(xué)術(shù)機(jī)構(gòu)組織和運(yùn)行的規(guī)則, 人才成長(zhǎng)的規(guī)律, 學(xué)術(shù)創(chuàng)新的機(jī)制, 提煉出許多具有啟示意義的思考。
作者通過(guò)對(duì)史語(yǔ)所的研究, 認(rèn)為史語(yǔ)所從籌建到運(yùn)行, 各種成績(jī)的取得, 處處彰顯出人才的優(yōu)勢(shì), 成為20 世紀(jì)上半葉 “規(guī)模最大成績(jī)最好的學(xué)術(shù)研究團(tuán)體”, 主要是三個(gè)方面的原因: 一是傅斯年作為史語(yǔ)所的創(chuàng)立者和終身所長(zhǎng), 他學(xué)貫中西、 通博古今, 具有科學(xué)教育救國(guó)的理念和學(xué)術(shù)獻(xiàn)身精神; 二是史語(yǔ)所創(chuàng)所時(shí)期凝聚的精英人士長(zhǎng)期團(tuán)結(jié)合作、 努力奮斗; 三是科學(xué)的人才培養(yǎng), 使每個(gè)人盡其才能, 發(fā)揮其特長(zhǎng)。 史語(yǔ)所確立的學(xué)術(shù)宗旨, 形成的優(yōu)良學(xué)風(fēng), 先進(jìn)的人才培養(yǎng)、 管理模式以及各種制度規(guī)范在今天仍有重要影響, 如果認(rèn)真總結(jié), 可以從中獲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