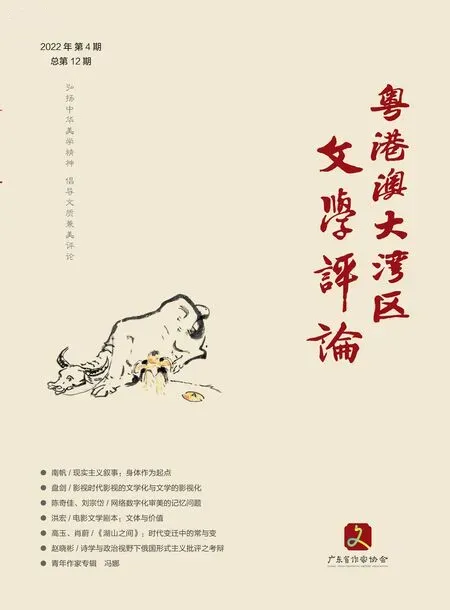網絡數字化審美中的記憶問題
陳奇佳 劉宗岱
摘要:審美活動在網絡數字化技術的出現之后發生了改變。網絡數字化技術作為一種實體化的物質,直接介入了人的意識活動,導致審美活動的基礎與機制發生了變化。其中突出的一點表現在對人類記憶方式基底的改造。由于記憶本身的性質與活動機制均發生了改變,如從儲存轉向檢索、可視化活動獲得支配地位等,網絡數字化時代生產了一些相應的審美新現象,如個人化記憶的充分表達、記憶與物的關系被改寫等。它也可能產生某些新的審美困惑如超憶癥等。
關鍵詞:網絡數字化;審美;物質性基礎;記憶
馬克思認為:“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1]物質生活的變化總是多層面、全方位地沁入人們意識活動的各個環節中。物質生活之于意識的這種作用,有時非常迂曲,甚至要以幾代人的精神變遷才能明顯看出,但有時則表現得非常直接。在我們看來,當下網絡數字技術作為一種實體化的物質存在對人們意識活動的介入性便是非常直接的,這甚至在審美的意識活動中成為明晰的現象。人們能夠說:審美活動已形成了網絡數字技術之“前”“后”的區別。當然,這一問題龐大而復雜,我們試圖借網絡數字化時代的記憶問題,對這一點略加討論。
揚·阿斯曼(Jan Assmann)指出,在藝術活動中,記憶問題具有一種類似轉換器一般的功能作用。記憶固然也可以直接作為審美對象,但更重要的是,各種外部事物,更不用說“各種各樣的符號系統”如“儀式、舞蹈、深化、圖式、服裝、飾物、文身、路徑、繪畫、景象等”,[2]都需要通過記憶的中介活動,把這些對象轉化為“自己關心的”[3]東西,構成藝術創作的沖動。因此也不妨說,記憶方式如果發生了根本變化,也必然生成新的審美生產機制。
一
作為一種物質技術,網絡已經深度地跟我們的日常生活捆綁在了一起。人們獲得的新鮮生存體驗包括但不限于:生活娛樂性質的網絡直播,網絡游戲,網絡短視頻;工作應用性質的大數據搜索,萬物互聯,網絡創作;傳播交流性質的網絡社群,網絡課堂,數字記憶工程等等。網絡產生最大的影響即是改變了人類生活的物質性基礎。它使得“網絡數字化”成為人們觀念建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要分析理解這些新現象,就需要“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形成”[4]。馬克思指出物質性基礎改變是導致觀念產生變化的根本原因。這些現象表明伴隨著物質性基礎的改變,人對物的感知方式發生了變化。我們在此就重點討論幾種涉及記憶話題的網絡數字化條件下的物質性基礎的改變。
首先應當指出的是,以網絡為代表的物質性技術及其應用設備已經成為審美活動得以順利進行的物質性基礎。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認為“信息系統指的是一切以各種形式處理和傳遞信息的行為。”[5]作為現代信息系統的基礎,數字化是指將信息轉化成以數學二進制為基礎的代碼,再引入計算機進行統一處理的過程。從理論上來說,數字化可以對一切事物進行描述、記錄、表達,即原初的對象按照統一的規則被描述為一連串的數字信息,再通過各種硬件被轉化為一系列聲音、視覺、觸覺等物理信號。這種強大的兼容性是傳統語音和文字所不具備的。讓·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早年曾經預見的“真實的定義本身是:‘那個可以等價再現的東西”,[6]在今天已頗成為一種實體化的事實。據此,審美活動中精神與對象的關系也就談不上什么“表現”與“再現”的區別。當然,需要指出的是,在當前技術條件下,這種物質性基礎數字化所引發的人的感官基礎變革,突出地體現在視覺和聽覺方面。這是由當下科學技術和硬件設備的特性所決定的。數字形象成了最真實的“真實”。這也是鮑德里亞預見的一種現象 :“擬仿物本身,就為真實。”[7]
其次,虛擬性是“網絡數字化”最根本的性質。以網絡中的圖像為例,我們從屏幕上感受的色彩、對比度、亮度等要素實際上是經過數字化編碼處理的信息。這是由“0”和“1”組成的數字信號對物理硬件進行調控協作的結果。通過點擊輸入、語音輸入的人機交互過程也是如此。因此,在大小各異的屏幕上呈現的都是現實的“擬像”。此外,人在網絡中也是虛擬性的符號。馬克思認為人“不是處在某種虛幻的離群索居和固定不變狀態中的人,而是處在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發展過程中的人。”[8]然而在網絡中,取一個昵稱基本就完成了創造網絡身份的全部流程。昵稱并不具有獨特性,相同的名稱可以被不同的人重復使用;也不具備真實性,昵稱和處于屏幕之外的人之間并不具有能指、所指在語言中約定俗成的穩定聯系。因此,“在自我同一性中,表達了某種相互矛盾的關系:作為一個一般的人,自我與所有其他的人都一樣;但作為一個個體,他卻絕不同于其他個體。”[9]網絡中的主體成為人和技術相融合的產物,是被建構的數字主體的“人”,而非現實中真實的人。
第三,在網絡數字化時代,網絡提供了新型的認知外界的方式。曼紐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指出“我們的社會逐漸依循網絡與自我之間的兩極對立而建造。”[10]在網絡數字化時代,互聯網結合人工智能(AI)、增強現實(AR)、虛擬現實(VR),建構了網絡生存環境。這并不意味著網絡將人變成了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所描述的“缸中之腦”,而是說網絡既是物呈現自身的新方式,也是人感知物的新方式。“‘實時網絡的問世可謂大事記,它不僅把數據送往信息數字處理中心,同時也融匯了供所有人索取的模擬資料。”[11]即時上傳與下載成為網絡活動的基本行為模式之一。人對物的感知不再受到“在場”的限制。借助網絡傳播的速度優勢,人們可以隨時獲得跟物相關的數字化信息。于是,包括審美在內的諸多感知活動中,主體并不必須“在場”,只需要做到“在線”。網絡與現實生活的高度關聯依托信息的高效傳播而實現。斯蒂格勒認為“信息的真諦是光速時間”[12],這指信息的傳播速度近乎光速,也指數字化技術幾乎消除了信息生產和接受兩端之間的距離。這兩點保證了通過設備和軟件就能實現從現實到網絡的平滑過渡。于是就認知外界這一行為而言,現實實踐和網絡檢索是殊途同歸的兩種路徑。
于是,以數字化作為基本的邏輯框架、以網絡作為具體的應用實踐,兩者緊密結合、共同建構的“網絡數字化”已經成了當下社會文化的重要語境。因此,我們可以斷言說:“網絡數字化”以數字化為底層邏輯,以虛擬性作為基本屬性,使得技術成了審美活動不可或缺的環節。“宗教、家庭、國家、法、道德、科學、藝術等等,都不過是生產的一種特殊方式,并且受生產的普遍規律的支配。”[13]以電影、短視頻、電視為代表的藝術作品必須在屏幕上才能表現為完整的審美對象,人們也必須借助電腦、手機等工具才能夠通過網絡完成審美活動,因此技術將審美主體、審美對象與自身融合在一起,消解了審美距離。通過觀察生活我們便能發現,老一輩人所使用的收音機、影碟機已經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他們需要重新學習使用手機、數字電視才能獲得娛樂。相比之下,出生于網絡數字化時代的小孩們從小的生長環境充斥著手機、電腦、平板等現代高科技設備。錄音機和影碟機幾乎不再出場。于是代際之間便會產生審美差異,其中的關鍵就是存在于各種各樣設備之后的技術。伊格爾頓說:“美學是作為有關肉體的話語而誕生的。”[14]現在,我們可以說,當下美學話語亦將隨著網絡數字化技術所改造的肉體而變化發展。
二
審美的直接物質性基礎——人的肉體/身體,在“網絡數字化”的語境中,發生了根本變化。“主觀性的‘誰開始‘客觀地解構了”[15],同時“技術物體不是一種用具”[16],這就導致數字技術不可避免地成為記憶觀念的重要組成部分,記憶觀念自身也發生了變化。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記憶觀念的核心從“儲存”變成了“檢索”。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使用“文本痕跡”來描述“文學作品在它們的作家死后和它們的語境消失之后保存下來的”[17]生命力,此處的“痕跡”既意指文字的痕跡,也意味著對作品的閱讀和傳播。我們可以借用“痕跡”這個詞語來描述“網絡數字化”背景下記憶觀念的改變:即由于互聯網大數據的技術特性,人類在網絡上的一切活動都會留下“痕跡”,只不過這些行為都被軟件和大數據默默地記錄在服務器中。我們翻翻亞馬遜、支付寶、瀏覽器等軟件,就能發現這些盡職盡責的“管家”將我們生活的證據滴水不漏地保存了下來。于是,生活在網絡數字化時代的人們并不需要自己去記錄這些事項,只需要通過“檢索”即可找到相應的記錄。因此,記憶對于人們來說,第一要義不再是“儲存”,而是“檢索”。
其次,外置儲存設備使記憶的分類儲存真正地成為現實。隱喻是用來解釋記憶儲存模式的常用方式。“黑板”模型,“倉庫”模型,包括被稱作“記憶宮殿”的記憶術等都是對記憶結構和過程的隱喻。記憶是否擁有可認知的結構與形態,實則沒有人說得清楚。關于這個問題,“網絡數字化”給出了一個回答——采用 “目錄樹”結構的數據儲存設備。“目錄樹”結構擁有一個根目錄,在其下可以進行子目錄的設置,并以此類推形成一個樹狀結構。各個部分之間的邏輯關聯一目了然。“目錄樹”結構以一個點作為中心而向外生發的形式為集體和個人提供了建構記憶、組織記憶的邏輯范式,使記憶擁有了具象化的邏輯框架。這種結構具有可復制性和可傳播性。這實則意味著記憶可以按照標準進行分類,進而使得記憶的批量化生產成為可能。這種結構不僅可應用于思維導圖等個人記憶,也可應用于社會群體組織的檔案管理,可謂是古羅馬記憶術的數字化形式。
第三,記憶在現實中擁有了可視化的表征。相比于書籍,當下的數據儲存設備擁有更大的容量和更多樣的形式。穩定的數字編碼系統為信息建立起了統一的描述模式,這樣一來,信息不再因為語言、文化、區域等因素的差異而具有獨特性和差異性,而是成為“被計算出來的狀態以及1和0這兩個編碼的開啟和閉合”[18]所客觀描述的對象。在這樣的信息系統中,人的記憶在具有統一性的標準下被記錄。于是,在網絡世界中,電子編碼配合大容量、高性能的儲存設備加劇了人們將記憶保存于外部物質設備的趨勢。檔案、光盤、硬盤等等都成了物質性記憶的表征。就這樣,記憶終于有了直觀上的“輕重”與“多寡”,物跟記憶的關系從未像現在這么緊密過。在這樣的語境中,“物”比人包含了更多的記憶。“物”不僅僅是記憶的載體,其本身就是對記憶的可視化呈現。
既然現在的儲存科技如此發達,網絡又擁有強大的記錄和檢索功能,因此“記錄下來的東西遠遠多于人的記憶能保存的,這種可能性的產生打破了文化記憶的收支平衡。”[19]那么人的記憶是不是在互聯網時代就會面臨終結?其實,人的記憶不僅不會消失,其重要性和價值在網絡數字化時代越發突出。在“網絡數字化”的語境中,記憶是審美觀念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方面,網絡并沒有改變記憶是審美活動的基礎條件這一事實。大數據通過捕捉我們的消費記錄、瀏覽記錄,甚至我們日常溝通中的輸入記錄和語音信息,將這些數據通過算法進行處理,進而對每一個不同的個體定向推送“喜聞樂見”的網絡內容。比如在短視頻軟件上瀏覽某一類型的視頻,我們會發現隨著瀏覽次數的增多,軟件就會推送更多與之相關的內容。這實則是通過對局部記憶進行不斷重復來達到強化的效果。這樣一來,人們的審美經驗將高度集中于某些具體的部分。當下,以動漫二次元為代表的亞文化圈層的興起便說明了網絡大數據記憶對審美觀念形成的作用。二次元是動漫圈的專門用語,發源于日本,字面意思是指空間意義上的“二維”,即早期的漫畫、動畫、游戲等都包含在這“二維”之中。本著對“二次元”的喜愛,愛好者們不滿足于觀看動畫、漫畫等,還開始進行相關的同人創作,cosplay(角色扮演),販售周邊等活動,并且借助網絡來分享相關內容。在這一過程中,網絡和愛好者之間的互動幾乎都是正反饋,于是二次元很快從愛好者的小群體逐漸發展為亞文化圈層,以至現在形成了如今與主流文化之間的壁壘。一定程度上來說,當下越來越精細的審美圈層的分類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種現象(如“飯圈文化”等)便是由這種審美趣味記憶的可算化而生產出來的。
另一方面,在網絡數字化時代,個人的記憶成為網絡審美共同體建構的重要組成部分。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在《理解媒介》一書中將人類的媒介發展歷程分為了口頭傳播時期、文字印刷傳播時期、電子傳播時期。這其實也描述了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以及人保存和傳播記憶的歷程。語言使記憶的保存和傳播成為可能,文字和書籍使記憶能夠長久保存。“網絡數字化”不僅繼承了之前的優勢,還為記憶打開了新的面向。共享是網絡世界的核心特點之一,因此在網絡中的記憶多了“喚起”的作用。相比于印刷出來就成為封閉整體的書籍,網絡中的記憶建構是充滿了互動的過程。或是由一個話題引發,或是一個人引出話頭,網民便可以持續性地參與到討論之中,貢獻出個人記憶中與之有關的部分。由于網民的人員構成復雜、層次不一,在網絡中建構的記憶往往擁有極大的時間跨度,涉及極為多樣的社會層面,包含了文字、圖片、視頻等各種各樣的藝術形式。個人閱歷難以達到如此的豐富程度。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通過網絡共建起來的記憶跟哈布瓦赫提出的集體記憶不同,因為并不需要一個“社會框架”來進行理解。跟瓦爾堡“將記憶視為‘苦難寶藏”[20],試圖通過藝術經驗來表達記憶的理念相差甚遠。跟時下熱門的“文化記憶”也有所區別,它不由儀式、慶典等莊嚴的集體性活動所引發,也不必然涉及民族歷史這樣厚重的內容。網絡中的記憶建構實則強調“有記錄,就有發生”的理念。這樣看來,網絡上的記憶書寫更像是編輯人類活動名目詞條的資料書,人人都有權利將自己所見的內容發表出來,不斷地豐富詞條下的義項。
三
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指出記憶“是處理全社會的總體性問題的一種特別的方式。”[21]“網絡數字化”時代,審美物質性基礎的改變為人們帶來了新的生存體驗。記憶現象也成為我們認識時代精神的一個面向。
首先,個人記憶的表達越來越受到重視,個人的記憶表達成了當下的熱門話題。自傳是描述自我人生經歷和精神歷程的文學體裁,目的是對記憶中具有重大意義時刻的記錄。狄爾泰(Wihelm Dilthey)認為“自傳是對于個體對他自己的生命的反思的文字表達。”[22]法國自傳研究者菲力浦·勒熱訥(Philippe Lejeune)的定義則更加嚴格,認為“當某個人主要強調他的個人生活,尤其是他的個性的歷史時,我們把這個人用散文體寫成的回顧性敘事稱作自傳。”[23]文學史上有許多大作家用自傳的形式揭露了自身精神的發展歷程,比如:圣·奧古斯丁(St. Augustine)的《懺悔錄》,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懺悔錄》,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的《詩與真》,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的《墓畔回憶錄》等等,此外還有各個領域的名人回憶錄,這些數不勝數的書籍成了豐富人類精神世界的文獻。細想起來,這些自傳、回憶錄并不能代表人類記憶的全部,它們僅僅是一小群精英的自我書寫。歷史上真實存在過的絕大多數人都默默地走過,不著一字。隨著網絡數字化時代的來臨,記憶寫作的物質和技術門檻大大地降低了,普通的個人成為記憶表達現象中的生力軍。文字不再是唯一的記錄手段,圖像、音頻、視頻提供了更多可供選擇的形式。跟文字不同的是,在“網絡數字化”背景下,圖片和音、視頻的背后已經存在著一套敘事邏輯,人們只需要往里面填充記憶的內容,再進行簡單的編輯處理即可。另一方面,圖片和音、視頻直接與人類的聽覺、視覺相通,人們并不需要習得額外的表達規則。這便是網絡中視覺化的圖像和畫面在記憶表達上比文字更直接,更受到歡迎,易于傳播的主要原因。
其次,記憶與“物”的關系是網絡數字化時代藝術所要探討的主要主題。物質和抽象是兩種并行不悖的記憶保存形式,而網絡數字化的出現卻放大了兩種記憶形式之間的差異。這一點在藝術領域表現得尤其明顯。德國新表現主義藝術家安塞姆·基甫(Anselm Kiefer)通過將金屬制成雕塑來探討“物”是如何承載記憶的。金屬給人以穩定和堅固的感覺,這些由鉛制成的“書” 將記憶由精神世界的活動落實為現實中的實體,詮釋了“物”承載記憶的功用。“圖像是用來把某些知識內容賦予強烈感情、加強記憶的”[24],物體的造型和外觀在對于人類自身的記憶來說具有重要意義。“物”的物質性則是記憶可靠性和穩定性的保障。
而在網絡時代,數字化的虛擬性提供了保存記憶的新形式。谷歌藝術與文化(Google Arts& Culture)在這方面已經做出了不少探索,它打造的數字博物館[25]成為連接藝術品和觀眾的新空間。通過掃描技術,現實中的作品擁有了數字化的替代形式。借助電子屏幕、VR等設備,審美主體變成了人和設備的結合體。作為審美活動必要條件的“在場”也在網絡數字化的語境中變成了“在線”。得益于精細化的掃描技術和虛擬性的網絡技術,從邏輯上說,數字化藏品不僅保留了原作品中光澤、顏色、紋理等等方面的細節,還可以通過點擊放大、旋轉等現實參觀中難以實現的方式來滿足我們對藝術品的認知需求。這樣一來,數字化博物館的“擬象”似乎給人以更真實豐滿的體驗。當然,這種看起來層次更多元、更豐富的記憶感觸方式就能取代那種觸摸“鉛書”全身心的感覺,或者說,人類面臨鉛、銅、鐵、木頭這類具體的物感覺以及由此而連帶、申發的記憶是否真的能夠為數字化技術而復現,值得商榷。這不單是一個技術問題,更是關乎人對自身認知、定位的問題。從這個角度說,數字化博物館等對藝術品記憶屬性諸種新的展示和保存形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拓展了“記憶與物”的關系域的邊疆,也仍然是一個需要細加斟酌的話題。
此外,還需要注意到情感已成為網絡數字化時代記憶表達的主要內容。現代社會分工的精細化導致知識面和見識都越來越專業,故而人的記憶和精神體驗都變得越來越局限化,難以通過個人的生活經驗映射出社會的整體性樣態。越來越快的生活節奏和社會變遷并沒有給我們留下足夠多的時間來進行自我反思和認識世界。碎片化不可避免地成了網絡數字化時代記憶的特點。人能夠絕對把握的只有自己的情感體驗。于是,當下的記憶表達所追求的不是個人生命與時代命運相交融的宏大敘述,也不是通過個人生活來記錄社會變遷,而是對于生存體驗的情感表達。這便是時下許多流量短視頻能夠爆火的原因:人們的情感需求通過網絡被放大了,而這種欲望能夠很快地在網絡的視聽體驗中得到呼應或滿足,繼而引發新的需求。在一個相對封閉的時間維度里,這種記憶的情緒化生產一旦吸引了媒體和人們的關注,就成了“流量密碼”,接著就會引發大量跟風和模仿。這種記憶的“生產-消費”循環周而復始,人們卻樂此不疲,這是否可能導致所生產的同質化和淺薄化?這是我們面對新興記憶技術的審美效應時必須直面的一個問題。
由網絡中海量數據的堆砌所造成的“超憶癥”和“失語癥”等現象,同樣是我們在今天考察新興記憶技術的審美效應時應當重視的問題。“超憶癥”本來是指一種醫學現象,指人擁有超乎常人的記憶力的同時卻幾乎喪失了遺忘的能力。這些人能夠將自己多年來經歷的各種細節記得一清二楚。在網絡之中,人們的所有操作無法被真正地刪除,“被記憶”成為一種常態。人們的交流記錄和日常出行、消費記錄都由大數據默默做好了詳細的記錄。已經習慣了上網生活的人們不用專門寫日記都能通過這些記錄精準地還原出過去某一天的生活安排。甚至想要知道歷史上哪一天發生了什么事情,只需要在搜索引擎中輸入關鍵詞便能夠獲取相應的信息。這樣一來,網絡不僅是一個無所不包的巨型記憶“倉庫”,它還成了連接現在和過去的通道。然而,這些詳細的記錄并不能夠還原出生活原本的樣貌,事無巨細的記錄反而成為生活碎片化的證明。這些記錄大大增加了過去部分的比重,打破了過去、現在、未來三者之間的平衡。這樣看來,記憶也可能成為一種負擔。
跟“超憶癥”相關聯的則是“失語癥”。人腦的算力能夠超過世界上任何一臺計算機,但是人卻不能自如地運用這項能力。當面對網絡呈現出的海量數據時,人腦反而不能像計算機那樣井井有條地處理。一方面,網絡數字化時代信息的產生速度已經超過人的接受和理解的速度。以出版行業為例,每天新出版的書籍數量就已經超過了人一生的閱讀量。再者說,為了吸引注意力,網絡通常會針對人們的興趣點來生產信息,大數據甚至能夠通過算法來定向推送相關信息。在習慣這種高強度的刺激之后,人的精神世界的貧瘠程度大大地加深。于是,在網絡之中便會出現確實看過很多東西,但當人們想要進行表達的時候,又覺得沒有什么給自己留下深刻印象。這就是網絡“失語癥”。分析至此,我們發現,相較于“記憶”,用“記錄”來描述網絡中的數據堆砌更加合適與準確。尼采認為真正意義上的生活必然包含遺忘,“不管是最微小的幸福還是最強烈的幸福,它總有一樣東西是讓它成為幸福的:那就是遺忘力,或者用更學術性的話來說,在整個過程中感覺到‘非歷史的能力。”[26]因為人是有限的存在,并不能夠在時間永恒地飛逝和流變中把握自身的存在。正是因為遺忘,我們才能思忖并區分出記憶中寶貴和平庸的部分。這樣看來,在網絡數字化時代,人們或將逐漸重視“遺忘”的重要性。
四、結語
“電腦作為一個模擬的外置記憶,以及大腦研究中關于搭建和拆除神經網絡的新認識,都為文化學研究的問題領域打開了一個引人注目的新視野。”[27]網絡數字化技術已經深度介入我們的日常生活,網絡成為當下討論問題的重要文化語境。網絡數字化技術的新奇之處在于其產生和提供了新的物質性基礎,改變了人們的感知方式和思維模式,由此也引發了審美活動和記憶觀念的改變。厘清這一問題具有相當的難度,除卻網絡自身發展的迅速,更是還有商業資本等其他力量的參與。其內容之廣博非一人之力可以應對。本文的探討也只是就其中的部分現象做出粗淺的分析。細細想來,文明的發展無一例外地伴隨著對記憶的探討。記憶的功用不再局限于知道過去發生了什么,它在“網絡數字化”的語境中已經成為人的一種生活方式。人通過對記憶的表達來建構連續的自我,從而對抗網絡數字化時代碎片化的生存境況。從這個角度來說,記憶建構是否能構成審美自律在“網絡數字化”語境中的一種表現形式?至少,在任何一個時代,某種自覺的審美抵抗姿態都是必要的。
[注釋]
[1][4][8] [德]馬克思、[德]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頁、第92頁、第73頁。
[2][德]揚·阿斯曼:《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金壽福,黃曉晨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46頁。
[3][17][18][19][20][21][24][27] [德]阿萊達·阿斯曼:《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潘璐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頁、第200頁、第478頁、第475頁、第431頁、第10頁、第344頁、第8頁。
[5][11][12][15] [法]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2:迷失方向》,趙和平,印螺譯,譯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頁、第122頁、第130頁、第113頁。
[6] [法]讓·波德里亞:《象征交換與死亡》,車槿山譯,譯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頁。
[7] [法]尚·布希亞:《擬仿物與擬像》,洪凌譯,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公司1998年版,第13頁。
[9] [德]哈貝馬斯:《交往與社會進化》,張博樹譯,重慶出版社1989年版,第93—94頁。
[10] [美]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夏鑄九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4頁。
[13] [德]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1頁。
[14] [英]伊格爾頓:《審美意識形態》,王杰,傅德根,麥永雄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頁。
[16] [法]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1:愛比米修斯的過失》,裴程譯,譯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頁。
[22] [德]狄爾泰:《歷史中的意義》,艾彥譯,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31頁。
[23] [法]菲力浦·勒熱訥:《自傳契約》,楊國政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4頁。
[25] 此處附上谷歌文化與藝術(Google Arts&
Culture)里面國荷蘭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Rijksmuseum)的數字化藏品網頁地址:https://art
sandculture.google.com/partner/rijksmuseum?hl=en。
[26]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歷史的用途與濫用》,陳濤,周輝榮譯,劉北成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頁。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