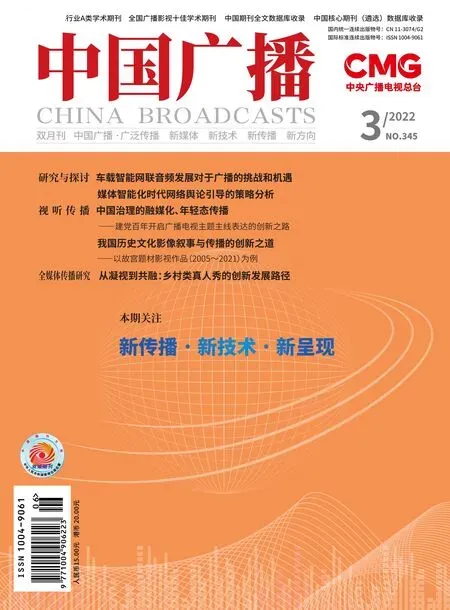心流理論視域下互動視頻的用戶體驗
☉王 敏 鐘 焯
一、互動視頻:以用戶需求為導向的技術變革產物
1967年,一部名為《自動電影:一個男人與他的房子》(Kinoautomat:One Man and his house
)的黑色喜劇電影上映。當播放至劇情轉折點時,影片戛然而止,觀眾需要按下座位上的不同按鈕,以決定片中主人公下一步該怎么做,并選擇后續的劇情走向。整部電影中,這樣的選擇共有9 處,但無論做出何種選擇,最終的結果都殊途同歸。這便是世界上最早的互動電影,也是當下互動視頻的雛形。這種理念和技術在當時廣受好評,卻因某些因素而未得到廣泛發展和應用,此后進入漫長的沉寂期。隨著影視市場分眾化,創作者們迫切需要發掘與受眾有效交流的新方式,視頻中加入互動元素重新進入主流視野。同時,后端軟件開發、流媒體平臺和智能手機釋放了創作者制作交互式內容的潛能以及觀看者參與決策的才能。面向用戶提供分支劇情選擇、視角切換、畫面交互等功能的全新互動視頻形態由構想變為現實,為用戶帶來沉浸式的互動觀看體驗。集成了制作平臺、服務平臺、播放系統等模塊的互動視頻系統,通過互動播控信令、互動播放引擎技術等制播流程中的關鍵技術,使得劇情分支或不同視角的視頻數據能在用發布交互指令時被調動。生產技術的變革賦予傳統視頻創作者極大的創新空間,創作的重點從巧妙地安排情節、敘述故事,轉向讓用戶在故事演進中獲得更多有意義的參與和控制體驗;彼端的受眾也早已從單一接收者角色升格為帶有明確主體需求和選擇能力的用戶角色,在智能終端和網絡傳輸技術的支撐下,不斷向媒介市場提出人性化的需求。互動視頻正契合用戶日益增長的參與、體驗需求,形成一種賦權用戶、協作交流的景象。
互聯網給信息社會帶來巨大變革,強調用戶的主體地位,注重用戶體驗感受,成為媒介產品競爭的共識。自2016年起,Netflix、HBO、YouTube 等國外視頻網站紛紛布局在線互動視頻業務(見表1)。Netflix 在互動電影《黑鏡·潘達斯奈基》(Black Mirror: Bandersnatch
)大獲成功后,于2019年追加互動視頻投入至150 億美元。互動視頻在域外升溫讓國內視頻網站看到商機。Bilibili(以下簡稱B 站)、愛奇藝、騰訊等頭部視頻平臺均將互動組件設為平臺標配,2019年被稱為國內“互動視頻元年”。截至2022年5月19日,B站共上傳11.6萬個互動視頻,播放量達32.6 億次。無論是UGC(用戶生產內容)還是PGC(專業生產內容),中長視頻平臺入局互動視頻領域,成功的關鍵在于用戶增量的拓展、用戶黏性的增強和用戶體驗的提升。
表1:國外主流視頻平臺代表性互動視頻實踐⑨
常用于分析用戶沉浸體驗的心流理論(Flow Theory),也可用于闡釋互動視頻中的用戶體驗。為此,本文基于心流理論,考察B 站中具有較高用戶參與度的互動視頻,嘗試回答觀看互動視頻過程中用戶產生了怎樣的情感體驗,以及這種體驗產生的機制是什么,旨在探索增強用戶黏性、提升用戶體驗之道。
二、彈幕文本:研究B 站用戶體驗的表征
在包含敘事元素的互動視頻中,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種是給用戶設立明確任務目標的“成就導向型”,另一種是不會設立明確的目標,重在探尋各種互動操作之后未知發展的“探索導向型”。本文聚焦于邏輯性更強、用戶參與度更深的“成就導向型”互動視頻。
B 站是目前國內互動視頻制作、分享、傳播與分發的重要陣地。B 站彈幕作為用戶即時的表達和互動方式,常作為研究者分析的對象或工具。有學者總結,當前研究發現彈幕有解構視頻文本、建構儀式狂歡等功能。在持建構儀式立場的研究中,學者注重挖掘用戶心理訴求的滿足。實際上,需求滿足是積極的用戶體驗得以生成的基石,認知與情感需求得到何種程度的滿足決定了用戶體驗水平的高低。因此,研究彈幕使用的心理動機和滿足程度與研究用戶的體驗有重疊區域,從彈幕文本理解用戶使用動機和行為的方法,也可以用于窺探B 站互動視頻這一新媒介形態帶給用戶的體驗,即彈幕文本可作為研究互動視頻用戶體驗的表征。
本文選取B 站互動視頻《你被困在2019年10月25日,如何逃出這一天?》(以下簡稱《如何逃出這一天?》)為研究案例,將其彈幕文本作為研究對象,結合該視頻的劇情設置,解析用戶在觀看過程中的情感體驗。從傳播效果來看,《如何逃出這一天?》上傳于2019年10月25日,斬獲B 站首屆互動游戲開發大賽的“全場最佳”獎項;截至2022年4月17日,視頻播放量達1189.5 萬次,全站排行榜最高至第2 名,形成現象級的傳播效果;同時,視頻總彈幕數達73.5 萬,體現出觀看者充分的表達欲和參與感,也為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樣本數據支撐。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主要采用參與式觀察和文本分析:一是通過參與式觀察法獲取直接情感體驗,并觀察其他用戶的體驗。為獲取研究樣本,筆者以普通用戶身份參與《如何逃出這一天?》視頻互動,在經歷了一次假結局和一次彩蛋結局后,最終達成了真結局。此后,筆者又點擊進入其他循環,經比對去重,共獲得25 個獨立視頻,并利用Python 爬蟲技術提取出每個獨立視頻的彈幕文本,共計6555 條。二是通過文本分析法探索用戶的情感體驗流變及其背后機制。
筆者基于Python 的開源中文分詞工具JIEBA 全模式對彈幕文本進行分詞;經人工剔除無實際意義的詞語(如“沒有”“一個”“一下”)后,統計詞頻并將排名靠前的高頻詞匯進行匯總。結果表明,高頻詞匯主要有兩類。一是與視頻設定的劇情、角色高度關聯,如“循環”“回頭”“救兵”等;二是涉及用戶體驗過程中的情緒,如“終于”“哈哈哈”“恭喜”等。然后,本文以高頻詞為關鍵線索,進入到彈幕文本的具體語境及對應的劇情畫面或互動選項節點,分析用戶在觀看參與互動視頻過程中產生的情感體驗。
三、互動視頻用戶的情感體驗流變及其產生機制
(一)未知挑戰:用戶感知任務目標
清晰的目標、未知的挑戰、即時的反饋是引發心流體驗的關鍵因素。《如何逃出這一天?》視頻標題開門見山,創設情境“你被困在2019年10月25日”,并給出清晰的任務目標——“逃出這一天”,激活用戶參與視頻互動的注意力。而互動技術的搭載讓用戶的選擇點擊都會有即時的反饋,進而切換到下一個情境;并且記錄做出的選擇,幫助用戶在體驗過程中知曉視頻完成度,或在解鎖任務的過程中清楚上一次的選擇,以便綜合思考,讓故事發展有跡可循。這兩者構成了視頻互動的機制。
通過詞頻分析發現,“標記”是彈幕文本中的高頻詞,貫穿于視頻始終。結合具體語境和畫面來看,其最主要的意義在于給自己或他人“提示、標志”,結合“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循環”“回來”等表示經歷次數的高頻詞觀之,大部分用戶在清晰目標的指引下,為了達成任務經歷多輪循環。這也從側面佐證了任務挑戰的高難度與未知性。
美國心理學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賴(Mihaly Csikszentmihalyi)的心流理論模型表明,任務或活動的挑戰和主體技能水平相平衡即可讓人進入心流狀態。但后來的研究者將米哈里的“三通道”模型進一步完善為“八通道”模型,提出當二者都處于低水平時,即使達到平衡,人們也很難進入心流狀態,可能會出現冷漠(apathy)狀態,失衡時會進入無聊(boredom)、焦慮(anxiety)等負面狀態,只有挑戰和技能水平都達到較高程度且平衡時,心流通道才會產生。《如何逃出這一天?》創作者介紹,視頻的循環體是隨機化的,最初的萌新角色始終由用戶駕馭,但循環體中的其他角色可以被理解為由其他人在駕馭,每個用戶的決策都是隨機的,過程靈活多樣。而達成真結局的唯一方式是“跳入水中,讓自己(救兵身份)活下來(此選項只有在達成假結局后才會解鎖)”。這種由概率選項環環相扣、步步為營推進劇情的方式,使得每一個選擇對劇情走向都有意義,造就了挑戰的未知之境。
在此過程中,結局與之前的選擇及所在的循環體緊密相關,用戶只有在經歷過一輪或多輪失敗之后,才能進一步推導達成真結局的路線。因此,用戶需要調動邏輯思維進行推理,形成較高程度挑戰與決策技能的相對平衡。同時,平衡也是動態漸進的,最初可能是隨性選擇,但隨著陷入循環、重回起點,用戶需要推敲上一輪每一次選擇的正確性,綜合考慮,找到“通關”策略。正是這種平衡,才讓用戶不會感到厭煩或無聊,而是在求勝欲的刺激下多次嘗試,達到心流狀態,即忘乎時間的沉浸感和興奮感。
實際上,不僅是互動視頻,傳統的影視作品也在給予觀眾認知和邏輯的挑戰,需要觀眾掌握與之匹配的認知技能才能理解其中的故事脈絡、人物的情緒波動等,只不過這種挑戰和技能是隱性的,無異于一般傳播機制所需要的傳受雙方的解碼條件。互動視頻則在清晰的目標、未知的挑戰、即時的反饋等機制作用下,外化和凸顯了這種挑戰和技能的沖突,使用戶形成區別于傳統觀影享受的沉浸體驗。
(二)停頓冒險:用戶代入參與選擇
互動視頻與傳統視頻最大的區別在于顛覆了形式上的流暢,劇情停頓、彈出提示框、用戶點擊、進入下一個畫面,看似每一步都在考驗著用戶的冒險精神。事實上,對于邏輯嚴謹、選擇點關鍵且有意義的互動視頻而言,停頓選擇不是對劇情的阻礙,反而具有兩層積極意義。
其一,用戶獲得真正的主動,形成掌握主角的主體感。通過停頓、自主選擇,用戶真正從被動的觀眾角色轉換為主動的角色。《如何逃出這一天?》中,雖然創作者一開始就在視頻標題和開頭創設了指向用戶主體“你”的情境——“你被困在2019年10月25日”,但用戶能否真正代入角色,以強烈的主體使命感參與劇情還取決于后續的情境。……“自己”這一彈幕高頻詞顯示了多數用戶已經把自我代入視頻中,不斷“成為”“救兵”角色,在視頻軌跡的各個節點做出自己的“選擇”,掌控自我的命運。
其二,用戶以一種體念冒險的方式參與視頻的共建。外在的停頓并不是缺陷,而是對舊有媒介功能的超越,給用戶營造出仿佛在同一場域下與創作者共建協作的景象。創作者提供“半成品”的作品,用戶選擇之后能夠獲得即時的反饋,即進入下一個不同的場景,不斷使作品趨向完成,形成法國作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所述“可寫文本”式的參與敘事形態。因此,停頓和物理空間的斷裂,實際上強化了創作者與用戶之間的內在聯系,弱化了雙方的距離感,而成為某種意義上的合作伙伴。從“成功”“失敗”“回頭”“進洞”“這里”等與視頻場景或選項直接相關的彈幕高頻詞來看,用戶的彈幕行為、停頓選擇行為基本依附于原有的視頻,表明用戶沉浸于參與視頻的互動,而非脫離原有敘事的節奏。用戶僅僅是在行為表層抽離開原有的觀看動作而實施點擊交互動作,對結局的期待導致用戶在情境置身與行為抽離的相互博弈中,做出繼續點擊觀看的決定。
總的來看,不論是成就導向型還是探索導向型互動視頻,用戶都能夠通過自主選擇,參與視頻的共建或完成視頻任務而取得成就,或動手構建出故事的全貌。這種主體感、參與感的累積,化解了觀眾在觀看普通視頻時由于劇情走向和結局不符合主觀想象而造成的遺憾,也讓用戶產生身臨其境的沉浸感,進入心流狀態。更深層次來看,這種選擇感并非僅僅是來自滑動屏幕、選擇方向這些表層意義的互動操作,其更強調不同環境下的價值觀選擇。用戶在身份代入下產生更多思考,審視自己的內心愿望,自主表達和實現個體的價值。
(三)沉浸快感:用戶感知互動樂趣
以上分析,多從心流體驗的產生條件出發,闡述了互動視頻用戶在互動機制的作用下調動相應技能應對挑戰,通過停頓選擇、代入角色、感知控制感和參與感,從而進入心流狀態。下面將側重從用戶的話語表達行為方面,分析用戶在心流狀態下的沉浸快感。
對比“達成假結局”“從假結局回到第一循環體的開始片段”以及“達成真結局”三個視頻的彈幕文本,可以明顯發現用戶在“達成真結局”時的興奮感。“終于成功了!”“哈哈哈哈哈哈我達成真結局了啊啊啊啊”“成功了,我天”……298 條彈幕文本中,“通關”“哈哈哈”“成功”“終于”等高頻詞匯充分顯示了用戶在經歷多輪循環(失敗)、戰勝重重挑戰后,最終贏得勝利的滿足。他們愿意為了這一刻的滿足,在面對多次失敗時不放棄,反復嘗試。如進入“達成假結局”,彈幕文本中雖有表達對“假結局”的失落,如“完了 假結局 梅開二度了要”“不是吧,第二次假結局???”“又是假結局”,但“標記”“真相”“結局”“選擇”等高頻詞表明用戶的情緒并沒有陷入完全沮喪的狀態,依然沉浸在任務進程中。從假結局回到第一循環體的開始片段中,用戶雖同樣表達了“第二次從假結局回來”“我從第三循環回來了”“第四次被彩蛋扔回來 我腦子這么不好使嘛”等挫敗感,但并沒有表達放棄、厭煩的情緒。可見,在應對挑戰的過程中,用戶有挫敗和失落的情緒,但更多的是沉浸在“解題”的充實感中。
心流理論指出,個體在進入心流后會表現出全神貫注等特征,并且帶來情緒、行為上的積極變化。對于互動視頻,用戶這種積極的變化正是用戶在參與自主選擇、面對適度挑戰、置身故事情境,進入全神貫注的心流狀態后,體會到互動視頻所帶來的快樂并且沉浸其中。快樂既可以來自攻克挑戰后對自身能力的認可滿足,也可以是過程中純粹的選擇感、參與感、冒險感,用戶可能會為正確選擇而雀躍、為錯誤選擇而沮喪,但無論成功失敗,都是他們的樂趣所在,因為這是前所未有的自主體驗。
四、互動視頻用戶體驗優化與主流媒體傳播力提升
英裔美國物理學家、心理學家和傳播學家威廉·斯蒂芬森(William Stephenson)提出:“不以傳播信息作為特定目的,而是單純地為受眾傳遞快樂,并使其完全沉浸其中”。互動視頻的娛樂性和消遣性是吸引用戶參與互動的關鍵因素,在媒介過剩、受眾會基于娛樂動機接觸媒介的背景下,互動視頻更具吸引力。
主流媒體的新聞生產同樣需要重視用戶體驗,互動視頻值得嘗試。新華社在2020年全國兩會期間推出“首部新聞互動微紀錄片”《她的故事,“觸”處動人》,有一定創新,在制作了用戶多面立體素材之后,由用戶選擇了解人物哪方面的故事。但互動方式比較分散、互動張力有限。2021年,新華社再推互動視頻——《“鬼先生”和最后的女獵人》(又名《轉行》),以扶貧為主題,讓用戶體驗兩個虛擬人物的選擇——從已經淡出歷史舞臺的行業“轉行”,擺脫貧窮落后的命運。視頻中“鬼先生”和“女獵人”的故事原型取材于新華社兩篇優秀的報道,但視頻更似一款游戲。未來,主流媒體可嘗試在人物報道、宏大主題上使用互動視頻。比如法制案例的互動視頻化,讓用戶不論如何選擇劇情,終歸讓犯罪難逃法網,以此體現法治權威;另外,還可以從真實新聞場景出發,營造一個仿真空間,讓用戶作為一個新聞場景的親歷者(路人、記者),既可以切換不同觀看視角,也可以與新聞主人公對話互動。
總之,互動視頻本身即富有創意。視頻不再是封閉的,從生產到傳播的過程也不再是單向流動,一個個半成品待用戶加工、創造。這種創意正是在技術和人性雙重驅動下媒介深度融合的縮影。
注釋
①“Groundbreaking Czechoslovak interactive film system revived 40 years later”,english.radio.cz,https://english.radio.cz/groundbreakingczechoslovak-interactive-film-system-revived-40-years-later-8607007.
②?倪泰樂、陳應雙、吳金龍:《從觀眾到玩家:論互動視頻的演化路徑》,《傳媒》,2021年第7 期。
③張媛:《用戶體驗與互動敘事:互動電視劇的興起與觀眾角色的演變》,《電影文學》,2020年第21 期。
④“Is ‘Interactive Storytelling’ the Future of Media? Or does passive and active content serve different purposes? ”,onezero.medium.com,https://onezero.medium.com/is-interactivestorytelling-the-future-of-media-df6de5138520.
⑤《互聯網互動視頻數據格式規范:GY/T 332-2020》,國家廣播電視總局,http://www.nrta.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spm=chekydwnc f.0.0.1.XHOeR1&classid=0&filename=0d7d39695 06a49269a0eabcf7c06261b.pdf.
⑥《5G 高新視頻——互動視頻技術白皮書(2020)》,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科技司,https://gdj.ah.gov.cn/group6/M00/01/BC/wKg8Bl-8hMGABFIUACj6uQbnHHU954.pdf.
⑦“Netflix Planning More Interactive Content After Bandersnatch Success”,screenrant.com,https://screenrant.com/netflix-planning-interactivecontent-bandersnatch-success/.
⑧蘇武江:《產業化發展趨勢下互動視頻發展研究》,《傳媒》,2021年第23 期。
⑨表1 資料均來源于維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Adventures_of_Puss_in_Boots,https://en.wikipedia.org/wiki/Mosaic_(murder_mystery),https://en.wikipedia.org/wiki/Black_Mirror:_Bandersnatch,https://en.wikipedia.org/wiki/A_Heist_with_Markiplier.
⑩趙瑜:《敘事與沉浸:Bilibili“互動短視頻”的交互類型與用戶體驗》,《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 期。
?王蕊、劉瑞一、矯立斌等:《走向大眾化的彈幕:媒介功能及其實現方式》,《新聞記者》,2019年第5 期。
?宮承波、梁培培:《從“用戶體驗”到“媒體用戶體驗”——關于媒體用戶體驗幾個基本問題的探析》,《新聞與傳播評論》,2018年第1 期。
?金燕、楊康:《基于用戶體驗的信息質量評價指標體系研究——從用戶認知需求與情感需求角度分析》,《情報理論與實踐》,2017年第2 期。
?仝沖、趙宇翔:《基于內容分析法的彈幕視頻網站用戶使用動機和行為研究》,《圖書館論壇》,2019年第6 期。
?播放量、總彈幕數等數據為B 站平臺2022年4月17日當日顯示數據。
?B 站彈幕池存在上限。彈幕數超過上限后,系統按照時間順序替換早期彈幕以維持在特定水平。本文爬取的數據是2022年4月17日當天彈幕池存放的彈幕。
?姜婷婷、陳佩龍、許艷閏:《國外心流理論應用研究進展》,《信息資源管理學報》,2021年第5 期。
?張鶴煬:《影游互生視角下國產互動劇的傳受特征分析》,《當代電視》,2020年第1 期。
?袁韜、楊欣怡:《傳播游戲理論視角下的搞笑網紅現象解析》,《傳媒》,2020年第7 期。
?劉小草:《用互動游戲講脫貧故事,這創意“亮”了 新華網破億爆款創意互動視頻〈“鬼先生”和最后的女獵人〉,帶給玩家滿滿的脫貧攻堅參與感》,《新華每日電訊》,2021年3月2日,第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