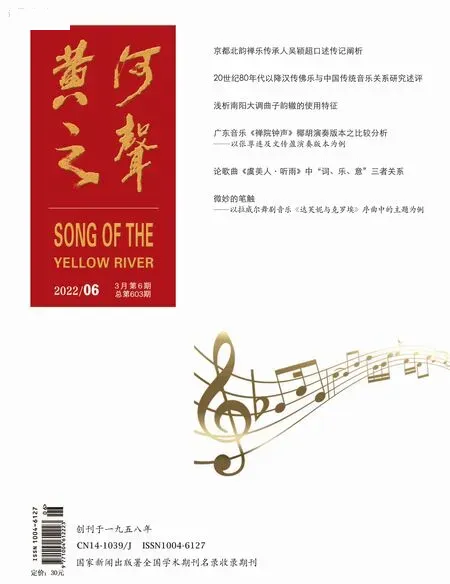論合唱作品的分析和處理方法
邵夢旗
合唱作品的演繹不只是演唱好音準、節奏和音色。在合唱作品的演繹中,作為指揮,還應發掘其作品中的深層內涵,了解作曲者構思和目的。作曲者在寫出了另人陶醉的、感同身受的作曲技法的同時,也兼顧了合唱中人聲的演唱技術難點,設計出了完整的、貼合歌詞的旋律。而我們作為合唱中的指揮者、排演者,在排練合唱作品之前的案頭工作中,不僅要熟讀總譜,更需要準確的推斷出作曲者想要表達的內容和效果,對合唱作品中的橫向、縱向發展和歌詞中邏輯重音等多方面進行分析。只有進行充分、精細的分析和處理,掌握合唱作品的細節,才能更完整的詮釋音樂,演繹出讓人陶醉的音樂旋律。
一、合唱作品中橫向發展的分析和處理方法
(一)音級的律動產生的聲音張力變化
作曲者在譜寫具有音級遞增或遞減傾向的樂句時,一般都具有目的性和預見性。通常在人聲的演唱中,音級越高,音色的緊張度會越強,合唱團員在作品的排演時,遭遇音域在小字二組以上的音時,對于音量的控制是非常困難的。指揮在觀察到該段落出現音級爬升時,應分析該樂句是否有音量增大的趨勢,并決定是否作出相應的漸強或者語氣強調的音樂處理。同理,在合唱聲部中,該聲部段落出現逐漸下行的音級,音量和張力也會自然的降低。在旋律進行中,音級發生由低到高的跳進,人聲的音色也會相對的繃緊,其張力感也會出現對應的變化。作為指揮者,應注意旋律的起伏所對應的人聲的緊張程度,合理的利用人聲在演唱時所產生的自然規律,對具體的旋律添加對應的語氣色彩,進行合理的音樂處理。
(二)休止符位置和節奏型變化產生的音樂動力
在樂句中,休止符位置僅在強拍出現時,通常前面伴隨著樂句以弱拍的形式結束,或后面新樂句弱起的開始。以休止符為中線,可以著重分析該休止符是否改變了新樂句和舊樂句的語態,其前后旋律形象是否因休止符改變為“重新啟動、補充說明、緊促敘述、伴奏支聲、語氣配合、鞏固色彩,抒發情感”等音響效果的形象。在合唱作品中,休止符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動力,調節了整個樂句的語態和音樂色彩。
在樂曲進行中,節奏型的變化會產生不同的音樂動力。關于節奏在樂曲行進中的變化,我們可以大致分為“節奏平穩行進”和具有推動性的“節奏變化行進”。我們在合唱作品中經常看到多個樂句,樂句之間節奏相同但音高不同,節奏型穩定無變化性。一般在這時,聽感會專注在音高旋律的變化和歌詞變化上。通常情況下,如果節奏穩定,那么旋律就有概率是具有推動性的,推動力的大小可以根據平穩節奏下音高的變化幅度來推斷。另外在根據節奏變化來進行音樂處理時,也應注意樂句中是否存在“起承轉合”的結構模式。
“節奏變化行進”較為常見,比如各聲部節奏型由“較為散碎”和“錯節”,轉變為多聲部同節奏行進時,作曲家通常會給這個小節的和聲色彩設定為“相對濃郁”。但其先決條件,必須是前后節奏產生了充分對比,才能凸顯“濃郁”音響效果的目的。通常在樂譜中沒有強弱標記的情況下,節奏型突然轉變為多聲部節奏重合,在自然規律下其音量也會變大,反之則會變小。
在作曲者的譜曲過程中,還有很多節奏設計目的。如單一聲部節奏較為密集或寬松時,展現出的音樂動力也是不同的。節奏密集時,演唱歌詞時具有緊湊感,而寬松時,則具有抒發感。另外影響樂曲旋律的動力感的還有附點節奏、切分節奏、全音符等節奏型的出現,比如在歌曲《漁光曲》中,為了凸顯邏輯重音“魚”,在歌詞“魚——兒”中,通過節奏變化設計,把長時值的節奏安置在“魚”上,短時值的節奏安置在“兒”上等情況。
(三)連音線的音樂處理方法
在合唱作品中,連音線有著連貫演唱音符的含義,但在合唱排練中還需考慮到人聲的細節。作曲者在書寫連音線時,不僅會考量到連貫演唱該樂句的音響效果,同時也會考慮每句連音線的開頭和結尾的人聲演唱效果。通常合唱的發聲習慣會像交響樂團一樣,在自然演唱下,音量和歌唱狀態出現會啟動延遲,出現該樂句音量不均衡的情景。以臺灣大學合唱團演唱的《蒲公英》(潘行紫旻作曲)為例,每個連音線都掌握并順應了其特點,整個曲子在演唱中都把連音線的開頭唱的具有啟動感,連音線的結尾具有降落感。但并非所有作品都應如此處理,指揮應根據作品的不同,來判斷其連音線的處理辦法,揣測作曲者的設計目的。一般來說,被連音線選中的音數量越多,跨度越長,產生這種傾向的概率就會越大。
二、合唱作品中縱向發展的分析和處理方法
(一)縱向發展中排列法的分析和處理方法
通常在合唱作品中,我們經常使用的和聲排列法為開放排列和密集排列以及混合排列法。其中不同的排列法所產生的音響效果是不同的,其中密集排列法通常在合唱的和聲聽感中具有收縮感,音響較為濃厚,集中,聲部之間融合感更強,在音響效果上單一聲部的音色不夠突出。而開放排列法則更具有張力,各聲部的音色特點明顯,音程之間距離相對較寬,聲部音色更具有對比的表現力等特點。混合排列法的特點則在于兩聲部之間的關系,音程距離較近的聲部和較遠的聲部會產生不同的對比聽感,可能產生“襯托、支聲、避讓”等聽感效果。
在樂曲縱向旋律行進中,遇到排列法突然改變時,我們可以聯系該和弦的前后和聲以及前后樂句進行分析和音樂處理。作曲者通常在突然改變和聲排列法時,都具有著目的性。例如在大開大合的開放式后,緊接著進行了平穩融合的密集式,那么這時就可以權衡能否對這個和弦在演唱時的語氣和音量上來進行改變和二度創作。
同樣我們在合唱作品的進行中,發現作曲者并沒有改變排列法或者進行音級跳進,但和聲的排列有逐步向外擴張或者逐步向內收縮的趨勢,那么該樂句的和聲張力就處在逐漸縮小或者擴大的過程中。在這種樂句行進中的和聲細節上,指揮可對其自主進行語氣、斷句、聲部之間音量均衡與失衡設計等方面的音樂處理。
(二)縱向節奏織體的分析和處理方法
在大多數多聲部的合唱作品中,多聲部的節奏并不是統一不變的,我們在實際排演中經常會發現作品中存在大量的縱向的不同節奏交織,例如女聲部以相對平穩的節奏進行伴奏,突出男聲部的變化性節奏以及旋律,女聲部為男聲部提供支撐,這種和聲織體現象也可以稱作“襯托”。在“襯托”中,作曲者的主要目的在于表現出某個別聲部的音色或者旋律,其他聲部作為伴奏襯托。指揮者可以根據作曲者的設計目的來判斷,使各聲部音量上得到合適的平衡或者差異,可以適當調節伴奏聲部與主旋律聲部的音量強弱和語感表達。
節奏交織往往也會出現對比效果,例如在合唱作品中,往往會出現在某一強拍上或者某一段落上,之前沒有出現的其他聲部突然出現,又在下一拍或者下一小節中突然消失。通過“音響飽滿”和“音響單薄”的對比寫作手法展現其獨特音響效果,增加了音樂的律動性。作為指揮者,要聯系前后進行整體的分析,調節該節奏聲部所需的音量和語態效果為整部作品所需要的聲音,從而改變對其的演唱效果,達到音樂處理的目的。
節奏的交錯進行還包括著情景模擬的作用,其中以《羊角花開》(向琛子、陳萬編配)(譜例1)為例,該合唱作品的開頭以各聲部先后進入的吟唱開始,節奏充分的錯節。在指揮者接收到新的作品,進行初步讀譜時,首先要看到的就是曲作者留給了各聲部進入時“展現音色美感”的目的。再可以進一步分析為什么曲作者要以這種錯開的聲部節奏形式來展現樂曲開頭的引子部分。二度創作者可以根據作品排演出自己的理解和音樂處理,比如理解主題為羊角花“花開”并通過不融合的音色,借由聲部來展現出花瓣展開的動態畫面形象。又比如在女聲合唱《水母雞》中多次出現細碎的節奏交織,來模擬水母雞群的動態畫面感。

譜例1

譜例2
(三)不同和弦張力的分析和音樂處理方法
一般在同一調式的背景下,以各級音為根音,總共可以產生七個和弦,分為Ⅰ至Ⅶ級和弦,其中Ⅰ,Ⅳ,Ⅴ級和弦為正三和弦,是起到支柱地位的三個和弦,其余四個和弦為副三和弦。以上下方三度關系分類,每個正三和弦的上方三度或者下方三度,都含有一個副三和弦,兩個副三和弦和主和弦一起,構成了“主功能組和弦”,主功能組和弦又有三個:Ⅳ級,Ⅰ級和Ⅲ級和弦,“下屬功能功能組和弦”為:Ⅱ級,Ⅳ級,Ⅵ級和弦,“屬功能組和弦”:Ⅲ級,Ⅴ級,Ⅶ級和弦。在不同的和弦組中,各級和弦所扮演的角色是不相同的,由于和弦之間音程距離不同,功能組和弦之間的產生音響效果的“聯系”也不同。相對來說調式下主和弦通常含有著開始,結束,穩定的音響色彩,而屬和弦相對較不穩定,有暫未完成的感受,屬和弦具有向主和弦推動的動力感。下屬和弦往往有種前后連接,具有“橋梁、承接”的聽感作用。我們以現代和弦記號來舉例,若該合唱作品為C調,在和弦連接中發生了C→Am→F→Dm→G7→C的和弦連接,那么我們可以在聽感上歸類,把C→Am分為一組,具有開始和延伸的作用,其中Ⅵ級和弦“Am”含有主音,功能傾向于主功能組,可將其音響效果根據作品不同,歸為開始和延伸的作用。而F→Dm則具有新的和弦,出現承接感的音響效果,而G7則具有回到主和弦的推動和待解決的聽感,最后回到主和弦C。在實際合唱作品的音樂處理中,應該根據和弦張力的不同,具體進行分類與處理,設計和演唱出相應的和弦特色,對應歌詞,分析作曲者在本和弦里想要表達的音響效果。另外在一些合唱作品中,我們經常見到其他下三聲部不變,因上聲部的音進行了改變,從而改變了和弦功能,那么就要聯系前后分析這個和弦的具體形象,來決定聲部進入時展現的音色和音量。
三、合唱作品中歌詞的邏輯重音分析和處理方法
我們常用的“邏輯重音”是為表達語氣而服務的,音樂作品的色調的改變和“邏輯重音”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旋律的起伏和抑揚頓挫以及樂句色彩的改變都能通過邏輯重音進行表達。一部好的音樂作品通常伴隨著大量的語感設計,指揮在演繹作品前通過對詞曲作者內涵的理解,深度發掘作品中的語氣表達細節,才能讓作品更加完整,讓聽者引起共鳴。
通常我們常用的對于語氣的理解為表述者對表述內容的所持態度,一般具有陳述、疑問、祈使和感嘆四種語氣,語氣的表達通常在交流中用語調和語氣詞等進行表述。在合唱作品中,旋律的寫作一般是以歌詞為依據進行譜寫的,作曲者會用作曲法寫出邏輯重音,來模仿詞作者想要表達的語氣,所以通常在譜寫作品中,先后順序為“作曲者先向作詞者進行溝通和理解,再進行譜曲,把樂曲附著在歌詞上”。而我們作為指揮者,一般無法直接的通過交流來了解詞作者的想法。但在我們中文語法的學習中,主語,賓語,謂語,代詞,名詞,狀語,動詞,形容詞等都可以進行分類。在實際音樂處理中,除了閱讀理解詞意,我們還可以在把這些詞語分類后,根據節奏,和弦功能性,和聲織體等來綜合推測合適的邏輯重音,達到加深音樂處理的目的,把作品分析出的內容真正的應用在音樂作品的演繹上。
結 語
很多時候,我們進行對合唱作品的二度創作,容易和作曲者的本意相背離。我們對合唱作品進行主觀的理解和二度創作時,應在遵循詞曲作者的意圖下進行演奏演唱,并發掘該作品的個人的理解。指揮作為作品的演繹者,只有敢于創新和發掘細節,才能賦予作品新的意義。在掌握理論基礎的同時,樹立屬于指揮自己的音樂風格特點。合唱指揮者對作品進行的二度創作時,除了要與“作曲家的個性”保持一種微妙的平衡關系外,還要在風格上注意與其他演繹者的區別。在掌握音樂理論的基礎上,再去擺脫理論的束縛,從傳統的和現代的固定演唱模式中走出來,開創屬于指揮自身的獨特音樂風格,賦予作品獨特的魅力,才能更好的詮釋合唱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