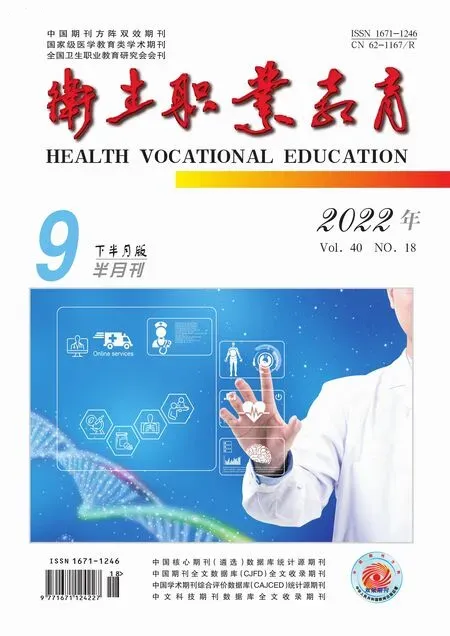基于SEM的東莞市居民基層首診就醫行為影響因素分析
黃秋虹,甘奇慧,蔣 菲
(廣東醫科大學人文與管理學院,廣東 東莞 523808)
2015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進分級診療制度建設的指導意見》[1],要求建立“基層首診、雙向轉診、急慢分治、上下聯動”的分級診療模式,而基層首診是分級診療模式的關鍵環節,對于提高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總體效率、優質醫療資源有序有效下沉、降低居民就醫負擔以及形成合理有序的就醫秩序等目標的實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由于基層首診的選擇行為受忠誠度影響[2],故本研究從東莞市居民的基層首診忠誠度出發,探討影響居民基層首診就醫行為的因素,為加強分級診療制度管理、推進醫改進程提供參考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于2020年10月,采用問卷隨機抽樣方法,共抽取341人作為調查對象。統計結果顯示,調查對象來自東莞市4個街道、28個鎮。本研究共發放問卷341份,回收有效問卷327份,問卷有效率95.89%。
1.2 研究方法
通過借鑒何德華等[3-4]關于影響因素研究的文獻,設計了《東莞市居民對基層首診的認知度及就醫行為分析問卷》,問卷內容分為調查對象的人口學特征信息和問卷部分。問卷部分包括調查對象對基層首診的認知度、支持度、忠誠度和調查對象對基層醫療機構的信任度4個維度共計15道題目,并采用Likert 5點量表設計題項備選答案。
1.3 統計學方法
1.3.1 描述性分析 借助統計軟件SPSS 24.0對調查對象的人口學特征進行描述性分析,對調查問卷進行信度和效度檢驗。
1.3.2 結構方程模型分析 結構方程模型(SEM)是用于討論觀測變量(顯變量)和潛變量(隱變量)之間關系以及潛變量和潛變量之間關系的多元統計方法。結構方程模型包括測量模型和結構模型兩部分,測量模型是研究觀測變量對潛變量的解釋度,結構模型是研究潛變量與潛變量之間的影響關系。結構方程模型的構建包括以下4個步驟:(1)模型設定;(2)模型識別;(3)指標估計;(4)模型評價與修正。模型擬合指數主要包括模型正規擬合指數(NFI)、非正規擬合指數(NNFI)、擬合優度指數(GFI)和殘差近似誤差平方根(RMSEA)等。如果模型擬合情況不佳,需對模型進行修正[5]。
2 結果與分析
2.1 調查對象基本情況
本研究共發放問卷341份,回收有效問卷327份,問卷有效率達95.89%。其中,男性133例(占40.67%),女性194例(占59.33%);年齡以 31~45歲為主,有 142例(占 43.43%),其次為18~30歲,有139例(占42.51%);文化程度以本科為主(111例,占 33.94%),其次為高中/中專/技校(73 例,占 22.32%);工作以政府工作人員為主(115例,占35.17%),其次為農業/畜牧業工作者(85例,占25.99%);參加的醫療保險類型集中在城鎮職工醫療保險(230例,占70.34%)和城鎮居民醫療保險(97例,占29.66%);平均月收入以5 001~10 000元為主(118例,占36.09%)。
2.2 結構方程模型
2.2.1 研究假設的理論推演(1)認知度、信任度和支持度對忠誠度的影響。居民對基層首診的認知度主要依賴居民對于基層首診相關制度、政策信息的記憶,通過基層醫院、基層政府等相關部門組織的宣傳、親朋好友的口口相傳以及居民自身感受到的政策優惠體驗等[6],從而形成對基層首診制度的認知。居民對基層首診的認知度是居民對基層首診忠誠度的基礎,居民對基層首診制度的了解程度越高,居民就越愿意去基層醫療機構就診。因此,提出以下假設,H1:居民的基層首診認知度對居民的基層首診忠誠度有正向影響。
居民對基層醫療機構的信任度是維系、順利推行基層首診制度的關鍵[7]。居民對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信任度主要來源于居民在基層就診過程中對醫療機構的了解和體驗,當居民與基層醫療衛生服務機構之間的信任建立時,居民會減少質疑和抱怨,尊重和寬容提升,從而形成良好的醫患關系和看病就診氛圍,甚至未來繼續就診、積極推薦他人到基層首診。由于信任度顯著正向影響人們的購買意愿[8-9],我們提出以下假設,H2:居民的基層醫療機構信任度對居民的基層首診忠誠度有正向影響。
居民支持包含態度支持和行為支持兩個方面[10],居民的態度支持度越高,內心對基層首診制度的認同感與歸屬感就越強烈,忠誠度就會得到提升;居民的行為支持度越高,對基層首診制度的便利性和優惠性的體驗就越深刻,從而更愿意去基層看病就診。因此,我們提出以下假設,H3:居民的基層首診支持度對居民的基層首診忠誠度有正向影響。
(2)中介作用。中介作用是指一個變量通過中介變量去影響另一個變量。在呂妮萍等[11]關于消費者購買意愿影響因素的研究驗證了認知度的中介作用。仲理峰等[12]對員工工作敬業度和工作績效的影響因素研究發現,組織支持度起中介作用。因此,我們提出以下假設,H4:基層首診認知度在基層醫療機構信任度和居民忠誠度之間起中介作用;H5:基層首診支持度在基層首診認知度和居民忠誠度之間起中介作用;H6:基層首診支持度在基層醫療機構信任度和居民忠誠度之間起中介作用。具體見圖1。

圖1 假設模型
2.2.2 變量描述 本研究共提取認知度、信任度、支持度以及忠誠度這4個因子作為東莞市居民基層首診影響因素的主因子,并從問卷中提取出相對應的15個觀測變量,具體見表1。

表1 研究潛變量及其觀測變量
2.2.3 信度和效度檢驗 通過檢驗,表明所收集問卷數據的信度及效度符合要求。(1)問卷信度檢驗。為了考查問卷的可靠性,采用內在信度Cronbach's α系數進行問卷信度檢驗,檢驗結果發現,Cronbach's α 系數為 0.746,在 0~1之間,達到 0.7時表示問卷具有一定的信度,可知本研究問卷具有良好的信度,測量結果可靠。(2)問卷效度檢驗。采用經KMO檢驗和Bartlett's球性檢驗進行問卷效度檢驗。檢驗結果發現,本研究調查問卷KMO指數為0.814,大于0.8,非常適合做因子分析,Bartlett's球性檢驗P=0.000,小于0.05,調查問卷的效度非常好。
此外,本研究還檢驗了不同變量之間的區分效度。通過計算各個變量的平均萃取變異量(AVE)平方根數值(見表2)可以看出,AVE平方根均大于與之對應的行和列中相關系數的最大值。因此表明,本研究中的測量數據具有較好的區分效度。

表2 潛變量相關系數及AVE的平方根
2.2.4 結構方程模型的建立 根據周晶等[13]關于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忠誠度影響因素的分析進行結構方程模型建模,并通過Amos 24.0軟件對全模型數據擬合檢驗并進行一系列的模型修正,最終得到修正后的結構方程模型,見圖2。

圖2 東莞市居民基層首診就醫行為影響因素的SEM
2.2.5 結構方程模型的評價 結構方程模型以F1~F4為潛變量因子,對應X1~X13、Y1~Y2這15個顯變量因子,求得結構方程模型的適配度指標和擬合結果(見表3)。經與適配指標給定參考值進行比較,大多數指標適配理想,模型擬合度較好。

表3 SEM整體適配度的評價指標體系及擬合結果
2.2.6 路徑分析與假設檢驗結果 結構方程模型顯示,在對F4(忠誠度)有影響的因子中,因子F1(認知度)通過F3(支持度)對F4的間接影響權重最大,為0.15;其次是F2(信任度)通過F1間接影響F4的權重系數為0.11;最后是F1對F4的直接影響權重為0.01。可以得出,認知度、信任度和支持度的高低會對忠誠度的高低產生影響。從觀察變量對潛變量的影響系數可知,X2(社區首診制度)和X3(逐級轉診制度)是影響F1的重要因素;X9(醫療藥品)和X10(醫療環境)對F2的影響較大;X13(患常見病、多發病時基層就診)是影響F3的主要因素。基于以上分析,東莞市居民基層首診就醫行為的影響因素結構方程模型所提出的6個研究假設檢驗結果見表4。

表4 研究假設檢驗結果
3 討論
3.1 居民基層首診認知度直接影響居民對基層首診的忠誠度
居民基層首診認知度是居民基層首診忠誠度的影響因素之一,提高居民的基層首診認知度有利于居民基層首診忠誠度的提升。提高居民對基層首診的總體認知度,一是要完善社會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優化醫保費用補償機制[14],合理設置不同級別醫院的支付比例[15],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醫保杠桿引導作用;二是醫院要明確逐級轉診的標準,簡化轉診流程,保障患者轉診路徑通暢,提高醫療衛生服務的連續性;三是要加強全科醫生的培養,通過規范化培訓、進修、繼續教育和學習資源共享等去提高家庭醫生的醫學水平以及簽約上門服務質量,增強簽約居民對家庭醫生的信任感,促使居民長期接受家庭醫生簽約服務[16],從而推進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制度的實施[17];四是加快推進基本藥物和零差價銷售政策的實施,增加基層醫療衛生服務機構的基本藥物供給品種,提高藥品供給力度與補償比例[18],實施藥品零差價銷售政策,以此為基層首診的實現提供有力支撐。
3.2 居民基層醫療機構信任度以居民基層首診認知度為中介對居民基層首診忠誠度有正向影響
居民對基層醫療機構的信任度無法直接影響居民對基層首診的忠誠度,這與周晶和吳穎敏的研究結果相悖。說明調查對象雖然情感上信任基層醫療衛生服務機構,卻很難在實際行動上做到對基層首診的忠誠。為了促使居民情感上和實際行動上對基層醫療機構的十足信任,基層醫療機構需做到:在醫療藥品方面,備足常見病、多發病等疾病的相關藥品,滿足患者基本用藥需求;在醫療環境上,醫護人員要給患者提供整齊、衛生、舒適、安全、安靜的診療環境,維護好護患關系、病友關系,以此促進患者的治療效果和疾病的轉歸;醫療設備上,加強舊設備的管理和保護,定期檢查和維修,引進先進的設備,提高醫療設施設備水平;此外,還要立足于患者基層就診的需要,對基層醫務人員進行有針對性而非全能式的培養,充分發揮醫聯體下優質醫療資源和數據信息共享[19],鼓勵大醫院專家、醫生下沉至基層醫療機構出診或指導[20],以此提高醫生醫術。
3.3 基層首診支持度在基層首診認知度和居民忠誠度之間起中介作用
支持度在認知度和忠誠度之間起中介作用,說明提高居民基層首診的支持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居民對基層首診的忠誠度。在調查過程中發現,有70.3%的調查對象擁有基層就診經歷,大多數是出于距離較近、報銷比例大以及價格低的考慮,說明基層首診的醫保報銷制度、就近原則以及基本藥物等制度對基層首診制度有很大的推動作用,這些制度和政策的進一步完善能調動居民基層首診的積極主動性。關于實施強制基層首診制度,調查對象中有65.4%反對,原因包括就診環境、設施比較差,藥品質量差、種類少,對高級醫院更加信任,轉診流程和手續復雜等,只要能解決這些問題,居民就會減少對實施強制基層首診制度的抵觸。此外,大多數居民在患常見病、多發病時愿意選擇基層首診,這主要歸功于醫療衛生服務的可及性以及便利性,小部分居民不愿選擇基層就診,仍存在“基層只能用來做一些小檢查,只有大醫院才能看好病”的思想,說到底還是歸結于對基層醫療機構不信任這個問題。總之,基層醫療機構提供的常見病、多發病服務符合大部分居民的醫療期待,但術后康復治療與上級醫院的銜接還存在很多問題亟待解決[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