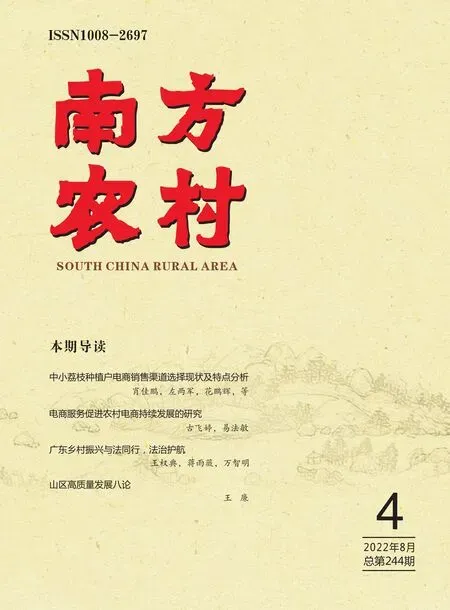基于Supe r-SBM模型和Malmquist指數的我國農業用水效率分析
覃夢香,伍國勇,2
(貴州大學1.經濟學院(西部中心);2.貴州基層社會治理創新高端智庫,貴州 貴陽 550025)
一、引言
近年來,我國農業農村部以加快發展節水農業為舉措,全面推進農業綠色發展為戰略目標,制定了一系列農田節水意見,針對水資源稟賦不同的地區采取不同的耕作技術和灌溉施肥制度,促進我國節水農業開發工作取得明顯進展[1]。我國農業水資源仍存在總量不足、地區分布不均、生產結構不合理諸多問題[2]。2019年,我國用水總量的61.2%用于農業生產,農作物受旱達到7838千公頃,農業用水消耗了我國大部分的水資源,我國干旱缺水的國情沒有得到根本性變化,農業生產活動的水資源依然缺乏。對照《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全面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和綠色低碳發展”的要求,實現資源節約,降低農業用水總量的任務仍然艱巨。《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中指出我國作為人口大國,糧食以及重要農產品需求量在很長一段時間仍將剛性增長,因此加快推進農業由增產導向轉向提質導向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中共十九大報告中也強調了資源全面節約和循環利用才是開發利用資源的正確方法。為打好黃河流域深度節水控水攻堅戰,我國相關部門印發了《黃河流域水資源節約集約利用實施方案》,指出要推動重點領域節水,推進非常規水源利用。我國農業是用水大戶,同時也是耗水大戶,通過分析比較我國農業用水效率的地區差異,并探析其差異特征,為制定合理的農業用水政策提供實證依據,促進我國農業健康發展。
二、文獻綜述
對農業用水效率的分析已成為國內外研究的熱點問題。目前國內對農業用水效率的研究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探討。
在測算方式上,屈曉娟、方蘭(2017)根據BC2模型和Malmquist指數對西部地區11個省份的農業用水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進行實證測算[3]。方琳、吳鳳平等(2018)利用我國31個省市1998-2015年面板數據,在考慮環境容量、生態承載力以及發展條件的基礎上,建立共同前沿SBM模型,探討不同區域類型農業用水效率的差異、變動趨勢以及潛力[4]。張向達、朱帥(2018)通過建立技術效率和影子價格的彈性需求分析模型,利用隨機非參數包絡分析法,估算黑龍江省農業灌溉用水的技術效率和影子價格[5]。佟金萍、馬劍鋒等(2021)基于超效率DEA和Tobit模型對長江流域10個省市農業用水效率進行測度,并分析1998-2011年間用水效率的變動趨勢[6]。楊騫、武榮偉等(2017)利用Global超效率DEA模型測度我國省際以及六大區域農業用水效率[7]。馬劍鋒、佟金萍等(2018)基于投入與產出面板數據,利用全局DEA框架計算了長江經濟帶11個省份的農業用水全局技術效率,并建立空間計量模型探討農業用水效率的空間相關性[8]。
在提高農業用水效率的分析上,國內學者主要從用水效率影響因素出發,多采用Tobit模型進行實證分析。李靜、徐德鈺(2018)根據MinDW和Tobit模型和考察農業水資源效率及規模變動,結果表明地區稟賦并不是唯一影響因素,需針對不同地區的實際情況開展水資源管理、建立合理的農業用水水價以及規模化的生產方式提升用水效率[9]。張玲玲、丁雪麗等(2019)運用地理加權回歸分析不同省份提高農業用水效率策略,提出南方地區要著力于強化蓄水、節水、截水等水利基礎工程建設,而新疆提高農業用水效率的出路在于調整用水結構和種植結構[10]。許朗、陳杰等(2021)認為農業收入占比、用水成本和是否采用灌溉技術等因素對不同農業經營主體的農業灌溉用水效率產生正向影響[11]。
基于已有的基礎,本文將2011-2019年我國31個省(市、區)作為分析對象,試圖運用Super-SBM模型和核密度函數評價農業用水效率,通過Malmquist指數法分解農業用水效率比較三大區域效率的動態變化和差異特征,為農業用水政策制定實施提供實證依據。
三、研究方法和指標選取
(一)Super-SBM模型
數據包絡分析(DEA)是美國著名運籌學家Charnes等人提出來并在相對效率評價概念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關于非參數檢驗的一種方法。傳統的DEA模型主要包括CCR和BCC模型,并且只能橫向比較決策單元在同一時間上的生產效率。與傳統DEA模型相比較,非徑向、非角度的超效率SBM模型能考慮“松弛”變量,減少效率分析中可能產生的誤差,也能客觀地反應各投入產出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借鑒劉雙雙、韓鳳鳴(2017)[12]建立Super-SBM模型公式,假定i個決策單元,分別有n個投入以及m個產出,選取規模報酬可變的非徑向Super-SBM模型,公式可列為:

上列公式中,a,b為各省份的投入產出要素,ρ為Super-SBM模型所計算的農業用水效率值,xi0為各個省份的投入變量,yβ0是各個省份的產出變量,產出與投入變量的松弛變量記作s+,s-,γ為公式的權重。
超效率SBM模型的優勢在于評價某一個決策單元時除了將自身排除在參考外,還排除了多個效率值為1的狀況,并使自身效率值大于1,進而能夠對有效單元進行評價排序。公式中,ρ代表每個決策單元的效率值,當ρ≥1時,代表決策單元是有效的,反之則無效。
(二)核密度估計
Kernel密度估計作為非參數估計方法,可以用連續密度曲線來描述隨機變量的分布形態[13]。相對于傳統的參數估計方法來說,不僅降低了對樣本容量的要求又具有一定的穩健性。假設隨機變量Ei的核密度為f(x),那么其核密度函數可以表示為:

其中,函數K[·]稱為“核函數”,即權重函數;i為農業用水效率;h為帶寬;n為公式的觀測值。常用的核函數主要包括均內核、三角核以及二次核,本文主要選取二次核作為計算函數分析我國31省(市、區)農業用水效率動態變化。
(三)Malmquist指數模型
上述的Super-SBM模型和核密度估計是對我國農業用水效率在不同面板數據的靜態觀測方法,但Super-SBM方法會出現當期效率絕對值大于上期的情況,因此無法判斷效率值是否進步。由于農業用水效率的提升本身就是一個動態的變化過程,包含了農業生產技術效率和以管理、政策創新為主的技術進步,Malmquist指數法是一種能夠反映在評估期內綜合效率、技術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模型,能動態呈現不同時期樣本效率值的變化情況。Malmquist指數法最早是由Malmquist(1953)提出,經Caves以及Fare等人將其進一步完善[14]。Malmqusit指數法認為綜合效率變化是由科學技術變化和技術效率變化所引起的,不需要考慮價格條件,避免了由于價格而引起的信息不對稱等問題。以t時期的技術T為參考,Malmquist指數表示為:

由于Malmquist指數是根據不同時期樣本距離的比率進行幾何平均進而計算不同時期的綜合效率的變化。d(yt,xt),d(yt+1,xt+1)分別代表t時期和t+1時期的距離函數。當指數大于1代表從t時期到t+1時期的農業用水效率上升,指數小于1代表從t時期到t+1時期的農業用水效率下降,指數等于1則代表農業用水效率不變。同時構成TFP的各項指標大于1時,代表該指標對總農業用水效率正向影響較大,小于1時說明該指標對總農業用水效率負向影響較大。
全要素生產率變化(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簡稱TFP)等于技術效率指數(Effch)與技術進步指數(Techch)的乘積,而技術效率指數(簡稱EC)又等于規模效率值(Sech)和純技術效率值(Pech)的乘積,因此Malmquist指數還可以根據上述公式變形為:

(四)指標選取和數據說明
本文中所選取的數據全部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以及各省(市、區)的地區年鑒。黑龍江省由于缺失2011至2013年的第一產業從業人員數,所以采用插值法補充數據,遼寧省缺失2019年第一產業從業人員數采用臨近點平均值處理。本文選取農林牧漁總產值作為產出變量,農業用水總量、第一產業從業人數、化肥施用量、農機總動力、農林水事務支出以及有效灌溉面積作為投入變量,如表1所示。

表1 指標選取表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Super-SBM模型測算結果
本文利用2011-2019年我國31個省際面板數據,通過DEA-SOLVER Pro5.0軟件計算我國農業用水效率值,結果如表2。根據31個省份九年的農業用水效率年均值來看,最大值1.022,最小值0.249,均值0.607,標準差0.234,說明我國整體農業用水效率良好,省際用水效率差異較大。

表2 我國各省份農業用水效率(2011-2019年)
對農業用水效率值大小進行劃分,將農業用水效率ρ≥1省份劃為用水高效地區,將1>ρ≥0.5的省份劃為用水中效地區,將ρ<0.5的省份劃為用水低效地區。全國各省份以用水中效地區為主,用水低效地區個數呈遞減趨勢,說明我國農業用水效率整體提升,部分用水低效地區轉為用水中效區。
全國農業用水效率從2011年的0.581上升至2019年的0.779,增長了0.198。自2011年以來北京的用水效率值均大于1,位居全國第一,說明該市的農業用水實現了高效利用。31個省(市、區)中貴州省的農業用水效率值增幅最高,達到0.766,而內蒙古增幅最小,低至0.039。青海、西藏等省份的多年效率均值均在0.8以上,最高達0.883,但新疆、內蒙古以及寧夏地區的效率值在0.3左右,由此可見西部地區內部各省份分化明顯。
從我國三大地區來看,東西中部地區用水效率差異顯著,多年均值分別為0.813,0.520,0.454。2011年至2019年東部地區效率均值最高為0.988,相比于中西部地區,經濟地理條件優勢、更高的農業技術水平以及資源投入向集約型的轉變,使得東部地區有更高的農業用水效率。受資源稟賦約束,基礎農田設施投入不足、粗放的農業資源投入方式等方面影響,西部地區農業發展受限較大,農業用水效率提高不明顯。
(二)核密度函數估計結果
我國31個省(市、區)農業用水效率的動態趨勢如圖1所示。從核密度時間曲線來看,從2013-2019年整體曲線趨勢向右移動、延伸面積逐年增加存在右拖尾現象,說明全國農業用水效率整體上升,且農業用水效率較高的省份逐漸增加,高水平農業用水效率的省份增長速度較快。從曲線的形狀上來看,全國農業用水效率存在雙峰值現象,主峰和次峰隨時間逐漸向右移動;峰寬逐年加大,次峰峰值整體上呈現上升狀態,峰寬于2016年增大,峰尖呈現扁平化趨勢(2013年次峰消失,2016年重新出現),說明農業用水效率在各地區之間分極明顯,但絕對差距因技術進步得到改善。

圖1 農業用水效率核密度分析
(三)Malmquist指數模型測算結果
運用DEAP 2.1對我國31省(市、區)的全要素農業用水效率變化進行測度,結果如表3。從時間上來看,我國31個省份全要素農業用水效率處于波動狀態,現有的技術水平與技術進步提高了總體全效率。從表3來看,2014-2015年TFP最低值為0.962;TFP最高值處于2018—2019年,達到了1.111。據圖2顯示,2011年—2019年我國全要素農業用水效率變化整體呈現上升趨勢。技術進步是影響全要素生產率變動的主要原因,技術進步指數在2014-2015年呈現下降趨勢,其他時間增幅明顯。從技術效率變動來說,2011年至2019年技術效率值按時間趨勢是遞減的,但存在2016年至2017年回升的現象,說明我國在農業用水技術效率需要進一步提高。因技術效率變化又可以分解成純技術效率(PC)與規模效率(SC)。在純技術效率(PC)方面,2015—2016年間達到最小值0.980,而整體均值0.997小于1,說明我國的農業用水投入沒有帶來產出的最大化。2017年以后的農業用水規模效率值(SC)下降幅度最大,從最高值1.013下降至0.983,農業用水規模逐漸減少,說明近年來我國在提高農業用水效率,降低資源消耗方面成效顯著。

表3 分年份Malmquist指數結果

圖2 全要素生產率變化示意圖
表4顯示了我國31個省份Malmquist指數及其分解的結果。2011-2019年間,我國24個省(市)的TFP指數變動超過1,但仍有河北、上海等7個省、市的全要素生產率小于1處于下降趨勢,占總體的22.58%。貴州、青海、西藏、陜西、云南的全要素生產率排名靠前,TFP均超過1.070;技術進步指數最高的是青海、西藏、貴州、江西和陜西,分別增長了10.4%、9.5%、8%、7.1%和7%。通過全要素生產率和技術進步的對比發現,技術進步指數和TFP排名靠前省份基本一致,因此技術進步指數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較大。從地區上來看,東部地區河北省、上海市兩地整體TFP低于1,農業用水效率下降,農業用水全要素生產率變化主要在于技術進步指數的變動;中部地區,湖南省和安徽省全要素生產率最低,僅有0.969,主要也是受到技術進步的制約;西部地區,貴州省技術進步指數達到1.080,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核心動力在于技術進步的提高。

表4 我國各省份Malmquist指數結果(2011-2019年)
2011-2019年山西、內蒙古的純技術效率處于下降趨勢,分別為2.4%、2.3%,其TFP排名在18和20名,說明較低的純技術效率會制約TFP的提高。而四川、上海規模技術效率下降趨勢大,均為1.9%,相對應的TFP排名在21和27名,說明了較低的規模效率也會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五、結論
本文基于Super-SBM模型、核密度以及Malmquist指數分析法計算我國2011-2019年31個省(市、區)的農業用水效率,并分析我國三大地區農業用水效率時間變化趨勢,相關研究結論如下:2011-2019年我國整體農業用水效率未達到最優化,但有明顯的提升,農業用水效率從2011年的0.581上升至2019年0.779,增長34.08%,同時不同省份的農業用水效率存在著較大的差異。發達的東部地區處在農業用水效率的最前沿,其次是西部地區,用水效率最低的是中部地區,多年均值分別為0.813,0.520,0.454。農業用水效率高的省份效率值提升不明顯,但陜西、云南、貴州等西部地區農業用水效率較低的省份增長速度快效率值提升高。中部地區作為全國農業用水效率最低的區域,用水效率的發展潛力最大。
從Malmquist指數分解結果發現我國全要素農業用水效率變化在2011—2019年間整體趨勢向上但呈現波動的狀態,基本維持在1水平以上,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國全要素農業用水效率存處于上升趨勢,但在31個省份中有15個省份的技術效率低于1,反映現有的技術水平和技術進步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技術效率是制約農業用水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因此資源稟賦較弱的西部地區應抓緊西部大開發發展機遇,在現有的水利政策和節水農業政策基礎上,加強節水灌溉的應用,進一步引進農業技術,發掘農業節水潛力,提高用水效率。東、中部地區發揮自身經濟優勢,繼續提高農業機械化水平,加大科技創新投入,推廣滴灌噴灌技術,改變粗放式農業水資源利用方式。另一方面也要加強農業用水管理上的創新,如種植結構調整、強化節水意識的宣傳以及制定農業用水相關的其他政策,避免因管理無效導致農業用水效率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