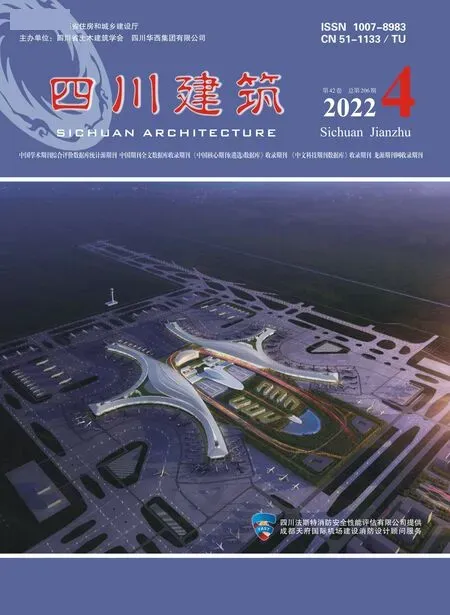大跨度隧道下穿鐵路施工的地層固結影響分析
楊建烽
(西南交通大學交通隧道工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四川成都 610031)
隨著我國交通設施的發展,大跨度隧道下穿既有鐵路工程給既有線路變形控制帶來了極大挑戰。變形原因除施工的直接影響外,還有下穿施工擾動帶來的穿越地層排水固結因素。其中后者是由于施工擾動導致的超孔隙水壓消散,固結變形過程與地層損失造成的沉降相比緩慢且變形更大[1],因此有必要從下穿施工擾動引起的地層再固結角度對路基沉降與地層超孔隙水壓力間聯系進行研究,分析路基穩定影響。
1 工程概況
國內一某擬建大跨度城際鐵路隧道在軟土地層中下穿上方運營鐵路,前期根據下穿開挖影響比選采用復合式襯砌的支護形式[2]。新建隧道的斷面信息及支護形式見表1。

表1 大跨度隧道斷面及支護形式
2 固結原理及模型
本文計算采用有限元計算軟件Midas GTS NX,地層的滲透固結模擬基于Biot固結理論。
2.1 Biot固結方程
(1)
Biot假定土體為連續介質,從其基本方程出發,建立了可反映孔隙水壓力消散與土體變形間耦合感化的固結理論,如式(1)[3],包括4個偏微分方程,式中位移u是關于坐標和時間的函數。
2.2 數值模型
在前期用于分析施工影響的三維模型基礎上,選取一個典型縱斷面建立長120 m、高80 m的平面模型,見圖1,其中水位設置在地表0 m處,隧道拱頂埋深22 m。采用實體平面應變單元模擬圍巖、土體、路基及隧道襯砌。左右、底面設置法向位移邊界,軟黏土及不透水層之間設置排水邊界。

圖1 固結二維數值模型
2.3 模型參數及計算步序
模型中涉及的圍巖及支護物理力學參數如表2。其中黏土層各向滲透系數為2.95×10-9m·s-2,風化巖層不透水。

表2 圍巖及支護物理力學參數
大跨度隧道下穿后固結的模擬過程包括4個關鍵計算步:①建立初始應力場;②增添鐵路路基,并完成地層固結;③模擬隧道下穿施工;④設置時間步,使超孔隙水壓力降低,模擬工后沉降。
3 模擬結果及分析
隧道的下穿施工會對土體及賦存水壓環境帶來擾動,提高了圍巖的超孔隙水壓,而后期的水壓消散將伴隨著上伏路基的沉降變形,因此通過研究隧道圍巖的超孔隙水壓消散與路基變形的過程建立兩者間的聯系。
3.1 開挖引起的超孔隙水壓
天然狀態下,土體內超孔隙水壓力為0。在黏土層上方施作了不透水的鐵路路基后,黏土的超孔隙水壓受荷穩定后會維持在一個定值,對比其與隧道開挖后引起的最大水壓狀態(圖2)進行隧道下穿施工引起超孔隙水壓變化的分析。

圖2 隧道開挖后最大超孔隙水壓力狀態
經計算施作鐵路路基固結后的超孔隙水壓均為負壓,最大-97.5 kPa。而從圖2由下穿施工引起的超孔隙水壓區域可以看出:隧道開挖后對上下引起的超孔隙水壓為負壓,降低了原賦存水壓;對隧道兩側圍巖引起正壓,相比原穩定水壓(-77.9 kPa)增加59.4 kPa。同時兩側及底部的水壓增量比上部區域大。另外由大斷面開挖引起的超孔隙水壓力變化區域集中在隧道斷面周圍約1~1.5倍洞徑的圍巖區域內,越靠近隧道,水壓增量越大,其余不透水層幾乎無變化。
3.2 超孔隙水壓消散過程
在具體施工過程中,大斷面開挖及初支過程會引起最大的水壓力增量,而施作二襯后將開始消散,因此對不同位置的超孔隙水壓力消散過程進行研究。研究的節點選擇如圖2中A-C所示,研究的固結時間從最大水壓力狀態開始,由0~360 d不等,各個節點的超孔隙水壓消散過程如圖3所示。

圖3 各節點超孔隙水壓力消散過程
從圖3中可以看出各節點處的超孔隙水壓均向路基穩定后的地層狀態趨近;下穿施工后的30 d內水壓變化速度最快,30 d時各節點的超孔隙水壓增量減小約50%~60%;施工后約180 d時超水壓基本穩定。分別位于隧道圍巖上、下方的A、C組點的超孔隙水壓增加,位于兩側的B組點減小,其中下方C組點由正超水壓變化為負超水壓。各組點中靠近隧道襯砌的1號點變化量均最大。
3.3 路基沉降過程
取填筑的鐵路路基表面沉降作為研究對象,研究沉降曲線在下方地層固結沉降過程中的變化規律,見圖4。可以看出路基受到影響而沉降的范圍在下穿節點前后30 m范圍;下穿施工引起的沉降為-2.65 cm,施工30 d時沉降約為總沉降的40%;后期180 d時固結沉降基本穩定在19~20 cm,固結沉降量約為施工沉降的6倍。

圖4 路基沉降過程
由圖5可以看出,超孔隙水壓的消散過程與路基的固結沉降穩定過程基本吻合,在180 d左右達到固結穩定。

圖5 路基沉降與超孔隙水壓力消散對比
4 結論
通過模擬大跨度隧道下穿施工后路基固結沉降的過程,研究地層中的超孔隙水壓力狀態,得出結論:隧道開挖引起的超孔隙水壓力變化區域在斷面附近約1~1.5倍洞徑范圍內,越靠近隧道,超水壓增量越大;施工擾動后地層固結引起路基沉降量約是施工瞬時引起沉降量的6倍;超孔隙水壓的消散歷程與路基的沉降穩定過程在變化趨勢與各時段的變化百分比上基本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