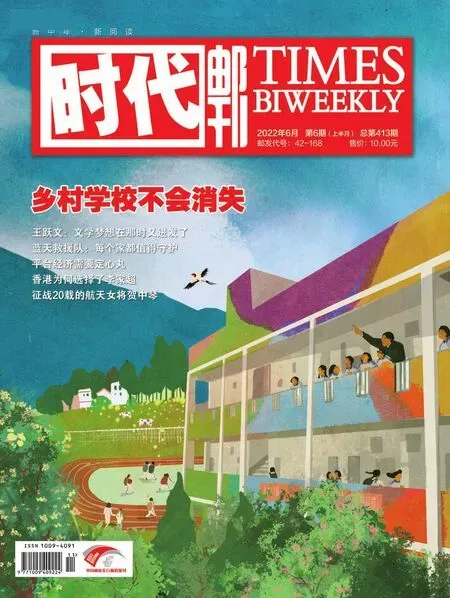辦好鄉村學校,送孩子們去光明未來
● 楊三喜

1996年,我國有近20萬個農村教學點。那年,我上小學一年級,班上有60多名同學,用今天的標準來看,算得上是“超大班額”。
等到我小學畢業時,全校學生不過百名。大概就是這個時候,農村中小學校布局調整政策出臺,鄉村小規模學校開始大規模撤點并校。經過近10年的撤并,到2010年時,我國農村教學點只剩下6.54萬個。
而我所就讀的村小,也在幾年前徹底關停了。雖然2012年教育部一度暫停了農村“撤點并校”,但在2013年至2019年,仍有超5萬所鄉村小學被撤銷或合并。我的“母校”只是其中的一個故事。
教育“天平”上的鄉村學校
“征集一百萬位同志,創設一百萬個學校,改造一百萬個鄉村。”1926年,陶行知放棄大學教授的優渥待遇,發表《中華教育改進社改造全國鄉村教育宣言書》,著手普及平民教育的工作,掀起了一場席卷全中國的鄉村教育運動。
當時,晏陽初、梁漱溟等教育家都把目光投向了鄉村教育,希望通過教育農民,改進鄉村生活和推進鄉村建設。教育者們的躬身實踐,一定程度改變了局部地區農村教育的落后面貌,促進了教育觀念和思想的創新,但抗日戰爭爆發后,這些實踐未能繼續深入。
新中國成立后,鄉村教育有了穩定的發展環境,從掃盲運動到實現“兩基”(基本實施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農村教育由基本均衡邁向了優質均衡。
70多年,中國農村教育事業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鄉村教育落后的面貌得到徹底轉變,鄉村教育為社會建設培育了大量人才,闖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教育建設和人才培育之路。
但受制于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差距,鄉村教育仍是我國教育體系的短板所在。鄉村學校的命運牽動著公眾的心,尤其是在“撤點并校”政策的推動下,農村學校數量迅速減少甚至面臨著農村教育“終結”的威脅。
20世紀90年代以來,出生率下降使得鄉村學齡兒童減少,而城鎮化進程加快,農民大規模進城,農村學校生源進一步減少,師資也加速流失,教學質量出現下滑。由此形成了惡性循環,生源和師資流失,導致辦學質量下降,引發更多的家長“用腳投票”。
為追求規模效益,農村中小學校開始布局調整,一所所鄉村學校消失在“撤點并校”的大潮中。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育投資效益和教學質量,尤其是在教育經費相對緊缺的情況下,撤并學校對優化農村教育資源配置來說意義重大。
公開數據顯示,全國的小學數量從2001年的49萬多所減少到2020年的16萬余所,平均每天有45所小學消失,而這其中多數是農村小學。
大規模“撤點并校”也帶來了一系列問題。上學路途遙遠,學生及其家庭的負擔加重,甚至出現輟學率反彈。此外,遠距離上學路程導致的安全事故增多,尤其是校車事故頻發,更是引發了全社會的反思。而農村生源過度向城鎮集中,也加劇了城鎮學校教育資源緊張。在這樣的背景下,大規模撤并現象終結,農村中小學調整布局的指針,從效益撥向公平。
然而,即便眾多農村小規模學校的價值被重新肯定,面對生源減少的趨勢,如何合理布局農村教育資源仍然是擺在各地教育決策者面前的一道難題。
鄉村學校的價值
鄉村學校有著什么樣的功能?在我國教育體系中充當什么樣的角色?只有進一步理解這些如毛細血管般分布在廣袤農村的存在,我們才能理解鄉村學校的價值。
民國時期,陶行知、晏陽初、梁漱溟把發展鄉村教育作為鄉村建設的重點,踐行著“教育救國”的理想。而今天,鄉村學校的建設作為基本公共教育服務中不容忽視的一部分,承載著有關教育公平的夢想。
時至今日,許多生活在農村的群眾仍身處收入不高、社會經濟地位比較低的家庭,甚至很多家庭剛告別貧困。因此,鄉村學校的存廢及發展好壞,關系教育起點公平,更關系社會公平。要維系公平,首先就要保障這些農村孩子基本的受教育權利——就近入學,不讓他們輸在起跑線上,從而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
從基礎教育生態優化的角度來講,鄉村學校的辦學質量提升后,農民還是更愿意把孩子留在身邊,而不是舍近求遠把年幼的孩子送去城鎮讀書。江西弋陽、安徽宿松、山西鄉寧等地本著“窮縣也要辦教育”的理念,在農村小規模辦學點的教學資源、教師培養等方面大力投入,實現了令人驚嘆的大量農村生源回流,這不僅幫助農村孩子就近接受優質教育,也有助于化解周圍城鎮“大班額”問題。
此外,學校的狀況也是鄉村宜居的重要指標。從學校與鄉村發展的角度來說,鄉村學校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是農民進城、生源減少的結果;同時,鄉村學校的衰落乃至于“消失”,讓接受教育這一基本需求得不到滿足,又會進一步迫使農民離開土地,加劇鄉村空心化。而建設好鄉村學校,方便孩子就近上好學,滿足農民的基本公共服務需求,無疑可以增加鄉村的吸引力,為農村留住人才、吸引人才。
鄉村教育承載著傳播知識、塑造文明鄉風的功能,更是阻斷貧困代際傳遞、助力農村脫貧致富的基石所在,是鄉村振興的一個重要支點。
鄉村振興,教育先行。鄉村振興要靠人才,人才的培養要靠教育。吸引人才立足鄉村、扎根鄉村,并不容易。而通過高質量的鄉村教育,可以增進學生對于鄉土的文化認同、情感認同,培養他們服務鄉土、貢獻社會的愛鄉意識,這關系鄉村振興的長遠布局。
鄉村學校的瑯瑯書聲,是回蕩在廣袤田野上的空谷足音。而學校的消失,某種意義上是在抽離鄉村的文化之魂。發展鄉村教育是重振鄉村文化的需要,鄉村學校可以成為保護和推廣鄉村文化的重要載體。
一方面,挖掘和整理散落的鄉村文化要素,并將其融入鄉村學校課程中,使教學貼近學生的實際生活,拉近鄉村教育與鄉村社會的距離,增強學生的鄉土文化情感。另一方面,實現鄉村文化與現代文化的融合,激發鄉村文化的活力,進而從整體上推動鄉村精神文明建設。
廣東清遠的多所鄉村學校就將醒獅、排瑤刺繡、瑤族長鼓舞等項目融入學生的文體活動、技能培訓和德育活動,本土文化資源與現代教育的融合使得孩子們的校園生活變得豐富有趣,鄉土文化寶藏也“后繼有人”。四川蒲江成功踐行現代田園教育,在“以人為本”等現代教育理念的推動下,讓農村教育呈現出“回歸自然、回歸農村、回歸書院”的特質。
守護一方文化、振興一方鄉土,離不開人,離不開這方水土教育滋養出來的人。辦好鄉村學校,是為鄉村振興賦能蓄力。
鄉村學校會有新的春天
辦好高質量的鄉村教育,無外乎從硬件和軟件兩方面入手。
從硬件上講,近年來,鄉村學校的辦學條件不斷改善。尤其黨的十八大之后,中央財政每年投入幾百億元,用于改善貧困地區義務教育薄弱學校的基本辦學條件,兜住了鄉村教育發展的底線。而持續改善學校基本辦學條件,仍然是未來推動城鄉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的重點所在。
“最安全的地方是學校、最漂亮的建筑是校舍、最美的環境是校園。”不斷完善優化的辦學硬件設施為農村學校辦好優質教育、引回生源增添了底氣。在教學環境改善方面,許多幫扶團隊不僅出資出力,更是用心用情。如浙江省淳安縣富文鄉中心小學經過改建,有了五彩斑斕的閣樓城堡造型校舍,讓人仿佛置身童話世界;湖南大山深處的坪坦鄉中心小學,一間柴棚被巧妙改造成融入了千年侗族木構建筑技藝的“發光”書屋,成為當地孩子們“夢中的房子”。
從軟件上講,特崗教師計劃、鄉村教師支持計劃等系列政策全面推進,鄉村教師隊伍的水平和待遇顯著提升。今年4月,教育部等八部門聯合印發《新時代基礎教育強師計劃》,其中明確要求以中西部欠發達地區教師培養為重點,推動師資優質均衡配置,引導優秀人才向鄉村學校流動;針對教師待遇問題,還提出要落實補助政策、傾斜職稱評聘、加強周轉宿舍建設和住房保障。
不僅是待遇上要加強保障,還應支持鄉村教師的職業發展,讓更多鄉村教師獲得接受高質量教師培訓的機會,直面年輕鄉村教師的教學和成長需要,以更富前瞻性、更接地氣的職業培訓助力他們的專業成長;賦予鄉村學校充分的辦學自主權,讓鄉村學校具備不斷培養優秀教師的內生動力,這樣才能長久留住優秀教師。
地處偏遠地區、經費短缺、硬件條件差、發展規模受限、教師隊伍不穩定……這些都是鄉村學校發展的劣勢所在,也使得鄉村學校一度成為“小而弱、小而差”的代名詞。
但“小”其實也是一種優勢。對比城市中的學位緊張和“大班額”問題,鄉村小規模學校恰恰擁有開展小班化教學的先天優勢。正是因為學生少、班額小,這才便于精細化管理,便于教師因材施教,能讓每個孩子得到個性發展,讓特色教育得到更好實踐。甘肅崇信專門展開了農村小班化教學改革,以培養農村孩子的自信、自立、自強品格為核心,設計充滿活力的課程和課間活動,正因為班級規模小,孩子的音樂、美術、書法等興趣愛好得到了充分的關照和培養。
生活即教育,立足和取材于鄉村實際生活的鄉村教育可以將兒童從書本中解放出來,在自己熟悉的生活環境中對人、事、物形成獨到認識。鄉村學校可以利用身邊豐富的教育資源,幫助兒童累積生活經驗、提高生活能力,使教育內容和農村生產生活相融合。在北京九渡河小學,學校缺老師,于是校長招來了會做豆腐、剪紙、養魚的輔導員,甚至還有廚師,讓學生跟著他們學習。孩子們在這些課程中,掌握了生活技能,也通過各種活動學習了語文、數學等學科知識。
這些優勢恰是城市學校難以求得的,如果鄉村學校能夠找準定位,堅持“為農而教”,把豐富的鄉村資源轉化為育人資源,立足學校的本土特色發展,實現“小而美、小而優”并非不可能。
鄉村學校或許會減少,但鄉村學校不會消失。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一系列強有力政策的出臺和落地,以及一批批鄉村教育者的創新改革與潛心付出,鄉村學校將迎來新的春天,每個農村孩子都能站到光明未來的啟航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