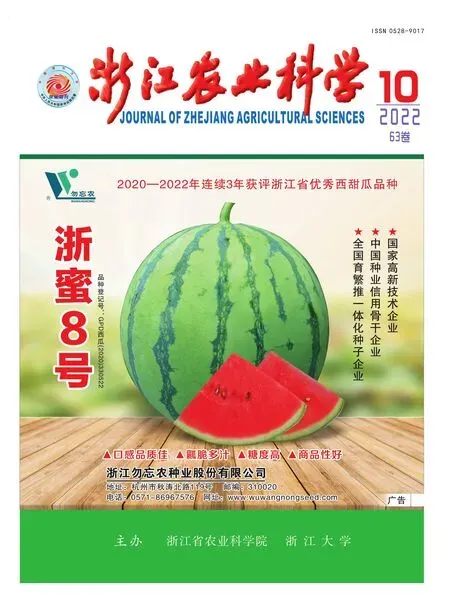南澳縣鄉村旅游村民感知效應的研究
潘麗輝, 嚴楠, 鄭殷岳
(汕頭職業技術學院,廣東 汕頭 515000)
鄉村旅游指的是以旅游度假為宗旨,以村莊野外為空間,以人文無干擾、生態無破壞、以游居和鄉野行為特色的村野旅游形式[1-3]。近年來,我國鄉村旅游發展方興未艾。2020年,近七成游客在一年內曾到城郊或省內鄉村旅游,五成以上游客近一年內多次到鄉村旅游,近兩成游客一個月內多次到鄉村旅游[4]。通過大數據推演預測,未來中國鄉村旅游熱還將持續10 a以上,2025年將達到近30億人次[5]。
從供給側來看,鄉村旅游已經成為鄉村產業的新亮點、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內生動力,對于解決“三農”問題,實現鄉村振興戰略具有重要作用。村民是決定鄉村發展的內生力量、鄉村旅游發展的直接利益相關者和重要參與者,其對鄉村旅游效應的感知是鄉村旅游產業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村民對鄉村旅游效應的感知影響其對發展鄉村旅游的態度、意愿。
1 研究區域選擇與概況
汕頭市南澳縣是一個海島縣,全縣農業人口占總人口近八成,農用土地面積占全縣土地面積超七成。全縣擁有豐富的鄉村旅游資源,當地政府堅持“以點帶面、軸線結合、連片開發、整體推進、覆蓋全島”的思路,大力規范發展多種模式的鄉村休閑旅游。近年來,南澳縣依托首批省級新農村示范片建設創建工作,持續推進鄉村環境整治,以生態宜居為抓手,補足基礎設施短板,全力打造廣東省生態宜居美麗鄉村示范縣,梯次打造生態宜居美麗鄉村示范村,全面掀起精美農村建設新高潮。鄉村旅游也在此基礎上蓬勃發展,南澳島慢生活鄉村路線入選“廣東省鄉村旅游精品線路”,村居體驗成為海島旅游新熱點。
2 研究設計與數據來源
2.1 研究設計
南澳縣鄉村旅游村民感知效應研究,主要采用訪談調研和問卷調查等方法進行。南澳縣鄉村旅游村民感知效應問卷內容:1)村民個人基本信息;2)村民對鄉村旅游效應感知;3)村民參與鄉村旅游情況。
村民個人基本信息包括性別、年齡、學歷、職業、家庭收入等方面的信息。量表設計借鑒了旅游扶貧效應測量量表[6-10],包含經濟效應感知、社會文化效應感知、生態環境效應感知三個維度。
村民對鄉村旅游效應的感知用鄉村旅游村民感知效應量表進行測量,量各維度分別設計了正面效應因子和負面效應因子進行測量。村民參與鄉村旅游行為主要包括政治參與、經濟參與、社會參與等維度[11-14],主要以村民參與本地旅游發展規劃的重要決策、參與旅游相關的培訓、參與旅游相關的行業合作組織、旅游相關收入占比等作為因子進行測量。
2.2 數據來源
調研小組于2020年9—10月到南澳島典型村鎮進行問卷調查。共計發放紙質問卷398份,其中無效問卷8份,累計回收有效問卷390份,有效率為98.0%。
2.3 被調查村民個人基本信息分析
從性別方面看,男性占53.6%,女性占46.4%,男性被調查者人數略多于女性。從年齡方面看19~49歲的村民占83.6%;≤18歲和>60歲的被調查者占比較少。從職業方面看,個體戶占比最高,其次是農民(漁民)事業單位或公務員。從受教育水平看,初中及以下學歷的被調查者占比26.7%,高中和中專學歷的被調查者占比35.9%,大專及以上被調查者占比37.4%。被調查者受教育程度水平高于我國村民平均受教育水平。從家庭年收入看,2萬~<4萬元占比24.4%,4萬~<6萬元占比23.8%,6萬~<8萬元占比21.5%,年收入≥10萬元較少(表1)。

表1 南澳縣村民社會人口學特征分析
3 鄉村旅游村民感知效應研究分析
3.1 鄉村旅游村民感知效應均值分析
本研究采用李克特5刻度制量表[15]對南澳縣鄉村旅游村民感知效應進行測量。參考前人研究成果,量表得分均值在3.5~5.0分表示感知較為顯著,2.5~3.4分表示中立,1.0~2.4分表示感知不顯著。
鄉村旅游村民感知效應的均值分析結果表明(表2):村民對旅游帶來的影響感知較為顯著;其中,經濟影響感知(3.74)最為顯著,其次為生態影響感知(3.64),最后為社會文化影響感知(3.55)。

表2 南澳縣樣本人口統計學特征分析
在旅游發展帶來的正面影響中,感知均值超過3.7的測量題項包括“增加了就業機會”(3.78)、“環境得到美化和綠化”(3.75)、“促進了對外交流與合作”(3.73)、“提高了家庭經濟收入”(3.70)。在旅游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中,感知均值超過3.7的測量題項包括了“生活成本提高”(3.91)、“物價上漲”(3.89)、“造成交通擁擠”(3.85)。
3.2 不同背景特征的村民對鄉村旅游效應感知差異分析
通過單因素方差分析法,分析不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家庭年收入等背景特征的村民鄉村旅游經濟效應、社會文化效應、生態環境效應因子感知差異。分析結果表明,不同性別特征的調查樣本鄉村旅游效應感知差異不顯著,不同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家庭年收入等背景特征的樣本對部分效應因子感知差異顯著。
3.2.1 不同年齡段的村民鄉村旅游效應感知差異分析
不同年齡段的村民對“增加了就業機會”“提高了家庭經濟收入”“加快了本地脫貧致富”“促進了對外交流與合作”“促進了歷史文化的保護和傳承”“環境得到美化和綠化”“造成交通擁擠”等7個效應因子感知具有顯著差異性。≤18歲村民“增加了就業機會”“提高了家庭經濟收入”等效應因子的感知均值高于其他年齡段村民感知均值;40~60歲村民對“加快了本地脫貧致富”,社會文化效應中“促進了對外交流與合作”“促進了歷史文化的保護和傳承”“造成交通擁擠”等效應因子的感知均值高于其他年齡段村民感知均值;>60歲村民對“增加了就業機會”等7個因子的感知均值均低于其他年齡段村民感知均值(表3)。

表3 不同年齡階段的南澳村民對鄉村旅游效應感知差異分析
3.2.2 不同教育程度的村民鄉村旅游效應感知差異分析
不同教育程度的村民對經濟效應中“物價上漲”“社會風氣變差”等效應因子感知有顯著差異。對比平均值,隨著教育程度越高,對“物價上漲”因子的感知均值更強,其中本科以上學歷對“社會風氣變差”的感知均值低于其他學歷層次村民(表4)。

表4 不同教育程度的南澳村民對鄉村旅游效應感知差異分析
3.2.3 不同職業的村民鄉村旅游效應感知差異分析
不同職業的村民對“物價上漲”“生活成本提高”等效應因子感知有顯著差異。對比平均值,其中“個體戶”與“退休人員”對“物價上漲”“生活成本提高”因子感知均值高于其他職業(表5)。

表5 不同職業的南澳村民對鄉村旅游效應感知差異分析
3.2.4 不同家庭年收入的村民鄉村旅游效應感知差異分析
不同家庭年收入的村民對“物價上漲”“生活成本提高”“造成交通擁擠”等效應因子感知有顯著差異性。對比均值,家庭年收入6萬元以上村民對“物價上漲”“生活成本提高”“造成交通擁擠”的感知均值高于平均值(表6)。

表6 不同家庭年收入的南澳村民對鄉村旅游效應感知差異分析
3.3 不同參與行為的村民對鄉村旅游效應感知差異分析
通過單因素方差分析法,分析參與本地旅游發展規劃的重要決策、參與旅游相關的培訓、參與旅游相關的行業合作組織、旅游相關收入占比等方面存在差異的南澳村民鄉村旅游感知效應差異。
3.3.1 不同程度參與本地旅游發展規劃重要決策的村民對鄉村旅游效應感知的差異
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表明,在參與本地旅游發展規劃等重要決策方面來看,村民的參與性一般,過半的被調查者沒有參加過。
不同程度參與本地旅游發展規劃重要決策的村民對“提高了家庭經濟收入”“加快了本地脫貧致富”“拉大村民之間的貧富差距”,生態環境效應中“動植物等生物資源得到保護”“環境得到美化和綠化”“噪聲污染嚴重”“造成交通擁擠”等效應因子感知具有顯著差異性。
對比均值,本人或家庭成員經常參與本地旅游發展規劃重要決策的被調查者對“提高了家庭經濟收入”“加快了本地脫貧致富”“動植物等生物資源得到保護”“環境得到美化和綠化”等正面效應因子的感知均值高于本人或家庭成員沒有參加過和偶爾參與的本地旅游發展規劃重要決策被調查者;對“噪聲污染嚴重”“造成交通擁擠”等負面效應因子感知均值低于本人或家庭成員沒有參加過和偶爾參與的本地旅游發展規劃重要決策被調查者(表7)。

表7 不同程度參與本地旅游發展規劃重要決策的南澳村民對鄉村旅游效應感知的差異
3.3.2 不同頻次參與旅游相關培訓的行為的村民對鄉村旅游效應感知的差異
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表明,在旅游相關培訓方面村民的參與性一般,調查樣本中沒參與過旅游相關培訓占比54.1%。單因素方差分析顯示,不同頻次參與旅游相關培訓的行為的村民對“生活成本提高”“水體得到保護和污染治理”“動植物等生物資源得到保護”“噪聲污染嚴重”“造成交通擁擠”等效應因子具有顯著差異性。對比均值,村民或家庭成員參加過相關培訓對正面影響“水體得到保護和污染治理”“動植物等生物資源得到保護”的感知效應比未參加過更高,對負面“生活成本提高”“噪聲污染嚴重”“造成交通擁擠”感知效應較低。因此,相關的旅游知識培訓有利于提高村民對鄉村旅游產業發展的感知效應與帶來正面的影響(表8)。

表8 不同頻次參與旅游相關培訓的行為的南澳村民對鄉村旅游效應感知的差異
3.3.3 不同程度參與旅游相關行業合作組織的村民對鄉村旅游效應感知差異分析
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表明,在旅游相關行業合作組織方面村民的參與性一般,調查樣本中沒參與旅游相關行業合作組織的村民總比57.4%。單因素方差分析顯示,村民參與旅游相關行業合作組織的行為情況對“居民的思想觀念進步”“改善了本地的道路和水利等基礎設施”“社會風氣變差了”“造成交通擁擠”等效應因子感知具有顯著差異性。對比均值,村民或家庭成員“參與2個旅游相關行業合作組織”的樣本對“居民的思想觀念進步”“改善了本地的道路和水利等基礎設施”等正面效應因子感知均值高于其他樣本;村民或家庭成員“參與多個旅游相關行業合作組織”的樣本對“居民的思想觀念進步”“改善了本地的道路和水利等基礎設施”“社會風氣變差了”“造成交通擁擠”等效應因子感知均值均低于其他樣本(表9)。

表9 不同程度參與旅游相關行業合作組織的南澳村民對鄉村旅游效應感知差異分析
3.3.4 旅游相關年收入在家庭收入中不同占比的村民對鄉村旅游效應感知差異分析
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表明,超七成樣本家庭收入中有與旅游相關的收入。單因素方差分析顯示,旅游相關年收入在家庭收入中不同占比村民對“增加了就業機會”“提高了家庭經濟收入”“加快了本地脫貧致富”“拉大村民之間的貧富差距”“促進了對外交流與合作”效應因子感知具有顯著差異性。對比均值,旅游相關的收入在家庭收入中占比越高的村民對“增加了就業機會”“提高了家庭經濟收入”“加快了本地脫貧致富”等正面效應因子的感知均值越高(表10)。

表10 南澳村民與旅游相關的年收入占比情況對鄉村旅游的感知效應的差異分析
4 小結
村民對鄉村旅游發展帶來的經濟、社會、生態效應感知均值分析表明:村民對鄉村旅游發展帶來的經濟、社會、生態效應感知都較為顯著,旅游業發展在給居民帶來了正面影響的同時,也給居民帶來了負面影響。在21題項中,排在前四位的正面影響題項是“增加了就業機會”“環境得到美化和綠化”“促進了對外交流與合作”“提高了家庭經濟收入”;排在前三位的負面影響題項是“生活成本提高”“物價上漲”“造成交通擁擠”。
單因素方差分析不同背景特征的村民在鄉村旅游效應感知方面的差異表明:不同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家庭年收入的南澳村民在對鄉村旅游的經濟效應、社會文化效應、生態環境效應的感知存在差異。從年齡特征來看,40~60歲村民對于正面效應因子感知均值高于其他年齡段村民,>60歲村民對正面效應因子感知均值低于其他年齡段村民。從受教育程度特征來看,隨著教育程度提高,對“物價上漲”等因子的感知均值更強。從職業特征來看,個體戶和退休人員對物價上漲等因子感知均值較為顯著,個體戶由于從事經營業務,對由于物價上漲引發的經營成本上升較為敏感;退休人員由于鄉村旅游發展帶來收入增量幾乎為零,因此對于“生活成本提高”等因子較為敏感。家庭年收入>6萬元村民對“物價上漲”“生活成本提高”“造成交通擁擠”的感知均值高于平均值;家庭年收入>6萬元村民和游客的需求和消費較為重疊。
單因素方差分析不同程度參與鄉村旅游發展的村民對鄉村旅游的經濟效應、社會文化效應、生態環境效應感知存在差異。參加過相關培訓的村民對“水體得到保護和污染治理”等環境保護正面效應因子感知均值比未參加過相關培訓的村民更高,對“生活成本提高”等負面效應因子感知均值低于未參加過相關培訓的村民。旅游相關的收入在家庭收入中占比越高的村民對“增加了就業機會”“提高了家庭經濟收入”“加快了本地脫貧致富”等正面效應因子的感知均值越高。
對于鄉村旅游的正面效應和負面效應,村民均能顯著感知,在鄉村旅游發展過程中,行政管理部門可著力研究如何強化正面效應,如何弱化負面效應。不同特征的村民對鄉村旅游效應感知存在差異,要關注不同村民群體的感知差異,為正面效應因子感知較為顯著的村民群體提供更多的參與渠道;為負面效應因子較為顯著的村民群體提供更多的保障措施;從政治活動、社會活動、經濟活動等方面為村民創造更多的參與機會,讓村民成為鄉村旅游主要供給者,切實受益者,忠誠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