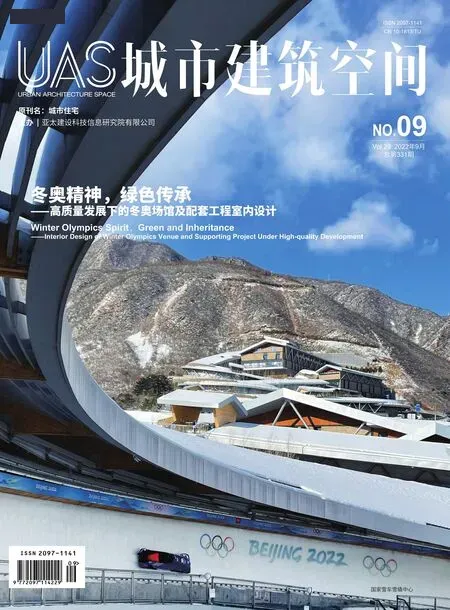以歷史文化網絡優化構建促進數字化建設策略研究*
文/南京信息工程大學藝術學院 高 原
0 引言
伴隨數字化城市的建設與發展,數字化助力城市歷史文化保護已成為一種必要的手段和趨勢,《“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國發〔2021〕29號)的頒布為數字化城市建設帶來更多可能。南京作為首批歷史文化名城,對其歷史文化保護與發展的數字化策略研究具有重要的引領作用與借鑒價值。數字化助力城市歷史文化保護的前提是從整體方法論的角度進一步優化現有歷史文化網絡架構,完善歷史文化網絡信息層面的全面構建。在構建與實踐下,提出“歷史文化網絡優化+數字化助力提升+協同組織”的模式。
1 歷史資源采集和創新統籌下的“織網”行動
針對歷史文化名城,吳良鏞院士提出整體保護設計理論,研究基于此將孤立散存的點狀和片狀結構整合為更具保護意義的網狀系統,參照歷史城市整體保護價值與特征類型,建立“基底-斑塊-廊道”的健康網絡層級,實現從歷史文化保護的斷裂結構到兼具多樣性與連續性的新系統構建。將城市空間分為3個維度,形成從社區、街道、城市的自下而上的序列網絡空間;從脈絡空間上建立3項串聯,圍繞自然與人文、建筑與環境、人居與記憶構建友好型城市形態;從傳統空間上構建3種綜合方式,進一步延續線性文化廊道下的文化旅游、公共服務與數字化賦能。通過增加多元觸點、激活歷史節點、提升脈絡關聯、平衡傳統與數字化比重等方式,構建新時代城市歷史文化網絡發展的新模式(見圖1)。

1 歷史城市保護“織網”架構(圖片來源:作者自繪)
2 社會參與和多元網絡協同下的可持續發展
歷史文化保護需要專家的前瞻性推送,又需要依靠社會和民眾的集體力量,重視城市發展中大眾社會共識培育、宣傳教育與公眾參與。在不斷完善由政府牽頭的法制規范、組織保障、財務支持、體制創新維度下,優化社會共識與保護活動機制的架構;借鑒HUL理念關注數字化建設保護和遺產可持續利用的多元思路,提出多維信息交互發展、人景互動、定制化與數字能力培養等創新參與式概念,通過信息服務向知識服務的助力轉化,探索具有城市特征的遺產信息服務模式和數據結構,實現更多元的網絡協同活動與可持續變化(見圖2)。

2 HUL理念下的系統發展模式(圖片來源:作者自繪)
3 數字化建設高位統籌下的一體化方案
在推進歷史城市網絡優化構建的過程中,建議南京注重數字化高位統籌、數據化系統推進,通過多重網絡化高效融合,圍繞歷史文化資源保護、政策協同管理機制、社區網格化下的公眾參與模式,貫通數字化服務網絡建設。充分發揮多元網絡架構下的協同性,突出數字化建設所帶來的利益相關者的主體地位,加強大眾在遺產地信息采集、整理和傳播過程中的參與度與貢獻度,促進城市歷史景觀遺產價值的延續和發展。
3.1 數字化高位統籌
在中央頂層設計的指導下,各級政府應關注新型智慧城市和數字化建設對于南京歷史城市保護與發展的重要價值與意義。站在全局發展的高度,以戰略思維、系統思維、辯證思維,通過統籌推動、協同優化城市公共服務,提升城市綜合管理服務能力。構建城市信息模型平臺和運行管理服務平臺,因地制宜地建設數字孿生城市,全方面推進數字化模式下歷史城市信息網絡的共建、共享及多元融合的發展格局,實現數字化助力發展的目標(見圖3)。

3 數字孿生城市下的數據模型框架(圖片來源:光輝城市產品手冊)
3.2 數據化系統推進
考慮南京歷史城市網絡優化構建的復雜程度,基于數字化信息服務,完善相關部門之間統籌安排、信息共享、工作聯動的協調機制,形成信息互通、力量互補、功能共享、手段綜合的高效模式;基于數字化建設的歷史城市數據信息的傳播與采集工作,發揮政府、高校、企業、群眾的個體優勢,從政策頒布、理論研究、技術研發、實踐驗證等層面出發,形成基于動態數據支撐的全域化視角下城市歷史信息的多維度界定與完善。
3.3 網絡化高效融合
在歷史城市保護與發展過程中,南京的城市化快速發展是導致其變化與重組的重要原因,在近40年的系統保護與規劃中,歷史信息、保護制度、發展模式已形成較為完整的體系與系統,但并非一成不變。目前,保護形態呈現變化大、多視角、全方位、動態化、多元化等特點,故應從動態化發展的視角看待歷史城市保護與發展問題。圍繞歷史基質與政策支撐的橫縱向網絡的構建以及自下而上的參與模式,以數字化手段作為鞏固、串聯、激活歷史城市保護與發展的科技方法與實踐手段,反哺現有模式根基,織補更加合理、高效的網絡模式,實現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
4 結語
數字化助力歷史城市文化保護需進一步踐行“歷史文化網絡優化+數字化助力提升+協同組織”的模式,深耕歷史資源,同時在時代發展中需要不斷完善保護與發展的理念及架構模式。以城市文化網絡協同構建的思路為基礎,以數字化技術助力為支撐,進一步引導社會參與和多元網絡協同下的可持續發展路徑,進一步推進歷史文化網絡構建織補與完善,激發自下而上的持久動力,形成數字化建設背景下歷史城市文化網絡構建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