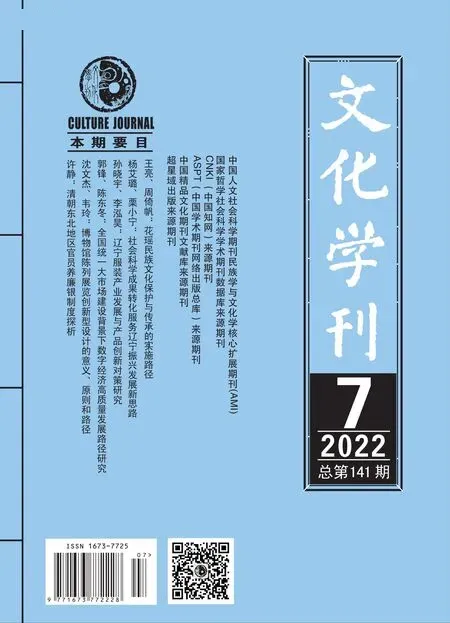試論格雷馬斯語義結構理論的自我突破
鄭麗凡
作為一門學科的符號學與作為一種方法的結構主義相結合,使得文學符號學獲得較大的發展。格雷馬斯將符號學引入敘事學,為敘事學的研究開拓了新思路,在結構敘事學的形成和發展方面做出了一定貢獻。與符號結構相結合的敘事學,受到了結構主義方法的影響,將研究重點聚焦在文本的敘事結構分析上,力圖排除結構之外的因素。然而在格雷馬斯的結構語義理論中,這種研究的重點卻同時展示了另一事實即他對原本被排斥在結構之外的其他因素也有所注目。通過對《結構語義學》和《論意義—符號學論文集》的研讀,可以從中分析歸納出他對結構之外的主要關注點,一是對社會文化這一因素的考慮;一是對價值的描寫。
一、對社會文化因素的關注
格雷馬斯認為詞匯學是一門能為人文學科提供強大理論工具和方法論工具的學科,因為詞匯學本身關注意義,他在《結構語義學》中力圖建構言語表現之前關聯意義類型及其發展的獨立層面,旨在從語義學方面證實風格學的脆弱以及辭格的紛雜和多余,在他這一階段的研究中,語義學代替了詞匯學,并且與某種詞匯語言學和符號學拉開了距離。[1]在《論意義》論文集中,他試圖進一步談論意義,符號學代替了語義學,將符號學與結構意義相結合。[2]通過對他的兩部著作的梳理和思考,可以發現在他對語義結構和意義的分析研究中,似乎并不能撇開作為外在的文化因素對結構意義的影響,即使只是一定程度上的影響,也沒有被格雷馬斯所忽略,且他對于敘事結構解釋的一些關聯模型,客觀上也適用于對社會文化的批評。這些與完整封閉的結構不相適應的部分,散見于他的理論著作中,在本文中只能針對一些比較突出的體現之處作相關的分析闡述。
在論及意義的基本結構時,為了盡量清晰地呈現形式與實體的關系,格雷馬斯首先對“關系”作了界定,“關系有時被視為語義軸,有時被看作義素接合。而對這一關系的分析所產生的結果遠遠超出了如何定義結構這一考慮。”[3]33也即是格雷馬斯在試圖展現形式與實體的關系之前就已經意識到這一結構所涉及的關系意義會超出結構本身。為了證明自己的這一觀點,他借用了葉姆斯列夫的關于色譜的經典例子。他認為語義軸極具普遍性,“可以斷言,它存在于所有的自然語言中,沒有色差的文化實難想象。”[3]33而且這種普遍性是與“文化”的因素相關聯的。他承認文化的差異性能夠影響形式與實體之間的關系。而且在這種具體不同的關系中,能夠給人提供辨別文化差異的依據。他借用英語和威爾士語的義軸上的義素結合比較來說明兩種文化的差異。“這些不同的義素接合無疑構成了色譜的特征,同時也構成了許多語義軸的特征,但它們不過是對世界所做的不同歸類,定義了一些文化和文明的特殊性。”[3]33格雷馬斯在此認同葉姆斯列夫的“內容形式(這類語言的接合方式)”和“內容實體(這類語言接合的語義軸)”的定義,因為他本人也關注到了文化文明的因子對結構意義的影響作用。甚至在他將符號學代替語義學之后也仍不忘在論語詞單位之前先將其置于一定的文化背景之下。如他在對論“憤怒”的詞義之前就預先設定了文化背景,“毫無疑問,我們描寫所依托的背景依然是法蘭西文化。超越文化的局限、建構普遍的模型之途徑和方法,則屬于另一個范疇的問題。”[4]229在語義結構的定義上也是如此,“關于語義結構,我們應把它理解為具有社會性和個體性(文化或個性)的、不同語義域的——給定的或僅僅是可能的——一般組織形式。”[4]36“于是,語義結構便像是一個虛擬的聯合體,但卻是一個窮盡了義素類別的聯合體,而語義實際用法和語義行為則相當于一些個性化顯現,顯現受到文化和個性形式的約束。因此,有可能采用兩種平行但卻不同的方法:a)探索開放的虛擬語義域,將其看作人類創造的各種可能性;b)描寫以往和現存的語義域,但這些語義域是實現了的并受約束的,它們覆蓋了人類的整個歷史維度和類型維度。”[4]38-39格雷馬斯顯然無法超越文化的局限來談論詞義并且將這歸于他所要探討的語義結構范疇之外的問題,他的論意義實際上無法獨立于文化系統之外,而是在文化和個性的限制之下的“意義”。
格雷馬斯在《真言契約》中首先提出了“逼真性”與社會文化背景之間無法隔絕的聯系。“逼真性似乎是話語投射在自身之外的一種具有評判性的參照,其對象是現實,準確地說是某種現實觀。這一術語的應用需要某種社會背景,其特點反映了一種對語言的態度,一種對語言與其外在現實之關系的態度。逼真性的概念必然具有某種文化上的相對性,因為它在地域和時間上對應于某個我們可以圈定的具體文化圈。”[4]106格雷馬斯接著談及因文化或時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詞類理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的語言意義理論沒有脫離對社會背景中文化內涵的考察。“逼真性”并不是一個絕對性的存在,而是一個建立在文化差異基礎上的相對性存在,當然也不僅是文化的差異所造成的相對性。因為“在給定的文化背景下,逼真性標準僅適用于某類話語,但各類話語間的界限難以確定。”[4]107可見格雷馬斯認為文化差異是影響逼真性的最基礎的一方面,同時,各類詞語的逼真性還要考慮在各類文化背景之上的人們對世界的認知能力的差異。“逼真性概念不僅是某個社會的文化產物,對它的把握需要長期的學習,而后才有可能認識世界之‘現實’,其基礎是某種成人理性。”[4]107“逼真性”概念的確立,在格雷馬斯這里與文化背景一直緊密相連。“文化背景變了,問題的性質也變了:話語是其他事物的表征,逼真性概念與這一話語觀緊密相連,那么想判定某一話語為‘真’,就必須提出一個疑問:真實話語本身的地位以及生產和消費它的條件。”[4]108話語本身的真實性確定必須考慮它在當前社會文化語境中的地位以及它產生和被消費的條件,很顯然這樣的話語并不是獨立的自足體,它的產生和意義離不開社會文化的土壤。
不論格雷馬斯如何進一步論及意義,作為前提之一,他都不忘語言結構體系之外的文化背景的前提。從個人話語到社會話語,一些“社會契約”的形成也是社會文化背景歷史變遷的產品。格雷馬斯在此引洛特曼的理論以作說明,“某些宗教性文本在中世紀被奉為金科玉律(被視為真理),但過了幾個世紀卻被當作文學性的東西(虛構的產品)來消遣,據說,這是因為社會文化背景的歷史變遷,因為文本被依次地納入到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此等闡釋假設文本自身是一個不變量,而受話者機制的內部卻發生種種變化,對文本的多樣性讀法就生自于此類外在于文本的變化。”[4]109文本自身結構不變,但是多樣性的讀法卻能讓文本在歷史文化的變遷過程中產生新的意義,這中新的意義的產生又離不開對文化的依賴。[5]隨著理論的層層推進深入,格雷馬斯的論題最終進入了文化符號學層面,他借葉姆斯列夫的思路,把符號看作是一種結合表達、內容之表意關系的產物,而符號又獨立于表達和內容的關系組合形式,依次推理出“我們所談的話語不過是一些復雜的符號,各文化對其符號所采取的‘態度’就是其內涵性的元表達符號學的闡釋。對該問題的反向推論是:并不是文化背景在對(宗教的或文學的)話語進行定義,恰恰相反,而是話語的內涵闡釋在對文化背景(即各類文化)進行定義。”[4]110由此格雷馬斯設想了一種理想的結構類型劃分,即根據各種認識“態度(他也稱之為符號)”——話語的各種內涵性闡釋。借此劃分根據需要來說明文化背景的時空嬗變,解釋具體文化格局中話語類型分布,雖然這種理想的結構并沒有實現,但是對它的設想表明格雷馬斯沒有遺忘文化背景承擔的角色。
此外,在討論真言問題的過程中,格雷馬斯進一步談到了“真實”與“確信”。“在我們生活的這個炒作的時代里,真實與確信、知與信之間的區別尤為明顯。致力于解構并揭示真話之建構程序的批判努力認為科學話語的基礎是意識形態,該努力或多或少獲得了成功,結果便是建立在近乎純粹的信則靈的基礎上的烏托邦話語的大盛行。信譽匱乏的社會里反而涌現出眾多盲目輕信的潮流,世人皆受騙于一些政治的、說教的、廣告的話語。關于知識中有許多陷阱的知識,也完全起不到解毒的作用。‘越荒謬越有人信’,這一從中世紀流傳至今的痛苦哭號,用在上述種種騙人勾當、超意識和無意識把戲身上倒是十分恰當,只是其中已沒有了痛苦的意味。”[4]116筆者認為格雷馬斯的這段論述雖然是為了圍繞“真言契約”而展開的,但同樣也適用于當下的文化批評。首先,他在此希望強調的是不相同的意識形態背景會對“信”的概念產生模棱兩可的影響;其次,自從中世紀至今(不僅是格雷馬斯完成此作的1970年,也意味著現如今的當下)“信”就是一個融“疑” 于一體的復雜概念;再次,在全社會范圍的認知范式下,意識形態的話語會對真言契約的兩個獨立部分知與信,真知與堅信都造成很大程度的影響;最后,對社會潮流的過度吹捧恰恰能說明一個社會的信的缺失。
二、對價值的描寫
在對結構語義進行描寫的同時,格雷馬斯也試圖對價值進行描寫,《結構語義學》一書中,他在敘事的轉換模型探索中對敘事的兩種解釋就明確涉及了關于價值的問題,并進一步在敘事的非時間性意義中論及了價值與契約(既定秩序)之間的關系。[6]在此先闡述他對敘事的兩種解釋:首先是敘事開頭和結尾作為兩個序列由兩個義素范疇組成,它們的形式或正或負:

“第一種解讀包括非時間性地感知以范疇形式出現的各組成項,并在兩個范疇之間建立關聯:
這就意味著:契約(既定秩序)的存在與契約(秩序)的不存在對應,如同異化與對價值的充分享用對應。”[4]307
第二種解讀考慮到了各組成項的時間性布局,故能將它們之間的關系看作蘊含關系:

“對此我們大致可作這樣的評論:在一個沒有法律的社會里,各種價值被顛倒了,價值的重建使法制有可能恢復。”[4]307

在《結構語義學》之后的《論意義—符號學論文集》中,格雷馬斯在探討意義問題之前,首先便論述敘述符號學的一個問題即價值客體。價值的語言符號身份首先是文化價值。“唯有把研究素材擴大到更為復雜的敘事上去,我們才有可能建立一份不說是全面至少是具有代表性的清單,里邊將收入被印歐文化圈放在第三功能神靈保護下的諸如愛情、健康、美貌、多子等基本價值。”[4]17格雷馬斯對“價值”表現出了極為關注的態度。“我們一直都是在語言學意義上來使用價值這個術語的,它一個約定的稱謂,涵蓋著一個無法言說的語義結構,其定義只能是否定的,即一個排除所有不是它的東西之后、落實在名為客體的句法板塊上的語義場。然而,對價值的這個定義雖說在符號學中具有操作性,卻沒有擺脫與它有關的價值論闡釋,比如說價值被定位在名為客體的區域,出場的目的是顯現客體,價值與主體發生關系。”[4]20他試圖在符號學中對價值作出描寫,從而將與“價值”有關的闡釋也帶入到對結構意義的探索當中,這無疑是格雷馬斯結構主義敘事學理論對結構體系的一種自我突破,并且自客觀上,格雷馬斯也擴大了他的敘事理論應用分析的范圍。
作為著名的結構主義敘事學家,格雷馬斯以符號模型來定義意義的基本構成模式,對結構和意義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他的理論體系不失嚴謹,但是在對結構和意義的論述過程中,格雷馬斯的考察因素中不時地涉及社會歷史文化的內容,這對于結構主義敘事學家而言,原本是與他們基本的理論主張即排斥符號文本之外的一切因素,是有所背離的,然而正是對封閉結構的突破讓敘事學獲得了新的發展,為后經典敘事理論埋下了伏筆,將敘事學的研究對象從文學擴大到各個人文科學領域,因此格雷馬斯結構敘事學理論自身的這種突破值得我們去關注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