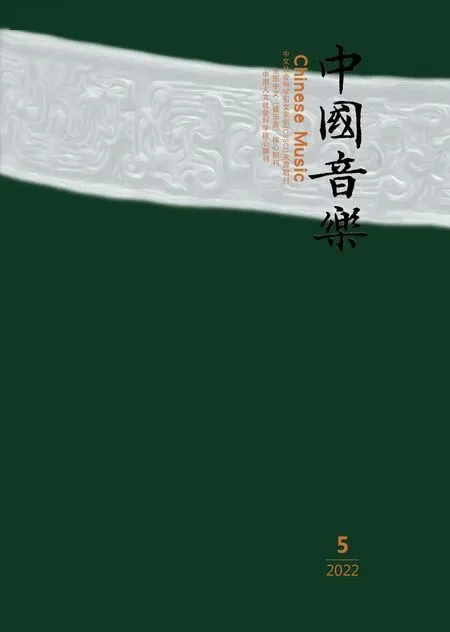從文本解釋到意義闡釋
——賈達(dá)群《第二弦樂四重奏:云起》研究
○ 鄭 艷
賈達(dá)群教授的《第二弦樂四重奏:云起》(后文簡(jiǎn)稱《云起》)是2016年受新西蘭“為弦樂四重奏而作的流動(dòng)的新音樂”項(xiàng)目委約創(chuàng)作的作品,全曲分為《漂浮的云》《山之聲》《流水情思》三個(gè)樂章。作曲家在樂譜前寫道:“云,流動(dòng)的水氣與塵埃之結(jié)合物,在浩瀚環(huán)宇的星空包裹并護(hù)衛(wèi)著脆弱的地球。它千姿百態(tài),變幻無窮,不僅映射出人類已知的燦爛圖景,還啟發(fā)著我們無限的想象聯(lián)覺。《云起》,或云與山水,既是云層山水意象之音響造型,又借云層山水態(tài)勢(shì)而言志抒情。”①賈達(dá)群:《云起(第二弦樂四重奏)總譜2016》,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19年,扉頁(yè)。作曲家既明確指出創(chuàng)作該曲時(shí)采用的序列音樂、音級(jí)集合、音色織體、多重結(jié)構(gòu)等具體作曲技術(shù),又揭示了其本人“對(duì)流動(dòng)行進(jìn)態(tài)勢(shì)速率的多維感知,抒發(fā)對(duì)云層山水風(fēng)姿意韻的諸多感悟,并通過對(duì)大自然的抽象表述來寄托自身的思緒情懷”②賈達(dá)群:《云起(第二弦樂四重奏)總譜2016》,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19年,扉頁(yè)。這一理念。作曲家在此提供了理解該作的豐富多元信息:一、作曲家本人對(duì)云的認(rèn)知;二、作曲家如何處理作品與云的關(guān)系;三、作曲家有關(guān)該作形式化程序的作曲技法提示;四、作曲家創(chuàng)作此作之目的與意圖的相關(guān)審美提示。通過分析與聆聽,其流動(dòng)的萬千線條、豐富的織體造型、斑斕的音響音色激起筆者對(duì)此作品進(jìn)一步分析與解讀的熱情。綜合作曲家提供的作品簡(jiǎn)介、樂譜音響、手稿設(shè)計(jì)等,筆者嘗試結(jié)合哲學(xué)詮釋學(xué)中有關(guān)“解釋”和“闡釋”的詞源范疇與意涵邊界,從其所指的視域與維度對(duì)《云起》展開研究。
一、哲學(xué)詮釋學(xué)中的“解釋”與“闡釋”
從詮釋學(xué)的角度展開音樂文本、音樂表演的研究已經(jīng)在音樂學(xué)界形成了豐碩的成果。在西方,“音樂詮釋學(xué)”這一概念最早由克雷茨施馬爾在其三卷本音樂評(píng)論文集《音樂廳指南》(1887—1890)的基礎(chǔ)上于1902年首次提出③陳新坤:《音樂詮釋學(xué)的三種意義取向》,《音樂研究》,2017年,第5期,第79頁(yè)。,經(jīng)舍林、佛勞洛斯、埃格布雷特、達(dá)爾豪斯、科爾曼、科恩、克萊默等人的發(fā)展④關(guān)于音樂詮釋學(xué)的發(fā)展歷程,具體可參見陳新坤:《論音樂詮釋學(xué)的起因、訴求與歷程》,《南京師大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7年,第6期,第129-136頁(yè)。,形成了一條成熟的學(xué)術(shù)研究道路。實(shí)證主義與詮釋學(xué)一般被認(rèn)為是音樂研究路向的兩大對(duì)立論域:實(shí)證主義強(qiáng)調(diào)對(duì)音樂史料、樂譜文本、作曲技法的客觀性考證研究,具有一定的封閉性特點(diǎn);詮釋學(xué)則突出從技術(shù)、文本到審美與思想的意義考察,具有更多的不確定性因素。本文嘗試回到哲學(xué)詮釋學(xué)的學(xué)術(shù)語(yǔ)境,通過把握其核心關(guān)鍵詞“解釋”和“闡釋”的概念、意涵邊界等理論基礎(chǔ),將這兩個(gè)關(guān)鍵詞直觀地勾連音樂分析的兩個(gè)維度,并做出進(jìn)一步思考:音樂研究中實(shí)證主義與詮釋學(xué)兩大視角是否有可能通過音樂作品這一載體在一定層面上相互融合,進(jìn)而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補(bǔ)性更好地實(shí)現(xiàn)對(duì)音樂的解讀、理解與研究?
從詞源學(xué)以及狄爾泰的《狄爾泰全集》、伽達(dá)默爾的《真理與方法》等著述中可以得知,“解釋”(interpretation)被界定為“說明”(erkl?rung)和“闡釋”(auslegung)兩個(gè)維度。中國(guó)哲學(xué)家洪漢鼎在《論哲學(xué)詮釋學(xué)的闡釋概念》一文中對(duì)其學(xué)術(shù)基本理論、基本問題、基本概念進(jìn)行了梳理與再反思,從概念史、本質(zhì)、指向、標(biāo)準(zhǔn)、方法五個(gè)層面明確了“詮釋”作為當(dāng)代哲學(xué)詮釋學(xué)核心概念的學(xué)術(shù)問題。通過詞源學(xué)以及《狄爾泰全集》中“erkl?rung”和“auslegung”兩個(gè)德文詞所用語(yǔ)境的考察,對(duì)《笛卡爾式的沉思》《邏輯研究》《存在與時(shí)間》《真理與方法》等著述的中文術(shù)語(yǔ)翻譯探討,洪漢鼎對(duì)“解釋”“說明”“闡釋”三者的意涵進(jìn)行了客觀的再界定。
洪漢鼎指出“erkl?rung”的意義是澄清、搞清,偏重于從原則或整體上進(jìn)行描述性的說明,其意義就是指這種通過方法概括和歸納法的解釋,是一種具有客觀性的、描述性的解說,因而這里的解釋具有“說明”(erkl?rung)的意味。⑤洪漢鼎:《論哲學(xué)詮釋學(xué)的闡釋概念》,《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2021年,第7期,第115;115;116頁(yè)。“auslegung”的詞義則具有“從某處把不明顯的、隱藏的東西闡發(fā)出來”的意味,因此,“auslegung”不是那種通過方法論和歸納法進(jìn)行客觀性和描述性的說明,而是偏重于從主體本身出發(fā)對(duì)事物進(jìn)行闡發(fā)性的和揭示性的解釋,⑥洪漢鼎:《論哲學(xué)詮釋學(xué)的闡釋概念》,《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2021年,第7期,第115;115;116頁(yè)。因而該德文詞被譯為“闡釋”更具合理性。
洪漢鼎認(rèn)為:“Interpretation(解釋)一詞的外延比Auslegung(闡釋)廣,它的意思應(yīng)偏中性,它既有客觀性的和描述性的說明(Erkl?rung)這一弱的意義,又有揭示性的和闡發(fā)性的Auslegung(闡釋)這一強(qiáng)的意義。… …Auslegung(闡釋)意思比Interpretation(解釋)的意思徹底,強(qiáng)調(diào)揭示性的和闡發(fā)性的更深一層意思。”⑦洪漢鼎:《論哲學(xué)詮釋學(xué)的闡釋概念》,《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2021年,第7期,第115;115;116頁(yè)。之所以將西方詮釋學(xué)中的核心關(guān)鍵詞進(jìn)行意義上的梳理與解讀,原因在于詮釋的過程與音樂分析有著諸多共通之處。我們可以將“基于作曲技術(shù)理論的客觀分析”與“解釋”相聯(lián)系,重在通過方法的概括和歸納法的解釋來分析文本;將“基于審美意象層面的意義解讀”與“闡釋”相聯(lián)系,重在闡釋作曲家通過作曲技術(shù)賦予作品的思想性與文化性。接下來筆者就從這兩大視域與維度對(duì)《云起》展開分析與研究。
二、《第二弦樂四重奏》文本分析與解釋
作曲家在樂曲前用文字明確標(biāo)明了該作所運(yùn)用的主要作曲技術(shù),即“序列音樂、音級(jí)集合、音色織體、多重結(jié)構(gòu)”。接下來筆者將聚焦該作的音高、節(jié)奏、織體、結(jié)構(gòu)等作曲技術(shù)理論問題,融入實(shí)證的方法,在文本視域下圍繞作曲家如何運(yùn)用作曲理論建構(gòu)樂譜這一過程展開解釋。
(一)基于四音列建構(gòu)不嚴(yán)格十二音序列的音高設(shè)計(jì)思維
第一樂章《漂浮的云》以一開始的四音列C-G-A-D為核心音型,通過音高的移位與變形、節(jié)奏的擴(kuò)大與縮小、聲部的模仿與對(duì)位等不同形態(tài)和手法貫穿全曲,并通過音色、速率、織體的多樣性描寫了漂浮的云的千姿百態(tài)。從構(gòu)成四音列的音高材料來看,作曲家強(qiáng)調(diào)相距大二度的兩個(gè)純四度音程的橫向結(jié)合,即“純四+大二+純四”,這一音高表述方式成為四音列的基本音高輪廓。更為有意思的是,作曲家通過對(duì)該四音列的移位與變形建構(gòu)起一個(gè)不嚴(yán)格的十二序列。
以第一小提琴為例,作曲家一開始用兩組四音列(C-G-A-D和B-#F-#G-#D)構(gòu)建起十二音序列的前八個(gè)音,并將第九個(gè)音落在#C這一長(zhǎng)音上,隨后,作曲家再次重復(fù)一開始的兩組四音列,之后加之在第3小節(jié)延展出的另外兩組四音列(D-A-B-E和#C-#G-#A-F)中的E、#A、F三個(gè)音,由此完成了一個(gè)完整十二音序列的建構(gòu)。(見譜例1)顯然,這是一個(gè)不嚴(yán)格的十二音序列。從橫向上來看,我們可以觀察到作曲家以四音列為材料,通過移位、變形等靈動(dòng)的藝術(shù)處理手法,生成一系列節(jié)奏相同、輪廓相似的四音列,最終從音高的層面完成了一個(gè)十二音序列的陳述。十二音序列僅僅是音高的基礎(chǔ)材料,作曲家賦予其無限的想象空間。
譜例1 第一樂章《漂浮的云》第1—7小節(jié)

就具體音高材料而言,作曲家強(qiáng)調(diào)了以五聲化音高素材建構(gòu)四音列的手法,旨在追求協(xié)和的音響效果。從縱向上來看,四件樂器在第1—4小節(jié)構(gòu)成不嚴(yán)格的模仿關(guān)系,如:一開始的四音列C-G-A-D(0,7,9,2)先在第一小提琴聲部出現(xiàn),隨后在中提琴、第二小提琴、大提琴聲部先后進(jìn)行模仿;第二個(gè)四音列B-#F-#G-#D(11,6,8,3)在第一小提琴聲部出現(xiàn)后則分別在大提琴、第二小提琴、中提琴聲部模仿。其不嚴(yán)格模仿的手法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gè)方面:1.模仿聲部的進(jìn)入位置頗為自如;2.作曲家對(duì)四音列中某一個(gè)音的時(shí)值進(jìn)行延長(zhǎng);3.通過插入材料或重復(fù)的手法對(duì)四音列進(jìn)行修飾。如:中提琴聲部第2—3小節(jié)中,作曲家先對(duì)第二個(gè)四音列B-#F-#G-#D(11,6,8,3)中的第二個(gè)音#F進(jìn)行延長(zhǎng),隨后插入第一個(gè)四音列,之后再回到第二個(gè)四音列,由此完成了對(duì)大提琴聲部的模仿。
聲部之間做不嚴(yán)格模仿的過程中,作曲家設(shè)計(jì)了“第一小提琴與中提琴”“第二小提琴與大提琴”兩對(duì)聲部在縱向上以小二度或大二度的關(guān)系形成碰撞,聲部進(jìn)入時(shí)有意在縱向上強(qiáng)調(diào)音響的不協(xié)和效果。第1小節(jié)中提琴進(jìn)入時(shí)以C音與第一小提琴的B音形成小二度的并置;第2小節(jié),大提琴進(jìn)入時(shí)以B音與第二小提琴的A音形成大二度的并置;第5小節(jié),四個(gè)聲部同時(shí)進(jìn)入,第一小提琴F音與中提琴G音構(gòu)成大二度,第二小提琴C音與大提琴D音構(gòu)成大二度。顯然,作曲家在作品的關(guān)鍵位置強(qiáng)調(diào)了不協(xié)和音響的“二度”關(guān)系,并在一定程度上賦予了“二度”的音響意義。
通過分析我們可以觀察到作曲家建構(gòu)音樂作品的材料、程序與過程。如果說十二音序列是作品音高邏輯的基礎(chǔ),那么五聲性的四音列則凸顯了材料的獨(dú)特性,“二度”關(guān)系則體現(xiàn)了作曲過程中不同四音列相連接的核心邏輯。
(二)音色織體與音響造型分析
織體是音樂元素被編織的外在形態(tài),所謂音色織體即作曲家在編織音樂元素的過程充分挖掘樂器的音色效果,通過開拓同一件樂器的不同演奏法、設(shè)計(jì)不同樂器音色的多元組合方式,來尋求有意味的音響與聲音,并時(shí)常以復(fù)調(diào)的方式讓獨(dú)具個(gè)性的聲音在空間中進(jìn)行分層、延續(xù)、擴(kuò)散乃至消失。
第二樂章《山之聲》就主要運(yùn)用了音色織體的寫作手法。作曲家將每一個(gè)單音用多種音色進(jìn)行表達(dá),一方面增強(qiáng)了聲音的多樣性,另一方面賦予了音響意象性的效果。以第1—8小節(jié)為例。在短短的八小節(jié)里,作曲家運(yùn)用了用弓拉奏、滑奏、人工泛音、撥奏等不同演奏技法,并規(guī)定了具體音高所應(yīng)拉奏的琴弦。(見譜例2)
譜例2 第二樂章《山之聲》第1—8小節(jié)

一開始大提琴奏出的旋律線條表達(dá)了“大山中的獨(dú)白”,核心音高素材為C-G。作曲家要求演奏員先在C弦(空弦)上用弓演奏長(zhǎng)音C,輔以漸強(qiáng)的力度記號(hào),隨后滑奏至G音,之后在兩音之間以滑奏的形式進(jìn)行徘徊;之后,C音在第3小節(jié)移高八度出現(xiàn),在G弦上奏出,并經(jīng)過第4小節(jié)的B音進(jìn)行至移高兩個(gè)八度的C音;第4小節(jié)的G音則沒有以滑奏的形式到達(dá),規(guī)定在A弦上演奏,緊接著第5小節(jié)的G音則以泛音的形式出現(xiàn)。第二小提琴和中提琴則表現(xiàn)了“大山中行走的腳步聲”,同樣以C-G為核心音高素材,作曲家通過撥奏和逐漸加密的節(jié)奏律動(dòng)表達(dá)了步伐的加快。整體而言,作曲家通過滑奏、人工泛音、撥奏等演奏法將相同的核心音高素材營(yíng)造出不同的音色效果,并將其編織于一體構(gòu)成音色織體,進(jìn)而表達(dá)了“山之聲”。
同時(shí),作曲家以視覺化的預(yù)設(shè)進(jìn)一步豐富織體的表達(dá)形式,將可視化的音樂輪廓轉(zhuǎn)化為織體的編織樣式,試圖在聽覺與視覺之間追求一種“音響造型”,以此作為建構(gòu)音樂作品的藝術(shù)表達(dá)形態(tài)。以第二樂章《山之聲》第19—24小節(jié)為例,作曲家以構(gòu)圖的方式設(shè)計(jì)了音高的輪廓與運(yùn)動(dòng)軌跡并形成一張視覺化的草圖(見圖1),具體形態(tài)為:第一小提琴與大提琴、第二小提琴與中提琴的運(yùn)動(dòng)軌跡均為鏡像倒影的關(guān)系,作曲家有序地設(shè)計(jì)了兩組樂器的運(yùn)動(dòng)軌跡,在旋律輪廓上呈現(xiàn)為不同維度上的平行進(jìn)行、反向進(jìn)行兩種形態(tài),進(jìn)而編織出一張視覺化頗強(qiáng)的藝術(shù)造型圖。作曲家基于該圖,將音高材料置入,并融入震音、顫音、自然泛音以及常規(guī)用弓拉奏、靠近琴馬演奏等演奏法形成的音響體,進(jìn)而以音響造型的方式厚實(shí)了音色織體的具體表達(dá)形式。

圖1 《山之聲》音響造型設(shè)計(jì)圖(第19—24小節(jié))⑧該圖是作曲家設(shè)計(jì)的結(jié)構(gòu)圖手稿。
從作曲家的手稿設(shè)計(jì)圖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四個(gè)聲部的起伏、對(duì)稱、交疊等具體形態(tài),事實(shí)上,這是作曲家借用“山”的具體形象形成的視覺化表達(dá),并通過四音組序列、鏡像倒影、音色織體等與之對(duì)應(yīng)的作曲技術(shù),將具象的視覺造型轉(zhuǎn)化為抽象的音響造型。需要指出的是,作曲家曾專業(yè)學(xué)習(xí)繪畫長(zhǎng)達(dá)八年之久,基于視覺藝術(shù)的聯(lián)覺轉(zhuǎn)換充溢于其音樂創(chuàng)作之中,其對(duì)“云”“山”“水”三個(gè)樂章主題內(nèi)容的寫作均融入了這一方式,這也成為作曲家重要的作曲技法之一。
(三)多重結(jié)構(gòu)形態(tài)分析
“多重結(jié)構(gòu)”是賈達(dá)群教授多年來音樂創(chuàng)作實(shí)踐的理論總結(jié),是其建構(gòu)音樂作品的主要策略,強(qiáng)調(diào)以“對(duì)位”的方式共時(shí)性地呈現(xiàn)不同層面的結(jié)構(gòu)類型。作曲家曾指出:“通過對(duì)多重結(jié)構(gòu)的觀察和研究,我們會(huì)發(fā)現(xiàn)作品中顯現(xiàn)或隱含的若干音樂事件,探究多重結(jié)構(gòu)相互之間的關(guān)系,我們會(huì)發(fā)現(xiàn)這些音樂事件是通過什么樣的方式得以關(guān)聯(lián)或通過某種關(guān)聯(lián)而形成他種結(jié)構(gòu),并以此引申或強(qiáng)調(diào)某種意圖的謀略。”⑨賈達(dá)群:《結(jié)構(gòu)對(duì)位之層級(jí)與類型》,《音樂研究》,2016年,第2期,第108頁(yè)。
第一樂章《漂浮的云》在宏觀結(jié)構(gòu)上主要運(yùn)用了變奏曲式與回旋曲式兩種結(jié)構(gòu)形態(tài),而在微觀層面,作曲家進(jìn)一步納入了“鏈?zhǔn)浇Y(jié)構(gòu)”(或稱“瓦式結(jié)構(gòu)”),作為建構(gòu)次級(jí)結(jié)構(gòu)的手法之一。如:排練號(hào)2開始的中提琴聲部就運(yùn)用了這一結(jié)構(gòu)形態(tài),具體特點(diǎn)體現(xiàn)在兩大方面:一、作曲家將該部分以兩小節(jié)或三小節(jié)為一個(gè)單位,將其分為五句,每一句均運(yùn)用了不同的音響體,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出上述論及的“音色織體”特征。第一句以十六分音符構(gòu)成的四音組和顫音音型為主,并運(yùn)用了靠近指板演奏、滑奏兩種演奏法;第二句則為靠近琴馬演奏的震音和人工泛音兩種音響形態(tài);第三句轉(zhuǎn)為常規(guī)的演奏法,并將原來的四音組音型變形為三音組或五音組;第四句將原來的四音組時(shí)值擴(kuò)大一倍,改為由上波音修飾的四個(gè)八分音符的組合,并運(yùn)用了常規(guī)、靠近琴馬和靠近指板三種演奏法;第五句則回到用常規(guī)演奏法的十六分音符四音組,具有收束之意味。二、句與句之間大都以休止符隔開,同時(shí),前一句的結(jié)束音又常常是下一句的起始音,體現(xiàn)出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瓦式特點(diǎn)。如:第一句與第二句用小字一組的C音連接,第三句與第四句用小字二組的C音連接。整體而言,“鏈?zhǔn)浇Y(jié)構(gòu)”體現(xiàn)了拼接的思維,與電子音樂的建構(gòu)手法具有相通之處,作曲家以不同的音響體表現(xiàn)云層的千姿百態(tài),匯聚于一體則展現(xiàn)了“漂浮的云”這一動(dòng)態(tài)過程。
根據(jù)作曲家的手稿設(shè)計(jì)圖可知,第二樂章《山之聲》采用了復(fù)二部曲式與三部曲式相結(jié)合的結(jié)構(gòu)原則。二部性與三部性如何融合于一體呢?作曲家的設(shè)計(jì)非常巧妙。從作品建構(gòu)的順序來看,作曲家先設(shè)計(jì)了一個(gè)帶再現(xiàn)的二部曲式,即圖2中的“aa|ba”,之后是另一個(gè)不帶再現(xiàn)的二部曲式,即“c-|ba”。從設(shè)計(jì)圖中可以看出,下方結(jié)構(gòu)圖中的“c-”是對(duì)上方結(jié)構(gòu)圖中“cac-”的簡(jiǎn)化(見圖2中筆者標(biāo)記的虛線方框與指示箭頭)。同時(shí),作曲家在設(shè)計(jì)圖中明確地用“=”表示了兩個(gè)二部曲式構(gòu)成的復(fù)二部曲式。因此,從這一視角看,該作品具有二分性的特征。然而,如果將“c-”視為與前后形成對(duì)比的結(jié)構(gòu)部分,該樂章又具有三分性的特點(diǎn),即首部A(aa|ba)、中部B(c-或c-|ba)、縮減的再現(xiàn)部A1(ba)構(gòu)成的三個(gè)部分,作曲家在結(jié)構(gòu)圖下方用小寫字母“a”“b”“a”進(jìn)行了標(biāo)記。由此,二分性與三分性以結(jié)構(gòu)對(duì)位的形態(tài)在此得到了融合,展現(xiàn)了作曲家提出的“天然結(jié)構(gòu)態(tài)”概念,是表層豐富的結(jié)構(gòu)樣態(tài)在深層結(jié)構(gòu)框架上的邏輯建構(gòu)。

圖2 第二樂章《山之聲》多重結(jié)構(gòu)設(shè)計(jì)圖⑩該圖根據(jù)作曲家設(shè)計(jì)的結(jié)構(gòu)圖手稿制作而成。
第三樂章《流水情思》則采用了奏鳴回旋結(jié)構(gòu)和拱形結(jié)構(gòu)兩種結(jié)構(gòu)形態(tài),二者同樣在宏觀結(jié)構(gòu)層面形成共時(shí)的對(duì)位形態(tài)。同時(shí),材料的擇取、力度的設(shè)計(jì)也均有其獨(dú)特的結(jié)構(gòu)思維。就材料而言,呈示部運(yùn)用了第一樂章的材料,展開部則主要運(yùn)用了第二樂章的材料,再現(xiàn)部則對(duì)第一、二樂章的材料進(jìn)行了綜合運(yùn)用,具有一種“分—分—總”的結(jié)構(gòu)思維;就力度而言,作曲家將三個(gè)部分設(shè)計(jì)為“弱—強(qiáng)—弱”的三分性結(jié)構(gòu),體現(xiàn)了“再現(xiàn)、回歸”的結(jié)構(gòu)思維。具體結(jié)構(gòu)形態(tài)如圖3所示。

圖3 第三樂章《流水情思》多重結(jié)構(gòu)圖?該圖根據(jù)作曲家設(shè)計(jì)的結(jié)構(gòu)圖手稿制作而成。
第三樂章的“呈示—發(fā)展—再現(xiàn)”結(jié)構(gòu)思維體現(xiàn)出黑格爾“正題—反題—合題”的三段式原則,在“否定之否定”中尋求統(tǒng)一,強(qiáng)調(diào)動(dòng)態(tài)的發(fā)展過程;拱形結(jié)構(gòu)凸顯了對(duì)稱、平衡的特點(diǎn),偏重于靜態(tài)的形式表現(xiàn)。二者正是在動(dòng)與靜這一對(duì)矛盾中辯證發(fā)展,形成其獨(dú)特的結(jié)構(gòu)樣式。作為國(guó)內(nèi)具有代表性的結(jié)構(gòu)主義作曲家,賈達(dá)群非常重視音樂創(chuàng)作中的結(jié)構(gòu)構(gòu)建方式,多元性、多維度及其相互的對(duì)位化幾乎在他的每一部作品中均有刻意的體現(xiàn)。多重結(jié)構(gòu)思維體現(xiàn)了個(gè)性與共性辯證發(fā)展的結(jié)構(gòu)原則,我們或許可以聯(lián)想到畢加索立體主義風(fēng)格的畫作,或者是蘇軾的詩(shī)句“橫看成嶺側(cè)成峰,遠(yuǎn)近高低各不同”,簡(jiǎn)言之,我們可以在不同的維度上看到不同的結(jié)構(gòu)形態(tài)。這與作曲家“萬物錯(cuò)綜復(fù)雜、相互纏繞的世界觀”“立體多維、全景觀照的審美觀”“多樣化結(jié)構(gòu)、多元化形態(tài)的創(chuàng)作觀”密不可分。可以說,“多重結(jié)構(gòu)”手法已經(jīng)成為賈達(dá)群建構(gòu)音樂作品宏觀結(jié)構(gòu)的代表性作曲理論。
三、《第二弦樂四重奏》意義闡釋
蘇珊·朗格指出:“藝術(shù)是人類情感符號(hào)形式的創(chuàng)造。”?葉松榮:《結(jié)構(gòu)詩(shī)學(xué):音樂分析學(xué)的審智之美》,《音樂研究》,2021年第6期,第136頁(yè)。這里的“符號(hào)形式”在音樂創(chuàng)作中涉獵音高、節(jié)奏、音色、織體、結(jié)構(gòu)等音樂元素的具體樣態(tài)以及它們之間構(gòu)成的內(nèi)在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作曲家在建構(gòu)音樂作品的過程中,賦予不同“符號(hào)形式”的內(nèi)在意義,是一種“主體性”行為;音樂分析者在解讀“符號(hào)形式”內(nèi)在意義的過程中,常常拓寬作曲家賦予作品意義內(nèi)涵的邊界,則是一種“主體間性”行為。正如賈達(dá)群曾論及的:“即便言及‘意義’,作品也不是把單一的意義施加于不同的人,而在于作品向單個(gè)的人表明各種不同的意義。… …音樂分析進(jìn)入作曲家的世界,指的是他(她)創(chuàng)造音樂形式的狀態(tài)和程序。至于該狀態(tài)和程序后面的精神世界,則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賈達(dá)群:《音樂結(jié)構(gòu)研究的詩(shī)學(xué)策略》,《藝術(shù)百家》,2014年,第4期,第133頁(yè)。伽達(dá)默爾在1931年寫的教授資格論文《柏拉圖的辯證法倫理學(xué)——〈菲萊布篇〉現(xiàn)象學(xué)解釋》導(dǎo)演中,明確寫道:“人們可以嘗試這一悖論:作為歷史文本的解釋(Interpretation),它要闡釋性地理解(Auslegend verstehen)歷史文本中那種不言而喻的東西。”?同注⑤,第117頁(yè)。
上述作曲技法分析中,我們已經(jīng)圍繞音樂本體形態(tài)進(jìn)行了所謂“元素或結(jié)構(gòu)前的分析與解釋”。接下來,筆者結(jié)合賈達(dá)群在此作中運(yùn)用的音級(jí)集合、音色織體、多重結(jié)構(gòu)三大作曲技術(shù),從建構(gòu)的過程對(duì)其意義進(jìn)行闡釋,嘗試以“主體間性”的立場(chǎng),以自己的淺見論及該作的思想性與文化性特征,進(jìn)而在解釋者和文本相融合的視域下完成“意義闡釋”,或稱為“建構(gòu)過程或結(jié)構(gòu)后的詮釋”。
(一)關(guān)于音高材料設(shè)計(jì)的意義闡釋
從作曲家有關(guān)音高材料的具體設(shè)計(jì)手法來看,我們可以提煉出幾條客觀的邏輯原則:一、橫向上突出五聲性的音響效果,如第一樂章一開始的兩組四音列(C-G-A-D和B-#F-#G-#D)分別建構(gòu)于C宮調(diào)式和B宮調(diào)式之上。二、縱向上突出二度關(guān)系的音響碰撞,主要體現(xiàn)在第一樂章聲部之間模仿與對(duì)位時(shí)強(qiáng)調(diào)的大二度或小二度音程關(guān)系。在此,我們對(duì)音樂作品的音高邏輯形成確定性解釋的同時(shí),也值得我們?nèi)ニ伎甲髑屹x予這一音高邏輯形式的意義。接下來,筆者將在音樂文本分析與解釋基礎(chǔ)之上,結(jié)合對(duì)作曲家的訪談嘗試作出回答。
首先,在橫向?qū)用妫髑野l(fā)揮了五聲音階原本的意義與功能,因該音階不含有小二度,一般被貼上協(xié)和音響效果的標(biāo)簽。作曲家將五聲音階視為單純、純潔的象征,并用其指代“個(gè)體”,將音響的協(xié)和寓意為社會(huì)各層關(guān)系的和諧,進(jìn)而表達(dá)了個(gè)體在發(fā)展過程中無拘無束的自由與和諧之勢(shì)。其次,在縱向?qū)用妫髑医栌谩岸汝P(guān)系”的不協(xié)和之意,將不同聲部的縱向結(jié)合指代為一個(gè)“集體”,不同個(gè)體的對(duì)位、模仿構(gòu)成對(duì)話關(guān)系,個(gè)體在集體中的“各抒己見”則形成不協(xié)和的音響效果,進(jìn)而將二度關(guān)系隱喻為一種對(duì)立。可以說,作曲家以具有一定邏輯關(guān)系的音高材料表達(dá)了個(gè)人與集體、協(xié)和與對(duì)立的矛盾。
除此之外,作曲家在音樂發(fā)展中進(jìn)一步探索了二度音程的修辭性角色,用以感嘆人生無常。作曲家將這個(gè)不協(xié)和的因素作為一種符號(hào)的象征,置于音樂發(fā)展的過程,以不同的姿態(tài)對(duì)音樂進(jìn)行修飾。以第二樂章《山之聲》第38—53小節(jié)為例,作曲家將每一小樂句的最后兩個(gè)音均設(shè)計(jì)為下行的二度關(guān)系,并且以滑奏的演奏法進(jìn)行連接。具體呈現(xiàn)形態(tài)為:第一個(gè)音為長(zhǎng)音,常用兩個(gè)十六分音符構(gòu)成的裝飾音對(duì)其進(jìn)行修飾。如:第一小提琴聲部中第38—39小節(jié)的長(zhǎng)音G接近三個(gè)四分音符的時(shí)值,第41小節(jié)的C音和第42小節(jié)的F音均為三個(gè)八分音符的時(shí)值,我們能夠感受到第一個(gè)音被有意拖長(zhǎng)的效果,正如人們?cè)诖笊街泻艉皶r(shí)的起音;第二個(gè)音時(shí)值較短,且以滑奏進(jìn)入,則如人們?cè)诖笊街泻艉皶r(shí)的落音。(見譜例3虛線方框內(nèi)的音型)
譜例3 第二樂章《山之聲》第41—42小節(jié)
從譜例3可以看出,置于句尾的“滑奏下行二度音程”在此具有了符號(hào)的象征意義,我們可以從旋律的橫向發(fā)展中感受到一句接一句的嘆息之聲,同時(shí),聲部之間在縱向上相距一個(gè)四分音符有規(guī)律地先后進(jìn)入,正是以聲部模仿的手法營(yíng)造出大山中的回聲效果。作曲家形象地描寫了山中的歌唱,仿佛是將自身置于大山之中詠嘆出的“山的悲歌”。
(二)關(guān)于音色織體與音響造型的意義闡釋
作品的標(biāo)題《云起》源于王維《終南別業(yè)》中的詩(shī)句“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shí)”,從詩(shī)句的字意而言,描寫的是“走到水的盡頭就坐看行云變幻”的情境,實(shí)則刻畫了一位隱居者的形象。作曲家借用其詩(shī)句,將詩(shī)意內(nèi)容置入作品之中,并通過有組織的音色織體與音響造型形成賦有內(nèi)涵意義的表達(dá)。
首先,作曲家通過織體描寫云層,借用云層暗指人生,以云層的變幻莫測(cè)傾訴了人生的跌宕起伏。云層是多變的、夢(mèng)幻的,作曲家通過音響的不同造型將云層的特點(diǎn)描寫至極致:以織體的厚薄表現(xiàn)濃與淡,以主題材料的呈現(xiàn)音區(qū)表現(xiàn)高與低,以實(shí)音與泛音的不同演奏法表現(xiàn)實(shí)與虛,以變換的流動(dòng)速率表現(xiàn)動(dòng)與靜,給人以無限的想象空間。創(chuàng)作此作時(shí)正值作曲家事業(yè)軌跡發(fā)生變動(dòng)的階段,其以豐富多變的織體形態(tài)隱喻了復(fù)雜的各束社會(huì)關(guān)系,善與惡、名與利,一切均在包羅萬象的云層中顯現(xiàn)。
其次,作曲家突出四音組的節(jié)奏變形和半音關(guān)系的“音程游移”兩大作曲技術(shù),以此隱喻流動(dòng)的云與水,一方面呼應(yīng)“為弦樂四重奏而作的流動(dòng)的新音樂”這一委約主題,更重要的是借此表達(dá)作曲家當(dāng)時(shí)的寫作心境。節(jié)奏原型為四個(gè)十六分音符,作曲家在寫作過程中將其變形,時(shí)而打破原有的律動(dòng),時(shí)而將其中一個(gè)音符延長(zhǎng),時(shí)而轉(zhuǎn)為三個(gè)十六分音符構(gòu)成的三連音與一個(gè)八分音符的組合,等等。“音程游移”(見圖4)則突出基于某一個(gè)音向上或向下半音關(guān)系的偏離,根據(jù)對(duì)作曲家的訪談可知“這一技法源自四川的方言”?引自筆者對(duì)作曲家的采訪,訪談時(shí)間:2021年8月17日,地點(diǎn):上海。關(guān)于該技法的詳細(xì)分析與論述也可見鄭艷:《“傾聽之眼”還是“觀景之耳”?——賈達(dá)群〈漠墨圖〉中的聲景研究》,《音樂藝術(shù)》,2019年,第1期,第107頁(yè)。,筆者認(rèn)為,運(yùn)用該技法建構(gòu)的音響在此作中具有“音樂化的嘆息之聲”之社會(huì)人文含義。

圖4 節(jié)奏變形與“音程游移”設(shè)計(jì)手稿?該圖根據(jù)作曲家手稿制作而成。
最后,作曲家借用“坐看云起時(shí)”這一主體性行為表達(dá)解脫與釋放的心境。一方面,作曲家以超然的態(tài)度接受社會(huì)中的諸多現(xiàn)實(shí);另一方面表達(dá)了作曲家作為社會(huì)中的個(gè)體,佛性、隨緣的立場(chǎng),是其精神層面的升華。這也呼應(yīng)了作曲家的哲理思想:“人怎樣想,就怎么做,形隨意轉(zhuǎn),意隨心轉(zhuǎn)。”?賈達(dá)群:《結(jié)構(gòu)詩(shī)學(xué)——關(guān)于音樂結(jié)構(gòu)若干問題的討論》,上海:上海音樂學(xué)院出版社,2009年,第11頁(yè)。如果說第二樂章《山之聲》是作曲家在大山中的呼喚與感嘆,那么第三樂章《流水情思》則是其精神層面的灑脫、釋放以及對(duì)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欣然接受。
新音樂學(xué)家蘇博特妮可在闡釋音樂與社會(huì)的聯(lián)系時(shí)談道:“音樂和社會(huì)功能之間有親密的關(guān)系… …這是為什么任何特定的音樂都是以它特定的方式闡明一些基本的概念,這也是獲得對(duì)其本質(zhì)特征洞察的依據(jù)。”?黃宗權(quán):《走向新闡釋與尋求新意義——“新音樂學(xué)”的音樂分析與闡釋觀探析》,《音樂研究》,2013年,第6期,第55-56頁(yè)。在實(shí)證分析基礎(chǔ)之上,本部分有關(guān)音色織體與音樂造型的意義闡釋,可以讓我們體察到該作的社會(huì)性與文化性特征。
(三)關(guān)于多重結(jié)構(gòu)的意義闡釋
“音樂結(jié)構(gòu)的邏輯規(guī)律和程序使聲音產(chǎn)生了意義,音樂結(jié)構(gòu)的詩(shī)性功能闡釋又形成了一整套既開放又復(fù)雜的‘語(yǔ)法系統(tǒng)’,通過這套系統(tǒng),音樂的結(jié)構(gòu)才得以被構(gòu)筑、被演繹、被認(rèn)知,其意義才有可能被理解、被升華,甚至超越。”?同注?,第134-135;135頁(yè)。接下來,筆者將借鑒賈達(dá)群《音樂結(jié)構(gòu)研究的詩(shī)學(xué)策略》中的“詩(shī)性”問題對(duì)該作的多重結(jié)構(gòu)進(jìn)行意義闡釋。
“詩(shī)性”強(qiáng)調(diào)“每一個(gè)結(jié)構(gòu),每一個(gè)充溢形式感的瞬間都極具審美意義”?同注?,第134-135;135頁(yè)。。該作在微觀層面運(yùn)用“鏈?zhǔn)浇Y(jié)構(gòu)”凸顯不同音響體的拼接,正是在音樂結(jié)構(gòu)的邏輯規(guī)律和程序?qū)用嫱瓿闪司哂幸欢ㄏ笳饕饬x的聲音呈現(xiàn),即表達(dá)云層的瞬間變化。根據(jù)作曲家的手稿可知,作曲家賦予作品詩(shī)性意義體現(xiàn)在結(jié)構(gòu)層級(jí)的建構(gòu)過程中,一個(gè)主題、一個(gè)瞬間均充滿著詩(shī)意,體現(xiàn)了作曲家的思想發(fā)展過程。以第二樂章《山之聲》為例,第一部分A(a-b-a)中,作曲家以三個(gè)形容詞和一個(gè)動(dòng)詞表達(dá)了音樂的明暗色彩與運(yùn)動(dòng)形態(tài),并輔以視覺化的圖形,分別是:明亮的(bright)、流動(dòng)(flow)、灰色的(grey)和黑暗的(dark),這些色彩性的詞語(yǔ)正是作曲家通過音樂所要描寫和表達(dá)的情感。中間部分(c)下方則寫著:“由a延伸出來一首山之歌謠,同質(zhì)或模仿chant”(見圖5)。顯然,c由a延伸而來并被作曲家賦予圣詠般的特質(zhì),可以說,這是作曲家的一種文化性寫作,他將圣詠的“肅穆、節(jié)制,最大地排除世俗的感性欲念”這一特質(zhì)注入自己的音樂,構(gòu)成其獨(dú)特的詩(shī)性表達(dá)。與第一樂章中借“漂浮的云”描寫“坐看云起時(shí)”的主體性行為相比,該樂章是其精神升華的又一詩(shī)性表達(dá)方式,作曲家欲借助圣詠遠(yuǎn)離喧囂的社會(huì)。從這一視角來看,作曲家以文字或圖像的形式將音樂預(yù)表達(dá)的內(nèi)容與意義在手稿中進(jìn)行預(yù)設(shè),作品建構(gòu)過程的每一瞬間均充溢著作曲家的思想與詩(shī)性。

圖5 第二樂章《山之聲》第1—53小節(jié)設(shè)計(jì)圖?該圖根據(jù)作曲家手稿制作而成。
作曲家對(duì)于該作的宏觀結(jié)構(gòu)設(shè)計(jì)秉持了其原創(chuàng)的結(jié)構(gòu)理論——多重結(jié)構(gòu)(或稱結(jié)構(gòu)對(duì)位),將不同的結(jié)構(gòu)原則置于同一作品,使作品具有了多解性的特征。如第一樂章中,作曲家運(yùn)用變奏曲式與回旋曲式兩種結(jié)構(gòu)思維,一方面凸顯變奏曲式的核心主題“以不變應(yīng)萬變”的貫穿發(fā)展特征,另一方面則突出回旋曲式中主部不斷回歸、插部不斷更新,二者在對(duì)立中呈現(xiàn)螺旋上升的結(jié)構(gòu)發(fā)展原則。再如第三樂章中,作曲家運(yùn)用奏鳴回旋曲式與拱形結(jié)構(gòu)兩種結(jié)構(gòu)思維,一方面體現(xiàn)了德國(guó)哲學(xué)家黑格爾“正題—反題—合題”的三段式發(fā)展原則,另一方面彰顯了至臻完美的對(duì)稱性與平衡性的特點(diǎn)。在此,變奏、平衡、對(duì)稱、再現(xiàn)等在作品中具有了更深層的結(jié)構(gòu)意義,既是一種形態(tài)樣式的展現(xiàn),也可被領(lǐng)悟?yàn)槭挛锇l(fā)展過程中賦予其思想性的一種人生態(tài)度。多重結(jié)構(gòu)既是作曲家賦予作品的個(gè)性樣態(tài),同時(shí)也為分析者提供了可闡釋的巨大空間。
高為杰先生提及:“優(yōu)秀的音樂作品總是兼具主體性(即作品的個(gè)性)和主體間性(即作品的可交流性)的。”?高為杰:《書序五則——賈達(dá)群:〈結(jié)構(gòu)詩(shī)學(xué)——關(guān)于音樂結(jié)構(gòu)若干問題的討論〉序》,《中國(guó)音樂》,2014年,第4期,第149頁(yè)。“主體性”強(qiáng)調(diào)了作為作曲家身份的音樂創(chuàng)作行為,“主體間性”則突出了作為音樂學(xué)/音樂理論家身份的音樂分析與詮釋行為,高先生尤其指出了二者兼具才是優(yōu)秀的音樂作品。楊燕迪教授也曾提出“以音樂作品中所體現(xiàn)的作曲家創(chuàng)作構(gòu)思‘立意’為中心參照點(diǎn)”,他認(rèn)為這是可以“有效分析和闡明作品的藝術(shù)特征、突出特點(diǎn)、創(chuàng)作意圖和文化內(nèi)涵”的重要途徑。?楊燕迪:《音樂作品的詮釋學(xué)分析與文化性解讀——肖邦〈第一即興曲〉作品29的個(gè)案研究》,《音樂藝術(shù)》,2009年,第1期,第75頁(yè)。關(guān)于“立意”的論述可見楊燕迪:《音樂理解的途徑:論〈立意〉及其實(shí)現(xiàn)(上)(下)——為慶賀錢仁康教授九十華誕而作》,《黃鐘》,2004年,第2、3期,第4-8、52-58頁(yè)。本部分是基于具有實(shí)證色彩的作曲技術(shù)理論客觀分析之上形成的意義闡釋,筆者嘗試基于作曲家的“立意”,把握一定的限度,以“主體間性”的角色完成對(duì)該作的意義闡釋,并從中挖掘了作品的思想性、文化性與社會(huì)性。
結(jié) 語(yǔ)
筆者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基礎(chǔ)之上,嘗試跨越實(shí)證主義與詮釋學(xué)對(duì)立的鴻溝,將實(shí)證的文本解釋與主觀的意義闡釋進(jìn)行有邏輯、有指向的勾連,從研究范式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借鑒了哲學(xué)詮釋學(xué)與“新音樂學(xué)”的理論基礎(chǔ)。關(guān)于如何把握闡釋的方法與邊界,我們可以再次從哲學(xué)的學(xué)術(shù)語(yǔ)境中得到啟發(fā):伽達(dá)默爾提出了“視域融合”的路徑,即解釋者、文本、當(dāng)下情景三個(gè)視域的融合,強(qiáng)調(diào)歷史與現(xiàn)實(shí)、解釋者與被解釋者之間的匯合。洪漢鼎對(duì)此解釋道:“文本的意義既不可局限于原作者的意圖或文本的原意,同時(shí),文本也并非完全開放的系統(tǒng)任由理解者或解釋者按其所需而任意詮釋。”?同注⑤,第138頁(yè)。音樂詮釋學(xué)研究的突出代表克萊默認(rèn)為:“意義沒有一個(gè)中心點(diǎn),也非一成不變,而是一個(gè)相互聯(lián)系的網(wǎng),它在詮釋的過程中不斷展開,可在任何地方發(fā)生,詮釋學(xué)的解釋根本不能被系統(tǒng)化和學(xué)科化,而僅僅追求它所發(fā)現(xiàn)的東西,‘它更像一種姿態(tài)而非實(shí)體’。”?同注④,第133頁(yè)。音樂分析亦是如此,把握客觀層面的作曲技術(shù)理論分析與主體間性的審美意象解讀是解讀與闡釋音樂作品的兩個(gè)維度,進(jìn)而在“看(文本)、聽(音響)、說(意義)”中達(dá)到“視域融合”。本文從以上兩個(gè)層面對(duì)賈達(dá)群《第二弦樂四重奏:云起》展開研究,一方面對(duì)序列設(shè)計(jì)、音色織體、多重結(jié)構(gòu)等作曲理論形成了客觀的解釋分析,另一方面對(duì)這些技術(shù)理論表達(dá)的思想內(nèi)涵進(jìn)行了有限度的意義闡釋。筆者認(rèn)為,這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詮釋學(xué)“視域融合”在音樂分析中的有效實(shí)踐。因此,立足“文本解釋”與“意義闡釋”兩個(gè)維度,融入實(shí)證的方法,在“視域融合”中解讀音樂作品或許能夠?yàn)橐魳贩治鎏峁┮粭l可靠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