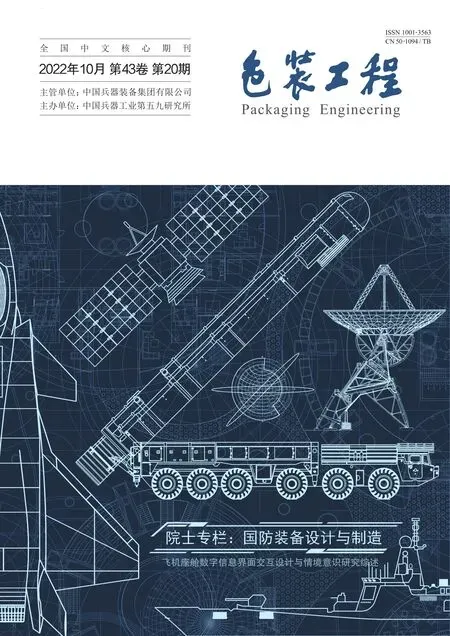飛機座艙數字信息界面交互設計與情境意識研究綜述
周海海,張哲睿,蔡林峰,王延斌,陳黎,張嵐云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 機電學院 工業設計系,南京 210016)
隨著飛機機載計算機的數據處理能力和多模態交互技術的不斷發展,飛機座艙數字界面的人機交互設計及其觸發飛行員情境感知,引起了國內外人機交互領域學者的關注。尤其是未來空戰將會面臨更為復雜和極端惡劣的戰場環境,需要在多維立體環境條件下執行多平臺、多任務的高度信息化作戰式樣[1]。飛機座艙人機界面作為飛行員與飛機之間進行人機對話和信息交換的媒介,飛行員需要與座艙的顯示與控制系統(顯控系統)進行交互,以此來獲取飛機的狀態信息和周邊態勢信息。由于飛行環境多變,任務困難度高,信息顯示界面往往存在信息密度大、結構關系復雜的問題,飛行員不僅需要對數據信息進行逐一讀取,還需要結合當前飛行任務,進行綜合判斷并做出決策。由于數字化顯示在飛機座艙的應用使人機界面信息的呈現方式及內容相較于傳統顯示方式有了巨大差異,操作者的角色從手動控制者轉變成監控者和決策者,需要一系列認知與交互行為來執行飛行與作戰任務。因此,運用人機交互設計技術優化飛機座艙人機界面的交互設計,提升飛行員的情境感知能力就顯得尤為重要。
1 飛機座艙人機交互界面的發展
飛機座艙人機交互界面的發展主要經歷了3 個階段:以機械顯控為主的物理人機界面;以電子顯示器和數字屏幕顯控為主的2D 數字界面;基于AR(增強現實)、VR(虛擬現實)、MR(混合現實)等技術(統稱XR 技術)的新型虛擬增強型人機交互界面,見圖1。
早期飛機座艙顯控系統以機械式儀表、操作桿和操作按鈕為主,因此,該階段的人機交互界面可以稱作物理人機界面。物理人機界面的特點是,因技術限制,只能以操縱桿、實體按鈕、實體開關進行信息輸入,以物理實物形式的指針、數字刻度盤、數字滾輪進行信息輸出。例如,飛機可以通過機械式儀表感知外界的氣壓,并將其數值轉化為飛機的高度和速度數值,并用儀表指針在刻度盤上指示出來[1]。二戰時期的P-51 野馬戰斗機座艙的機械顯示儀表已經超過10個,座艙的信息顯示和控制開始變得復雜。
在20 世紀40 年代至70 年代,飛機座艙顯控系統由電子顯示器和綜合控制系統共同形成。隨著電子綜合顯示儀表的出現,飛機座艙的人機交互界面產生了顯著的改變。機械按鈕和開關在這一階段是主要的信息輸入手段,電子儀表盤則是進行信息輸出。20世紀80 年代,CRT 顯示器被引入飛行儀表系統中。為了改變儀表越來越多使飛機駕駛員認知負荷提高的問題,在全面進入2D 數字屏幕界面階段后,飛機座艙只有少數的傳統機械儀表被保留,大部分的飛行信息數據都由計算機分析后再在主飛行顯示器(PFD)上顯示出來,這種獲取信息的方式大大增強了飛行員駕駛的安全性。平視顯示器(HUD)是飛機座艙人機交互界面的另一種形式。HUD 可以減少飛行技術誤差,在低能見度、復雜地形條件下向飛行員提供正確的飛行指引信息。隨著集成化和顯示器技術的不斷進步,20 世紀末至今,飛機座艙有著進一步融合顯示器、實現全數字化界面的趨勢。例如,我國自主研發生產的ARJ21 支線客機、C919 民航客機,其座艙的人機界面設計均采用觸控數字界面技術代替了大部分的機械儀表按鈕[2]。
20 世紀70 年代,美軍在主戰機上裝備了頭盔顯示系統(HMDs),引發了空中戰爭領域的技術革命。在虛擬成像技術成熟后,利用增強現實(AR)技術可以直接將經過計算機運算處理過的數據和圖象投射到駕駛員頭盔的面罩上。例如,美國F-35 戰斗機的飛行員頭盔使用了虛擬成像技術,將計算機模擬的數字化信息數據與現實環境無縫融合,具有實時顯示和信息疊加功能,突破了空間和時間的限制。
20 世紀90 年代,美國麥道飛機公司提出了“大圖像”智能化全景座艙設計理念,之后美國空軍研究實驗室又提出了超級全景座艙顯示(SPCD)的概念,充分調用飛行員的視覺、聽覺和觸覺,利用頭盔顯示器或其他大屏幕顯示器、交互語音控制系統、AR/VR/ MR 系統、手/眼/頭跟蹤電子組件、飛行員狀態監測系統等,把飛行員置身于多維度的顯示與控制環境中。此外,在空間三維信息外加上預測信息的時間維度功能也是未來座艙顯示器的發展趨勢[3]。2020 年,英國宇航系統公司發布了一款第六代戰斗機的概念座艙,去除了駕駛艙中所有的控制操作儀器,完全依靠頭盔以AR 形式將操作界面顯示出來。由上述分析可知,未來基于XR 環境下的虛擬增強型人機界面將成為飛機座艙人機交互的全新途徑之一。
在學術界,有關飛機座艙人機交互界面的研究也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其中代表性研究成果見表1。

表1 飛機座艙人機交互界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Tab.1 Representative research results of human-machine interface in aircraft cockpit
2 飛機座艙數字信息界面設計相關研究
2.1 座艙數字界面信息表征設計研究
當數字化信息界面引入飛機座艙,飛行信息的視覺表征設計便成為飛機座艙人機交互設計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飛機功能越復雜,飛行數據的信息量就越大,對信息表征的設計要求就越高。國內外有關飛機座艙數字界面的信息表征設計研究以數字界面信息的架構與層級化、信息的頁面布局與視覺編碼元素,以及界面的視覺風格統一為主。
在界面的信息結構上,仇岑等[20]提出了生態界面設計方法,利用抽象層級分析人機界面的工作領域,并提出數字界面信息圖形化、可視化設計的原則。Michalski 等[21]研究了圖形對象(圖標)的計算機屏幕界面設計及其分組(圖表結構)的幾何設計特征對人機交互的任務效率的影響。李珍等[22]基于座艙布局需求,提出了以提升人機功效為目標的飛機座艙顯控設備布局設計,從駕駛員操作舒適的角度得到各類設備在座艙空間中的尺寸約束,結合駕駛員生理需求對座艙空間進行分區,提高了人機交互效率。
在界面的圖符元素上,任宏等[23]應用層次分析法(AHP),建立了飛機座艙界面信息元素(文字字體、標記形式、符號形狀、字符色彩)的辨識度評價體系,發現三角形的符號形狀辨識度較高,黃黑和綠黑是辨識度最高的信息與背景的色彩搭配。王國軍[24]研究了人用視覺來認知和處理信息的過程,描述了數字界面的信息元素由顯示界面到駕駛員的傳遞全過程,給出了典型任務下的數字界面設計流程。張磊等[12]研究了飛機座艙顯示界面的編碼方式,得出腦力負荷大小會影響文字編碼方式。同時顏色的編碼差異十分顯著,其中紅色和黃色適合作為需要準確認知信息的編碼,淡綠色和黃色適合需要快速認知信息的編碼,藍色不適合用作編碼方式。張慧姝等[25]利用匹配測試和排序測試對圖符設計進行了實驗,得出紅色實心的三角形圖符適合用于識別敵方飛機,藍色或綠色實心的圓形圖符適合用于識別友方飛機,黃色實心的方形圖符適合用于識別不明飛機的結論。因此,在設計圖符時應該更注重識別性的優劣,而非僅僅考慮美觀和功能。
在視覺的風格統一上,范瑞杰等[26]對人機數字信息界面設計的一致性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表明一致性設計在人機界面設計中可以降低飛行員的認知負荷,從而提高飛機駕駛的安全性和效率。張德斌等[27]提出飛機座艙人機交互界面應采用友好直觀的設計、有序的儀表布置及和諧統一的色彩。數字界面的布局、顯示的內容、時間和信息量都對人機功效有很大的影響。牛亞峰[28]研究了數字界面的腦機交互和腦電評價方法,提出了數字界面視覺元素的腦電實驗范式設計,對數字界面利用ERP 腦機交互進行整體和局部實驗的評價方法及數字界面視覺元素的評價指標進行了實例驗證。Nakajima 等[29]使用了雙任務方法進行了實驗,得出頭盔顯示器比移動設備需要更多的腦力負荷,在視覺風格統一的基礎上,再使用音頻通知系統可以有效降低認知負荷。田筱越[30]根據飛行任務和視覺認知建立了符合數字界面顯示規范的注意力分配模型,優化了數字界面的視覺效果,使駕駛員能夠更舒適地與數字界面交互,并更準確地認知數字界面輸出的信息。
本研究團隊基于某型號空中加油機后艙人機界面設計項目,針對飛機數字界面信息表征中的視覺立體化特征、視覺動效特征與認知負荷的關聯開展了系列研究,提出了可控認知負荷水平下的飛機座艙人機界面設計原則,見圖2。


圖2 某型號空中加油機后艙人機界面設計研究Fig.2 Design research on human-machine interface of the air tanker back-cockpit of a certain model
綜上所述,近些年有關飛機座艙數字界面信息表征設計的研究,主要從飛行員認知特性與人機界面設計要素兩個視角進行研究。對于復雜信息界面設計,信息的視覺設計直接關系到用戶認知,不僅要考慮界面美感、秩序感,還要從用戶認知的視角考慮整體人機界面的邏輯架構、前后關聯與一致性,從而提升人機界面的使用體驗和可用性。
2.2 座艙數字界面設計中的認知工效研究
飛機座艙數字界面在飛機操縱時的人機信息交流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飛行員從數字界面中獲取的視覺信息占所有信息的80%以上[31]。當信息界面和操作邏輯的復雜性提高,便會增加飛行員的認知負荷,從而產生飛行安全隱患,而簡潔高效的數字界面設計則會提高飛行員識別信息的效率。美國航空航天局設計了一種NASA 任務負荷指數(NASA–TLX)量表[32],用于評價任務的腦力負荷。NASA–TLX 量表分別從腦力需求、體力需求、時間需求、努力度、受挫度和績效水平六個維度對飛行員的腦力負荷進行評估,從而發現人機界面設計的問題。
陸崑等[33]采用績效測量法,主觀評價法和生理測量法,研究得出腦電、心電和眼動指標都可以較準確地反映飛機座艙數字界面腦力負荷變化特性,提出了與NASA–TLX 量表判別準確率接近的雙生理測量指標綜合評估模型。Wilson[34]應用多種心理和生理指標分析飛行員的心理負荷,并進行了眼動測量實驗,得出在認知負荷較大、視覺要求較高的飛行段,飛行員眨眼率會下降,任務難度和信息加工負荷會影響飛行員瞳孔直徑大小。柳忠起等[11]將飛行員的視覺信息源劃分為座艙內和外景兩個區域,并利用眼動實驗證明外景區域有更多的注視點和注視時間,客觀地反映了飛行員飛行過程中注意力的分配規律。Wei 等[35]結合飛機座艙界面顯示系統的設計評估,討論了心理負荷測量方法的研究進展與局限性,并指出了飛行員心理負荷評估的未來發展趨勢。曹恩龍等[36]分析了人機工效對座艙人機界面的設計要求,并結合了飛行員的實際操作需求,提出了可以有效降低飛行員認知負荷的顯控界面設計準則。姚施琪[37]設計了可應用于HMDs界面的飛機座艙數字界面動效方案,運用基礎動效手段的組合,表達出常見的態勢反饋動效,有效降低了飛行員在態勢感知過程中的認知負荷。Liushang 等[15]為預測飛行員在不同顯示界面和任務下的態勢感知變化,提出了一種定性分析和定量計算的聯合態勢感知模型,并根據ACT-R 理論分析并驗證了飛行員對情境要素的認知過程。
本研究團隊基于某型號大型運輸機座艙數字畫面優化設計項目,對飛機主飛行界面(PFD)、燃油、飛控、空投等40 多個界面進行了優化設計,并邀請5名飛行員(南京航空航天大學飛行學院學員)開展了認知工效測試實驗,融合了被試眼動、腦電、操縱行為數據,對優化設計頁面進行了評估,驗證了設計的有效性。見圖3。

圖3 基于多模態數據的飛機座艙數字界面認知工效研究Fig.3 Research on cognitive efficiency of cockpit digital interface based on multimodal data
總結以上有關飛機座艙數字界面設計的認知工效研究,主要采用主觀心理量表和客觀生理數據測量相結合的方法評估飛行員的認知工效。數字界面的交互邏輯、設計元素、布局架構均會對飛行員的認知工效產生影響,屬于影響認知工效的外部因素。同時值得注意的是,飛行員本身的認知結構、工作記憶也會對認知工效產生影響,屬于內在和相關認知負荷。多維的影響因素對認知工效的研究帶來了挑戰。如何通過信息界面的優化設計降低認知負荷、加強態勢感知、提高飛行員信息認知效率仍是未來該領域重點研究的課題之一。
2.3 座艙數字界面設計中的認知體驗研究
隨著飛機功能的日臻完善,以飛行員為中心,優化座艙的人機設計和飛行員的操縱體驗,逐漸被研究者們所關注。作為飛機座艙人機設計模塊之一的數字人機界面,關系到飛行員的心理活動和認知效率乃至安全。田馨[38]基于體驗設計理論,分析了體驗設計的理念,提出實用功能需求,感官設計需求,交互設計需求,情感設計需求這4 條體驗設計的應用需求,以及通用航空飛行器體驗的三個主要體現方面:功能體驗,感受體驗,參與體驗。陳甜甜[39]運用感性工學的方法研究飛機顯控界面系統,結果表明感性工學在小型飛機顯控界面設計領域具有包容性和合理性,可以有效提高設計的科學性和客觀性,優化了飛行員的用戶體驗,對小型飛機座艙顯控界面引入新的設計思路。劉昕[40]構建了新型混合感性工學模型,采用改進BP 神經網絡和改進粒子群實現布局優化的方式,建立了感性意象到設計元素的映射關系,提出了座艙內人機交互設計的新方法,有助于解決飛機座艙此類復雜艙室的設計問題。
以VR/AR/MR 為代表的XR 技術逐漸應用到飛機座艙的虛擬人機界面設計,飛行員通過虛擬界面控制飛機全局,其操作飛機過程中產生的臨境感是飛行員感知自己身處虛擬環境的一種主觀體驗,也是評價虛擬交互模擬真實交互環境有效性的重要指標之一。在全數字化、虛擬化界面的發展趨勢下,飛機座艙數字界面的臨境感逐漸成為飛機駕駛員操縱體驗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國軍事研究所的Bob G. Witmer 等[41]于1992 年首次提出了臨境感的概念,并于1998 年設計了一種用于評價臨境感的“WS–PQ(Presence Questionnaire)”問卷,定義了臨境感為處在某個地點或者環境的主觀感受,即使物理上實際處于另一個地點或環境。周榮剛等[42]從生理指標、行為指標、心理物理學、主觀評價和績效等方面衡量了對臨境感的測量方法,結合了人機交互和系統論的觀點將影響臨境感的因素分為系統因素(主要指計算機設備)、用戶因素(個體差異)和交互因素(反饋、預期、信息交互的感覺通道和交互方式)。Daniel Paes 等[43]比較了沉浸式和非沉浸式虛擬環境的三維感知和臨境感,展示了沉浸式設計的認知益處。黃藝華[44]基于可用性概念框架,提出了虛擬現實臨境感設計過程中的基本原則是可理解性和高效性,空間臨境感是由部分感知知覺的設計要素給予用戶身臨其境的體驗,自我臨境感的設計核心是用戶的精神集中狀態和對內容的信任度。Slater 等[45]研究了虛擬環境中臨境感的概念,提出了個人的主導表征系統會影響他們的臨境感,而這種臨境感與堆疊深度有關。
在XR 環境下的虛擬增強型界面,臨境感作為評價虛擬環境中用戶體驗的一個重要指標而逐漸受到重視,目前的臨境感主要評價方法有主觀評價和生理指標評價兩種。而在未來虛擬增強型的座艙環境下,飛行員情感體驗和臨境感的研究將更加富有意義,從而帶動飛機座艙人機界面用戶體驗的不斷提升。
3 飛機座艙人機交互中的情境意識研究
情境意識[46](situational awareness,SA)是人因研究的方向之一,它是最早被航空心理學提出的一個概念,是指操作員感知特定時間和空間內的動態環境因素,并根據其對相關因素的認知和理解,做出對環境變化的預測和對應操作。根據澳大利亞運輸安全委員會的調查研究表明,70%航空安全事故由人為因素導致,而其中涉及SA 的占85%[47]。由此可見,SA不僅在航空安全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也是飛機座艙交互設計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3.1 個體情境意識與系統情境意識相關研究
1995 年,美國的空軍科學家Endsley 首次提出了SA 的概念,并提出了信息加工三層次模型[46]。他將SA 劃分為三個層次,分別為感知層(感知當前環境)、理解層(理解當前所處環境中的要素)、預測層(在理解的基礎上,根據自身的經驗和判斷,預測未來的情境狀態并作出決策),三個層次逐層遞進,見圖4a。
針對航空領域的復雜情況,考慮到并非個體情境意識單獨作用,Endsley 進一步提出了系統情境意識模型[46],模型揭示了更多影響SA 形成過程的因素,見圖4b。首先,每個人獲得SA 的能力都與其自身的能力、工作經驗和訓練時長有關。此外,任務前的預期和目標也會影響SA 的過程。而從系統角度看,飛機座艙傳達所需信息的能力,任務的工作量、壓力及復雜度都與獲得SA 的過程息息相關。

圖4 個體情境意識與系統情境意識相關研究Fig.4 Research on the relevance of individual and systematic situational awareness
經過20 多年的發展,系統情境意識模型已經越來越多地被應用在飛機座艙信息界面的設計研究當中。如周穎偉[47]通過研究光照、顏色與字符大小對飛行員操作績效的影響,建立了高情境意識水平的界面信息表征參考,以系統情境意識模型作為設計指導,以探索如何降低操作界面的認知負荷,符合飛行員的認知習慣;基于Wickens 信息處理模型與情境意識理論,曾效良[48]建立了新的飛機座艙信息界面設計策略,以此為指導的座艙界面改良設計提高了飛行員在靜暗座艙環境中的情境意識水平和操作績效;舒秀麗和蔣浩[49-50]則通過分析導致低情境意識水平的原因,使用觸摸交互局部代替實體操作單元,降低了飛行員的腦力負荷和空間壓力。
綜上所述,情境意識理論不僅被應用于飛機座艙界面交互設計的后期評估,也更多作為理論指導,指導座艙界面前期的開發設計工作。通過運用系統情境意識模型,分析飛機座艙環境、座艙界面的各類元素和操作方式對飛行員感知、理解和預測的影響,能在系統層面降低操作的復雜度,降低飛行員的認知負荷和心理壓力,從而提高情境意識水平和操作績效,避免了界面交互設計中過多的主觀設計成分,減少界面設計開發過程中的迭代修改,從而更好地指導復雜系統數字界面交互設計,提升界面的使用體驗和人機工效質量。
3.2 情境意識測量與評估方法研究
飛行員通過處理大量的飛行信息并做出決策,而情境意識水平能夠直接反映飛行員操縱飛機的信息認知績效,因此,情境意識水平的測量也引起了眾多學者的關注。根據文獻梳理,情境意識測量主要分為定量測量和定性測量兩類方法。
3.2.1 情境意識評估的定量方法
此類方法通過對比被試對環境要素的理解認知和周圍環境的真實狀態,直接評估被試的情境意識水平。主流的測量方法有[51-53]記憶探查測量法、作業績效測量法及生理測量法等。
3.2.1.1 記憶探查測量法
記憶探查測量法中常用到回溯測試、實時評估和凍結提問3 個子方法,以不同時間間隔喚醒被試,通過其對情境狀態的理解和記憶來回答相應的問題,以回答結果作為評估相應時段情境意識水平的依據。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方法有:SAGAT 情境意識全面評估技術(Situation Awareness Global Assessment Technique)、SACRI 情境意識控制室清單(Situation Awareness Control Room Inventory)、SAVANT 情境意識驗證和分析工具(Situation Awareness Verification and Analysis Tool)等。
通過SAGAT 測量飛行員的SA,并比較SA 與其心理運動追蹤測驗成績之間的相關性,Endsley 與Bosltad[54]發現SA 與心理運動測驗之間的相關性系數為0.72。因此,Endsley 等認為優秀的心理運動能力可以讓被試將節約的注意資源用于SA 感知,從而提高了情境意識水平。而Liu[15]等創新地將ACT-R(思維的自適應控制,理性)理論用于解釋SA 形成的過程,并通過SAGAT 技術驗證了其合理性。
3.2.1.2 作業績效測量
作業績效測量法的主要評估指標為被試的任務操作績效。其通過任務完成質量的好壞來間接評估情境意識水平的高低,一般作為情境意識測量中的輔助測量指標。Endsley[55]將作業績效測量法分為3 類:整體測量法、外部任務測量法和嵌入任務測量法。整體測量法僅僅關注整體任務的績效。而外部任務測量法一般通過除去或改變顯示器上的信息,記錄被試對除去或改變的信息作出反應的時長,以此為評價被試情境意識水平的依據。但這種測量方法易受干擾,此外,考慮到被試即使注意到信息的變化也不一定會立即反饋的情況,測量結果的準確性也會大打折扣。嵌入任務測量法則是通過評估次任務的完成水平來評價被試的SA。
3.2.1.3 生理測量
與作業績效測量法一樣,生理測量一般作為輔助方法,輔助評估被試的情境意識水平。它一般通過腦電、皮電、眼動數據等生理參數關聯相應的認知加工過程,以此評價操作者的情境意識層次。在Vidulich[56]的研究中對比了在高低不同情境意識水平情況下被試生理數據的不同(其中一種顯示界面有助于被試獲得保持良好的SA,相反,另一種則不利于SA 的獲得)。通過記錄12 名被試在模擬的空對地戰斗飛行任務中記錄腦電與眼動數據,發現在低水平SA 情況下,被試的腦電θ波的活動水平較高,α波的活動水平較低,而眨眼時間短,頻率高。
3.2.2 情境意識評估的定性方法
定性測量情境意識水平主要由實驗被試自身評估,因此,評價量表的合理性是情境意識水平測量結果能否擺脫主觀化和差異合理泛化的保證。目前主流的評價量表有[51-53]:里克特7 點量表工具、CARS 成員意識評級量表(Crew Awareness Rating Scale)、MARS 任務感知評級量表(Mission Awareness Rating Scale)、3 維SART 量表(Situation Awareness Rating Technique)及10 維SART 量表等。這些主觀評價量表主要可分為兩類:自我直接評估和自我對比評估。自我直接評估即讓被試評估自己的SA,例如直接通過里克特7 點量表評估自己的SA。其評價過程既可以在任務中進行,也可以在任務完成后進行。Sarter和Woods[57]則認為這種評價方法忽視了獲取SA 的過程,只把SA 作為結果來測量。而Taylor 提出的另一種自我直接評估方法——SA 評價技術(Situation Awareness Rating Technique,SART),通過10 維或3維的SART 量表來測量被試的SA。
自我比較評估要求被試對不同的設計進行對比評價,如比較不同的座艙設計。該評價方法有兩個潛在的不足:第一,它僅適用于設計優化的情境;其次,同所有的主觀評定一樣,不能保證被試間評價的一致性。Vidulich 和Hughes[58]通過研究發現約一半的被試將他們注意到的信息量作為評價SA 的依據,而另一半被試則通過估計其沒注意到的信息量來作為評價SA 水平的依據。
情境意識水平受人機界面的交互設計,用戶心理等多維因素影響,單一的客觀或主觀測量方法都不足以全面地評價人機界面的SA 水平。通過SA 的定量測量可實時評估飛行員情境意識水平,而通過完成飛行任務之后的定性測試可以作為實驗測試的補充和印證。根據上述思路,本研究團隊結合某大型運輸機座艙人機交互設計項目,開展了眼動數據與主觀問卷相結合的主飛行界面情境意識評估方法研究,見圖5。

圖5 主飛行界面情境意識評估實驗Fig. 5 Situational awareness evaluation experiment of main flight interface
4 結語
隨著新型交互技術和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以及未來飛機復雜功能信息集成的需求,包括新一代戰機需要應對復雜空戰戰況和瞬息萬變的戰爭態勢信息,未來飛機座艙人機交互設計將會在以下幾個方面產生變化。
飛機座艙未來交互理念發展趨勢變化。飛機座艙將從傳統的人為設計交互方式(觸控、鼠標與虛擬指針)向自然交互、無意識交互、智能交互轉變,人與飛機的交互方式更加自然,更加符合人的思維習慣、行為習慣,飛機也更容易識別人的意圖并作出準確反饋。例如腦控和眼控技術在飛機座艙的運用,飛行員指揮飛機更加自如,戰機的性能進一步提升,不僅能做到“指哪打哪”,更能實現“想哪打哪”的水準。
未來飛機座艙人機交互途徑的變化。如何通過多通道人機交互設計提升飛行員對飛機狀態和飛行環境(或戰場態勢)的感知和決策能力將是一種挑戰。與民用產品不同,飛機座艙人機交互處理的是海量飛行信息,以美國現役艦載機F-18 為例,僅在HUD 和多功能顯示器上,就有62 個顯示畫面,675 個符號(其中177 個符號通過不同大小顏色、虛線實線表達至少4 種含義),總的信息量達1 000 條以上。未來新型戰機的功能與信息量仍會增加,如何分配合理的交互途徑處理飛機不同種類信息將是未來座艙人機交互研究亟須解決的問題。
飛機座艙未來交互模式的變化。多通道交互技術運用,將對傳統人機交互模式帶來挑戰。以飛機座艙數字界面的功能菜單為例,在虛擬增強型交互界面中,傳統的觸控菜單交互和鼠標指針式交互將不再適用,飛行員在虛擬3D 環境下,無論采用視線追蹤菜單、虛擬指針式菜單還是其他交互模式,只要能夠降低認知負荷,提升飛行績效并減少出錯,都是具有研究價值的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