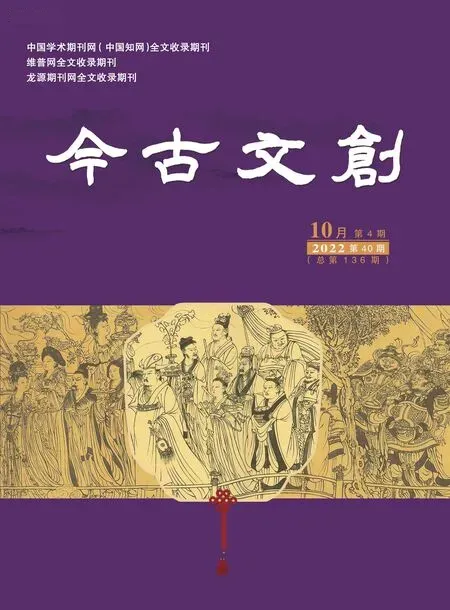電影《肖申克的救贖》敘事策略研究
◎郭玉冰
(河北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河北 石家莊 050024)
弗蘭克·德拉邦特執導的電影《肖申克的救贖》以極富新意的敘事手段講述了銀行家安迪的自我救贖之路,使其成為勵志故事片中的經典之作。安迪因被人誣陷槍殺妻子與情夫而判無期徒刑,在監獄中遭受欺凌,但仍然保持果斷、堅定與智慧,獲得了典獄長諾頓的重視且最終成功出逃。在19 年的監獄生活中,安迪一直心懷希望,不被監獄的體制化生活所馴服。電影中安迪在肖申克監獄中生活的點滴是當時美國小型社會的縮影,肖申克監獄對瑞德與老布的馴服,揭示了體制化的殘酷與美國社會的黑暗,引發了受眾深思。
一、在敘述者話語中了解敘事信息
麥茨從敘事接受者的第一印象出發,讓敘事接受者感知大影像師的存在,即陳述主體的存在。在電影敘事過程中,必然存在一位講述者講述故事事件,接受者即受眾處于同等的地位,理解陳述者傳遞的信息。演員在電影中不再是唯一發送敘事信息的載體,明現敘述者、旁觀者的敘述者與大敘述者等機制也可以發送敘事信息。
(一)明現敘事者對安迪的回憶
事中,安迪冒著生命危險向獄警提出幫助他逃避稅務,為每位修屋頂的獄友贏得三瓶冰鎮啤酒。在所有人喝啤酒的自由時光中,瑞德第一人稱的畫外音講道:“安迪呢,他窩在涼蔭下,臉上掛著奇異的微笑,看著我們喝他的酒,你可說,他想拍獄卒馬屁,或想博取囚犯友誼,但我呢,認為他只想重溫自由,即使只有一剎那。”明現敘述者瑞德的聲音只帶有自己的所猜所想,并沒有出現安迪本人的想法,使受眾對主人公產生親近感,且畫外音與畫面一同交代了安迪的與眾不同,呈現出幸福溫馨的監獄生活。此處明現敘述者的話語對觀眾轉變安迪看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為安迪重獲自由做了鋪墊。
(二)大敘述者提供額外信息
在敘事者敘述故事的過程中,熱奈特根據影片中人物介入敘事的多少,將同故事中的敘述者細分為次要人物與主人公兩類。在《肖申克的救贖》電影中,瑞德作為電影敘事的明現敘述者是故事中的主要人物,直接參與影片的敘事,此時電影畫外音中的“我”指瑞德,電影從始至終敘述的是瑞德自己的所見所聞,瑞德在影片中起見證與觀察的次要作用。
敘事學家托多羅夫曾用“敘事體態”來表示敘事者與人物之間的關系,將敘事體態分為敘述者>人物、敘述者=人物、敘述者<人物三種。在電影中,瑞德作為安迪的朋友直接參與了安迪的生活,他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來講述安迪在肖申克監獄生活中發生的事件,真實客觀地揭示了主人公安迪的性格,推動了情節發展。在修屋頂這一故
安德烈·戈德羅認為電影背后隱藏著一位不可見、躲在敘事文本背后的作者,他稱之為大敘述者。在小說文本中,全知視角敘述常常會導致讀者出現自相矛盾的情況。但在電影敘事中,暗隱的大敘述者借助蒙太奇、長鏡頭等電影視聽語言解決了上述問題。
大敘述者作為一種機制控制著明現敘述者的言行,向受眾提供各種敘事信息,承擔幕后全知視角的作用。在《肖申克的救贖》這部電影中,明現敘述者瑞德是由大敘述者虛構出來的人物。雖然大敘述者賦予了他講述故事的能力,但是受時間與空間的局限,仍存在一些不可知的額外信息。因此,大敘述者利用電影的視聽化特征為受眾建構一個更高層次的敘述者,彌補了觀眾獲得額外信息與明現敘述者不知道的情節,更具說服力。在影片開頭,明現敘述者瑞德因時空的限制,無法了解安迪在法庭審判這一情節。此時大敘述者便采取最直接的電影敘事方式,通過電影畫面與聲音等藝術元素的多元化組合來進行敘述,讓觀眾在大敘述者的全知視角中了解明現敘述者瑞德無法了解的事情,這一敘事手段與杰拉爾·日奈特提出的“零視點”觀點相吻合。
(三)老布借助書信方式敘事
旁觀的敘述者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講述故事,不僅使電影具有真實性,還拉近了與受眾的距離。在《肖申克的救贖》這部電影中,老布作為旁觀的敘述者在講述主人公安迪的遭遇時,也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阿布敘述者的敘事方式區別于以上兩種敘事方式,主要通過閱讀書信的方式對主敘述“加敘”。其源于一個事先的寫作行為,是一種不在場運作。阿布的遺書由安迪讀出,正屬于一個敘述者用詞語講述另一個敘述者用詞語所講述之事。老布利用書信的方式將觀眾從現在帶回過去,又通過安迪讀信的客觀鏡頭,將受眾從過去帶回到現在,影片具有時空轉換的靈活性。老布在書信中將出獄生活的不如意與對未來生活的迷茫、絕望施加在詞語、段落中,讓安迪以及受眾直觀感受阿布的痛苦與無助。阿布自殺悲劇的發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監獄制度下“體制化”所造成的必然結果。阿布一生中50 年的時光都是在監獄中度過,他早已習慣了監獄里被約束的生活。當被宣告獲得自由時,對未知社會、人物以及習慣的恐懼感油然而生。正如瑞德所說:“監獄是怪地方,起先你恨它,然后習慣它,更久后,你不能沒有它。”這正是監獄“體制化”的可怕之處。
二、在元故事與第一敘事的因果關系中解讀電影內涵
在現代電影中,敘事文本的交錯運作對于理解全部情節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分層”作為敘事學最基礎的專門用語,熱奈特認為“敘事講述的任何事件都處于一個故事層,下面緊接著產生該敘事的敘述行為所處的故事層。”在電影敘事文本中,可以擁有一個或多個敘述層次,但敘述層次之間并不是共生關系。《肖申克的救贖》電影的創作導演弗蘭克·德拉邦特等大攝影師是在第一層完成的行為,被稱為故事外層。而瑞德根據自己所見所聞講述的安迪事件是第一敘事講述的內容,屬于故事。講述主人公安迪入獄的原因、老布出獄自殺與安迪逃出監獄的三件事件稱為元故事事件。當受眾在觀看電影時,受眾可通過元故事與第一敘事之間的因果關系來全面客觀地了解電影情節,理解電影中所蘊含的深刻內涵。
(一)安迪入獄的原因
杰拉爾·熱奈特認為追敘是指對故事發展到現階段以前的事件的一切事后敘述。在《肖申克的救贖》這部影片中,對銀行家安迪入獄原因的敘述屬于追敘。導演以倒敘的方式將安迪妻子與昆丁教練偷情事件,插入到律師在法庭上提問安迪的情節中,故事內容本身的時間順序與電影敘事中安排的時間順序的不協調性,使觀眾對安迪是否酒后殺死妻子與教練產生了懷疑,制造了電影的懸念。敘事從故事中間開始敘述,繼之以解釋性地回顧妻子偷情與安迪在車內喝酒、裝槍的情節。這些蒙太奇鏡頭敘述的情節屬于解釋性倒敘的一個變種,即元敘事。其充分發揮了補充解釋主敘述層的作用。在這個元敘事結束后,明現敘述者瑞德開始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講述安迪的監獄生活。同時,給受眾留下安迪是否殺人的疑問,讓受眾在多重敘述者的講述中逐步了解故事真相。
(二)老布出獄自殺
從一個敘述層到另一個敘述層的過渡,原則上只能由敘述來承擔,敘述正是通過話語使人在一個情境中了解另一個情境的行為。在《肖申克的救贖》電影中,安迪和老布處在兩個不同時間與空間中,弗蘭克·德拉邦特導演通過書信的敘事方式讓受眾了解到阿布出獄后的世界與安迪講述時的世界。其不僅僅擴大了電影故事的敘述層次,并且通過畫面內容充分展現了老布從監獄假釋到自殺的生活經歷。阿布敘述者的書信話語冷靜客觀、簡單明晰,充滿著對未來生活的絕望與無助。阿布消極自殺的次一級敘述層與安迪樂觀、積極向上的內心狀態形成了強烈反差,突出了電影“心存希望,人生才能破繭成蝶”的主題。
除此之外,弗蘭克·德拉邦特導演在講述老布自殺這一事件時,還體現了敘事的轉喻效果。導演選擇呈現突出信息與省略不必要信息的方式,讓觀眾根據自己的理解來推斷事件的整個過程。在老布自殺的敘事過程中,導演僅僅描述了老布踩到桌子與上吊這兩個情節,至于中間老布購買作案工具等情節,導演并沒有在電影中提及,但觀眾可以自行想象此環節,重構對事件的完整理解。
(三)安迪成功出逃
重復敘事是指對發生或出現一次的事件或情景進行多次敘述。在主人公安迪成功逃出肖申克監獄后,影片中出現了兩次典獄長諾頓撕掉海報的鏡頭。兩個畫面鏡頭所表示的時空是一致的,但背面引出的兩個事件及兩個事件的時空是不相同的,在一定程度上屬于重復敘述。典獄長諾頓第一次撕開海報后,講述了警方順著洞找尋安迪,結果只找到安迪的囚服、石錘、肥皂等作案工具。典獄長諾頓第二次撕開海報后,講述了安迪以史蒂文斯的身份走進緬因國家銀行提取現金并公開典獄長諾頓貪污犯罪的信息。典獄長諾頓兩次撕開海報鏡頭后所發生的事件都具有不同的意義,豐富了電影“救贖”的寓意,起到強調、對比的作用。
在《肖申克的救贖》電影結尾處,導演以倒敘的敘事方式介紹了主人公安迪出逃監獄的過程、到銀行取錢以及駕駛紅色跑車去墨西哥的三個事件,帶領觀眾重新回憶安迪在監獄中的“精心準備”,對第一敘事故事做出解釋,解答了受眾的疑惑。安迪成功出逃的情節,再次揭露了只要心懷希望,不放棄,便可實現自我心靈救贖的電影主旨。
三、借物性空間與表意空間傳遞電影的“言外之意”
電影敘事空間作為再造的藝術空間,其接近于現實社會,但又以超越現實生活的樣式重現于人們面前。電影敘事空間可分為接納敘事時空轉變過程的物性空間和蘊含隱喻功能的表意空間。其中,物性空間指敘事中背景環境及人物活動的場景空間,表意空間是敘事主體在物性空間中敘事的基礎上,與受眾建立聯系后形成的傳達隱喻功能的空間。
(一)物性空間接納敘事的時空轉變過程
電影敘事的本質是空間。電影的空間敘事,就是把空間作為一種敘事方式。在電影敘事中,導演將事件放在一個符合電影敘事的空間環境中,以此來實現電影敘事的時空轉變。在《肖申克的救贖》電影中,肖申克監獄空間是影片中人物活動的場所,是觀眾在銀幕上可以直觀感受到的空間。在電影開頭,法庭空間向肖申克監獄空間的轉變,便是通過視聽語言的呈現,實現了電影敘事的大幅度的空間轉換。鏡頭運用俯拍鏡頭來展示肖申克監獄的全貌,預示著主人公安迪即將告別以往優越的生活,以囚犯的新身份在這里生活。
物性空間的轉變推動了電影情節的發展。電影中的物性空間是由典獄長諾頓、獄警赫德利、獄卒與囚犯共同建構的肖申克監獄空間。在狹小的監獄空間中,處處充斥著人性的險惡,顯示著權利的威嚴。在福柯看來,“空間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礎。空間是任何權力運作的基礎。”人們所處的空間通常與其社會地位、資源占有和所持權力成正比。典獄長諾頓作為肖申克監獄里最高的權利掌控者,控制著下層人物的行為。獄警與獄卒是肖申克監獄空間的執行者,其身份地位僅次于典獄長諾頓,可以隨意使用警棍威脅打罵囚犯。而囚犯屬于權力的被實施者,位于監獄中最底層地位。因此,肖申克監獄空間好比權力空間,等級極度莊嚴,不容任何人侵犯。《肖申克的救贖》這部電影選取肖申克監獄作為人物活動的環境空間,更貼近電影敘事表達的“向往自由,追求幸福”主題,符合弗蘭克·德拉邦特導演創作理念。
(二)建立蘊含隱喻功能的表意空間
馬賽爾·馬爾丹認為電影敘事空間“是人物生存空間與活動空間的綜合體,它不但承載地域、時代、歷史、民族、政治、經濟、文化、階級、地位等各方面人文領域的重負,也要包含人物思想、情感、心理、心靈等方面的人本領域的重要內容。”任何一部電影的物性空間的建構都是在表意空間的基礎上完成的。表意空間不直接呈現于銀幕上,而是借助物性空間中敘述者的講述,讓受眾逐步接受電影主旨內容。《肖申克的救贖》這部電影創作于兩次世界大戰后,戰爭帶來的毀滅性災難使得人們對人的本性產生懷疑,對未來感到迷茫與焦躁。因此,弗蘭克·德拉邦特導演借助主人公安迪在狹小的肖申克監獄空間中頑強反抗的事件來建立精神空間,揭露電影主題。
除此之外,弗蘭克·德拉邦特導演還通過安迪、瑞德與阿布三位主人公在物性空間中的表現,來反映當時人們對待事物的不同看法。他們三人雖然同時處于一個物性空間中,但是對待出獄后追求自由的態度卻截然相反。阿布在50 年的監獄時光中,早已向命運妥協,對假釋不抱有任何希望,是典型的被體制化了的“犧牲品”。突如其來的假釋僅僅使阿布獲得身體的自由,但其內心仍需要無形的秩序與規則控制他。出獄后規則的缺席也是使他走向死亡的重要原因。瑞德兩次申請假釋但都被無情地拒絕了,在一次次被拒的失望中,他對出獄已經不抱有任何幻想。在第三次申請假釋時,瑞德雖然成功獲得了假釋的機會,但40 年的監獄生活早已經讓他與外面的社會脫節,逐漸被體制化。而與安迪的約定,給了他堅持的理由。安迪作為電影的主人公在這里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引導瑞德一步步地擺脫監獄體制化機制。
主人公安迪是電影中唯一一個沒有被體制化的人物,他即便身體被束縛在狹小的肖申克監獄空間中,但內心始終沒有被束縛。他從一開始因為冤枉進入監獄以來,就一直為出逃做準備。“你需要它就不會忘記它。有些東西在內心深處,不能到達,不能出沒。它就是你的希望。”在肖申克監獄中,他一直心懷希望,試圖通過建立圖書館、幫助獄友考取文憑等方式,來改造囚犯的監獄生活,給獄友們帶來生活的樂趣。經過16 年的堅持不懈,安迪用一把小小的石錘撬開了通往自由之路的大門。影片中,阿布飼養的小鳥更是象征自由的符號,放飛小鳥預示著安迪即將獲得自由,擁有嶄新的未來。導演通過對老布、瑞德和安迪出獄后截然相反的人生結局,來深刻地揭示電影表達的“救贖、希望、自由”的主題。
《肖申克的救贖》電影采用的多重敘述者敘事、物性空間與表意空間結合的敘事手段讓受眾思考電影“救贖”的深刻內涵。元故事與第一敘事的交叉使用,使受眾在觀影的過程中構建故事,更加清晰明了地讀懂電影敘事內容,感受肖申克監獄空間中制度與人性的溫暖,具有更強的可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