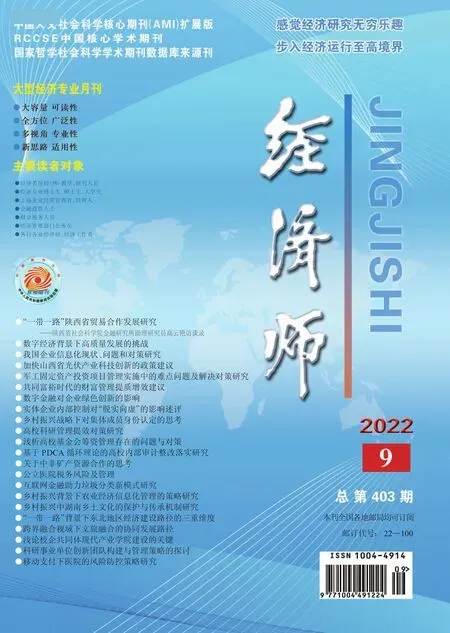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政策優化探究
——以揚中竹編為例
●丁 燁 葉惠夢珊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個民族,一個地區,一個時代的記憶,為了流淌在中華民族血液中對文化遺產的眷念,也為了我們在現代社會的急速洪流中也能抓住漂浮的靈魂的木舟,我們需要對它們進行保護。然而,由于市場的自然選擇,那些翻轉在指尖的藝術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因此對非遺的保護刻不容緩。
一、揚中竹編的歷史溯源及其政策保護的必要性
揚中市隸屬江蘇省鎮江市,位于長江中下游,土地肥沃,水草豐美。特殊的地理環境和土質環境,使得揚中盛產竹資源。揚中竹編起源于宋朝,由外地移民引入,豐富的竹資源吸引了許多竹制品手工藝人。傳統的竹編手藝,是一代代竹編手藝人不斷打磨傳承下來的,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上世紀90年代初,竹編藝人耿月新以純工藝品制造為主,對竹編題材及技法進行大膽創新,自此開拓了揚中竹編的新時代,極大程度上提升了竹編的文化水平和藝術價值。2006年11月10日,揚中竹編被列入江蘇省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目錄。
截至目前,揚中竹編有一位非遺傳承人,就是70余歲高齡的耿月新老人。上世紀90年代初,耿月新向市政府申請建立了油坊鎮非遺工作室,允許大眾參觀學習,同時也為收徒提供便利。自2006年起,他與省殘聯合作,每年為殘疾人開班。為殘疾人授藝,既能讓殘疾人有更多的方式發家致富,又能領取政府補貼,為學徒增加生活上的保障,同時還為非遺手藝的傳承提供更多的學徒和傳承人。當地政府采取了將非遺與旅游業相結合的方法,與鄉村文化相結合促進鄉村振興,發展特色產業,從而可以將揚中竹編打造為城市名片。竹編的傳承很難僅僅依靠老人自己收徒維系下去,因此政府的政策介入顯得十分必要。對于揚中竹編的政策性保護,目前已經突破搶救性保護的一環,然其后續如何將傳承延續,在當今的市場化大環境下,以期后人能將竹編文化發展下去,而不是走從前傳統手藝日漸衰退的老路,政策性的介入模式仍需進一步探索。
二、現階段揚中竹編保護政策的不足
(一)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行政幫助機制不足
根據最新的鎮江市非遺項目傳承人條例,只對急需搶救性保護、開展傳承和傳播工作確有困難的、有關資料亟需整理記錄和出版等條件的非遺傳承人進行行政資助。所涉資助范圍過窄,評定的機制相對模糊,只對非遺傳承人進行搶救性保護,對于非遺傳承的持久發展顯然缺少長久的保護機制和穩定的行政鼓勵機制。非遺傳承和保護非一朝一夕之功,需久久為之,對于傳承人的資助和鼓勵同樣如此。就揚中竹編的非遺傳承人耿老師傅而言,70多歲的老師傅總是優先向殘疾人授藝,因為殘疾人享受政府的殘疾補貼,因此能全心全意投入竹編學習,對其生計顧慮較少。竹編工藝因其工藝學習的特殊性,需要人們沉下心學習,耗時耗力,打磨出一個精品所需的時間更長。同時竹編的經濟屬性與很多現代市場產物相比相對較低,在其前期發展時期,政府更加細化和具體的行政幫助必不可少。
(二)對非遺傳承人的精英式評定方式存在缺陷
揚中竹編的代表性傳承人目前只有這位70多歲高齡的耿老師傅,老人在多次采訪中表示后繼傳人之艱難,自己每年都要織出幾幅大型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以期后人能模仿學習,這樣即使沒有傳承人,只要愿意鉆研學習,也能模仿其織作手法進行編織。不獨揚中竹編,全國各地非遺傳承人均顯示出后繼少人的態勢。我國各地的非遺繼承人大多采用“精英式”的個體保護政策,欠缺對不同非遺項目特殊性的因地因時因人制宜的考量。另外,傳承人既要繼續鉆研技藝、作出創新,又要對非遺技藝之外進行社會性傳播、教育,甚至要對地方經濟的增益發揮作用,他們承受著來自本業和社會各方的沉重壓力。這種“集中火力式”的保護方式至今在全國范圍內依舊十分普遍,將如此沉重的責任置于一個垂垂老矣的高齡老人之身是否合理?如果將傳承非遺的重任僅系于傳承人代表者一身,忽略眾多普通的民間傳承人,一方面挫傷了民間傳承人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很有可能會損害非遺的傳承和發展。對于傳承人的評定方式所反映出的問題,行政審批的過程可能需要加以完善,以適應不同非遺項目的特征。
(三)行政指導措施有所欠缺
在我國,政府在對非遺產品生產性保護進行行政指導時沒有統一的行政指導原則,在行政指導的方式方法上,存在比較單一的趨向,只將非遺產品置于市場監督管理下,容易造成傳承人為了迎合市場的風向而忘記非遺傳承的初心。因此對于非遺的行政指導需要采用更多元的方式,非遺的傳承除了需要市場化的支持,更多的是政府的行政指導性措施,增加社會各界對非遺文化的理解和認同。
三、國際視野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探索
非物質文化是國家和民族智慧的體現,也是人類的共同寶貴財富,這就是各國研究和保護非物質文化的原因,它們不僅有助于文化遺產傳承,而且有助于人類智慧的傳承。此部分,筆者將通過借鑒國際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國際立法以及法國優秀的法律保護政策,對如何保護和傳承的相關舉措、立法文件、活動如何進行規范,指出共同性與差異性,求同存異,取之精華,去其糟粕。因此,筆者將于國際的視角下對非遺政策現狀進行研究,旨在尋找探索出有益于解決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目前存在問題的方法與路徑。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差異性
1.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界定不同。國際上有關非遺界定的發展沿革歷經幾十年不斷完善。從1989年《關于保護民間傳統文化的建議》提出非遺是人類共同財產的內容,到2003年《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范圍的界定,包括語言形式、表演形式傳承的文化,傳統文化習俗,有關生存和發展的相關實踐經驗以及手工藝等。
2.發展和完善政策的不同。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一方面它具有公法性,另一方面其存在著私法性,那么,對于國際仲裁機構,在審理非物質文化遺產時,對于環節中的保密,以及仲裁自身具有的既處理公法糾紛,也處理私法糾紛的性質,仲裁機制則更適用于解決各國有關非遺所產生的糾紛。拓寬公眾對非遺的認知,讓公眾參與到非遺保護中。
(二)法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制度
1.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源于法國。對于非遺的保護,法國制度無疑具有領先性。法國是國際上第一批開展對非遺進行保護的國家,同時是首先在非遺保護方面制定現代化法律條款的國家,對于其制度運行現在已經規模完善,體系完整。
2.法國的保護措施。法國在其非遺保護的建構體系過程中,明確了民眾參與職責。因此,在其對于非遺的保護初期,不僅是政府職責,法國人民的參與度也極高。“因此,在此后,法國制定《歷史遺跡法》《文化資產保護法》等一個體系的法律保護,對法國民眾的教育程度印象更深。”法國在非物質遺產保護方面,不僅是中央與地方相結合,更是考慮到了極大的靈活性以及針對性,這是其成功的突出顯著優勢,形成了具有法國特色的保護體系。
(三)非物質文化遺產國際角度完善建議
綜合以上不同非遺保護的基礎上,總結我國非遺存在問題,針對其成功經驗,對我國非遺保護的政策進行完善。首先,為了對非遺進行更好的保護,應當從政府政策而言,在法律層次上加大立法保護;其次,對于手藝人不僅要保護其手藝傳承,也要在法律框架內保障其能夠獲得利益,同時繼承人的選定應當更加規范,認定程序上借鑒國外模式。建立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是否選進名錄的范圍的界定應當以法律予以明確規定。
四、對于完善“揚中竹編”非遺保護政策的建議
(一)完善行政幫助和行政鼓勵機制
我國已經有了針對非遺傳承代表人的行政幫助機制,在這一點上針對“揚中竹編”的鎮江市政府對于非遺的行政幫助規則直接沿用了非遺法中的條款,另外增加了代表人可申請政府資助的條款,然而對于非遺代表人的資助還是十分有限。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人的行政幫助不應只停留于對代表人生計保障的資助,對于代表人進行的相關宣傳、培訓、商業活動等也應有所支持。筆者建議,第一,將對非遺代表人的行政幫助和行政鼓勵納入地方政府財政預算中,對政府財政進行合理規劃,對于非遺傳承人的行政鼓勵政策制定更為詳細的規范和標準。第二,利用行政鼓勵機制合理吸納社會資金,鼓勵社會組織對于非遺活動進行經濟上的幫助和投入。第三,《非遺法》第三十七條規定地方政府應當對合理利用非遺項目的單位予以扶持,依法享受一定的稅收優惠。然而在許多地區,并沒有真正推出有關從事非遺保護事業的企業與個人可以享受稅收優惠的政策,因此地方政府可以采取制定相關稅收優惠政策,作為完善行政鼓勵機制的手段之一,激勵企業和個人投身非遺傳承和發展。
(二)優化非遺傳承人的行政確認方式
在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繼承人代表的認定方式都是通過個人申報然后通過地方層層篩選上報到中央,進行逐級評定,最后敲定。對非遺項目的認定方式主要還是通過不同地方行政機關的不同標準進行,差異化明顯,標準也相對不統一,造成許多申報人被淘汰。另外,民間的傳統手工藝人可能文化水平不高,對如何申報和評定的標準沒有認知,無形中可能形成幸存者偏差,錯失行將消亡的具有傳承意義的手藝或藝術。針對這兩個問題,筆者認為可以在行政確認的過程中增設譬如公眾參與的聽證或大眾投票的方式,增加大眾對非遺評定的參與度。一方面,非遺項目大多誕生于民間風俗或生活習慣,民眾更具有話語權;另一方面,增加大眾參與的渠道無形中對非遺文化進行大范圍宣傳,讓一些隱匿于民間的潛在非遺手藝人能有認知的機會,對非遺保護也大有裨益。
對于非遺代表人人數的認定。地方政府不一定囿于單一代表人的窠臼,對于傳承人人數可依據項目的瀕危程度,適當增設代表人。對非遺傳承人的行政確認制度可以借鑒日本的相關制度,將非遺傳承人分為三種情況:“對具有高度技能的個人進行認定,稱為‘個別認定’;對兩人以上成為一體共同表現的技能保持者進行認定,稱為‘綜合認定’;對技藝表現上缺少個人特征,且屬多人共同表現從而形成一體感的整體技能保持者進行認定,稱為‘保持者團體認定’。”從而規范和完善非遺代表人的行政確認制度。
(三)規范和完善行政指導的具體建議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核心在于文化,因此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過程中不能脫離文化遺產的文化生態,而只針對單一的非遺項目進行保護。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僅僅是將其作為“文化孤島”進行圈護,還需要對文化全局予以關注;不但要保護文化遺產自身及其外觀,還要注意它們所依托和因應的文化外部環境。對非遺的保護不能脫離其“原生土壤”,而“揚中竹編”的原生土壤正是在于孕育揚中竹編的鄉村文化。依據行政指導的非強制性原則和我國的鄉村振興政策,筆者建議當地政府發揮行政指導的優勢,將竹編文化與鄉村振興相結合,讓竹編回歸其鄉村文化產物的本質,探索竹編產業化與鄉村建設融合發展的模式。同時,在指導的過程中要依照法律法規規定,做到程序正當、實體公正,減少行政審批程序,發揮地方政府的職能,加強對我國非遺項目的有力指導,對行政主體在履行社會責任的各種行政行為進行規制和調控。
(四)提高社會公眾對非遺活動的參與度
2003年,UNESCO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界定:“各個群體和團體隨著其所處環境、與自然界的相互關系和歷史條件的變化不斷使這種代代相傳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創新,同時使他們自己具有一種認同感和歷史感,從而促進了文化多樣性和人類的創造力。”非物質文化遺產從來都是從社會群體文化中誕生的,非遺的傳播和傳承也一定是依靠人民群眾的,只有群眾對非遺文化有認同感和歸屬感,才能將其傳承下去,將非遺文化脫離群眾發展則如建造空中樓閣一般不切實際。目前我國很多地方對于非遺的傳承仍然只依靠政府單方面的行政幫助和行政指導,與民眾脫軌嚴重。“揚中竹編”在宣傳過程中積極呼吁公眾參與,采用與中小學教育結合的方式,在地方中小學建設特色課程,同時與旅游業結合。社會公眾的參與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大眾的非遺文化的再教育,使得社會公眾對于竹編文化更有認同感。筆者認為,可以在非遺行政確認和行政指導等方面加強公眾參與的程度,以行政法的公法性引導社會群眾對非遺文化的認同,吸引社會團體參與管理。
五、結語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全人類共同的財富。在我國,非遺凝聚了上下五千年傳統文化的智慧結晶,是中華民族的民族記憶的一部分。然而隨著傳承代表人的日漸老去,后繼逐漸式微,如何在非遺傳承中注入新鮮的血液成為大家共同關注的問題。無論是完善行政幫助機制、行政確認機制還是對公眾參與度的提升,筆者都是圍繞著如何吸引更多的年輕群體加入非遺傳承的問題中,進而提出政策優化。所謂傳承,有承才能有所傳,人類文明之所以得以延續正是依靠傳承的力量。非物質文化遺產,這個詞看似古老而遙遠,與現代生活仿佛格格不入,但是它們承載的記憶卻是屬于未來的。我們接過火炬,遙遙地望向未來。過去,現在,未來,以及更遙遠的未來,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生不息。